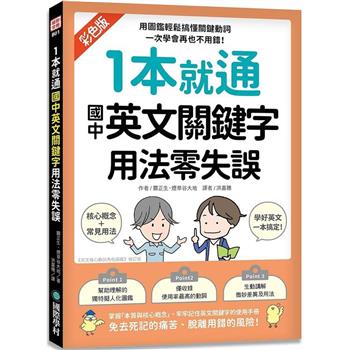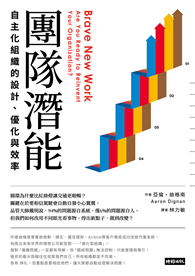瀟灑一生——懷念楊月蓀 白先勇
我跟楊月蓀很早很早就認識了,那是大半個世紀以前,一九六二年左右,我剛從台大畢業,月蓀正在《大華晚報》當實習記者,月蓀與我同年,兩個年輕人二十出頭,因為談得來,一下子便變成了知友,這份情誼一直維持到最後。
很快我們都出國了,我到愛荷華大學唸書,畢業後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找到一份工作,恰巧月蓀也到了舊金山,在舊金山州立大學中文班教中文。月蓀是北京人,一口京片子,他在美國教中文佔了很大便宜,於是我們在舊金山又見面了。
異國重逢自是興奮。那幾天,月蓀陪我遍遊舊金山,六十年代,正是美國社會劇變的狂飆時代,反越戰引起的嬉皮運動,就是由舊金山發起,遍街的Flower Children奇裝異服,長髮披肩,又唱又跳,這批戰後成長的青年,一反美國中產階級的成規價值,打破美國社會許多禁忌,導致日後種族、婦女、性別各種解放運動,我與月蓀那時剛到美國不久,在舊金山目睹這場熱鬧非凡的社會「街頭劇」,自然感到眼花撩亂,好奇萬分。
月蓀後來到蒙特瑞語言學校教書,我們時有來往。蒙特瑞(Monterey)是北加州的一個風景勝地。月蓀那幾年在蒙特瑞過了一段相當愜意的生活,教了一群美國大兵唸中文。有一年聖誕夜,我開了五個鐘頭的汽車,載了詩人王潤華、淡瑩夫婦一同到蒙特瑞與月蓀過聖誕,他親自下廚做了一桌子的佳餚款待我們,月蓀廚藝很有兩下,那是一個令人難忘的聖誕,大家都喝得有了幾分酒意。喝醉了酒,楊月蓀就愛唱歌,而且一唱就沒有休止。他的記性真好,當時的流行歌,不知他怎麼記得那麼多。
八○年代,楊月蓀最後還是選擇回台定居,在師範大學教授新聞英文,一直到他退休。在師大教書,可能是月蓀一生中做過比較有意義的事情,他教出不少優秀的學生,有的現在在新聞界已擔任要職,而且他的學生都很感念他,這本紀念文集,也是他的學生替他編纂的。
月蓀思維敏捷過人,眼快手快,其實是一流的記者材料,有一次他與陳香梅同機,飛機到達台灣,他已寫好一篇很像樣的訪問稿寄到報館了。如果他認真選擇新聞事業,他一定會成為一名名記者。但月蓀淡泊名利,偶而寫寫專欄,也就樂在其中。
月蓀其實是一枝好譯筆,他在美國多年,熟悉美式英語,又有記者訓練,文筆流暢。他譯過楚門.卡波第(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the Cold Blood),卡波第筆鋒銳利,出語尖刻,倒合了月蓀的胃口。《冷血》是一本記載一樁聳動美國謀殺案的報導文學,在台灣頗暢銷,但譯書也是月蓀興致所至的附帶品,他並沒有認真想做一個翻譯家。我看他的翻譯才能被投閒置散,很是可惜,便寄了一本田納西.威廉斯的回憶錄給他,鼓勵他翻譯出來,威廉斯一生大起大落,感情生活,落魄跌宕,就如他那些名劇一樣精彩。月蓀對威廉斯放浪無羈的個性,頗能認同,他譯的這本《田納西.威廉斯懺悔錄》深得原著精髓,是一本上乘譯著。月蓀最後一本譯書《借來的時間》,保羅.莫奈(Paul Monett)的《Borrowed
Time》,也是我敦促他翻譯的。月蓀那一陣子,精神沮喪,我覺得致力譯書也許可以助他療傷,莫奈這本回憶錄記載他與愛人羅杰共同抵抗愛滋病的辛酸過程,寫得驚心動魄,摧人心肝,月蓀讀後深為感動,花了很大力氣,把這本書譯完。但這本書的出版卻幾經周折,各處漂流十年之久,最後才由允晨出版。二○○八年,這本書到達月蓀手中,月蓀已經重病在床。保羅.莫奈在《借來的時間》中如此開場:「我不知道我是否還能活着完成這本書。」月蓀在允晨版的後記中也有類似的讖語。但幸虧在他生前最後一刻,終於看到他筆下的成果。
其實楊月蓀是個特立獨行,我行我素的人物。他能拋脫一切禮俗羈絆,放浪於形骸之外,任性飄蕩,恣意翱翔,按照他自身邏輯,走完他很不平常的人生路途。月蓀感情豐富,極端敏感,但在感情路上,他卻走得顛簸流離,迄無結果。從前我想到月蓀的一生,總不免有點替他惋惜,但近來我突然有了新的憬悟。也許月蓀這種不拘世俗,事業、感情任意揮霍的態度,正是他與眾不同之處,他瀟瀟灑灑過了一生,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在這滾滾紅塵中,一關關經歷過應有的劫數,還清孽債,完成他特殊的命運。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時代的回眸:楊月蓀作品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51 |
中文書 |
$ 351 |
現代散文 |
$ 359 |
現代散文 |
$ 359 |
社會人文 |
$ 379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時代的回眸:楊月蓀作品集
本書集結了楊月蓀老師生前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的作品。楊月蓀老師左批社會百態的怪象,右評藝術文化的生態,東寫傳統文人的抑鬱,西陳當代中堅的憂慮。在解嚴初期、報禁開放的風潮中,他秉持著知識份子的熱情與理想,對當時的台灣社會,時而諄諄告誡,時而大聲疾呼,看到台灣邁入現代化的轉型過程中,種種紛擾不安的脫序行為、悖離人性的社會價值觀念,藉著報紙一角,一吐胸中塊壘。
因為作品數量頗多,難以取捨,特商請月蓀老師的同事兼摯友等,經過數次會議討論後,決定收錄的文章分為七個面向:社會觀察、 文化評論、親子教育、兩性探討、旅居印象、生活感懷,以及親友側寫,期望能呈現月蓀老師廣泛的關懷層面與思考。
《時代的回眸》一書,呈現了楊老師以其犀利的人文角度觀察他走過的時代,展現了熱愛世界、關懷群眾、社會、朋友及家人的胸懷,透過文章中靈活的筆觸和生動的描述,無論是諄諄告示、切切呼籲、或叨叨絮語,月蓀老師以他獨具的風格,瀟灑地走完精彩的一生。
作者簡介:
楊月蓀,學者、編輯人與翻譯家。曾執教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讀者文摘》中文版主編及《大華晚報》主筆。譯著多種,代表作《冷血》、《東方快車謀殺案》、《田納西‧威廉斯懺悔錄》、《借來的時間》、《金錢簡史》、《媒體現形》、《不可靠的新聞來源》等,膾炙人口。
作者序
瀟灑一生——懷念楊月蓀 白先勇
我跟楊月蓀很早很早就認識了,那是大半個世紀以前,一九六二年左右,我剛從台大畢業,月蓀正在《大華晚報》當實習記者,月蓀與我同年,兩個年輕人二十出頭,因為談得來,一下子便變成了知友,這份情誼一直維持到最後。
很快我們都出國了,我到愛荷華大學唸書,畢業後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找到一份工作,恰巧月蓀也到了舊金山,在舊金山州立大學中文班教中文。月蓀是北京人,一口京片子,他在美國教中文佔了很大便宜,於是我們在舊金山又見面了。
異國重逢自是興奮。那幾天,月蓀陪我遍遊舊金山,六十...
我跟楊月蓀很早很早就認識了,那是大半個世紀以前,一九六二年左右,我剛從台大畢業,月蓀正在《大華晚報》當實習記者,月蓀與我同年,兩個年輕人二十出頭,因為談得來,一下子便變成了知友,這份情誼一直維持到最後。
很快我們都出國了,我到愛荷華大學唸書,畢業後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找到一份工作,恰巧月蓀也到了舊金山,在舊金山州立大學中文班教中文。月蓀是北京人,一口京片子,他在美國教中文佔了很大便宜,於是我們在舊金山又見面了。
異國重逢自是興奮。那幾天,月蓀陪我遍遊舊金山,六十...
»看全部
目錄
瀟灑一生─懷念楊月蓀 白先勇
率性一生─讀楊月蓀書信感懷 黃肇珩
社會觀察
菲籍女傭與泰國新娘的聯想
我悲泣,我痛恨!
面子與尊嚴
戰爭的聲音
重刑─能解決犯罪問題嗎?
悲劇人物
也談「大陸熱」
令人困擾的兩岸關係發展
談語言表達能力
富而無禮的例證
老得優雅
死得尊嚴
談明星的形象
從娜娜取消錄影談起
何必凡事都扯上政治
「多層面新聞」之必要
良知何在?
從「敬老」到老人問題
映象世界
「地球日」之後
生活中需要更多一點理性
「台北生活昂貴•名列世界第七」意味著什麼?
文化評論
文化的迷失...
率性一生─讀楊月蓀書信感懷 黃肇珩
社會觀察
菲籍女傭與泰國新娘的聯想
我悲泣,我痛恨!
面子與尊嚴
戰爭的聲音
重刑─能解決犯罪問題嗎?
悲劇人物
也談「大陸熱」
令人困擾的兩岸關係發展
談語言表達能力
富而無禮的例證
老得優雅
死得尊嚴
談明星的形象
從娜娜取消錄影談起
何必凡事都扯上政治
「多層面新聞」之必要
良知何在?
從「敬老」到老人問題
映象世界
「地球日」之後
生活中需要更多一點理性
「台北生活昂貴•名列世界第七」意味著什麼?
文化評論
文化的迷失...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楊月蓀
- 出版社: 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13-07-01 ISBN/ISSN:978986627493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648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