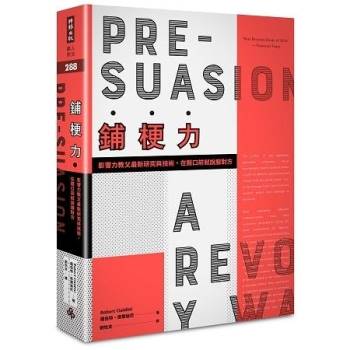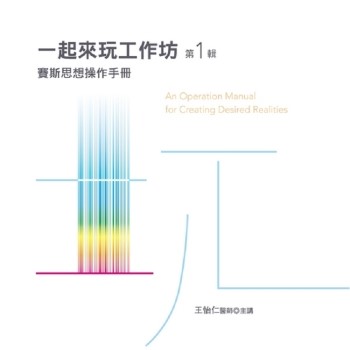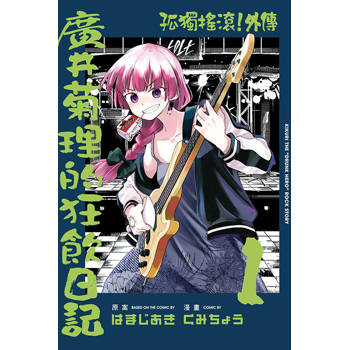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蛇女蕾米雅的圖書 |
 |
蛇女蕾米雅【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出版日期:2011-01-06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98 |
Others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165 |
中文書 |
$ 174 |
文學 |
$ 198 |
翻譯詩集 |
$ 198 |
世界詩集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她所吟唱的字句,是如此瑰麗,他彷彿已經為之著迷了整個夏季。
很快地,他的雙眼就飲盡了她的美麗,連一滴也不留在那迷惑的杯裡,
For so delicious were the words she sung,It seem’d he had lov’d them a whole summer long:And soon his eyes had drunk her beauty up,Leaving no drop in the bewildering cup,
★英國名詩人濟慈《蛇女蕾米雅》第一本全中譯本,中英對照,經典重現!
★新銳畫家Ethyrash精美配圖,揉和古典與現代,視覺令人耳目一新!
★西洋版《白蛇傳》,劇情曲折、意象豐美、風格奇幻、文字瑰麗,為美的極致呈現!
★《蛇女蕾米雅》,影響了美國名作家愛倫坡的創作!英國文評家蘭姆:「這首詩是歷來浪漫詩歌創作中,最華麗燦爛的一篇!」
傳說中,結局將是我倆彼此相遇。
這樣的命中注定,即使下輩子的我仍須受阻咒成為蛇女,也在所不惜。
蕾米雅(Lamia)在傳說、神話裡有諸多不同解釋:吞食兒童的利比亞皇后、引誘並吸食男性鮮血的魔怪,擁有女性上半身及蛇類下半身的生物(蛇女)等等。本詩中,濟慈借用此名,化為詩中的美麗蛇女,細述她與人類青年萊修斯(Lycius)相遇相戀的奇幻故事,有如西方世界的《白蛇傳》。《蛇女蕾米雅》在西方文壇上舉足輕重,影響了美國名作家愛倫坡的創作,英國重要作家蘭姆更盛讚它為「歷來浪漫詩歌創作中,最華麗燦爛的一篇」。
《蛇女蕾米雅》能得到如此地位,不僅是因為它富含精準具體的意象,華美、細膩而成熟的文字,也因為濟慈融合各種感官體驗,在詩中傳達整體性的美,同時展現出他對人生、社會責任的思考。
譯者簡介
葉欣
七年級生,天秤座,彰化鹿港人。清華大學外文系畢業,現就讀於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研究所。喜愛文學、畫作與音樂,自中學寫作小說與散文至今,已於私人部落格發表多篇散文與數部長篇奇幻小說。期待將國外優秀、精彩的文學作品及理論引介入臺灣,同時汲取更多寫作經驗,以同時走上創作、翻譯兩條道路,成為一名優秀的文字工作者。
繪者簡介
Ethyrash
夜空的窺探者,腦子永遠動得比手快,所以靈感總是劃過天際咻一下地不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