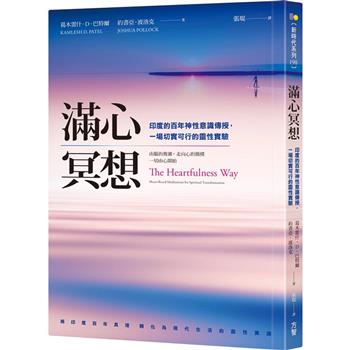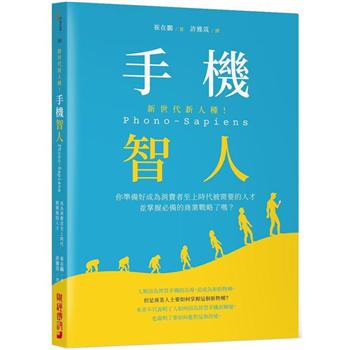蔣勳的私生活
一篇篇生活週記 橫亙二十四節氣
最雋永的「生活」與「情味」
「我想記憶生活裡每一片時光,每一片色彩,每一段聲音,每種細微不可察覺的氣味。我想把它們一一摺疊起來,一一收存在記憶的角落。」 ~~蔣勳
蔣勳,從「桐花」,而「新橋」,而「回聲」,而「肉身」,而「吾廬」,而「史記」,這五十篇的週記,竟可以寫得如此豐富多層次!……從肉眼觀象,到心眼體物,一枝文筆有如畫筆,將讀者逐漸導入哲理的美學境界。~~林文月
★ 收錄讓張小燕跨越喪夫之痛的〈願〉,雋永的人間深情!
★ 附贈蔣勳〈美與肉身的功課〉演講精華CD,共六大段落,約九十分鐘。為2011年9月17日,真如苑社會教育講座的演講內容,蔣勳先生心臟術後的第一場演講,細述了生病前後,對母親以及各種肉身緣份的深刻祝福!蔣勳先生表示此場演講,為近年來他最有感覺與深刻的演講。
★ 行政院文化獎得主,散文大家林文月專文推薦。
※他嚮往「自由」,夢想過一個城市,人們在頭上戴了鮮花,他們在街上相互擁抱、親吻、和善微笑…。
他寫「時差」,在幾天持續的時差裡,我懷疑自己:是不是衰老了。
他品嚐「甜酸」,甜味如果是純粹幸福的陶醉,酸味似乎多了一點憂愁。
他論「風尚」,直到今天,衣服露不露點,還是眾人樂於談論的大事。甚至特別設置機構,專門檢查露點。
他論「輸贏」,有意義的比賽,旁觀者不只在看輸贏,也在學習輸贏裡透露的生命品質吧。
他談「吾廬」,懷念起小時候種滿花樹的家,和雞鴨一起長大;懷念起現在的家,窗外有一條大河,月圓時會在窗台打電話給遠方朋友,要他抬頭看一看月亮。
他憶「雪——紀念母親」:
「母親因罹患糖尿病,一星期洗三次腎。我去V城看她的次數也越來越多。洗腎回來,睡了一覺,不知被甚麼驚醒,母親怔忡地問我:下雪了嗎?
我說:是。
扶她從床上坐起,我問她:要看嗎?
她點點頭。
母親的頭髮全灰白了,剪得很短,乾乾地飛在頭上,像一蓬沾了雪的枯草。
………
『好看嗎?』
我靠在輪椅旁,指給母親看繁花一樣的雪漫天飛揚。
母親沒有回答。她睡著了。她的頭低垂到胸前,裹在厚厚的紅色毛毯裡,看起來像沉緬在童年的夢裡。
沒有甚麼能吵醒她,沒有甚麼能驚擾她,她好像一心專注在聽自己故鄉落雪的聲音。」
一種毫不吝惜的揮霍,一種真實過後的回憶;
一種辛酸的自我完成,一種無以名狀的悸動。
草木山川皆可幻化,不變者唯此時真心……
本書原為2003年5月至2004年5月,蔣勳為〈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所撰寫的專欄集結,原名為《只為一次無憾的春天》。2012年,有鹿文化重編新版,名為《此時眾生》,並敬邀林文月老師撰序;文章亦重新編輯,按四季更迭,以及24節氣前行,呈現出一本有如美與生活的「週記」。
何名《此時眾生》?
「此時」,既是蔣勳文章中書寫的那個時刻,也是讀者閱讀交感的這個當下;蔣勳眼前心中的草木節氣、山川大地和有情眾生,彷彿我們心中有情而能映現返照的「眾生」。此時,因之變得普遍平等久遠;變的是時空節氣,不變者唯真心至情而已。肉身緣分,因為有情,可以祝福並且福報眾生!
附贈 : 蔣勳「美與肉身的功課」CD
※光碟內容為2011年9月17日,蔣勳參加真如苑社會教育講座的演講內容。
六大段落,約九十分鐘:
1. 經過加護病房前後的我
2. 官能所經歷的「美」和「品」
3. 甜、酸、鹹的功課:人生的況味
4. 辣的功課:以《紅樓夢》為例
5. 苦的功課:荒涼身體的肉身緣分
6. 從「美的覺醒」到「肉身功課」
此CD隨書附贈,非賣品,不得轉售。
作者簡介:
蔣勳
福建長樂人,1947年生於西安,成長於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藝術研究所畢業,並於1972年負笈法國巴黎大學藝術研究所。曾任《雄獅》美術月刊主編、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現任《聯合文學》社長。
多年來以文、以畫闡釋生活之美與生命之好,為台灣美學大師。寫作小說、散文、詩、藝術史,以及美學論述作品等,深入淺出引領人們進入美的殿堂,並多次舉辦畫展,深獲各界好評。近年專事兩岸美學教育的推廣。著有藝術論述 《新編美的曙光》《美的沉思》《徐悲鴻》《齊白石》《破解米開朗基羅》《天地有大美》、《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卷》《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等;散文《此生──肉身覺醒》《島嶼獨白》《歡喜讚嘆》《大度.山》《少年台灣》等;詩作《少年中國》《母親》《多情應笑我》《祝福》《眼前即是如畫的江山》《來日方長》等;小說《新傳說》《情不自禁》、《寫給Ly’s M》《因為孤獨的緣故》《祕密假期》,有聲書《孤獨六講有聲書》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畫布上的文筆
──《此時眾生》讀後感
林文月
勤於奔走散播美學,以深入淺出的語言對社會大眾殷殷解說何謂風格,什麼是品味的蔣勳,有一本非常精巧的書。這本書共收五十篇散文,每篇約在千二百字左右,從某年的五月開始,止於次年五月。剛剛一年,橫亙二十四節氣,周而復始的筆耕、成為這本《此時眾生》。
在台灣讀過中學的人,都有寫週記的經驗。所謂週記,往往是指青少年學子,每逢星期日晚上於做完各種功課後,邊打哈欠,邊提筆所記的一週流水帳而言;至於導師批改那些千篇一律的生活寫照,大概也是乏味至極的吧。然而,從「桐花」,而「新橋」,而「回聲」,而「肉身」,而「吾廬」,而「史記」,這五十篇的週記,竟可以寫得如此豐富多層次!蔣勳說:「我想記憶生活裡每一片時光,每一片色彩,每一段聲音,每種細微不可察覺的氣味。我想把它們一一摺疊起來,一一收存在記憶的角落。」
這些摺疊起來,收存在記憶角落的晨昏光影、花香葉色、林風潮響,乃至於蟲鳴蛙聲,遂藉由文字而好好的收藏起來了。許多的尋常往事,在記憶的角落裡安藏不露,好似已經不見了,或者被遺忘了;然而並沒有;有一天重讀,那些文字所代表的蟲聲、潮響、花葉,以及光影種種,又都回來了。文字使各種各樣的景象重現,使當初體驗那些景象的感動也重現;同時還讓閱讀那些文字的別人也感動。文字的力量如此。
蔣勳習畫,所以在他的文章裡,視覺畫境特別彰顯。
〈看見〉文中,寫火車座中所看見的風景,以人體的肉身毛髮形容山巒原野。寫到視覺,他說並沒有絕對的黑,以十七世紀林布蘭特(Rembrandt)的畫為例:「初看都是黑;靜下來多看一分鐘,就多發現一道光。」 〈回聲〉裡,寫窗台上看秋水中解纜的船:「越漂越遠,遠到變成一個小點,遠到最後看不見了。」「如果在黃公望的『富春山居』長卷裡,船只是空白裡的一條黑線……,一條船,不用退多遠,視覺上就只是一個黑點了。一座山需要退到多遠?一片秋水需要退到多遠?因為莊子,許多畫家從視覺的巧匠,慢慢過度成心靈視域的追求者;從得意於歡呼驚叫的技巧極限,一步一步,領悟到技巧的極限距離美的沉靜包容還很遙遠。」 蔣勳把感官所及的風景,從西畫、國畫的表現方法,予以解析和比較。從肉眼觀象,到心眼體物,一枝文筆有如畫筆,將讀者逐漸導入哲理的美學境界。
那些是「秋水時至」,是「不辨牛馬」,是「泛若不繫之舟」的意味。
五十篇散文,幾乎都書成於窗前。
擁有一個家,或者只是一個房間,在家鄉,或在此地彼地有一處熟悉的地方,有四壁將我們圍起來,框起來,令人感覺自己是屬於這個世界的,而又有一種從外界抽離的安全感。我讀這些文章時,也會有這樣子的感覺。或讀書,或工作,或靜思,或外,或出神。在家鄉,或在此地彼地,屬於、而又抽離於這個世界,大概是由於有窗子的關係吧。窗,使人感覺既聯繫而又隔離。作者原先可能在那隔離的一區寫文章,或者繪畫;偶一抬頭,便看到山光水色、寒林葉落、桐花如雪、鷺鷥雞鴨……,或許,竟因而推門出戶,走入景中,變成物象的一部分,與世界融合為一體;成為線、成為點、在畫面之中。
窗前書寫,自自然然。至於一年期間,定時千二百字左右的短文,用兩個字的齊一小題標示,或斷或續,隨興所至舒展開來:〈秋水〉、〈回聲〉、〈潮聲〉、〈品味〉、〈甜酸〉、〈風尚〉、〈布衣〉,這些篇章,分開來是獨立的散文,綴連起來卻又是綿延可以貫串的。
在目錄上,二字齊一的小題各篇最後,有一篇附錄的單字題目:〈雪──紀念母親〉。
蔣勳很用心的寫這篇文章。寫下雪的季節,去V城探望病中的母親。寫雪,寫看雪的自己,和下雪天的一些記憶。窗外的雪,「富麗繁華,又樸素沉靜」的下著,屋內的燈全熄了,只留母親臥房裡床頭一盞燈幽微的光,反映在玻璃上。遠處街角也有一盞路燈,照著白白的雪景。「白,到了是空白。白,就彷彿不再是色彩,不再是實體的存在。白,變成一種心境,一種看盡繁華之後生命終極的領悟吧。」
我想,蔣勳可能是以留白的方式,來寫他最珍惜的一個記憶和思念的吧。
《此時眾生》,遂成為他送給母親,最具深義的禮物了。
名人推薦:畫布上的文筆
──《此時眾生》讀後感
林文月
勤於奔走散播美學,以深入淺出的語言對社會大眾殷殷解說何謂風格,什麼是品味的蔣勳,有一本非常精巧的書。這本書共收五十篇散文,每篇約在千二百字左右,從某年的五月開始,止於次年五月。剛剛一年,橫亙二十四節氣,周而復始的筆耕、成為這本《此時眾生》。
在台灣讀過中學的人,都有寫週記的經驗。所謂週記,往往是指青少年學子,每逢星期日晚上於做完各種功課後,邊打哈欠,邊提筆所記的一週流水帳而言;至於導師批改那些千篇一律的生活寫照,大概也是乏味至極的吧...
章節試閱
雪——紀念母親
沒有甚麼能吵醒她,沒有甚麼能驚擾她,她好像一心專注在聽自己故鄉落雪的聲音。
雪落下來了,紛紛亂亂,錯錯落落。好像暮春時分漫天飛舞的花瓣,非常輕,一點點風,就隨著飛揚迴旋,在空中聚散離合。
每年冬天都來V城看母親,卻從沒遇到這麼大的雪。
在南方亞熱帶的島嶼長大,生活裡完全沒有經驗過雪。小時侯喜歡收集西洋聖誕節的卡片,上面常有白皚皚的雪景。一群鹿拉著雪橇,在雪地上奔跑。精製一點的,甚至在卡片上灑了一層玻璃細粉,晶瑩閃爍,更增加了我對美麗雪景的幻想。
母親是道地的北方人,在寒冷的北方住了半輩子。和她提起雪景,她卻沒有很好的評價。她拉起褲管,指著小腿近足踝處一個小銅錢般的疤,她說:這就是小時候留下的凍瘡。「雪裡走路,可不好受。」她說。
中學時為了看雪,參加了合歡山的滑雪冬訓活動。在山上住了一個星期,各種滑雪技巧都學了,可是等不到雪。別說是雪,連霜都沒有,每天豔陽高照。我們就穿著雪鞋,在綠油油的草地上滑來滑去,假裝各種滑雪的姿勢。
大學時,有一年冬天,北方冷氣團來了,氣溫陡降。新聞報導台北近郊的竹子湖山上飄雪。那天教《秦漢史》的傅老師,也是北方人,談起雪,勾起了他的鄉愁吧,便慫恿大夥上山賞雪。學生當然雀躍響應,停了一課,步行上山去尋雪。
還沒到竹子湖,半山腰上,四面八方都是人,山路早已壅塞不通。一堆堆的遊客,戴著氈帽,圍了圍巾,穿起羽絨衣,臃臃腫腫,彼此笑鬧推擠,比台北市中心還熱鬧吵雜,好像過年一樣。
天上灰雲密布,是有點要降雪的樣子。再往山上走,山風很大,呼嘯著,但仍看不見雪。偶然飄下來一點像精製鹽的細粉,大家就伸手去承接,驚叫歡呼:雪!雪!趕緊把手伸給別人看,但是湊到眼前,甚麼都沒有了。沒有想到真正的雪是這樣下的。一連下了幾個小時不停。像撕碎的鵝毛,像扯散的棉絮,像久遠夢裡的一次落花,無邊無際,無休無止,這樣富麗繁華,又這樣樸素沉靜。
母親因罹患糖尿病,一星期洗三次腎。我去V城看她的次數也越來越多。洗腎回來,睡了一覺,不知被甚麼驚醒,母親怔忡地問我:下雪了嗎?
我說:是。
扶她從床上坐起,我問她:要看嗎?
她點點頭。
母親的頭髮全灰白了,剪得很短,乾乾地飛在頭上,像一蓬沾了雪的枯草。
我扶她坐上輪椅,替她圍了條毯子。把輪椅推到客廳的窗前,拉開窗簾,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一剎時,樹枝上,草地上,屋頂上,都積了厚厚的雪。只有馬路上的雪,被車子輾過,印下黑黑的車轍,其他的地方都成白色。很純粹潔凈的白,雪使一切複雜的物象統一在單純的白色裡。
地上的雪積厚了,行人走過都特別小心。一個人獨自一路走去,路上就留著長長的一行腳印,漸行漸遠。
雪繼續下,腳印慢慢被新雪覆蓋,甚麼也看不出了。只有我一直凝視,知道曾經有人走過。
「好看嗎?」
我靠在輪椅旁,指給母親看繁花一樣的雪漫天飛揚。
母親沒有回答。她睡著了。她的頭低垂到胸前,裹在厚厚的紅色毛毯裡,看起來像沉緬在童年的夢裡。
沒有甚麼能吵醒她,沒有甚麼能驚擾她,她好像一心專注在聽自己故鄉落雪的聲音。
有一群海鷗和烏鴉聒噪著,為了爭食被車碾過的雪地上的鼠屍,撲嗤著翅膀,一面銳聲厲叫,一面乘隙叼食地上的屍肉。雪,沉靜在地面上的雪,被牠們的撲翅驚動,飛揚起來。雪這麼輕,一點點風,一點點不安騷動,就紛亂了起來。
「啊……」
母親在睡夢中長長唉嘆了一聲。她的額頭,眉眼四周,嘴角,兩頰,下巴,頸項各處,都是皺紋,像雪地上的轍痕,一道一道,一條一條,許多被驚擾的痕跡。
大雪持續了一整天。地上的雪堆得有半尺高了。小樹叢的頂端也頂著一堆雪,像蘑菇的帽子。
被車輪壓過的雪,結了冰,路上很滑,開車的人很小心,車子無聲滑過。白色的雪滲雜著黑色的泥,也不再純白潔凈了。看起來有一點邋遢。路上的行人,怕滑了跤,走路也特別謹慎,每一步都踏得穩重。
入夜以後,雪還在落,扶母親上床睡了。臨睡前她叮嚀我:床頭留一盞燈,不要關。
我獨自靠在窗邊看雪。客廳的燈都熄了。只有母親臥房床頭一盞幽微遙遠的光,反映在玻璃上。室外因此顯得很亮,白花花澄凈的雪,好像明亮的月光。
沒有想到下雪的夜晚戶外是這麼明亮的。看起來像宋人畫的雪景。宋人畫雪不常用鋅白、鉛粉這些顏料,只是把背景用墨襯黑,一層層渲染,留出山頭的白,樹梢的白,甚至花蕾上的白。
白,到了是空白。白,就彷彿不再是色彩,不再是實體的存在。白,變成一種心境,一種看盡繁華之後生命終極的領悟吧。
唐人張若虛,看江水,看月光,看空中飛霜飄落,看沙渚上的鷗鳥,看到最後,都只是白,都只是空白。他說:空裡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
白,是看不見的,只能是一種領悟。
遠處街角有一盞路燈,照著雪花飛揚。像舞台上特別打的燈光,雪在光裡迷離紛飛,像清明時節山間祭拜親人燒剩的紙灰,紛紛揚揚,又像千萬隻剛剛蜉化的白蝴蝶,漫天飛舞。
遠遠聽到母親熟睡時緩慢悠長的鼻息,像一片一片雪花,輕輕沉落到地上。
【小暑】到了峰巒的高處,雨恰好也停了。
大雨
夏至前一天,我從居住的城市出發,往南出城後轉東,經過一段彎曲迂迴盤旋上坡的山道,翻越大山連綿不斷的峰巒之後,可以從層層下降的山路上眺望遠處一片平坦開闊的翠綠田疇,如果天氣晴朗,可以一直眺望到海,可以看到浮在海上遠看如龜背、凸起於碧波之間的小島。
旋子,我們預計在傍晚時分抵達島嶼東北平原上一個以溫泉著名的市鎮,寄宿一夜,第二天清晨繞過東北角的險峻斷崖,驅車到東部的海濱。
沒想到出發時天色忽然變暗,原來豔藍明亮的天空飛來烏黑的雲團。遠方滾動炸開低沉的雷聲,好像長久被積鬱壓抑的憤怒委屈,滿溢到了要翻騰激盪,在大氣間左衝右突,尋找宣洩爆發的出口。夏日午後熱帶島嶼雷陣雨前鬱悶潮濕、
飽含水分的空氣,像一塊沉甸甸、濕答答、黏膩的布,緊緊貼在皮膚上。
車子在山路上行駛。烏雲大片遮蔽了天空,光線迅速暗下來。山壁上倒懸垂掛的蕨類植物的莖葉在風中驚慌顫抖旋轉。窒悶的沉靜裡聽見大點雨滴答答打在車篷上。開始是點滴響脆疏疏落落的單音,逐漸由疏而密、由緩而急、像點點的馬蹄聲由遠而近,噠噠噠噠,越來越快,最後連成一片,大雨傾注而下,瀑布一樣銀白色的重重雨幕遮蔽了視線,雨刷急速左右搖動,雨珠在車窗玻璃上飛濺四散,長久積抑的鬱悶似乎終於可以盡情放聲嚎啕大哭。
雨勢太大,山邊坡坎混凝土護牆裡裝置的排水管水流噴射而出,像千萬條水槍。山谷窪地頃刻都變成急湍,排水溝漲滿溢出,路面也都成了水道,車行水上,耳中都是大水重重拍打撞擊車頂的聲音。「這種雨不會下太久。」B一面開車一面說。他或者在安慰我,或者在安慰自己吧。
我們原來沒有預期會下雨,氣象報告也說連續幾天都是晴天。
但是下雨或許沒有甚麼不好。在一條漫長的道路上,前面會有甚麼事情發生,我們並不知道。預期只是主觀的假設而已,假設如果一一實現,我們得意忘形,假設也就變成了執著。有了執著,預期一旦落空,就要失望痛苦。其實,一條路走下去,因為處處可能都不盡如預期,也就處處充滿了繼續走下去的無限好奇與探險的快樂吧。
到了峰巒的高處,雨恰好也停了。
許多人把車子停靠在路邊,下了車,抬頭看雨斂雲收之後一碧如洗的晴空,眺望重重山路下面連綿不斷的平原,眺望雨後新綠閃亮的稻田連接著沐浴在明晃晃陽光裡的湛藍大海,下車的人伸展腰骨四肢,轉動頸脖,有人微笑,有人跳躍歡呼。
旋子,我沒有預期甚麼,或者,我只是預期一次單純的出走吧。
我預期陽光,結果聽到了大雨滂沱。我預期晴日開朗,卻看到了最低鬱苦悶的嚎啕。我預期走在平坦順暢的康莊大道上嗎?卻為何偏偏走來這曲折迂迴、盤旋險阻、隨時要警惕落石與絕壁的山路。
車子在斜緩的山路上蜿蜒而下,遠遠長長的風從車窗吹進來。整座山滿是流水的聲音,嘩嘩啦啦,淅淅瀝瀝,錚錚琮琮,點點滴滴……。從來沒有想到,大雨過後,山裡瀑飛泉流,灘湍潺湲,水聲如歌,一路同行,是如此富裕喜悅。
【白露】也許我們應該閉起視覺的眼睛,讓心靈的眼睛有機會張開。
看見
從島嶼北部一路南下,沿路風景都在改變中。
我靠在火車車窗邊睡著了,火車行駛中平緩規律的節奏,好像一首熟悉的歌聲,空咚空咚,重複的韻律催人入夢。慢慢地進入了視覺懵懂的境遇,可是另一種思緒,相對地,卻又異常清醒起來。好像在睡夢的窗口,忽然睜開了另一隻不常張開的眼睛,看到了平常不容易看見的事物。
我看見了山巒上慢慢移動的雲的影子。很綠很綠的山巒上一塊暗色的陰影,像人體身上的胎記,好像暗示著一個我們已經遺忘了的過去。所有山脈的起伏凹凸,也因為這塊雲影的移動,顯現出極優美豐富的婉轉曲線。
山巒是倒臥下來的人體的一個局部,我彷彿看見了古代神話裡描述過的情景。開天闢地之後,創世紀的大神耗盡了氣力,倒下來死了。祂的肉體轉化成了豐厚肥沃的大地原野的土壤,祂的骨骼轉化成了稜嶒的山脈丘陵岩石峭壁;祂的血脈流成了奔騰洶湧的長江大河,祂的毛髮叢生成深暗幽谷裡的苔蘚草叢樹木。祂的左眼變成了太陽,右眼變成了月亮;祂最後的淚水流成雨季潺湲不斷的雨滴;祂口中最後呼吐出的一口氣息,停留在空中,成為飄移在藍天上久久不肯離去的一朵雲……。
旋子,長久以來,許多繪畫的人想畫出那一直停在睡夢窗口的一朵雲影。想畫出它的潔淨、輕盈,想畫出那種悠閒與緩慢的律動,想畫出在光的變化裡層次豐富的白,想畫出它在瞬息間形貌不可思議的幻化,想記住它,記住在睡夢裡看見、卻總是在清醒時遺忘了的種種。
我不想清醒,我在睡夢的窗口,張大了眼睛,看著那朵雲在山頭慢慢移動的影子,拒絕醒來。
也許我們應該閉起視覺的眼睛,讓心靈的眼睛有機會張開,有機會引領我們去看見另一個不同的世界。
我感覺到車窗外斜射進來的剛剛入秋的陽光,拓印在我手肘和面頰的一部分。是暖金色的亮光,隨著車子晃動的角度忽強忽弱。陽光的金黃裡滲透著那朵雲的影子,滲透著鐵路兩旁大片稻田的濃綠,滲透著遍布鵝卵石的溪床裡流水的反光。
火車進入隧道,陽光隱藏在山洞外。車輪和軌道摩擦的聲音被逼得很窄,山洞裡都是回聲。在一個悠長闃暗的黑洞裡,我睡夢中所有可以睜開的眼睛都打開了。我看見了很細微的光,在山洞的石壁上閃動。
視覺裡並沒有絕對的黑,心靈的視覺裡也沒有絕對的黑暗。
黑暗裡都是光在活躍,的確像是在看林布蘭特(Rembrandt)的畫,初看都是黑;靜下來多看一分鐘,就多發現一道光。
十七世紀的林布蘭特是在蠟燭的光、火炬的光裡畫畫的。他也觀察從黎明到日落的光,觀察日落到月升的光。在北國幽暗的冬天,他專心凝視夜晚雪地上一點點不容易覺察的光,專心到疲倦了,他閉起了眼睛。
我總覺得,在閉起眼睛之後,林布蘭特才看見了最美的光。那些光流動在衰老母親翻閱經書的手背上,手背上都是皴老的皺紋,皺紋隙縫暗處飽含著細細的光。
這個睡夢裡的幽深隧道好長好長,我睡去的肉身上,張開一個一個的眼睛,充滿好奇地探視著四周,我看見山壁上蕨類莖葉在風過處顫動,我看見石縫裡滲出水滴,我看見一些微細的沙塵在空中翻轉,我看見了雲變成了山巒的胎記,帶著山一起流浪。
【立冬】也許,我夢想的,更是社會學上的自由,倫理學上的自由。
自由
我從時差裡醒來,知道身體某個不肯睡去的故鄉在那裡。而此地已是深秋,遍地落葉。
旅店的窗口向南,東方初昇的太陽從左側照亮窗外的港灣。港灣很長很長,一帶藍色的水,在黎明的光裡微微發亮。
港灣的北端有一些巨大的起重機械的裝置,好像是停卸貨物的碼頭。因為距離遠,看不清楚細節,感覺不到碼頭的雜亂。或者,也還是清晨,一切忙碌尚未開始,船舶似乎也還在沉睡。
有一條很長的鐵橋,從港灣的北端向南延伸。鐵橋從我的窗口看去,是一條清晰的黑色的線。剛開始,黑線貼著水面,逐漸加高,從水面升起,跨過海灣,連結著南方的一片陸地。
我眺望陸地遠處,有一座城市。密聚的高樓堆擠在一起,在長長的海灣和陸岬之間,看起來像一個突兀的神話。
關於這個城市,有過一首美麗的歌。歌一開始就告訴你:如果要去這個城市,別忘了在頭上戴一些花。
年輕時候唱過的歌,總是很難忘記。
年輕時候也很容易相信,一個要戴著花前去的城市,一定是美麗的城市。
旋子,美麗究竟是甚麼?
美麗是心裡永遠不會老去的一些夢想嗎?
我們夢想甚麼?我們夢想過甚麼?
我坐在窗口,隔著一大片海灣,遠眺那座我夢想過的城市;隔著歲月,回看我夢想的細節。
細節都不清楚了,我只記得,那麼渴望過自由。自由是甚麼?也並不具體。或許像一對翅膀,可以飛起來。即使在肉體最沉重的墮落的重量裡,仍然可以藉著心靈夢想的自由,輕盈地飛起來,飛在城市的上空。
如果我的故鄉使我心靈沉重,我就在頭上戴了花,流浪到遠處去,尋找一個使我可以飛起來的地方。
我夢想過一個城市,人們在頭上戴了鮮花。他們在街上互相擁抱、親吻,他們彼此和善微笑,他們在憂傷的時刻,彼此依靠。
我夢想的自由,不僅僅是政治上的自由,也不僅僅是經濟上的自由。
也許,我夢想的,更是社會學上的自由,倫理學上的自由。是從一切人為的規範限制裡解放的自由吧!
這麼多年之後,我才開始領悟,我夢想的自由,其實是審美上的自由。
政治的自由,使人從牢獄迫害裡走出來。經濟的自由,使人從貧窮飢餓裡走出來。社會的自由,使人從階級裡走出來。倫理的自由,使人從宗教家族的禁忌裡走出來。
然而,我還是不自由的。我的心靈可以是自己的牢獄。我們可以衣食無缺,但是心靈貧窮。
旋子,我在無階級的社會裡沒有看到真正的平等。旋子,我無法解釋,每一次倫理的革命之後,都又樹立了新的權威與禁忌。
「他們不美!」我今天在街道上看到一個老人,他手上拿著一個牌子,上面書寫著幾行反對戰爭的句子。他批判戰爭,批判他的政府,他的國家,批判政客與官僚,批判庸俗貪婪的財閥。
路上行人匆匆走過,或停下聆聽。我注意到老人稀疏的白髮鬢邊戴了一朵紅色的花。
【春分】春雨連綿,麻雀會來屋簷下避雨,他們不多久飛去,再來時口中啣草。 吾廬
春雨連綿不斷,幾隻麻雀飛來簷下避雨,停棲在我窗台。不到一尺距離,我停下工作,細看麻雀轉頭顧盼,小心翼翼,抖擻身上雨珠。我不確定,牠們是否看懂我臉上微笑,逐漸沒有戒心,一步步靠近,與我相對凝望。
想起陶淵明的詩「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麻雀暫來屋簷下託身,使我一時眷愛起自己的家。
童年住在城市邊緣,家的四周是菜田。走在田陌間,菜花招來蝴蝶飛舞。清溪水渠環繞,水聲嘩嘩。腳步踏過,青蛙紛紛跳入水中。我低頭看,濁水澄清處,水上漂著浮萍、菱葉,水底密聚螺螄、蚌殼、蛤蜊。
菜田邊一排四棟黑瓦平房,是省政府宿舍,我家是第一戶。斜屋頂,洗石子灰牆,竹籬圍繞一圈。因為是邊間,院子特別大,種了許多植物。柳樹、扶桑、芙蓉、番石榴高大枝椏橫伸出竹籬,常引來路人攀折;低矮的草本花卉有海棠、美人蕉、雞冠花、雛菊,菜圃裡還有母親種的番茄、茼蒿、蕹菜、辣椒、茄子。紅嫣紫翠,顏色紛紜,一年四季都好看。
每日下課,回到家,幫忙餵雞餵鴨是我的工作。我先跟姊姊去池塘,用竹篾編的籮撈浮萍,再隨哥哥去溝邊挖蚯蚓,這兩樣都是餵鴨子的食物。黃昏以後雞鴨鵝都回家,各在院子佔一角落,相安無事。偶然一隻公雞跑去追鴨,母親厲聲喝止,罵道:「做雞也不安分!」母親語言挺奇怪,我聽不懂,公雞卻似乎知錯,低頭回到雞群,乖乖臥下不語。母親高興,便讚美:「比人還懂事。」
我家養了雞鴨鵝,沒有養豬。附近鄰居幾乎家家養豬,家門口都置一土甕,用來盛裝廚餘餿水。後來我才知道,「家」這個漢字,象形著屋頂下養了豬。漢代墓葬出土最多豬圈,豬圈形式不一,方的圓的都有,造形稚拙可愛。一隻肥大母豬,躺在地上,五、六隻小豬仔趴著吸奶。漢代綠釉陶製作的豬圈、水井、灶間,洋溢著生活的幸福感,使人領悟,「房子」並不等於「家」。「房子」只是硬體,「家」還是要有人的生活內容。現代城市的建築,無論多麼富麗堂皇,不知道為甚麼,總讓我覺得,屋頂下常常少了內容,「家」變成空的殼子。
農業時代,屋頂下總要豢養點牲畜,才像一個家。灶間總要鍋碗瓢盆,有點柴米油鹽氣息,才像一個家。現代工商業社會,屋子裡豢養牲畜當然困難,工作忙碌,家裡自己開伙的也越來越少。我常常在想,如果再造現代漢字的「家」,屋頂下應該放進甚麼內容?
屋頂下是否至少應該有個「人」呢?我不敢確定。
許多講究的住宅設計,總讓我覺得是一個櫥窗,櫥窗只需要在外面觀賞,並不需要生活,不需要有「人」做內容。一個朋友邀我看她的家,說是「極簡」風格。我走進廚房,進口的廚具簇新,外層的護膜還在;我又走進衛浴間,全白的顏色,從天花板到地面,乾乾淨淨,鍍金的水龍頭發著冷冷的光。一面很大的鏡子,映照出我和主人的臉。我問主人:「在這裡住了多久?」她想一想,說:「兩年了。」聽起來好荒涼。
我沒有說甚麼,我懷念起自己的家,懷念起小時候種滿花樹的家,和雞鴨一起長大,黎明時會被殺豬的淒厲叫聲驚醒。我也懷念起現在的家,窗外有一條大河,月圓時會在窗台打電話給遠方朋友,要他抬頭看一看月亮。
春雨連綿,麻雀會來屋簷下避雨,他們不多久飛去,再來時口中啣草,在簷下隱蔽處跳躍忙碌,似乎決定此處是可以安身的處所。
雪——紀念母親
沒有甚麼能吵醒她,沒有甚麼能驚擾她,她好像一心專注在聽自己故鄉落雪的聲音。
雪落下來了,紛紛亂亂,錯錯落落。好像暮春時分漫天飛舞的花瓣,非常輕,一點點風,就隨著飛揚迴旋,在空中聚散離合。
每年冬天都來V城看母親,卻從沒遇到這麼大的雪。
在南方亞熱帶的島嶼長大,生活裡完全沒有經驗過雪。小時侯喜歡收集西洋聖誕節的卡片,上面常有白皚皚的雪景。一群鹿拉著雪橇,在雪地上奔跑。精製一點的,甚至在卡片上灑了一層玻璃細粉,晶瑩閃爍,更增加了我對美麗雪景的幻想。
母親是道地的北方人...
目錄
〈畫布上的文筆〉林文月
〈願〉
卷一 夏天
桐花
月桃
螢火
相思
棲霞
大雨
溪澗
瀑布
魚肆
月升
葉子
卷二 秋時
渲染
新橋
沙灘
眼前
翅果
看見
蘋婆
秋水
回聲
欒樹
潮聲
鴨子
卷三 冬季
時差
自由
候鳥
銀杏
寒林
舞者
黑暗
溫泉
泡湯
野溪
燒水
風景
卷四 春日
竹內
眾生
肉身
品味
甜酸
風尚
布衣
吾盧
城市
遲行
速度
輸贏
華山
卷五 夏天
退之
史記
【附錄】——雪
【編者後記】〈如是因緣〉許悔之
〈畫布上的文筆〉林文月
〈願〉
卷一 夏天
桐花
月桃
螢火
相思
棲霞
大雨
溪澗
瀑布
魚肆
月升
葉子
卷二 秋時
渲染
新橋
沙灘
眼前
翅果
看見
蘋婆
秋水
回聲
欒樹
潮聲
鴨子
卷三 冬季
時差
自由
候鳥
銀杏
寒林
舞者
黑暗
溫泉
泡湯
野溪
燒水
風景
卷四 春日
竹內
眾生
肉身
品味
甜酸
風尚
布衣
吾盧
城市
遲行
速度
輸贏
華山
卷五 夏天
退之
史記
【附錄】——雪
【編者後記】〈如是因緣〉許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