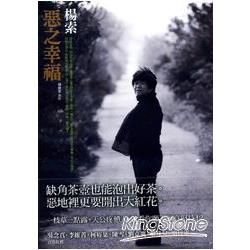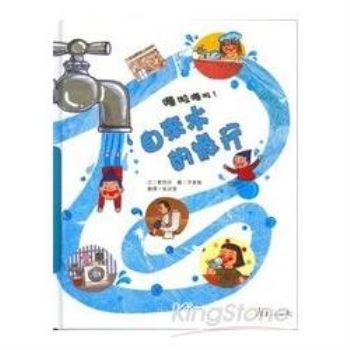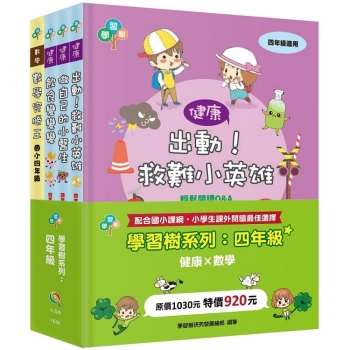有些記憶
回想時
像刀往深處鑽
見血了刺骨了
才得以釋然
而那一切都過去了,不會再有衝突、痛苦、哭泣
因為所有的冤錯,都被銘刻起來!
最衝擊的文字影像
最震撼的家族故事
最不忍的真實記錄
楊索勇敢揭傷,真誠自剖,打破『甜蜜家庭』的溫情濫調
草根的浮生群相,細瑣卑微,渺小平淡,楊索的筆讓他們浮凸顯影,呈現出周遭的景深明暗。
★吳念真、蔡珠兒、李維菁、柯裕棻、陳雪、劉克襄、駱以軍,真情推薦!
★楊索繼文壇處女作《我那賭徒阿爸》之後,再度回顧半生,譜寫成最深刻的懺情錄!
★名作家傅月庵、名設計者楊雅棠跨刀編輯設計,拿得起,絕對放不下的動人之作。
家族情感的斷裂、撕碎,對人生究竟有何影響?
惡是必然,因為生在人間。遭逢惡,是否即沒了幸福?
惡是一塊巨石,橫亙途前,你得用力攀爬,用心去滴穿。
有時不甘心,有時問天無語。但,走久,路也就出來了。
奮闘,即是一種幸福!
祝你健康!祝你青春美麗!祝你幸福!
作者簡介:
楊索
有土味的台北人,出生於台北市萬華,在永和長大,是城鄉移民第二代,父母來自雲林縣,楊索對父祖原鄉雲林充滿思慕之情。曾任職中國時報記者多年,調查報導社會底層議題。平時熱愛閱讀、動物,特徵是緩慢,著有《惡之幸福》、《我那賭徒阿爸》散文集。投入創作後,相信俄國小說家契訶夫所言:「作家有權利,甚至有義務,以生活提供給他的事件來豐富作品, 如果沒有現實與虛構之間這種永恆的互相滲透、參差對照,文學就會死於貧瘠。」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名人推薦
「從《我的賭徒阿爸》到《惡之幸福》,楊索筆下的少女長成了中年作家,父母親老了,弟妹們長大了,那些生命中盤旋不去的主題,貧窮、困窘、痛苦、難堪、悲傷還在作者身邊無情地變奏,然而,作者在自己的創作中成長,且看見了筆下描寫的世界亦同時隨著書寫維度的開展而成熟,寬闊,做為經驗者與寫作者的楊索,對抗著心中湧現的悲情或傷情,她持續書寫並持續地與這些主題搏鬥著,自覺孤獨渺小,卻不自覺地長成了一個勇者。」—— 陳雪
「來自最底層艱困的生活歷練,造就了作者沛然淋漓的書寫內涵,更照見了真實具體的下階層風貌。過去的散文創作少有這等面向,以及從此一角度帶來的菜市塲顯影。她從童年悲苦取樣,深邃地檢測出我們無從擺放的驚愕與感傷。」 ── 劉克襄
「當我們對昔日街景已變成一種時光博物館,老相片櫥窗;楊索的文字讓人驚痛,像一地粼粼閃閃的碎玻璃,被記憶的大掃帚掃得灰塵漫天。那讓我想到梵谷的〈食薯者〉,暗室裡一家人惶然、絕望,每一張臉浸沒在各自命運將被剝奪、損害、錘凹踩扁的陰影中,他們那麼艱難攀抓著「生存」本身,緊偎、互相憎恨、原諒、分開,再重新於衰老變貌、淚痕汗酸、油煙鑊氣的幽微黯影被這隻傷痛卻溫柔,鏽礪卻晶瑩的筆,一一打撈、尋回。」 ——駱以軍
「 這是楊索不斷淘洗自己內臟寫成的傷痕之書。
嗜賭的父親、受虐的母親、曾經明亮可愛卻被人生磨損到面目黯淡的兄弟姊妹,還有這個懷著嫌惡與罪惡感而叛逃離家的女子,一路從攤販、女工、記者成為作家。貧窮之逼迫,弱勢家庭隱藏的暴力與憤怒,原生家庭的傷害支配了一整家子的命運。
楊索以誠懇平實的方式一一寫下家庭記事,一個一個縈繞不去的記憶,沒有時興的家族華麗尋根追索,而是實實在在將六○年代以來的台灣社會變遷與底層生活的連結,一一記下。
楊索花了許多年,試圖以文字理清並卸下背了半生的重擔。她筆下的家,每人的腳步都走得顛顛簸簸,惡善難辨,暴力與軟弱交錯,人生最後,不見慈悲卻也終見寬容。
家是一群帶著缺陷的人,試圖餵哺卻又重傷彼此的過程。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終究都是渴愛之人。 」 ——李維菁
推薦序
苦海,女神龍
蔡珠兒
楊索是雲林二崙人,我是南投埔里人,兩縣之間,隔著一條滔滔的濁水溪。她在台北出生,永和長大,我六歲來台北,在木柵長大,兩地之間,隔著一條蜿蜒的新店溪。二十多年後,在新店溪的華江橋頭,我們才跨過溪流相遇,先是報館同事,後來成了知心好友。
那是一九九○年的初春,有一晚,辦公室照例鬧哄哄,人聲雜沸如夜市,我拿著膠水,正在發稿(這要注釋一下:那時的新聞稿不但手寫,還要把稿紙一張張黏接起來,以便快速排版),一抬頭,看到主管領著她走進來,矮矮的個子,飄飄的腳步,圓圓的臉,濃濃的眉,淡淡的表情,眼睛不大,卻晶亮有神。
四周頓時靜下來,只聽到同事竊竊私語,「從《新新聞》挖來的耶」,「聽說是個小辣椒,很兇悍喔」,「跑政治的,來文化版做什麼?」
小辣椒果然有料,文化新聞原本風花雪月,溫良恭儉讓,被她一跑,卻犀利明銳,稜角盡現,她的稿子擊中要害,常有迴響,甚至掀起波瀾,包括律師信,以及傳話或打電話來「關切」的高層官方。那個剛剛鬆綁的年代,表面狂飆釋放,自由開揚,底下卻仍暗礁重重,磕磕絆絆,要手摸腳踩,逐步上壘,才能得寸進尺,挪進空間。
楊索生猛奮勇,經常踩線越界,招呼人少得罪人多,讓長官頗傷腦筋,有時擺不平,只好忍痛把她調走,她跑過各種新聞,在報館換過不少單位,有人打趣說,楊索呀,就差沒派去食堂打菜了。但無論喜不喜歡,大家都知道,她是個身手不凡的「好咖」。想當年,那家報館雖然亂糟糟,鬧哄哄,好勇鬥狠又重男輕女,然而洋溢自由之風,管事的還是識貨,愛惜才情,看重個性,再不爽也要(至少裝作)包容。
我們在文化版相識,又在綽號「重案組」的資深記者室重聚,共事的時間並不長,卻因所見略同,聲氣相投,成了要好朋友。除了欣賞她的文筆和幹勁,我對她還有種深摯的親切感,覺得她彷彿「隔壁庄」的同鄉,有說不出的熟稔喜歡,我們因此有說不完的話,經常交換見聞觀點,彼此切磋打氣,相互戲謔或安慰。
更重要的是,我跟她同病相憐,患難與共,在政經掛帥的報館,我們屬於邊緣人,專寫旁門左道。她悲憫善感,關注不幸和災難,常潛進社會底層,披露暗角的弱勢族群,例如「流浪三部曲」,寫遊民、流浪兒和流浪狗的;我則寫些「沒路用」的現象觀察,什麼檳榔啊瑪丹娜啊空間文化啊,在同事眼中,這兩個簡直五四三,阿里不達。
我們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寫稿都很焦慮,又慢又龜毛,磨磨蹭蹭,塗塗改改,不停自我質疑,反覆推敲,煎熬個沒完沒了。我常深夜伏案,寫到報社人去樓空,不覺拂曉天光,清潔工推門進來,看到一個披頭散髮,面青唇白的人,嚇了一大跳。更多個晚上,我和她各據一角,在空蕩清冷,燈光陰慘的辦公室咬筆苦思,無聲奮戰,像兩縷出竅幽魂。
同事笑我們是「苦情姊妹花」,一起去吃宵夜,唱卡拉OK,我們兩個最愛唱的,的確也是悲歌,尤其〈孤女的願望〉和〈苦海女神龍〉。
「無情的太陽,可恨的沙漠,迫阮滿身的汗流甲溼糊糊,拖著沉重的腳步,要走千里路途………」,走音的哭調,低啞的嘶吼,淹沒在同事的笑語煙味中,K歌總是煽情膨風,小事就雪雪呼痛,沒人知道,那苦楚的歌聲,是真實的吶喊寫照。
和楊索雖然相熟,聊的卻多是工作和八卦,偶而提到家庭身世,她總是若無其事,寥寥幾句,淡淡帶過,我聽了,心底的震波卻迴盪不散。斷斷續續,點點滴滴,我知道她的成長經歷,終於明白,為什有對她有莫名的親切感,因為直覺的觸鬚,偵測到相近的心靈頻率,聞到孤獨與受傷的氣息。
我們都出身窮苦家庭,弟妹眾多,食指浩繁,父母是「出外人」,從外地遠來台北謀生,蝸居於衛星鄉鎮,在城市底層辛苦打拚。我們的童年匆促短暫,青春期暴烈憂傷,被迫提早進入成年,一路踉蹌跌撞,身心磨損內傷。
貧窮不是原因,家庭傷害才是元兇———那個年代誰不窮,當年的困苦匱乏,反倒激勵社會流動,造就出日後的成功傳奇。我和她的家庭,除了窮困而且破損,功能紊亂失調,表面上父母雙全,闔家團聚,內裡卻支離碎裂,鬆垮崩散,令孩童惶惑不安,雖然有家可歸,卻充滿孤苦無依之感。
然而比起楊索,我的經歷微不足道。不知是否因為來到台北,失落離群,父母親變成狂熱的教徒,寄情彼世他方,輕忽此生,漠視家庭和子女,我們缺乏關愛照顧,在半遺棄的狀態下,自己摸索成長。但父親是低層公務員,家裡至少有基本溫飽,在這庇蔭下,我能工讀完成大學,逆流上游,掙脫家庭和階級宿命。
雖說是好友與同類,但直到多年以後,讀完楊索的第一本書《我那賭徒阿爸》,我才悚然了解,那深鉅長遠,核爆般的傷害規模。父親好賭成性,母親憂鬱多病,窮困,飢餓,家暴,失學,哀愁,這個敏感早慧的少女,在人海浮沉,獨自求生,成長後又情路顛躓,總是碰上「錯誤的對象,缺角的戀情」,歷盡人生的風雨惡浪,炎涼滄桑。
然而,這書卻不是悲慘催淚的《阿信》,更非奇情曲折的《苦兒流浪記》,在我看來,更像《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有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味道,在命運悲劇與精神危機中,經由波折苦難,逼視人性本質。楊索以抽離內斂的文字,拉遠距離,拔出視角高度,沒有抽抽搭搭,哭訴怨艾,而是隔著時空大河,俯看自己的軌跡流脈,有一種洞察與蒼涼。這非常非常難,自我的焦距近了糊,遠了散,至少我就做不到,無法書寫家庭創傷。
六年後,楊索又出了這本《惡之幸福》,繼續以文字爬梳觀照,救贖治療,用素樸的白描,原汁原味的對話(這才是台語呀,不是偶像劇那種恐怖的塑膠腔),書寫家庭和人生。也許如她自言,時間磨平稜角,把人變得柔和,比起前作,此書較為平靜沖淡,文字密度清疏了,敘述濃度和感情強度,都比較鬆柔舒緩,意味著更加寬容同情———尤其對自己。
「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楊索勇敢揭傷,真誠自剖,打破「甜蜜家庭」的溫情濫調,固然感人至深,此書隱含的社會意義,更值得細思。
「家族書寫」是多重文本,縱橫深淺,有各種功能和讀法,文本的主旨,在於梳理廓清,藉此省察個人的身體、心理、性向、情欲、道德或群己關係,重現以及重建身分認同。然見微知著,推近及遠,這種書寫也是鮮活的社會切片,時代取樣,從中可見地域、性別、族群和階級的差異,透析出價值觀和文化衝突。
我和楊索分屬四、五年級,成長於一九七○年代,數十年後,台灣早已起飛轉型,兩岸相通,全球流動,家庭和故鄉的意涵,逐漸鬆動質變。現在的「出外人」,可能指上海的台商,紐約的台籍基金經理,往返頻繁,不知鄉愁為何物。飛機和高鐵貫穿島內,時空縮小了,但城鄉和貧富的差距,卻愈來愈大,家庭孕育的不幸,仍舊如宿疾般延續相傳。
都會邊緣,離鄉移民的第二代,依然沉澱在底層,繼續複製家暴和貧窮,就像楊索描寫她的三弟,是「台灣底層切面的一個微小的黑點」。至於她的二崙鄉親,當年那群北上討生活,被都市吸汲血氣魂魄的「青春鳥」,現在大概換成外勞了吧。這些草根的浮生群相,細瑣卑微,渺小平淡,楊索的筆讓他們浮凸顯影,呈現出周遭的景深明暗。
不過,這本書我最喜歡的一篇,不是寫家人,是〈解嚴與烤雞〉,寫早逝的攝影記者葉清芳,從不存在的烤雞,帶出一個悲劇人物,勾勒出一個崩亂虛無的年代。楊索寫人物是絕活,她直覺敏銳,有感性又有洞察力,文筆滋潤多情,卻又清淡凝鍊,意味悠遠,有獨特如簽名的沉鬱風格。
最後,既是好友,當然要講講這個人。別看楊索文字沉鬱,性格硬淨倔強,她其實熱情又幽默,對朋友像小貓般依順柔軟,體貼細心,但她又有獅子座之風,豪氣能幹阿莎力,親和有人緣,跟黑白兩道三教九流都有話說,去哪裡都能碰上光怪陸離之事,精采奇異之人,交遊廣,見識豐富。
近年楊索寫起小說,我很高興,她的裝備夠精良,醞釀也夠久,應該是發揮的時候了。就像種植一樣,生命的傷痛苦難,原是沉重惡劣的負擔,然而經過時間的漚養,終會轉化為深層的肥美養料,沃養心靈的深度與厚度,使人更清明更悲憫,對世間諸相,更有同情感應。
有苦海,才能浸煉出女神龍,家庭作業寫完了,我覺得楊索應該走出來書寫人生,她還有巨大的潛伏能量,尚未噴薄而出,淋漓湧現。
名人推薦:名人推薦
「從《我的賭徒阿爸》到《惡之幸福》,楊索筆下的少女長成了中年作家,父母親老了,弟妹們長大了,那些生命中盤旋不去的主題,貧窮、困窘、痛苦、難堪、悲傷還在作者身邊無情地變奏,然而,作者在自己的創作中成長,且看見了筆下描寫的世界亦同時隨著書寫維度的開展而成熟,寬闊,做為經驗者與寫作者的楊索,對抗著心中湧現的悲情或傷情,她持續書寫並持續地與這些主題搏鬥著,自覺孤獨渺小,卻不自覺地長成了一個勇者。」—— 陳雪
「來自最底層艱困的生活歷練,造就了作者沛然淋漓的書寫內涵,更照見了真實具體的下...
章節試閱
內文試閱一
惡之幸福
我一直沒有忘記那一幕。
九歲那年夏天,我走入巷口雜貨店,看著牆上、攤架上一堆抽糖果的抽抽樂,其中有一款全新、無人開張的抽紅包袋,攫住我的眼神。我拿出口袋裡的五毛錢給老闆娘,對她說:「我要抽紅包袋。」老闆娘看我一眼,收下五毛錢。我看著上下左右成列小紙牌,最後隨機抽起一張,剎那間眼睛發亮,因為我抽到頭獎,一張紅色的拾元鈔票!我拿著這張小紙給老闆娘,老闆娘一邊看,一邊狠狠地瞪我一眼,接著罵說:「查某囝仔人,那麼小就白賊,緊回去!」
我說:「我抽中拾元,汝怎不給我?」
老闆娘大聲罵:「黑白講,別在這裡亂我生意場。」
我大聲回嘴:「明明我抽中,汝怎麼可以按內?」
我們一來一往的爭執引來一群人圍觀,我脹紅臉不肯離去,老闆娘也執意不肯給。旁邊的人說話了:「拾元而已,就給她算了,散散去!」老闆娘瞪著眼說:「袂應,按內我這一袋還能賣嗎?」
我急得快哭了。又有一人掏出一張紅色紙鈔說:「查某囝仔,拾元拿去,緊返去厝。」我搖頭,大聲說:「我不要,伊欠我拾元,伊應該給我。」
吵吵鬧鬧時,有人通報我父母,父母親都來了。父親一見到我,衝上來給我一巴掌,罵說:「汝在這謝世謝正,還不趕緊返去。」說著就拉著我往回走。我雙腳緊抓著地,人蹲下來,硬是不走,口中喊著:「伊要給我錢,我花五毛錢抽的,伊騙我囝仔。」
父親力氣大,硬把我拖離巷口,我終究沒討到屬於我的拾元。
國中畢業後,我離家去幫傭,因為做不慣,幾個月後返家。父親在夜市賣油湯,我日夜幫忙出攤、掌攤。一日在家中裝填筒仔米糕,父親、祖母、母親一起忙碌著。
不知為何,父親說著說著,忽然指著我開罵:「我未將汝送至『查某間』,算是對汝很好了。」我聽懂「查某間」是妓女戶的意思,霎時暴怒,將裝筒仔米糕的錫罐朝父親臉部砸去,我沒有擲到父親,父親衝過來對我拳打腳踢,我激烈地和他打起來,祖母、母親圍過來擋在我前面,祖母發話罵父親:「阿堂,汝在衝啥,查某囝仔乖乖,無衝啥,汝打她做啥?」此時,怒氣衝天的父親才停手。
我走出家門,孤單地往河堤走去,心中想著:「這個家是絕對不能待了,我要靠自己,死也要死在外面。」
至今,我仍不明白,為什麼父親會對我說出如此不堪、無情的言語,那句話如發臭的魚刺鯁在我心中,不時仍刺痛我。
以後,我離家做各種工作,即使有苦,從不向人訴說。
十六歲那年,我在光復南路一處人家幫傭,雇主家人口單純,一對夫妻和一個二十六歲的兒子,三人都是上班族,夫妻兩人是民營企業的高階主管。
我平時早晨醒來,先做清潔打掃的工作,然後準備早餐,之後洗衣、買菜,就像一個家庭主婦;黃昏時,主人回家前要煮晚餐。忙過一整天,大約九點才能休息。
我住在靠近廚房的傭人房,狹小的房間只能放一張硬板床,牆上有一扇狹窄的小窗。一天夜裡,我迷迷糊糊醒來,感覺有一束燈光照著我,我睜眼去看光源,那是從小窗射進的一束光,來來回回照著我,我嚇呆了,依稀記起小窗的後面是廚房的冰箱,到底是誰移開冰箱?那一夜我充滿恐懼,但隔天,我並沒有問人,以後也就忘了。
時間過了半個多月,又有一夜,我半夢半醒間,忽然感覺有人翻動我的身體,正要脫卸我的內褲,我狂叫出聲,看不清的黑影奪門而逃,我驚嚇清醒,全身發抖地坐在床沿,一夜不敢入睡。
隔天下午,女主人提早回家,她沒說明什麼,只是算清楚工錢,命令我離開她家。我沒有說明分辯的機會,就如一個做錯事的人,被趕出她家。那天我走在街上,不知何去何從,我像遊魂一樣,走在路上,腦袋空蕩蕩,腳步輕飄飄。
夜已降臨,我不願如一個失敗者返回永和的父母家,走到累了,我才想到要去租一個房子。我在電線桿、布告欄努力搜尋,後來看到通化街的一處公寓套房出租,我依照地址找到這處地方,爬上三樓,和一個男人談價錢,房租談妥後,他要我留下一千元訂金,我也就掏出錢給他。
然而,走出這地方,我愈想愈不妥,又折回找房東,告訴他我不能租房子,他冷冷對著我說:「不租就算了。」
我向他索取一千元訂金,他冷然看著我說:「不租就要沒收訂金,這個規矩你不懂嗎?」
我急著說:「我沒有錢,這一千元是要租房子用的,拜託你還我好嗎?」這時,他推我出門,並說:「沒這回事,你有本事叫警察來好了。」
我又氣又急,但被他推走了。我走下樓,有一種要昏倒的感覺,接連遇到不公平的事,讓我極度憤怒、屈辱,我沿街走到派出所,進去後對值班警員說明這件事,有兩個警員圍過來,他們三人你一言我一語說起來:「那個房東很惡劣,以前也有房客來報警,帶她去找那個房東討錢。」
值班警員陪我去房東處,按鈴開門後,房東看到警員,低頭陪笑說:「這小姐年紀輕輕,我也不知她是不是來開玩笑,所以給她收訂金。」他掏出錢遞給我說:「小事情,你幹嘛麻煩警察,錢還你就是了。」警員一句話都沒說,我收下錢,默默地跟著警察離開。
那一夜後來去哪裡,我已不記得,但我討回了一點尊嚴。
世界待我特別惡劣嗎?我曾經以為是這樣。
我從國中畢業離家工作後,就未曾伸手向父母拿過一塊錢,即使是我非常需要一塊錢。有一天我回父母家,當時口袋裡只剩幾塊錢,想搭公車返回住處,還缺一塊錢,可是,我並沒有開口。離去後,我沿著永和路走上中正橋,再慢慢地走到台電大樓搭住處的交通車。路上,我告訴自己,我能一個人活下去,這不難。
輾轉換過幾個行業,做過不少工作。在幫傭或做女工時,我訂了一份國語日報的高中函授課程,閒暇時自己亂讀,文科的我都懂,英文、數學、物理、化學,我自己讀不懂,但努力瞎背。
民國六十八年左右,我要去考高中自學學力鑑定考試,但考試辦法修正,改為年滿二十一歲始得報考。當時,我十分執拗,告訴自己一定要考試,為此,我去國語日報找一位楊先生幫忙,他建議我去找立法委員吳延環,並且幫我用毛筆寫一封信,我還記得信中引用了韓非子的一句話:「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我就帶著這封信找到吳委員,向他陳情。身著長袍馬褂的吳委員十分親和,他看完信,立刻打電話到教育部長辦公室,向朱匯森部長說:「這小孩很努力,你要給她一個機會,讓她去考試。這樣吧!看你什麼時候有空,見見她。」因為這一番話,隔了一星期,教育部長在他的辦公室接見我,我靦腆、半口齒不清地向他陳述我的請求,朱匯森一邊聽,一邊點頭,然後應允讓我報考,並指示祕書安排我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見局長黃昆輝。
我就這樣一關關獲得報考許可。可是我仍有許多科目似通非通。不知哪來的膽量,沒有錢的我,混入南陽街的補習班偷聽課,結果被班導師發現,然而這個讀大學的班導師很善良,她不僅未告發我,還留各種試題給我,掩護我免費聽課。
民國七十七年,台灣報禁開放,《中時晚報》創刊正刊登招考記者的廣告,我非常興奮,躍躍欲試。那時,我告訴鄰居夫妻想去報考的心願,他們兩人都是台大畢業,兩人搖搖頭說:「不可能,你一定考不上。」
「我知道,但是我一定要去試。」我回答說。
我的身分證登記「世新肄業」,因為國中畢業後,我曾經考上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現世新大學)。就憑著這張身分證,我去考記者,並且獲得面試機會。
我還清楚記得,面試的地點是在中華路,原《中國時報》的廣告部大樓。當天,我帶著一個黑色的大文件夾,裡面有我報刊創作投稿的剪報,還有我做過展覽企畫的文宣品。
當輪到我面試時,我搭上電梯到十樓,眼前是一個狹長的辦公室,房間盡頭有兩張圓桌,坐著一、二十人。我緊張地深吸一口氣,在他們的目視下走過一道紅毯。
我在圓桌坐下時,這群人分別問我各種問題,我慢慢回答,之後主動問大家:「我有帶一些作品,大家要不要看一下?」這群人起身走到我身旁,我站起來,翻閱剪報給他們看,有人點點頭,翻完後,他們回到座位,這時我感覺口渴,隨手拿起桌上的一杯茶,喝了一口。
這時,我看到一個面目白皙、有雙大眼的男士問我說:「你有沒有興趣到副刊?」(以後我才知道他是高信疆先生)接著另一男士說:「她就是要做記者啦!」(後來得知他是採訪主任陳浩先生,也是我生命中的貴人)此時我心中微微顫動,似感覺一線希望。當天面試並無具體訊息,但相隔一個月後,我卻接到錄取通知,要我前去報到。我簡直不敢想像,能考上記者,當時那種雀躍之情仍記憶猶新。
等我進入中晚都會組,組長文念萱透露,原來我的筆試成績很差,根本應該淘汰,可是主考委員看我的自傳很有創意,文筆不錯,同意給我面試機會。
我還記得,我的那篇自傳是用問答體書寫,標題是〈你為什麼要當記者?〉我自問自答陳述想當記者的抱負和決心。而我錄取的臨門一腳,是陳浩告訴我,當時面試,前前後後有三、四十人,大家都很緊張,沒有人敢拿起桌上的水杯喝水,我是唯一喝水的人,這一幕讓大家印象深刻。陳浩力主:「這女孩有戇膽,給她一個機會吧!」
因為這句話,我得以進入新聞界,開始我的記者生涯。記者這行業是硬碰硬的工作,不管你前一日有多輝煌的戰果,每天醒來仍要面對新的壓力,我日日緊繃面對新的挑戰,表面上充滿自信,內心卻一直覺得自己是「冒牌貨」,因為我自知學養、經驗不足,平時比別人更努力,一心想把握這得來不易的機會。
年輕時能做一個記者是很幸運的事,特別是我身於波瀾壯闊的解嚴年代,能夠在第一線的新聞戰場去旁觀社會震盪,龐雜的社會事件如岩層般壓縮,我好似經歷了許多不同的人生,我在其中觀察、思考,這一切也成為我往後走向創作的養分。
世間之路並非坦途,行行復行行,總會撞上暗礁。世人千萬種,總也會遇上各種惡人。我少年出社會,徬徨彳亍人生行路,內心總無法排解那永恆的孤寂感。為我而言,生命是苦,人生是惡水,但我總須往前划呀划地,尋找前程的光亮處。在不知不覺中,我走到中年歲月,相對於昨日我年輕時的躁動難安,這是一段平穩、沉澱的時期,我漸漸摸索出自己的脾性,去分辨什麼是我想尋求,什麼是我不想要的。我終究釐清自己的人生終極追求方向,能夠不斷地深掘、拓寬創作這條路,這是莫大的幸福。
內文試閱二
年味
那是一九六八年的除夕深夜,鞭炮聲響徹巷弄,我睜著晶亮的雙眼,興奮得睡不著。床頭擺著一雙黑鞋、一雙白襪,還有一套新制服。我抱起這些衣鞋,恨不能立刻穿上,但是我必須等待,等隔天初一清早,才能穿上新衣、新鞋。
我小學三年級,已經會幫忙父親做生意。在過年前,我到市場跟著父親賣橘子,吆喝聲不輸給大人,還會幫忙找錢。等到黃昏市場攤販散了,我們移到大街,一直到深夜才收拾回家。
除夕夜晚上十點多,父親帶著我和姊弟妹去逛夜市,為我們每人選購過年穿的衣物。前幾天,我經過生生皮鞋的店門口,看到一雙有蝴蝶結的紅皮鞋,我非常渴望有這雙鞋,可是,我知道父母不可能買給我。父母要買鞋給我,是讓我開學穿的,在那時,有誰家小孩穿紅鞋去上學呢?
父親帶著我們走過一攤又一攤,一家又一家店,他口袋裡的錢不多,買每樣東西都需要好好考慮。我們是做生意人家,知曉愈晚逛街愈好,那時攤販、店家都準備休息,還價時會比較阿莎力。
那晚,夜市人擠人,很多大人、小孩和我們一樣都是要添購新衣、新鞋。差別是,他們多由母親帶隊,我們是跟著父親往人群擠。
母親留在家裡,是為了和祖母準備牲禮拜神。其實,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喜歡跟爸爸出門,爸爸雖然是市場攤販,每次外出,還是打扮整齊。他對自己的長相頗有自信,走路時腰背挺直,我們跟在父親後頭,也覺得有光采。
同時,父親的口袋,只要有足夠的錢,他還是捨得給我們買東西,甚至可能給弟弟們買玩具。夜市鬧哄哄地,人人臉上充滿喜氣,那時,我還不太懂得憂愁,因為左右鄰居的生活狀況都差不多。我們租屋處的房東有個養女叫小晶,和我同年,她天天挨打,即使是除夕早晨,她還是被打得哇哇叫。和她相比,我覺得自己的日子好多了。
父親領著我們在夜市繞了幾圈,終於給每個小孩買了新衣,姊姊和弟妹們都有一件新棉襖,我指定買新制服和新鞋、襪子。買完東西,我們隨著父親沿永和路走回家,夜已經很深,鎮上各戶人家開始放鞭炮,炮聲不斷,我很興奮,感覺一顆心如小鳥鼓翼撲張,咚咚咚地,跳得很厲害。
回到家,我已睏倦,但,我仍強睜著眼不想睡,床頭擺著初一早晨就可以穿上的新衣、新鞋和白襪,我感到發自內心深處的喜悅。
終於,強烈的睡意襲向我,朦朧睡夢中,我似乎聽到幾個大人的對話聲。阿媽對父親說:「阿堂,過年時陣,毋倘擱去搏(賭博),厝內一堆囝仔要食飯,你著卡識想一下。」阿媽話音未落,母親跟著說:「年尾拚年關,有本錢要留著年後做生意,毋倘去搏。」父親的聲音粗礪:「你查某人識什麼?誰講我會去博?」
我在一陣陣炮聲中醒來,姊姊、弟妹們早就出門去放水鴛鴦、金魚火花了,我趕忙穿上新衣新鞋。家裡只有祖母、母親低頭坐著,大年初一,她們倆人卻在落淚。我問說:「阿媽、阿母,恁是按怎?」她們搖搖頭回說:「無啥代誌啦,你緊去行春啦!」
我看著屋內,有發糕、年糕、菜頭粿,還有一整隻雞和一大鍋長年菜,心中雀躍。這是我家過年才有的食物。我匆匆喫了一碗菜頭粿湯,就出門去了。
一日日過去,年味漸漸淡了,過了十天,我才看見父親,他雙眼發紅,整個人有一種過度亢奮後的疲憊,我看得出來,他比過年前做完生意還更疲累。
父親進門時,祖母說:「阿堂,你擱會認得轉來的路喔!」父親坐下來,沒有回話,也沒有笑容。母親接著發話:「你是攏輸了了,是麼?」此時,父親忽然從椅子跳起來,對著母親罵說:「駛你娘,我衝啥,敢有需要你加講話!」掉淚的母親撲過去,喊說:「做生意的本錢,你攏輸了,歸厝內大大細細欲食啥,年猶未過完,你就輸了生意本,你敢是查埔人?」父親狠狠揮了母親一巴掌,五條指痕印在母親的右頰上。母親用雙手捶打父親,父親還手更重,母親被打到哀嚎,在混亂的扭打聲中,我聽到祖母哭泣的聲音以及罵聲連連:「我按怎歹命,生了這款敗家後生。」看見父母打了起來,站在旁邊的我和弟妹們嚇得哭了。
一片吵鬧聲,驚動我們居住的三合院鄰居,大人、小孩圍攏在門檻觀看。我回頭罵他們:「看啥?有啥好看。」我一怒,把木門關上。
父母打累了,倆人疲倦地坐下來。九歲的我望著他們,又從通舖的木窗望向河堤的方向,我怔忡呆坐著,忽然感覺一身的新衣、新鞋都舊了。那一刻,我感覺到一種莫名的況味。一年年過去,我再也尋不回那年將制服、新鞋、白襪放在懷裡入睡的甜美滋味。
內文試閱三
情人
當我寫下這兩個字,腦中掠過幾個身影。我的情感豐富,問題是,我沒有愛過正確的人,三十多年,胡打蠻纏,傷痕累累。
我天生反骨,小時候,父親多番告誡:「不准吃牛肉,吃牛肉命格會『破』」。
我想這是父親的迷信,偏偏不信,等我身上有錢,第一件事就是去吃牛肉麵。
我有三段情,那三個男人都屬牛。
第一頭牛是我的初戀,那個男人大我十歲。我十七歲遇到他,那時的我,天真、單純,對世界毫無防備,也無招架之力。
我們也和許多戀人一樣,看完深夜場的電影,在街頭漫步到天明,有時從景美步行至永和喝豆漿。
那段時期,我單獨走在路上時,經常心神恍惚,有時面紅耳赤,感覺街上的人都盯著我。他帶我去許多地方,讓我認識「真實社會」。他說:「社會有很多面向,要多看才能理解。」可是,我和他共同經驗的事務,已超出我的年齡。愛情,令人感覺既甜美又可怖。
時日一久,我漸漸看出他性格的陋限:懦弱、拖延、缺乏決斷力。他開立了一家卡片禮品中心,同時印製各式卡片、相本。每年到聖誕節旺季,各家紙品公司的聖誕卡已上市,他的還在印刷廠等待裁切。
我們交往了六年,每年的冬天都是我的噩夢。在冷雨的日子,我不是整夜在印刷廠烤松香卡片,就是在禮品中心整理存貨。當時,公館大學口有一位韓國華僑老太太賣煎餃、泡菜,我總是餓到深夜才去她的攤位吃宵夜。
我幾次想和他分手,卻未能成。我也是個軟弱的人,切不斷的情緣是一場災難。
一度,我們差點結婚。那是民國六十九年的初夏,前一夜,我們慎重地討論婚事,他找了兩位同學,約好隔天到台北地院公證處證婚。第二天上午,這兩位朋友穿著正式西裝,神采奕奕來了。我們倆人,他身穿兩、三天未更換的外出服,我則穿襯衫、牛仔褲。
我們四人進入公證禮堂,周圍是一群身穿西服、白紗禮服的新人,隊伍排得好長。當下,我覺得很累,於是對他們三人說:「算了,好麻煩,要排那麼久,改天再來。」兩位準證婚人很錯愕,可是準新郎似乎並不訝異。瞎忙一場,接近中午,我們四人走到附近桃源街,各吃一碗牛肉麵後回家。我記得,那天我吃清燉,滋味特別好。
後來,我和他終於散了,但也不是一刀兩斷。我們又拖延了一陣,直到有一天,我發現自己最要好的同學為他送便當,看到兩人的親熱互動,才斷絕聯繫。
結束這段感情後,我們近三十年未見面,三年前在館前路和信陽街的紅綠燈口,我們相遇,兩人都有灰髮,他依舊穿著麻布唐裝,衣領、袖口仍有汙漬。
我很開心遇到他,問他現在做什麼,他也問我做哪一行。我對他說:「好久不見,我們去喝杯咖啡聊聊?」結果他看一下錶,回答:「不了,我要趕著和人見面,遇到就好了。」我們在路口交談不到一分鐘,即各奔前路。
後來,我自己去喝杯咖啡定一定神。看到他,我並不覺傷感,我想起許久以前,曾與和他相戀的老同學通電話,同學對我說,她也是受害者。她說:「他有一次開車載著我,激動到要去撞火車。」是什麼因素,令他如此?我和同學並未多聊。我啜一口咖啡,回想方才所見的蒼老男子,慶幸當年只去吃了碗清燉牛肉麵。
第二頭牛,小我兩歲。我沒有以大欺小,或故做滄桑,我仍是無可救藥地一頭栽入。故事的文本經常以誤寫誤讀開始。那時候,我並不想談戀愛,而他剛失戀,在朋友的慫恿下,有意無意和我接近。
他是個長不大的男孩,身為家中的老么兼獨子,上有四個姊姊,從小像寵物被捧在手心裡。還好,他的心地善良,並不驕縱,只是在我眼裡,他蠢得無可救藥,又不知自己的侷限。
另一方面,他又聰明,在交往之初,這頭牛即告訴我:「我不適合婚姻,我不想結婚。」這句話擺明,他只想要相偎取暖,不要地久天長。我呢,我也沒想過,戀愛要跟婚姻劃上等號,寂寞的我,只是想和一個人建立關係。
他的眼、眉、笑容都很迷人,漸漸地,我愛上了他。倆人相處時,是我最開懷的時候,因為我們像兩個孩子,相互戲謔、追逐。然而,和所有的戀人一樣,感情投入愈深,對彼此的要求愈多,來自他家的阻力也開始增強。
我們不斷爭吵,又在淚水中重新開始。有一回我盛怒,打了他一巴掌,他摸著臉,問說:「你為什麼這樣對待我?」我答不出來。我怎麼說得出,那一巴掌夾雜著我對人生的憤怒。
有一天,我主動提出分手,他點起一根菸,面向牆壁,抽完菸,又續點一根,他沒有抽,只是讓菸燒成灰。之後,他對我說:「最近,我想要認真對待這份感情,想要好好愛你,現在你卻要斷了。」
殺了兩頭牛,我也短暫和雞兔同籠,但我仍不瞭解男人。曾經,有位男人點撥我:「男人都好色,好色勝於情。」而我其實渴望真情,只是皮相之下,如何問情?
我情路多舛,總遇不到對的男人。有一日,我忽然大悟,問題或許不在別人身上,而是在我內心深處。我畏懼被婚姻繩索綑綁,套牢一生,因此總是避開有可能走向婚姻的親密關係。
那些年,從我生命中走過的人,有好有壞,可是,人性不都如此嗎?在他們眼中,也許我才是個惡女呢!
二十年前,我認識了第三頭牛。他是埋頭犁地的牛,成日汲汲工作。我們若即若離,一年見幾次面。這段感情如細水不斷,正因彼此有各自的世界。
即使如此,在早期,我仍有情感豐沛到失控的場面。初識我未久,他已發現我是愛吃醋的人,而他個性開放,待人親切包容,相當有女人緣。
十年前的情人節,一位女性送他一盒心型巧克力,他怕我看見,迅速吃完,卻還是被我發現,我和他大吵大鬧,火氣大到摔破一個玻璃杯。這種在連續劇才看得到的場景,竟然發生在我身上,事後,我被自己的行為嚇到,冷靜剖析自己的衝動,才發覺內心的糾結好深。
痛苦、脆弱、不安、憤怒、恐懼,那麼多負面情緒的傷害,原來始終未曾因愛而痊癒。這頭牛給我甚深的愛,而我永遠覺得不足。愛人不易,被愛也很艱難。
如今,他和我都將老去,這頭體力勞動過度的牛,對我說:「牛的性格很特殊,牠很忠誠、盡責,就算拉不動車,也會使盡力氣到最後一刻,竭力至死。」他說,自己青春已遠,已是老牛拖破車。「我現在全部的精神,就用在好好過每一天。」他近來重複這句話,總使我憂傷。我五內俱傷的老牛啊!
我生命中的三頭牛以及情人們,我們的人生曾偶然相遇,彼此交錯光影,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路途。時間之流奔去,我們無法在同處重又濯足。過去已過去,願我記得甜美的部分,當我滿頭銀髮時,做為人生最後的回憶。
內文試閱一
惡之幸福
我一直沒有忘記那一幕。
九歲那年夏天,我走入巷口雜貨店,看著牆上、攤架上一堆抽糖果的抽抽樂,其中有一款全新、無人開張的抽紅包袋,攫住我的眼神。我拿出口袋裡的五毛錢給老闆娘,對她說:「我要抽紅包袋。」老闆娘看我一眼,收下五毛錢。我看著上下左右成列小紙牌,最後隨機抽起一張,剎那間眼睛發亮,因為我抽到頭獎,一張紅色的拾元鈔票!我拿著這張小紙給老闆娘,老闆娘一邊看,一邊狠狠地瞪我一眼,接著罵說:「查某囝仔人,那麼小就白賊,緊回去!」
我說:「我抽中拾元,汝怎不給我?」
老闆娘大聲罵...
作者序
這本書可說是懺情錄,其中追索我與母親的關係,篇章中有我痛苦的成長經驗,那是青春期與母親對抗的舊傷,傷口隨歲月結痂,但是內部仍很脆弱。我曾經以為和母親的衝撞,將永遠無法和解,但因為母親的寬諒,我們終於能平靜相處。
我也不瞭解父親,過去因為對他的恨意,我敵視他,我未曾接近過他。
在這本書,我還寫到弟弟妹妹,寫他們的辛苦奮鬥。書內也有其他親人,如我的二叔及當年來台北打拚的表哥、表姊們,他們的人生是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庶民縮影。
除了親人,我也寫到周遭的一些友人,還有我自己。這些點滴有的是悼亡,有的是我的成長記憶。我是個懷舊的人,舊事仍會引起我的內心波動。對我而言,書寫是一種撫平心靈的方式。
我的寫作有一條軌跡,字裡行間發散出來的是,對時間、記憶、情感的追逐、探究。向田邦子說:「記憶像是綻口的毛線,一旦找到了頭,就能一扯再扯,沒完沒了。」我不希望一扯再扯,我只盼望藉由寫作去織補綻口的痛處。
後記
這本書的寫作時間跨越五年,一段不算短的時間。我的書寫速度很慢,寫作量並不多。原稿原有七萬多字,刪改後只約六萬字,這是很薄的一本書。
攤開文稿,我不僅見到這些年的生活軌跡,也重溫童年以及與父母、弟妹、親人、好友的關係。
這五年,我感覺自己的心境有些變化,或許是人到中年,個性變得比較柔和、沉靜,過去的稜角磨平些。
這本書可說是懺情錄,其中追索我與母親的關係,篇章中有我痛苦的成長經驗,那是青春期與母親對抗的舊傷,傷口隨歲月結痂,但是內部仍很脆弱。我曾經以為和母親的衝撞,將永遠無法和解,但因為母親的寬諒,我們終於能平靜相處。
我母親這幾年老了許多,她掉了多顆牙齒,嚼食不便,食慾減少許多。母親長期揹負重物,身形變得佝髏。她一日日老去,但仍日夜為孩子的現況擔憂。
大妹開美髮店,日前我回去讓她染髮,染髮後,由於妹妹忙別的客人,就請母親給我洗髮,我原本強烈拒絕,母親卻一直說,沒關係,她常給客人洗頭髮。我拗不過她的好意,躺上座椅讓她洗髮,這恐怕是我成長以後,第一次和母親那麼接近,我感覺到她的呼吸,碰觸到她的身體。那麼靠近讓我很不習慣,我全身僵硬,只想快快洗完。
母親的動作慢條斯理,她傾身問我:「水有夠燒無?」「有啦!有啦!」對答間,我想起童年時,母親為我洗髮的情景,那時我大約八歲,母親燒一桶熱水,倒進大臉盆,輪流為孩子洗頭。小孩太多,母親很不耐煩,輪到我時,她按著我的頭,先沖一瓢水,再抹上肥皂,肥皂泡沫跑進眼睛,我很不舒服,只聽到母親說:「好了,好了。」很快洗完,遞給我一條毛巾,要我自己擦乾頭髮。
如今的母親已年邁,變得很有耐心,她慢慢沖水、洗滌,似乎想抹去我們之間的界線。我與母親的關係,是我一生的功課,我們似近猶遠,我仍然無法自然地靠近她。不過這幾年來,我漸漸感受到她的熱情,這不僅是對我們如此,母親對外人也一樣。每次我回家,母親總是不斷地拿出食物和水果,有的要我立刻吃,有的要我帶回住處。
我離去前,母親站在門口送我,有一次,我跟她說再見,她習慣性地說一串祝福我的話。我轉頭走了幾步,回頭看見她仍站在門口,我又走了幾步,她還是在門口看著我,我向她揮揮手,示意她回去屋內。我往前走了幾步,回過頭去,她還是站著,然後我看到她向我奔來,跑到我身旁問我說:「錢有夠用無?我提幾千箍銀仔予你,好嗎?」我覺得她很囉唆,有點惡聲惡氣回答:「有夠啦!免提錢予我!你緊轉去!」說完,我大步走了,不再回望她。
母親的心如此柔軟,她的內心藏有深愛,多少年來,我卻刻意漠視……
每當我寫到父親,仍然情緒激動,語氣總容易激昂,因此一刪再刪文稿。說實話,我的第一本書《我那賭徒阿爸》出版後,父親雖然沒有讀,但是多少知道我沒寫他的好話,所以並不開心。他並未責備我,但是對於我的家族書寫,並不鼓勵。
父親生長在雲林縣二崙鄉的邊仔頭,是靠近濁水溪的小村莊,去年,我提議帶他回鄉走走,沒想到他的反應是,如果沒有相當成就,他絕不輕易返鄉。父親已經八十一歲,仍然渴望衣錦還鄉。
我也不瞭解父親,過去因為對他的恨意,我敵視他,我未曾接近過他。有一次在永和的家裡,不知聊到什麼,他忽然對我說:「你大概猶無瞭解恁老爸是啥款人。」然後他說起一個少年時的故事,父親說,在國民黨軍隊來台後,有一天一個穿著破爛的軍人來到邊仔頭,問他要水喝。這個軍人很餓,父親就端一碗稀飯給他吃,軍人吃完謝過走了,沒想到不多久,這個軍人領來五、六人,來要東西吃。父親說,當時祖母在家,祖母非常有肚量,立刻燒柴煮稀飯,到園裡拔菜,又殺一隻雞,煮給這群軍人吃。這群身上長了虱子的軍人還洗過澡才離開,他們離去前向祖母及父親百般感謝。父親認為,他自己和祖母做了好事,觀世音菩薩因此庇蔭他,讓他面臨許多難關都化險為夷。
我聽著父親的故事,他的形象好似立體一些,父親一定還有許多故事,那裡面有他的人生經驗,或許有一些寶藏,等我去發掘。
在這本書,我還寫到弟弟妹妹,寫他們的辛苦奮鬥。書內也有其他親人,如我的二叔及當年來台北打拚的表哥、表姊們,他們的人生是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庶民縮影。
除了親人,我也寫到周遭的一些友人,還有我自己。這些點滴有的是悼亡,有的是我的成長記憶。我是個懷舊的人,舊事仍會引起我的內心波動。對我而言,書寫是一種撫平心靈的方式。
我的寫作有一條軌跡,字裡行間發散出來的是,對時間、記憶、情感的追逐、探究。向田邦子說:「記憶像是綻口的毛線,一旦找到了頭,就能一扯再扯,沒完沒了。」我不希望一扯再扯,我只盼望藉由寫作去織補綻口的痛處。
這本書能夠成形,我要感謝長期鼓勵我的蔡珠兒、陳映霞、許悔之。我也要謝謝好友魏寶貝,她做為第一個讀者,陪伴我細心改稿。同時也感謝有鹿出版社的煜幃、正寰等同仁。
當然,我要特別感謝為我跨刀相助的主編傅月庵先生以及美術設計楊雅棠先生。
這是我的第二本書,比起許多島內的創作者,我算是起步晚,又動作慢。文學這條路真是漫漫長途啊!可是,能夠寫作是多麼幸福的恩寵,我只願往後的歲月,能夠全心投入,一步一腳印,繼續耕耘。
這本書可說是懺情錄,其中追索我與母親的關係,篇章中有我痛苦的成長經驗,那是青春期與母親對抗的舊傷,傷口隨歲月結痂,但是內部仍很脆弱。我曾經以為和母親的衝撞,將永遠無法和解,但因為母親的寬諒,我們終於能平靜相處。
我也不瞭解父親,過去因為對他的恨意,我敵視他,我未曾接近過他。
在這本書,我還寫到弟弟妹妹,寫他們的辛苦奮鬥。書內也有其他親人,如我的二叔及當年來台北打拚的表哥、表姊們,他們的人生是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庶民縮影。
除了親人,我也寫到周遭的一些友人,還有我自己。這些點滴有的是悼亡,...
目錄
【推薦序】苦海,女神龍 ◎蔡珠兒
輯一 伊
懵懂時光
暴烈青春
祝你幸福
眼淚
擺攤
心
大運
街角
手藝
輯二 阮
普通的生活
我妹妹
小妹不要哭
弟弟的笑容
一封信
黑狗叔
青春鳥
輯三 亻因
飛呀飛
愛的微笑
忽忽,你要撐下去
忽忽大睡
解嚴與烤雞
飛往夢與黎明之間的商禽
輯四 己
情人
恆溫19℃
名字的故事
我的東方出版社
衣櫥
年味
一個人的過年
我的玫瑰
旅人雞酒
來時路
惡之幸福
後記
【推薦序】苦海,女神龍 ◎蔡珠兒
輯一 伊
懵懂時光
暴烈青春
祝你幸福
眼淚
擺攤
心
大運
街角
手藝
輯二 阮
普通的生活
我妹妹
小妹不要哭
弟弟的笑容
一封信
黑狗叔
青春鳥
輯三 亻因
飛呀飛
愛的微笑
忽忽,你要撐下去
忽忽大睡
解嚴與烤雞
飛往夢與黎明之間的商禽
輯四 己
情人
恆溫19℃
名字的故事
我的東方出版社
衣櫥
年味
一個人的過年
我的玫瑰
旅人雞酒
來時路
惡之幸福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