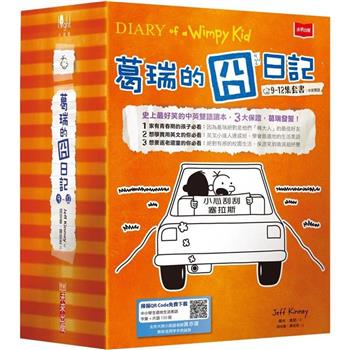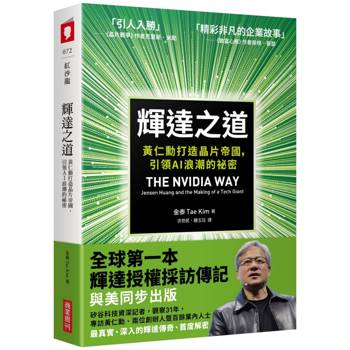一秒的Catch,一輩子只有一次
在路上,我們重新看見自己,成為自己。瞥見無所不在的美好!
事物稍縱即逝,這點你必須承認。
特別是旅行,不管時間多久,永遠進入不了真相。
Catch,抓取、捕捉、片段……
Catch尋找已久,躲藏在這裡的「天涯海角」:斯里蘭卡
「重點不在於『留住』瞬間的永恆,而是準備好了自己,放下自我的那些喋喋不休,願意隨著變化之輪前進,接受任何的起伏跌宕,參與這場生命的無常之旅,邁向寂靜的彼岸。」~~鄭栗兒
★ 心靈女作家鄭栗兒最打動人心的自我追尋之書,CATCH佛教古國的流動光影。
★ 15個聖境風景,15篇心靈詩語,帶領你我瞥見無所不在的美好。
一個人,一生中必然要有一次朝聖之旅,
赤足晃蕩,享受著散步、行襌,吹著風。
慢慢打開自己的心,看見了不逝的心靈風景……
熱的風,滑過斯里蘭卡的日與夜。五月,熱季的最後一個月,再來就是雨季來臨的時候。印度洋吹來的南亞季風「慢舒(Monsoon),拂開距離赤道僅七百公里的燠熱佛教國度──斯里蘭卡的神祕沙麗。
這座位於印度半島南方的島嶼之國,外形如梨,懸於印度洋的孟加拉灣上。既是南傳佛教的聖地,更保存最完整的原始佛教教義及象徵佛陀教法的古蹟:菩提樹、舍利塔及寺院、佛像。
從原始菩提樹到佛髮舍利塔,從坎迪古老山城到村口瑪莉海濱沙灘,這是一段用詩語記述的抒情筆記,帶領我們看見獅子國度的空寂之美,悠緩地訴說斯里蘭卡興起而衰頹的城市故事……
我繼續赤足晃蕩中,享受著散步、行襌,吹著風。慢慢打開自己的心,看見了斯里蘭卡不逝的心靈風景。
作者簡介:
鄭栗兒,本名鄭麗娥。作家、資深文學主編。
曾任廣告公司文案指導、時報出版文學主編、聯合文學執行副總編。
寫過一隻小壁虎、尋找星星小鎮和許多大修行者故事……共五十本以上的文學及心靈叢書。
創作、靜心、走路,與萬物交流,是每日的生活禪。
擁有一所療癒系的光之花園,分享靜心的美與喜悅。
個人代表作:
第一部城市散文《我是懶的》
第一部熱賣的青春之書《閣樓小壁虎》系列
第一部追尋愛的小說《尋找星星小鎮》
第一部為村上春樹編撰的《啊!村上春樹》
第一部走訪西藏高原的旅行書《日光城市‧雪之領域》
第一部晃蕩邊境島嶼的燈塔誌《台灣離島與燈塔》
第一部報紙專欄結集作品《紐約倉庫小島》
第一部關於編輯台的小說《最壞的時光》
第一部26本高僧故事全集《大師密碼A-Z》
第一部禪宗公案《我心不安》
章節試閱
【內文節選一】
第三章.
心靈風景——凱拉尼亞寺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一處心靈風景,這麼說時,我想起了三毛的撒哈拉沙漠,或者拉瑪斯瓦米吉(Rama Swamiji)的喜瑪拉雅山,以及夏卡爾(Marc Chagall)的俄國鄉村……。
我最愛的電影導演之一溫‧文德斯(Wim Wenders),在他出版的攝影書《一次》(Once)中,有一段經典話語:「每張照片都是對我們生命必會消逝的提醒,每張照片都關乎生和死。」
這位熱愛享受緩慢長期工作成果的德國詩人導演,他舉起相機或者拍攝電影,都是為了記憶那生和死的畫面,記憶消逝的生命,也因此,「孩子才會有的那種看事物的驚喜和快樂,文德斯保留了下來」。
我和文德斯一樣,對於尋凡之普遍的事物,都有一種極端熱愛,因為在這裡必然藏有一個背後的故事。於是,在每一場旅行的路上,我們舉起相機,奮力拍攝迅即無蹤的事物,要找到一個最美好的角度,構築畫面的情境與張力,將之鋪陳為永恆的心靈風景。
凱拉尼亞寺(Kelaniya Monastery),可以列為此趟旅行所捕捉心靈風景的第一組系列明信片。首張畫面,我為之下的標題為:赤足。
結束了荷塘國家文化體育場神聖的祈福盛會後,此行聖地觀光景點的第一站,就是經典中的經典──凱拉尼亞寺。
在遊覽車巴士上,導遊雷克斯要求我們下車前要將鞋子、襪子統統脫掉,光著腳ㄚ,踏入古老的佛陀聖殿,以斯里蘭卡沿襲已久的習俗,表達內心對佛陀至上的虔誠敬意。
我有多久,未曾赤足行走於地面了?腳踩踏在泥土與磚地間,感受大地的呼吸。從這一刻開始,就是朝聖的旅途,也是一種禪修的印記。雖然如此,一開始得知要光腳走路這件事,心底還是發出「啊」的一聲。
美麗的白色朝聖隊伍,就這樣沿著綠樹林蔭整齊行進著,腳踩踏在柔軟的泥土沙地上,以一種異樣的童真心情,悠緩地邁入山門。在等待領取蓮花做為供佛的短暫時刻,樸實佛像石刻牆間昂揚的一朵朵紫色小花,吸引了我。我輕輕一笑,她的美和祝福,我看見了,也收到了。
再往前,歷史悠遠,恍若從圖書館典藏的古書中現身的凱拉尼亞寺,其造型古典,有如諸神之所的黃色建築群已在眼前。寺門的兩側,聚集一群群斯里蘭卡信徒,好像不分季節時日,每一天他們都會來這座在斯里蘭卡佛教徒心目中僅次於坎迪佛牙寺的聖殿聚首,和佛陀打個招呼,感受祂散發出來寧靜慈悲的氛圍,調伏自己在俗世的煩惱、業障,並祈求透過佛法的教導,讓自己放下執著,證悟息苦的涅槃之樂。
這所帶有濃郁印度風格的佛寺,位於可倫坡近郊,亦是佛陀第三次造訪斯里蘭卡之地。據載,佛陀蒞臨的時間是他悟道後第八年的5月份,也就是我們現在來訪的時節,當年他在此處講經佈道的地點,即是位於寺院旁的白色佛塔位置。
現存的建築古蹟,原為斯里蘭卡國王爹哇南斯毗第之姪亞沙拉亞(Yatthalaya)於西元前一世紀所建,一九二七年重修主建築體,而寺院外牆的浮雕壁飾亦於二十世紀早期修復而成。不論是建築形式或是圖騰浮雕,以及寺院內所保存的珍貴壁畫,凱拉尼亞寺所呈現的一切,皆是斯里蘭卡獨一無二的佛教資產;並為此地信徒提供一處心靈的庇護所,人們在此誦經、禪坐,每當月圓時,尤其五月的月圓之日,更有無數信徒前來供花祈福,與佛陀的心靈接近。
我凝視著,走進古老的傳說,強烈感受到一股凱拉尼亞寺所散發出來的沉靜氣息,是不同於吳哥窟的衰朽凋敝,為什麼呢?當踏進玄關後,我明白了!這不是一座停滯的古蹟,只讓觀光客前來純欣賞殘骸遺跡,而是一所仍在進行式的寺院,仍有著與人們互動、聯結的美好波動。
迎面而來的每一巨大牆面,皆飾滿彩繪壁畫,道出斯里蘭卡最早的佛教故事。耳際傳來陣陣台灣僧侶群正虔心持念《心經》的洪亮音聲,他們佇足於大廳中央,面向繪有雪山背景的佛陀聖像前,為之誦經禮讚。據說親睹此尊佛像者,可消除一世的罪障。真的嗎?我感到好奇。
跟隨人潮前進,轉入這一方聖像小室內,整個磁場彷若是第三極所呈現出來的縹緲悠遠,似天空的一扇窗口,連接著宇宙星際。心靜了,也定了!盈滿說不出的感動,我在佛前,祈求未來善業的成就,餘皆無言。
又順著每一俯拾皆是的經典藝術之指引,穿梭在殿內一個個室堂中,無論是金色臥佛、長鼻象頭的毗濕努神(Vishnu)或是屋頂繁複的藻井天花、天鵝與蓮花的精緻牆飾,以及地上半月形的浮雕刻鏤……等等,其豐富多采的元素,呈現出無與倫比的佛教文化。而且和一般我們熟悉的漢傳佛教形式有很大的不同,帶有更動人傳神的神話色彩。
從一處木雕窗櫺縫隙,我拍攝到一位斯里蘭卡女孩虔誠祈求的表情,她將什麼心事託付給佛陀呢?她又許了一些什麼心願呢?我很想知道,一個斯里蘭卡人拜佛的內容和一個台灣人有什麼不同!
再入供奉佛舍利的側殿,就是最精彩的佛陀三次來斯里蘭卡的故事壁畫:佛陀第一次來斯里蘭卡Mahiyangana時,化解了部落衝突;第二次他到了北方的龍島Nagadeepa,也是觀世音菩薩的出生地留下足印;第三次便來到凱拉尼亞地區,當時斯里蘭卡國王供樣佛陀廿六公里大的土地……。其他還有原始菩提樹苗如何從印度乘船而來,佛陀的舍利子也盛滿了一個缽碗迎請到斯里蘭卡等等史實。每一道細膩流暢的筆觸,點綴華麗飽滿的顏彩,畫風生動活潑,為佛陀故事增添了奇幻文學的魅力,與我們熟知的敦煌風格截然不同。
這座古稱獅子國,位於印度半島南方的島嶼國度,外形如梨,懸於印度洋的孟加拉灣上。西元前三世紀,佛教在印度阿育王的大力弘揚下,由其子摩西陀(Mahinda)法師傳入斯里蘭卡,受他啟發成為第一位佛教徒的人,就是當時的國王:爹哇南斯毗第(中文另譯「天愛帝須王」,Devanampiya Tissa),從此,也開啟了上座部南傳佛教的全盛時期。而這段輝煌的佛教史,亦在當年佛陀三次造訪斯里蘭卡時給預言了!
步出了室外,轉入寺右側白色巨大的舍利塔,這種窣堵波式佛塔(Bowl-shaped Stupas)制建形式,傳承了最初的印度風格,是在方形的台基上,建一覆缽形塔身,亦如一座穀倉。外型簡單、明朗、大方,且蘊含四聖諦、八正道、八萬四千種法門之教義內涵。
烏鴉飛越停歇巨塔,形成黑與白的趣味對比,這裡的烏鴉多得像鴿群一般,盤踞在這一歷史悠遠的古寺內,恣意飛行在佛陀最早講經說法的地方,鴉聲停止時,便沉入很靜的無語狀態中;老婦安坐竹林角落閱讀經文,與一旁矗立的彌勒佛像、入定的打坐者,共同消融於整個佛寺的沉默裡。
我亦然,赤足滑行沙地上,順時針繞塔一圈、一圈,如虔誠的轉動經輪之西藏婦人一般……,真的很棒的一次行禪經驗,有一種時空的交會與了解。
再晚些,從高大的菩提樹間,灑下了黃昏金光,形成永恆的一瞥。雲朵懸浮鐘樓塔頂尖處,我拍著照片,也攝下了台灣來的明光法師正教著當地孩子們唱誦佛咒的畫面,他耐心地教導身旁圍成一圈的斯里蘭卡兒童,每個人都露出稚氣的表情,認真學習,這畫面讓人倍感溫馨,陌生的國度因交流佛陀的慈愛,而拉近彼此的距離。
我繼續赤足晃蕩中,享受著散步、行襌,吹著風。慢慢打開自己的心,看見了斯里蘭卡不逝的心靈風景。 〈….more〉
【內文節選二】
第十三章.
海潮低語——村口瑪莉與獅子岩
每一道海浪都有它獨特的呼吸,每一道海浪抵達沙灘時,是一陣磅礡的奔騰之聲,但離開沙灘時,卻是無數細膩呢喃的低語,這是潮汐的生命故事。
這一趟旅程的最後,我們終於來到海濱,村口瑪莉(Trincomalee)一彎新月般潔淨的沙灘,正等著我們目睹最美麗的印度洋,這也是此行唯一與海接近的時刻。
被印度洋包圍的斯里蘭卡,海岸線是其最著名的風光。從東海岸的尼剛伯( Negombo )到普他拉姆(Puttalam )綿延一百公里的海岸線,就是最著名的「漁人海岸」,當地漁民們常駕著一種名叫Katamaran的傳統船筏,在近海捕撈漁獲,也有類似台灣「牽罟」的捕魚方式,而在尼剛伯的荷蘭大教堂捕捉歸帆夕照,則是斯里蘭卡獨特的觀光景點之一,也成為最佳的明信片風景。
斯里蘭卡的新人們更愛選擇島上西南角、面向印度洋的高級沙灘酒店舉行終身大事。可倫坡與世界歷史遺跡高爾(Galle)之間,是斯里蘭卡高級飯店的密布區域,從浪漫的婚禮宴會、布置、禮服到傳統樂隊,乃至穿著華服的大象,皆一應俱全,新人們可在沙灘上讓大海見證永恆的愛情。
此外,在斯里蘭卡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捕魚的漁民多是基督教、天主教或是回教徒,很少有佛教徒,因為佛教徒不喜殺生的緣故,也因此當年南亞大海嘯時,許多住在沿海的漁民不幸罹難了,但佛教徒罹難的人不多,導遊雷克斯說起這事時,也讓我們感到無比神奇。
世界的海都是一樣的吧!印度洋的海岸線,使我想到新月的沙灘與迎風搖曳的椰子樹。斯里蘭卡將椰子樹稱為「天樹」或「萬能之樹」,光聽這個名號,就知道椰子樹對斯里蘭卡人的重要性。除了紅茶、香料外,斯里蘭卡亦是豐富的椰子產區,共有四種品種,其中國王椰子是最上品。椰子的果實可以品嘗外,整棵樹的每一部分也都可以充分利用,其中最特別的莫過於工人們以特技方式爬上椰子樹頂,摘採椰花蜜(Toddy),用來釀成美味的椰子酒(Arrack),這是一種低度淡香酒,也是當地的農村特產,深受當地人歡迎。
山與海構成了斯里蘭卡的絕妙風光,這與太平洋一角的台灣非常相似,而且更多了動物天堂。此行我們是無法品味Arrack的滋味,但可領略村口瑪莉椰影沙灘的熱帶風情。有趣的是,這一趟從波羅那露瓦前往更東北角村口瑪莉漁村行進的過程,簡直就是遊晃野生動物園的草原之旅,充滿了自然原始的風情。
我記得一位朋友年輕時曾前往馬來西亞工作,他說開車時,總會在大馬路上,突然發現一隻龐然大物悠然橫臥,一看原來是大蜥蜴。這原始生物的蹤跡也出現在斯里蘭卡,公路旅行的沿途,從大象、孔雀、猴子,乃至大蜥蜴和各種鳥類,從荒原草叢或者一席森林間逐一冒出,引起眾人的矚目與驚呼,只差沒出現一頭獅子。
斯里蘭卡建國者是最早的馴服獅子的勇士,斯里蘭卡梵語古名「僧伽羅」(Simhalauipa),即為「馴獅人」之意。玄奘在《大唐西域記》書中曾記載僧伽羅國最經典的神話。在更早的南印度時期,有一位國王迎娶鄰國的公主為妻,沒想到新娘卻被一隻獅子搶走,還生下一男一女。長大後,母子三人決定逃回自己的國家。這時,獅子父親來找孩子,四處肆虐危害百姓,國王抓不到獅子,便懸賞招募殺獅的勇士,獅兒子Sinda前來應募,他與獅父相遇後,拿起小刀將父親刺死。國王後來得知原委,認為Sinda弒父不當,將他的母親留在國內,給他和妹妹各裝滿了糧食珠寶大船,流放到斯里蘭卡,Sinda便留在這美麗的島嶼開始繁衍生息,建造一個新的國度。
做為半獅人的後代,神話背後的意義說明了斯里蘭卡源自於自然,並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關係,這裡的森林是活的,草原是活的,所有的生靈一起為斯里蘭卡創造友善的奇蹟。
最有意思的倒不是這些野生動物,而是處處可見斯里蘭卡的天然澡堂,據說斯國的自來水系統僅止於大城市,一般鄉村城鎮所用的水都來自於天然的河水、湖泊,不然就是水庫或地下水。午後的陽光正將湖水曬得溫度適中,人們不約而同群聚河邊、湖畔洗澡或洗衣,順便以水桶接水,頂在頭上帶回家使用。於是,旅人便看見所經過的每一處湖泊,皆有斯國男女公然洗澡,當然不是裸裎相見,女人們會以一條長布將身體裹住,避免曝光,看起來就像是在玩水一樣,不知情的人以為是在游泳,其實也是啦!沐浴本身就是一種放鬆,從這些悠閒的生活節奏,也體會到這個奇幻島國的自在與純樸氣息。
抵達村口瑪莉飯店,已是黃昏時刻了!椰林之後,迷人潔淨的白色沙灘與海岸形成一道極完美的弧線,展現在我和Iris眼前,海潮拍打的寧靜間,一群穿著白色回教衣服的女學生擁來的笑聲顯得更清亮。我嚇了一跳,被她們包圍住,請求與她們拍照,對她們來說,我們這些外國阿姨,就像我們看大蜥蜴一般稀奇。
一位當地的船夫一再遊說我,明天清晨搭他的船去到海上的小島,我說:沒辦法,因為隔天一早,我們就要離開前往佛髮舍利塔參訪。數年前海嘯災難也曾襲捲此地,同行的法師們在椰林旁的沙灘角落一隅,慈悲地為許多無形的眾生做一小型的煙供修法,香煙裊裊飄入天際,星星已出現在無垠的空中,陣陣的潮汐拍打聲使我憶及了屬於我的一九七三年的年輕海濱。
海洋的連結,總喚起我們與整體存在合一的渴望。每一朵海浪都來自海洋,於是我們都不孤單,因為我們都源自於整體的存在。雖然我不是回教徒,但這群回教女孩天真的笑也感染著我,我們聽不懂對方說些什麼,擁抱與微笑卻是最好的溝通。布施是佛教徒的善行,一個佛教徒最真誠的慈悲布施,也莫過於此,時時給予祝福,時時給予安慰,時時給予一個笑容,以笑迎接每一個天、每一場生命際遇,日日好日,學習海洋的寬闊、無限與包容。 〈….more〉
【內文節選三】
第六章
魔術時間——坎迪日落
日落前的魔術時間,總有一種神秘的光,令所有熱愛攝影的人們為之傾倒。那一刻,光的豐華、飽滿、穿透、輝映…種種奇幻的顯現,彷彿打開了時空的裂縫,將宇宙的無限奧妙,傾注於此。於是,快門一按,再蠢的傻瓜相機,都能攝下絕美動人的精采畫面。
這即是,魔術時間的魅力。
坎迪,Kandy,斯里蘭卡第二大城,舊王朝最後古都的美麗山城,其本身就是魔術時間的象徵。在這裡,所有古老時代、歷時數百年的傳統文物、建築、藝術、文化……,都被收藏在時空的裂縫中。其中最熠熠生輝,便是佛牙寺,縱使千年流逝,始終閃亮耀眼,盡展永無落日的風華極致。
所以,你可以錯過可倫坡的獨立紀念廣場、紀念碑或市政廳、新國會,但你絕不能錯過坎迪的魔術時間。
從可倫坡前往位於國境中部的山城坎迪,距離118公里,車程需費上3小時。我們出發,在警車的開道引導下,往山的方向疾速前進。
辛哈拉語中,坎迪為「山」之意。海拔465公尺的「山」,說起來,挑戰性是很低的,但沿途確然是山的風景與植被,慢慢也嗅出一絲微涼氣息。終年廿多度的平均氣溫,使坎迪少了熱帶國家的躁熱,而多出一分溫和舒適的優雅,是屬於皇家氣質。那當然是。
同樣歷經了百年歷史的淬煉,同樣有過分崩離析的心碎,當你想到的古城,比如羅馬,你想它是集合了混亂和聲音的城市,還有一份狂野的放肆,人們用很露骨的方式說話、表達情感。但是坎迪與它完全相反,她有一種安靜、乾淨的氛圍,略帶含蓄,舊時王都的高尚與尊貴感,處處有跡可循,你也往往能得到一個陌生微笑和誠摯的眼神。
在這座被山包圍住的古城,斯里蘭卡最大之河馬哈威利河穿越了層疊峰巒也來到這裡,聽說在坎迪更高的山區裡,在每年5月西南季風,及11月東北季風轉換時,都會帶來極豐沛的雨量,而造成河水氾濫及嚴重的土石流。5月吹來的南亞季風叫做Monsoon:慢舒,很美吧。但它所形成的對流暴雨,可是既猛且快,一點都不慢舒哩!
坎迪幸運躲過暴雨的肆虐威脅,於是任樹木恣意追隨陽光,筆直生長成巨大高壯模樣,從城中心的一泓清澈的坎迪人工湖向外擴展,周遭遍為各種深淺的蔥綠、翠綠所布滿。
斯里蘭卡最大、也是全亞洲最大的植物園,亦在此綿延成一片縱橫深密的熱帶森林與奇花異卉,是過去皇室貴族們方可進出的宮廷花園。(很遺憾,此行錯過了!)
也因為這樣的好風光,使坎迪成為了著名的佛教聖地外,還是重要的觀光與療養勝地,別忘了,在更高山區的茶園、香料園也是獨樹一格的景致。
在大巴士全力爬升的半途中,不知為何,一輛輛全都停靠在山路的邊上。原來是對面有一長排的小攤,賣些紀念品、香料、玉米及酪梨、香蕉等水果,許多人下車逛逛去了!回車時,手中多出許多戰利品,我們分享著酪梨營養甜美的滋味,在等待的片刻眺望著遠去的山色。
來自山西的中國同伴,秀出他購得的整排香料包,幾乎包含了斯里蘭卡生產的所有香料:胡椒、荳蔻、丁香、姜黃、肉桂……。
儘管我不是一個熱愛香料的人,也不懂得如何烹飪,但這個自古以香料、紅茶、寶石為貿易的國家,香料所帶來的商業利益及交流繁榮,使她不僅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香料國,更是海上絲路航線的重要一站,最早與中國通商的紀錄發生在西漢時期,當時中國喚她為已程不國。
熱愛香料的香料師,必然對斯里蘭卡的香料有一股莫名的狂熱,因為內行人說:它的每一顆種子都具有很強的生命力,無論你帶到哪裡,經過多少時間,只要不將它烘培,埋進土裡,給它陽光、空氣和水,它就可以開始成長。
這種斯里蘭卡香料種子的堅強韌性,來自於此處原始無染的環境,才能得以孕育。「原始」這個詞,含藏著最真的本始、最初之心,不僅僅香料在這裡保存了千年來的品質,原始佛教亦在此發揚光大,保存著佛陀最忠實、且最根本的教義:四聖諦及八正道……。
而關於坎迪最原始的故事,也是斯里蘭卡最早的神話,竟然和佛教無關,而是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後之番外篇。
傳說,亞當和夏娃離開伊甸園後,即在人間流浪,尋找一處類似天堂的地方。他們從西方一直找到東方,最後在印度南方小島上,名叫聖卡達加拉(Senkadagala)的山城小鎮,發現了人間最美、也最接近天堂的所在,於是他們就在這兒落腳,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也繁衍了子子孫孫,開始人類的故事。這個山城小鎮,就是今日的坎迪。
原本一樁略帶悲劇性的神話,到了坎迪,如此皆大歡喜,坎迪不愧是諸神加持的聖地,有段歷史可以證明,這是屬於坎迪真實的故事。
西元前6世紀時,印度王子比智雅渡海來斯島,建立了辛哈拉王朝(又稱僧伽羅王朝),無奈與南印度來的泰米爾族(Tamil)戰爭不斷,直到十六、七世紀,葡萄牙、荷蘭先後前來佔領殖民。為了抵禦西方侵略者,只好於1590年遷都坎迪,依賴內陸環山的有利地形,辛哈拉王朝得以安然無恙地延展下去。十九世紀初,王朝終於不敵英國人的入侵,在1815年正式落幕,坎迪也卸下長達225年的首都榮冠。
雖然如此,人們仍為坎迪這段抗爭的歷史喝采,而給予「馬哈龍瓦爾」(Mahanuwara):偉大城市的美譽。至今坎迪雖褪去政治色彩,卻仍為佛教聖地及藝術重鎮,依然有說不完的傳奇和故事。
我們閱讀坎迪的故事,從魔術時光開始。
那時,我們的龐然車隊已抵達了坎迪,並接受Sri Chandananda佛學院的盛情招待,大堂空間有限,我們只好在戶外四處流連拍照,一些等著表演的孩子們笑得靦腆又燦爛,我們捕捉他們的純真笑容,以及學院附近開著紫色、紅色花朵的群樹…。
等待宗教活動結束的小歇片刻,學院的工作人員帶領我們爬了五、六層樓,來到校舍樓頂的舍利塔處,俯瞰整個坎迪的山景暮色。一時間,這座城市的遠近全都在腳下了!佛牙寺隱藏在蘢蔥樹叢間,只能猜測大概方位;佛學院側旁足球場上,孩子們練習踢球,一副很賣力的模樣;淡淡雲煙將山城罩上一層薄面紗……。我們繞完舍利塔,日落前的夕陽光暉,已經開始展現它魔術般的千變萬化。攝影師Julie指導我們如何抓住夕陽的返照之光。
這是最美的魔術時間,讓我看見存在的本質,與本初的佛心。在久遠的獅子國古王都,空氣中的微塵吐露我與佛陀的呼吸,聯结著天啟的神秘。我環視著這個城市,看見她的興起,看見她的衰頹,看見她此刻散發出來的寧靜。思維著三法印的奧祕:「諸行無法,諸法無我,涅槃寂靜。」
然後,我笑了!原來這個城市至今的一切發生,也無非不在印證著三法印的道理。世界的本質與原貌,就是這樣的無常,因緣和合,因緣離散;這些不斷而來的變化,才能顯現魔術般的神奇,讓我們舉起相機,一再按下快門。 〈….more〉
【內文節選一】
第三章.
心靈風景——凱拉尼亞寺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一處心靈風景,這麼說時,我想起了三毛的撒哈拉沙漠,或者拉瑪斯瓦米吉(Rama Swamiji)的喜瑪拉雅山,以及夏卡爾(Marc Chagall)的俄國鄉村……。
我最愛的電影導演之一溫‧文德斯(Wim Wenders),在他出版的攝影書《一次》(Once)中,有一段經典話語:「每張照片都是對我們生命必會消逝的提醒,每張照片都關乎生和死。」
這位熱愛享受緩慢長期工作成果的德國詩人導演,他舉起相機或者拍攝電影,都是為了記憶那生和死的畫面,記憶消逝的生命,也因此,...
作者序
Catch移動的一秒
事物稍縱即逝,這點你必須承認。
特別是旅行在一個陌生的地域、陌生的國家,不管時間多久,你永遠是在表面滑過,永遠進入不了真相。
於是,握著可以隨時殺掉影像、抽換記憶卡的數位相機(更早前則是不斷浪費底片、又重又笨的單眼相機),透過車窗或是後視鏡,我開始學習用略帶詩意Catch的心情,拍攝著公路連續流動的場景:那些快速消逝,你已無法重新檢驗、咀嚼、判斷,甚至確定其存在的經過畫面。
其實不過就是前一秒而已,但下一秒時速超過五十公里的汽車或巴士,已經帶你去到別處,另一個稍縱即逝的生命風景。
Catch──抓取、捕捉、片段……,背後有一層純粹抒情的深義。或者,更像是紀念品。紀念永遠不可再的人生,和旅程。
有人用眼淚告別,有人用哀悼追念,我選擇隔著玻璃Catch一秒鐘的記憶,就像牡羊座電光石火、用過即丟的熱戀。隔著玻璃,有一種我永遠進不去的遺憾,以及我必須承認的距離。
夜雨降在日光城,黎明甦醒,從拉薩啟程,三百五十公里直抵日喀則的西藏高原之旅,像一首搖滾曲按鍵播放,隨時可能會拋錨或翻車危險的灰舊大巴士,不顧一切、勇猛地翻越一座又一座崇山峻嶺,往海拔五千兩百公尺剛巴拉山群最深處奔去。
這是星期幾?我忘記了!高山症困擾著我。
就算如此,我還能清醒地洞悉不朽。這裡充滿美麗事物,渾然天成。
除了含氧量較低的稀薄空氣我無法攝下之外,映在我相機鏡頭裡的,是亮透到不行的無垠天空,終年白色籠罩的冰川雪峰,以及帳篷炊煙升起的豐盛草原等等一連串奇異組合。
色澤接近原始的真,但沒有辦法完全一樣,這就是自然的奧祕,所有的擬仿物就只是擬仿物,就像是記憶就只能是記憶,你不能太貪心。
但絕美的「上部牧場之碧玉」──如夢的羊卓雍湖,出現在我眼簾時,我忍不住還是想貪心起來,想挽住這一座雪山淚滴集成的西藏第二大高山湖泊,挽住整個真實的羊卓雍湖風光。
此刻,一整層厚雲正停泊在祖母綠山巒和藍寶石般的湖面上,有如一則神祕天啟的示現。冷冽的山頂上,空蕩的巴士只剩我一人,隔著玻璃窗,面對著這種無息之美,凍得半死。其他人都下車了,去尋找「呀」(犛牛)的蹤跡,我只想獨處一會兒,領略著「上部」(西藏高海拔處)遼遠的空曠感,Catch我尋找已久、原來躲藏在這裡的「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每一個人擱置在心最深處的夏天夢境。
不知道一直待在這裡會變成什麼?一個綁辮子的西藏女人,天真地笑著,手拉著一隻「呀」,坐一次拍照收取五塊錢人民幣,或者抱著孩子伸手向觀光客討要零錢,隨著帳篷的遷移感受四季變化,一整天忙著酥油煮奶茶,把自己搞得全身都是那種味道……。
我笑了笑,握著相機,把這場夏天夢境Catch下來,繼續下一站的旅行,繼續荒野下去,把我的天涯海角交還給隨風飄揚的祈福經繙和西藏女人伸出的手。
我就從後視鏡一路跟它們說再見:從素妝銀裹的卡羅拉冰川,到沙塵飛舞的江孜古城;從盛開的黃色油菜花田,到頂尖莊園的日喀則;雅魯藏布江在往後中尼公路沿著礫石荒山一路同行,悠閒的藏族人隨意地在某個路邊展開野宴,還有空蕩了正在散場的賽馬會。
如果不是這一些Catch,那一年夏天的雪域遊蹤,不也就是像收攤的賽馬會一樣,只留下空中無語的回聲。如果不是這一些Catch,我又怎麼能進入另一場北海道的冬季戀歌。
在漫天飛雪的公路上,從函館奔馳到洞爺湖的深山,目睹著紛紛的白雪在我面前塑造了一所白色國度,雪原漫延到無盡邊境,延伸至一間間斜頂木屋,延伸至落盡樹葉的高大白樺林,遠處沉默的羊蹄山像靜止在冷酷異境的永恆停格,一直吸引著靈魂擁向它,擁向白色戀人的理想世界。
沒有任何顏色比白色更純潔,更令人著迷,也更難以留住,那些曝光過度的損毀底片,呈現一片絕望的黑,彷彿鎖住了某個重要的故事。讓我再想想,是一個被雪覆蓋失去遊客的冷清遊樂園,還是沒有鳥停駐斜傾的電線桿,或者不斷在鏟雪累壞的日本男孩?
我沒有把握,只好打開相片簿一張張翻閱,看看遺漏了腦海裡的什麼,但不小心卻又被另一些影像給迷住了。
那些橋,有著紅色、藍色、金屬色,或者圓拱式,或者懸吊式,或者古典,或者現代,逐一橫亙在整條流向東京灣的隅田川上,從日出棧橋碼頭乘上汽船開始到台場海濱,已經十幾座橋過去了,最後現身的是無數偶像日劇經常取景的彩虹大橋。
光在進行,水在流動。
隨船波動的,還有是沿途集結各國設計師、攪盡腦思創作的摩登大樓,搖曳在鏡頭中。
就像美國人對於燈火熄滅有著強烈的恐懼症,日本人對於關燈下班也有著同等的焦慮,在星星被光害遮住的夜晚八點鐘,這些數不清的東京摩登大樓依然亮如白晝,領帶斜歪、白襯衫帶著皺痕的上班族,猶在電腦螢幕前撥弄鍵盤,或者幾個人開會討論,偶爾有人對著落地窗伸個舒服的懶腰。
我坐在順著蜿蜒高架橋馳騁的遊覽車內,看著一個個燈火通明的辦公室,好像一個個柵欄,關著我們可憐的上班族,在不景氣的年代還能有上班的幸福,是值得感謝造物主,否則街頭優雅地翻動垃圾箱、試圖從飲料機的掉幣孔挖出零錢的遊民,不是要多更多!
當然也不必過度替他們擔心抗壓性夠不夠的問題,等到了九點鐘,另一波下班潮就會出現在霓虹燈海翻騰的新宿鬧區,在歌舞伎町不夜城獵色度過一宿放肆,或是連續兩攤的喝酒聯誼,發洩情緒。就算半夜三點鐘才終於打烊回家,隔天清晨JR山手線每一班列車,還是擠滿了通勤的上班族。列車關門後,在一片壅塞中,我張大眼睛小心避開打著呵欠的嘴,對於日本人的勤奮,還有什麼話好說呢?這可是不景氣的年代,廉價的中國工人搶去了多少商機!
光在進行,水在流動。
同樣這類Catch,還有汨汨不停的新加坡河。舊式渡輪晃呀蕩的,從小餐廳、酒館林立的克拉碼頭起航,劃過多座有一點點歷史味道浪漫的舊橋,從象徵國家標幟的魚尾獅像,到英國維多利亞式建築風格,以至現代感十足的金融大廈和包容多種族特色的各式樓宇,短短數十分鐘,已經濃縮了新加坡的過去和現在。
坐船是一種奇妙的感覺,它和汽車(飛機更別提)最大的差異是──速度較為緩慢,以及獨特的浮游感。那一年,我把這輩子能坐的船都坐過了,輪船、渡輪、漁船、快艇……。那一年,我也把這輩子能去的台灣最邊陲離島和燈塔都一一涉足了,用一種瘋了的精神。
在柴油味瀰漫,引擎聲轟轟叫響已成單調的背景音樂下,開往東吉嶼的漁船,正費力地隨著三級風浪起伏邁進。船長和旁邊的男孩一直在玩著抓身體的遊戲,算是無聊的海上行程的樂趣嗎?
偶爾總會出現幾隻燕鷗躍然於海面,在這之前赴花嶼途經貓嶼的海域時,已經見識過這些燕鷗,至少成千上萬隻吧!把整座島嶼都包圍起來的壯觀場面。
我帶著一種眩暈,Catch看不見的海上城市和光芒,陷入一種極特別的沉靜,彷彿化作一具淹沒水底的無聲鋼琴,或者變成一朵與海溶為一體的浪花。
我也還記得在開往馬祖的台馬輪迎接一天的開始,在早晨,淡雲藍空,透露朝陽純真的氣息,當第一眼初遇馬祖的門戶北竿島群,是在海上漂流整晚後,對陸地的想念與悸動,尤其一排山勢起伏的綿長島嶼忽地突出於海面,總讓人誤以為是沙漠中的阿拉伯人所搭起的連續帳篷。
在移動的狀態中,Catch移動的一秒,還有無數的畫面儲存在我的資料庫中,無法一一說明,比如陰天裡上班途中遠眺基隆河外的一○一大樓,等候飛機起飛窗外下著大雨的香港機場,或者穿過通往蘇北、跨越長江的巨型大橋,以及巴士即將轉彎近距離的東京鐵塔。
那些時候,我是懷抱著怎樣的心情?怎樣的思緒?是在一種溢出常軌的自由喜悅裡,還是勾動了某種歸屬的想念?甚至是莫名所以的深邃嘆息?
無論如何,這些個Catch,永遠不會再來了!就像我在七美石滬對執著於完美天光的攝影師林說:「不要再等了!就算沒有你所要的光,也趕緊拍吧!也許這一輩子你就來這麼這一次!」
沒錯,一秒的Catch,一輩子只有一次。
Catch移動的一秒
事物稍縱即逝,這點你必須承認。
特別是旅行在一個陌生的地域、陌生的國家,不管時間多久,你永遠是在表面滑過,永遠進入不了真相。
於是,握著可以隨時殺掉影像、抽換記憶卡的數位相機(更早前則是不斷浪費底片、又重又笨的單眼相機),透過車窗或是後視鏡,我開始學習用略帶詩意Catch的心情,拍攝著公路連續流動的場景:那些快速消逝,你已無法重新檢驗、咀嚼、判斷,甚至確定其存在的經過畫面。
其實不過就是前一秒而已,但下一秒時速超過五十公里的汽車或巴士,已經帶你去到別處,另一個稍縱即...


 2015/08/29
2015/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