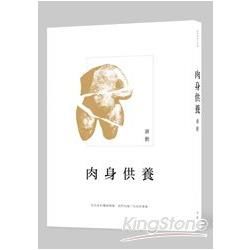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肉身供養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86 |
二手中文書 |
二手書 |
$ 86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300 |
散文 |
$ 300 |
哲學 |
$ 300 |
藝術美學/欣賞 |
$ 300 |
Social Sciences |
$ 342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圖書名稱:肉身供養
在溫柔之中,震碎我們生命的慣性思考,
在肉身邊緣,我們知道了生命如此尊貴。
2011年,我們在《此生—肉身覺醒》面對生死、探討肉身,讚嘆人在脆弱中的美好。
2013年,我們從《肉身供養》解讀關於美更深沉的隱喻,以及不可磨滅的肉身記憶。
美學布道者蔣勳動人分享、建築師安郁茜藝術指導,
關於文明、關於藝術、關於肉身,最美的沉思。
夏娃、佛母、莎樂美;哪吒、岳飛、文天祥……在漫長的文明發展史中,藝術裡的「肉身」與真實的肉身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辯證關係。而藝術家往往藉由顛覆舊有的身體造型,以全新的角度觀看、記錄、思考肉身。在《肉身供養》中,美學布道者蔣勳縱橫古今中西藝術傑作,試圖反思儒家主義長久以來所催化出的文化慣性,並帶領我們在形形色色肉身的處境中,毫不隱諱地探索,發掘出動人、高貴,以及更多不同的人性可能與美的可能。
「是身如焰,從渴愛生」,《維摩經》的句子常讓我震動。肉身像熾熱燃燒的火焰,如此渴望著愛。如果不輕蔑地對待肉身種種慾望的難堪卑微,是否可以認真向每一尊存在的肉身合十敬拜?也許肉身種種都有我不知道的艱難。——蔣勳
「一切難捨,不過己身」,最難捨去的竟是自己的肉身啊。古老的信仰或許使我們重新省視起了自己肉身的眷戀不捨。——蔣勳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