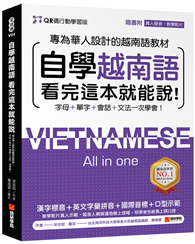暢銷四十年的英國國民讀物
二十世紀最佳英國電影第七名《Kes》原著小說
《衛報》票選「全球最佳五十部小說改編電影」第六名
藝人、作家 傅娟、影評人 聞天祥 溫暖推薦
我知道自己不討喜,
但,你們又算什麼……
比利是個沒什麼光明未來在等待他的男孩。同學欺負他、捉弄他、嘲笑他,認為他無藥可救,因為比利跟他們一樣,沒什麼不同,永遠會被困在這個煤礦小鎮裡。家人不關心他,單親媽媽每天打扮花枝招展,只為尋找自己的第二春而忙碌;身為礦工的哥哥,則把他下人般使喚、打罵。比利知道自己並不討喜,但他也不是太在乎,日子一天一天過,隨便這世界要怎麼對待他,他都接受。
無奈,但無法改變。直到凱斯的出現,比利從凱斯雛鳥時開始訓練牠,在這段過程中,他第一次體會到什麼是愛與信任,也知道,就像他自己一樣,牠或許可以接受訓練,但永遠不會馴服……
「這不過是一本薄薄的書,寫一個毫無希望的人和一隻鷹,但它就這麼奇妙地引起了共鳴。幾十年過去了,有些讀者其至告訴我,這本小說改變了他們的生命。」──貝瑞.漢斯(Barry Hines)
作者簡介:
貝瑞.漢斯(Barry Hines)
出生於霍伊蘭公有地(Hoyland Common)的礦村,地近南約克郡(South Yorkshire)的班斯萊(Barnsley)。就讀於厄克斯菲(Ecclesfield)文法學校期間,曾入選英格蘭文法學校(England Grammar School)足球代表隊。畢業後,成為礦地測量員的學徒,同時為班斯萊地區足球隊踢球(大部分是在第一隊),後來進入拉夫堡(Loughborough)師範學校體育系。轉為全職作家之前,於倫敦及南約克郡任教多年。
目前是英國皇家文學會(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的會員,同時也是雪菲爾哈倫大學(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的名譽教授。
累積出版作品共八部,除了《鷹與男孩》之外,《Look and Smiles》也已拍成電影並勇奪坎城影展青年影片獎。他也撰寫了諸多電視劇劇本,並獲得英國影視藝術學院(BAFTA)及廣播媒體協會獎(Broadcasting Press Guild Award)的最佳單元劇獎肯定。
譯者簡介:
賴肈欣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台北人。
譯作有《七日後》。
各界推薦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英國中學(約15歲)英文課程指定讀本。
◎1969年由肯洛區(Ken Loach)改編為電影《Kes》,名列英國電影協會(BFI)「二十世紀最佳英國電影」第7名、衛報「史上最佳小說改編電影」第6名。
◎入圍英國衛報和Book Marketing Group選出史上五十部最佳電影改編小說。
�為導演肯洛區的成名作品,獲選英國電影史上十大電影之一。
描寫成長挫折與困境的小說,以小孩與動物之間的關係為核心。雖無高潮起伏的劇情,只是描寫一般的日常生活,但仍能感動讀者,在陰鬱中帶著一絲幽默。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英國中學(約15歲)英文課程指定讀本。
◎1969年由肯洛區(Ken Loach)改編為電影《Kes》,名列英國電影協會(BFI)「二十世紀最佳英國電影」第7名、衛報「史上最佳小說改編電影」第6名。
◎入圍英國衛報和Book Marketing Group選出史上五十部最佳電影改編小說。
�為導演肯洛區的成名作品,獲選英國電影史上十大電影之一。
描寫成長挫折與困境的小說,以小孩與動物之間的關係為核心。雖無高潮起伏的劇情,只是描寫一般的日常生活,但仍能感動讀者,在陰鬱中帶著一絲幽默。
章節試閱
法辛老師跑著趕了過來。在衝突邊緣遊走的男孩們,像是被拒於足球場外的支持者,將這個消息散布了出去。消息在後排的人群間傳開,於是打結的人群鬆了開來,男孩紛紛急著趕在法辛老師到達前逃離現場。但是在衝突的核心,大夥兒都全神貫注,心無旁鶩,當法辛老師奮力往前擠,抓住男孩的手臂將他們拉開,大夥兒這才別過臉看他,情緒一下子從憤怒轉為吃驚,然後想起自己第一時間的反應,又啞然失笑。法辛老師將麥道威從比利身上拎起來,像小獵犬搖晃老鼠般搖晃他。原本煤堆的所在已經空掉了,旁觀者也撤到安全的距離。法辛老師環顧他們,怒火中燒。
「我給你們這些傢伙十秒鐘的時間滾回中庭去。如果十秒鐘過後我還看見任何一張臉,我會狠狠修理那張臉的主人一頓。」
他開始讀秒。四秒鐘後現場只剩下麥道威和比利。
「現在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比利哭了起來。麥道威用手背抹了抹鼻子,然後低頭看著抹過鼻子的手背。
「說啊!……卡斯伯?」
「都是他,老師!他先動手的!」
「我沒有,老師!是他先用煤塊丟我的!」
「嗯,那他為什麼要丟你呢?」
「沒有理由!」
「你說謊!」
法辛老師閉上眼睛,雙手在胸前擺出交叉狀,制止他們繼續解釋。
「閉嘴。你們兩個都給我閉嘴。千篇一律的說法:這不是任何人的錯,沒有任何人先動手,你們只是莫名其妙地碰巧在煤堆上打了起來。我應該把你們兩個都送交葛萊斯校長處理。」
他朝後方的校園撇撇頭,話從他緊咬的齒縫中迸出來。
「看看你們把這地方搞成什麼樣子。」
兩個垃圾桶翻倒在地,裡頭的東西灑得到處都是,三個垃圾桶的蓋子不翼而飛。煤堆被踐踏成彷彿一大片由煤塊組成的沙灘,零星的煤塊被踢到柏油路的另一頭,有些更被踢進了腳踏車棚。
「給我看啊!真令人作嘔!再看看你們兩個那副模樣!」
麥道威一邊的襯衫下襬從毛衣底下被扯出一截來,像是半條圍裙。比利前排的襯衫鈕釦一路迸開到底。一顆鈕釦不見了,對應的鈕孔也裂了開來。他們的頭髮看來彷彿兩人已經連續狠狠抓了自己的頭皮一個禮拜,而他們的臉則是煤礦工人的顏色。
「還有,別再哭了,卡斯伯。你又不是快掛了,小子!」
「等我逮到他,他就會掛了。」
法辛老師大步走到麥道威面前,彎下腰直視著他。
「你真是個很勇敢的男孩,不是嗎,麥道威?卡斯伯的體型跟你差不多,不是嗎?我請問你,如果你真的這麼想打架的話,幹嘛不挑個跟你體型相當的對手?嗯?嗯?」邊說邊在麥道威的肩膀上推了兩把。
「因為你會怕,是嗎?是不是,麥道威?」右刺拳,再一記右刺拳,麥道威每退一步,他就跟進一步。
「你只不過是個欺負弱小的惡霸。典型的欺負弱小的惡霸!就算不是卡斯伯,也是跟他差不多的孩子。不是嗎?麥道威?」刺。再刺。
他們把比利拋在後頭,一進一退,一路推進到腳踏車棚裡,活像一對練舞的舞伴。
「如果我把你壓在地上狂揍你的臉,你會怎麼說?」刺。刺。
麥道威哭了出來。
「你是不是會說我是欺負弱小的惡霸,嗯?而你說得一點都沒錯,因為我比你高,比你壯,我清楚知道在你來得及出手之前,我就可以把你揍成稀巴爛。就像在你面對每個你欺負的男孩時你也清楚知道這點,麥道威!」下兩記刺拳變成重捶。
「我要跟我爸告狀!」
「你當然會跟你爸告狀,小子。像你這樣的男孩,永遠都只會跟老爸告狀。那麼你知道我接下來會怎麼做嗎?我會跟我的老爸告狀。然後會發生什麼事呢?嗯?」
麥道威的後腦杓碰的一聲撞上車棚的後半部,鐵皮被撞得嘎啦嘎啦響。法辛老師踏出最後一步,再度縮短兩人之間的距離。
「而你知道嗎,麥道威,我老爸是世界重量級拳王?這麼一來,你老爸會有什麼下場呢?嗯?而你會有什麼下場呢?嗯?麥道威?」
法辛老師吼出這最後一個問題,然後直起身抓住麥道威的領口,把他拎了起來,讓兩人的臉彼此相對。此時麥道威已經哭到不可遏抑。
「現在告訴我,被霸凌是什麼感覺啊?你似乎不是很喜歡,是吧?」
他放下麥道威,狠狠一推,讓麥道威結結實實地撞在鐵皮上。
「如果你再被我逮到的話,你會更不喜歡的。」
他緩慢而仔細地將這句警告清楚地說出來,彷彿麥道威是有語言障礙的外國人。
「懂了嗎?」
「懂了,老師。」
「很好。現在給我回學校去,把自己弄乾淨,並且……等等,你下一堂課是我上的,對吧?」
「對的,老師。」
「那好,你就趁下堂課的時間好好給我把這一團亂恢復原狀。」
他回轉過身,將一坨煤塊踢回柏油路的那一頭。它撞上其他的煤塊,然後在滿地散落的煤塊中找到它的棲身之所。視線只要稍一離開,就再也找不到它了。
「當我十二點鐘下課回到這裡的時候,我要所有煤塊都回到原位。有問題嗎?」
「沒有,老師。」
「很好,那就開工吧。」
麥道威走了開來,邊走邊用指節及手背搓揉眼睛和臉頰。從比利身邊經過時,他停止動作並瞥了比利一眼。法辛老師跟著他緩緩地走出車棚,算準時間,當麥道威消失在建築物轉角時,自己剛好與比利面對面。
「那麼現在,卡斯伯,到底是怎麼回事?」
比利搖搖頭。
「搖頭是什麼意思?」法辛老師學他搖搖頭。「一定有什麼原因吧。」
「噢……我不能跟你說,老師。」
「為什麼不能?」
「就是不能。我不能,老師!」
比利臉部抽搐了一下,然後又哭了起來。
「他侮辱我,還扯到我爸媽和賈德,大家都在嘲笑我,而且……」
他啜泣得愈來愈激烈,不僅影響到他的呼吸,也打斷他的話。法辛老師舉起一隻手,點點頭。
「好了,小子,冷靜下來。現在沒事了。」
他一邊等著比利冷靜下來,一邊緩緩地搖頭。
「我不知道,你似乎老是會招來這些有的沒的事,不是嗎,卡斯伯?」
比利低頭站著,輕聲吸著鼻子。
「我實在很納悶到底為什麼?你覺得呢?」
「覺得什麼,老師?」
「為什麼你老是有麻煩找上門呢?」
「因為大家都欺負我,那就是為什麼。」
比利情緒激動地抬起眼,他那藏在交織的下睫毛裡的淚珠,像一顆顆不斷融化並閃爍的水晶。法辛老師撇過頭,以掩飾自己臉上禁不住的笑意。
「這我知道,但為什麼?」
「我不知道,他們就是不肯放過我。」
「也許因為你是個壞孩子。」
「也許我是,有的時候是。可是我沒那麼壞,我跟有些小孩差不多壞,可是那些小孩似乎都沒事。」
「那你認為你只是運氣不好?」
「我不知道,老師。我好像老是莫名其妙就會惹上麻煩。你知道,因為一些蠢事,像今天早上在禮堂就是。我根本什麼都沒做,只不過是打了個盹兒。我累得跟狗似的,六點鐘就得起床,然後東奔西跑地送報紙,又要跑回家看看老鷹,接著還得跑來上課。唉,我的意思是說,換成是你,你也會覺得累吧,老師?」
法辛老師咯咯地笑了起來。
「我應該會筋疲力盡吧。」
「不應該因為這種事而被打吧,是不是,老師?不應該因為太累而被打吧?不過這些話你可不能跟葛萊斯……葛萊斯校長說,他會殺了你的!你知道嗎,老師,今天早上有個同學跟我們一起站在他的辦公室外面,他不過是要替別的老師傳話,結果葛萊斯連他都打!」
法辛老師咧嘴露出笑意,接著忍不住張開嘴巴,笑出聲來。比利嚴肅地看著法辛老師面部表情的變化。
「對你來說這不痛不癢,老師。但對那個同學來說呢?他後來吐得跟條狗似的。」
法辛老師立刻回復嚴肅的態度。
「你說得沒錯,小子,這並不好笑。只不過你講故事的方式實在太有趣了。」
「還有早上上英文課的時候,就是我沒聽課的那時候。實在不是我不把它當一回事,只是我的手真的痛得要命!當你的手痛到不行的時候,根本沒辦法集中精神!」
「我想是沒辦法。」
「但我還是因此惹上麻煩了,不是嗎?」
「不過你將功贖罪了啊!」
「我知道,可是每次都是像那樣。」
「你是指?」
「老師們啊。他們從來不認為可能是自己的錯。」
「嗯,我想很少有老師會這麼認為。」
「他們認為自己永遠都是對的。可是有時候你真的不是故意的,就像今天早上一樣;還有比如說,有時候課程內容枯燥得要命,所以你不想聽,結果就挨打了。唉,我的意思是說,如果課程內容很無趣,根本沒辦法強迫自己聽進去,對吧,老師?」
「是沒辦法。」
「可是這種話你可不能跟老師說,他們會回你:『少自以為是了,臭小子!』然後呼的一聲就是一巴掌。」
比利直起身,搖搖頭,做出嚴厲的表情。然後他對著法辛老師和自己之間的空氣揮出一巴掌。看到他的模仿,法辛老師不禁大笑出聲。
「不過他們就是會那樣說,老師。」
「我也是老師,但我並沒有那樣說,不是嗎?」
「呃……」
「呃什麼?」
「你至少會試著教我們一些東西,其他老師就別提了。他們根本懶得理我們,就因為我們是四年丙班,你可以看得出來,他們跟我們講話的方式,就好像當我們是一坨屎。他們總是罵我們白痴、傻瓜、呆子,總是不停地看錶,想知道還有多久才下課。他們受夠了我們,我們也受夠了他們。然後每次發生什麼事,他們就找我開刀,因為我是個頭最小的。」
「他們不是全部都那樣吧,你是說真的嗎?」
「大部分都是,老師。而且,總之……我跟你比較聊得來。」
比利低下頭,漲紅了臉。法辛老師低頭看著他的頭頂。
「最近家裡怎麼樣?」
「還好,老師。應該跟平常沒什麼兩樣。」
「那警方呢?你最近有招惹上他們嗎?」
「沒有,老師。」
「因為你已經改過自新了?還是因為你都沒被逮到?」
「我已經改過自新了,老師。」
法辛老師對他微笑。但比利則保持嚴肅。
「是真的,老師,我已經幾百年沒做壞事了!那也是為什麼麥道威老是找我麻煩的原因之一,因為我不再跟他們一起混了。也就是我不跟他們一起混之後,就不再惹禍上身了。」
「發生了什麼事?你們吵架了還是?」
「沒有啊,老師,是因為我養了老鷹的關係。我對養鷹太著迷了,光是這件事似乎就占去我全部的時間。那時候是夏天,我都會在晚上帶著牠到住家附近的田野裡去。等到長夜(冬天)再度來臨時,我還是沒回去找麥道威他們。我再也懶得去找他們了。
「我盡我所能地找來一些馴鷹術的書,現在幾乎都快讀完了。我自己做新的兩開和其他道具。有時候我會到棚屋裡,點亮一根蠟燭,就這麼坐著。在那裡頭我感覺很自在。我找來一具煤油爐,讓棚屋裡變得很溫暖,我們就這麼坐在那裡。坐在那裡,聽著屋外的晚風,會讓人覺得十分溫馨舒適。」
「嗯,我相信。」
「比起在街上游蕩、無所事事,那實在是天壤之別。因為我們一向就是那樣。在國宅社區裡晃來晃去,到處鬼混,無聊又冷得要命。我在想那就是為什麼我會老是惹禍上身,因為我們經常闖進別人家裡偷東西,只是為了要找點刺激。那樣總算是有事情做,就這樣。」
「那青年俱樂部如何呢?學校裡有個青年俱樂部,每個禮拜有三個晚上都有活動。」
「我不喜歡青年俱樂部。我不喜歡玩遊戲。我們以前會進城去看電影,或者有時候去咖啡吧。可是無論如何,他們做什麼都行,只要他們開心就好。反正我現在已經懶得理他們了。」
「所以你現在變成獨行俠了?」
「我寧願這樣,我只希望大家別來煩我。可是永遠有人追著我跑。像是這節下課,我不過是繞到車棚裡來避風,結果等我回過神來,我已經跟人打起來了。在課堂上也是一樣,我只是乖乖坐著,結果等我回過神來,我已經被叫起來吃棍子或什麼的。他們總說我是害蟲,或說我是討厭鬼,講得好像我喜歡自討苦吃似的。可是我並不是,老師。
「在家裡也是,如果國宅社區裡發生了什麼事情,警察總是跑來我們家,即使我根本已經幾百年都沒為非作歹了。而且我說的話他們一句也不信!有時候搞得我真想出門做壞事,只為了要一洩心頭之恨。」
「別放在心上了,孩子。情況會好轉的。」
法辛老師跑著趕了過來。在衝突邊緣遊走的男孩們,像是被拒於足球場外的支持者,將這個消息散布了出去。消息在後排的人群間傳開,於是打結的人群鬆了開來,男孩紛紛急著趕在法辛老師到達前逃離現場。但是在衝突的核心,大夥兒都全神貫注,心無旁鶩,當法辛老師奮力往前擠,抓住男孩的手臂將他們拉開,大夥兒這才別過臉看他,情緒一下子從憤怒轉為吃驚,然後想起自己第一時間的反應,又啞然失笑。法辛老師將麥道威從比利身上拎起來,像小獵犬搖晃老鼠般搖晃他。原本煤堆的所在已經空掉了,旁觀者也撤到安全的距離。法辛老師環顧他們,怒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