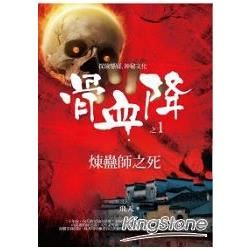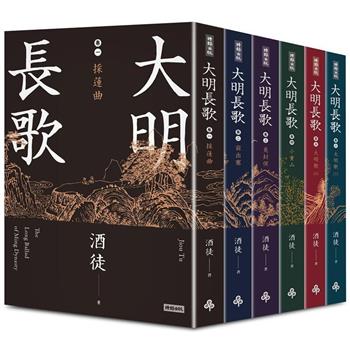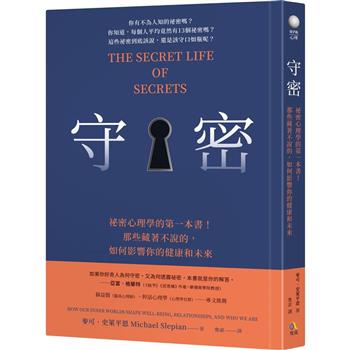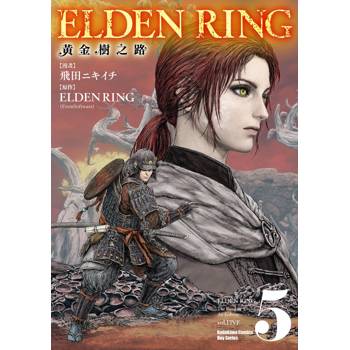1颱風夜
血案
「叮零零、叮零零」,電話鈴聲夾雜在窗外的暴風雨聲裏傳來,一下子將我從並不踏實的睡眠中徹底震醒。
我拿起電話,李慕珍那近乎歇斯底里的興奮叫聲衝耳而來:「阿天,阿天,我終於揭開了……我終於弄明白了,恭喜我吧,快恭喜我吧!兩千萬的獎金馬上就會落在我的錢包裏,而且全香港的大小醫院、幾萬名醫生們都會崇拜我、嫉妒我……」
啪的一聲,我打開臺燈,先看了看側面牆上的電子鐘,時針正指向凌晨三點鐘。
李慕珍是港醫大出了名的工作狂,向來沒有時間觀念,千家萬戶酣然入睡的時候,就是他據案鑽研、靈感如泉湧的工作時間。有這樣的醫生朋友,實在是我的不幸。
「老李,你看看現在幾點鐘了?你知道我剛從藏地回來,高山反應--」
「別管他媽的什麼高山反應了阿天!現在我已經有把握治好大亨的『骨血降』,最不濟,也能以毒攻毒,把他體內的所有毒素,逼迫到淋巴系統的某一末梢部分,然後用隔離手術,徹底地把它們消滅掉。我知道你到藏地去,也是為了尋找替大亨治病的良方,現在大家都不用再費心思了,一切困難在我手上迎刃而解,我就像手握長劍的亞歷山大一樣,閃電一揮,再困難的謎題都會哈哈哈哈……」李慕珍大笑,笑聲從聽筒裏鑽出來,震得我的耳鼓陣陣發麻。
「恭喜你。」我打了個哈欠,輕輕捶了捶木脹脹的太陽穴,腦袋昏昏沉沉的,沉重得像頂著一塊大石頭。
「阿天,快到我實驗室來吧,看看從大亨體內取出來的細菌樣本,在藥水的攻擊下狼狽死亡的樣子。快來,快來,我等你!」李慕珍聽不出我話裏的諷刺和無奈,興奮得像大年初一的小孩子。
我苦笑著長歎:「老李,饒了我吧,不如你現在打給大亨好了,給他看看你的新發明,順便要他把兩千萬獎金直接劃到你帳戶裏。現在,我必須回床上去跟周公作伴,再見。」
跟這樣的工作狂沒有道理可講,拂曉之前,我照例能沉睡一陣,才不會浪費時間和他一起瘋。再說,港島各路江湖高手都已經板上釘釘地確認:「大亨中的是瓜地馬拉黑巫術,與現代化醫學無關,兩者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知識範疇。」
「你--孺子不可教也!我發誓,我對天發誓,現在有百分之一千的把握,消滅瓜地馬拉黑巫術,讓大亨重新變得龍精虎猛、老當益壯的。阿天,你不信咱們就走著瞧,明天我就去見大亨。錢不重要,我不稀罕,我李慕珍就是要像李家的老祖宗李時珍一樣揚名天下﹑流芳百世……」
我又氣又笑地答他:「唔,我想大亨很樂意聽到這個好消息。要不,我把他號碼給你,現在就打給他?對了對了,你是他的專職中藥醫生,手裏有他的電話號碼,為什麼不打?是怕雷娜一生氣炒了你的魷魚嗎?」
李慕珍愣了一愣,聽出了我的嘲諷,沮喪地嘟囔著:「好好,我不跟你說,我打給蘇小姐好了,像她那樣冰雪聰穎的女孩子,一定能理解我在說什麼,睡睡睡,作你的大頭夢去吧!」砰的一聲,他重重地丟下電話。當然,他已經不是第一次摔我電話了,而且摔過就忘,下次有事還會不管三七二十一,照直撥進來。
我關了臺燈,窗外的雨聲時緊時鬆,後勁十足。
大亨的神秘怪病發作近五年了,最開始是以「癌症、骨髓惡性腫瘤」來治,但用遍了全球各地治療此類疾病的良藥,卻毫無控制病情的跡象。一年前,大亨終於在他的生日晚宴上,向最親近的朋友低調宣佈,自己中的是瓜地馬拉黑巫術,而且是最惡毒、最恐怖的一種--骨血降。
當時我也在場,親眼目睹了一干高手們聽到「骨血降」這個名字時,同時面色大變的情景。
「天知道李慕珍在搞什麼?如果中醫學能搞定那怪病,大亨何必將賞格在六個月內一提再提?」我翻了個身,把一隻天鵝絨枕頭蓋在自己臉上,昏昏沉沉地睡了過去。
「叮零零、叮零零、叮零零」,刺耳的電話鈴聲又響了,我勉強睜開眼,陽光正透過遮光窗簾的邊緣漫射進來,電子鐘顯示已經是上午十點鐘,這一次我竟然連睡了六個多小時。
「誰?」我拿起聽筒。
「我是陳泰。阿天,李慕珍死了,就在港醫大的實驗室裏。」一個低沉壓抑的男聲傳過來,夾雜在嘩嘩作響的閃光燈頻頻動作時產生的電子雜訊裏。
「什麼?」我猛然一驚。
「我說,李、慕、珍、死、了--我負責勘察現場。電話記錄顯示,今天凌晨他曾撥打過你的號碼,所以我想請你過來協助調查。」陳泰亦是我的朋友,以幹練沉穩的工作作風著稱,屬於警界後起之秀中的佼佼者。當他一字一句地告訴我這個死亡消息時,在我腦子裏殘存的那一點點睡意,立刻一下子飛到九霄雲外去了。
我深吸了一口氣,強迫自己冷靜下來:「我馬上來,是在薄扶林沙宣道嗎?」
陳泰簡潔地回答:「是,等你。」然後便掛斷了電話。
我以最快速度沖了個冷水澡,然後換裝下樓,開車出門。
車子剛剛進入沙宣道港醫大的西門,一輛計程車突然超過我,高速前行,直奔掩映在芙蓉樹叢裏的醫大試驗樓。我到樓前,計程車上跳下來的那個穿著白色連衣裙的女孩子,已經急匆匆地快步踏上了樓前的臺階,一邊走,一邊從手提包裏掏電話,一個白銅小圓鏡就在此時從她手邊跌落下來,在臺階上跳了幾下,一直滾到我的腳邊。
「呀--」她慌忙旋身,連衣裙如同一朵微微張開的夏晨蓮荷,一頭自然垂瀉的烏髮也無聲地飛揚起來。
我彎腰拾起小圓鏡,走上臺階,微笑著遞給她。
「謝謝,謝謝你。」她的唇邊綻開了一抹帶著歉意的笑容。
「不客氣,臺階有些陡,當心。」我從不渴求自己的生活中出現豔遇,對於一名喜歡流浪的江湖遊俠來說,多姿多彩的探險生活才是我的最愛。
我的電話恰在此刻響起來,那女孩子溫柔地點了點頭,算是告辭,先我一步進入大樓。
「阿天,我剛接到陳泰警官的電話,說港醫大的李醫生遇害,現在正趕往沙宣道港醫大試驗樓。你在哪裡?」雷娜說話向來是語速飛快、口齒清晰,辦事亦是雷厲風行、效率超高。
我常告訴她,如果戒掉以上四個「毛病」,多一些溫柔可人的女人味,身後一定會多一大群追求者,就可以在大亨雷霄漢六十歲金盆洗手大會前,將自己嫁出去,也了卻了她義父的這個心願。
「我在出事的試驗樓前。」我慢慢地在臺階右側的鐵藝花枝長椅上坐下來,向南面的歐式風格小花園裏望著。
「哦?這樣,等我五分半鐘,我馬上到。」雷娜連「再見」都不說,快速掛斷電話。
「一個恨不得把行程安排以倒計時排列的機器人式女孩子,嗯,跟李慕珍那個工作狂倒是一對--」我忽然醒悟李慕珍已死,這樣開玩笑甚是不妥,馬上呸呸兩聲,向地上連吐了兩次口水,以示妄言無忌。
雷娜是大亨雷霄漢膝下唯一的義女,與大亨的胞弟雷震一起撐起了雷氏企業的天空。
她今年雖只二十二歲,在港島黑白兩道上卻已經名聲赫赫,幾乎是眾人心目中想當然的雷氏企業未來接班人。「貌美如花、辣手無情」這八個字,足以刻畫出雷娜的形像,所以,很多富家公子把她當成了「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多刺玫瑰,止步於隔山隔海的遠程欣賞,不敢冒然追逐。
差七秒五分半鐘,雷娜的黑色豐田越野車,戛然停止在試驗樓前。
她摘下寬邊墨鏡,從車窗裏向我招手,仍舊穿著慣常的凡賽思品牌的白色亞麻洋裝,長髮盤在頭頂,用一支水晶簪子別住,高傲如一隻白天鵝般卓然不群。
我站起身,沒有迎下臺階,而是雙手插在口袋裏,靜等著她上來。
雷娜下了車,急步走上臺階,臉上臨時堆起笑容:「阿天,從藏地回來後,怎麼沒有打電話給我和義父,好讓我們給你接風洗塵?」
我知道,在這些話的背後,隱藏的是「藏地之行有收穫否」的潛臺詞。大亨的病是雷娜心頭大患,為了此事,她肩頭的擔子越來越重,臉上的笑容越來越少。
「藏地薩迦寺最著名的『藥菩薩』德吉上師已經答應,半個月內從尼泊爾加德滿都轉機過來。我曾詳細向他談過大亨的病情,隨身帶去了五年來所有的病歷、透視片,還有所用的中西藥品名。德吉上師之所以需要耽擱那麼久才過來,為的是準備一味非常難求的藥引子。他說過,瓜地馬拉黑巫術包含了煉蠱術、巫術、毒藥、移魂術等等多種手段在內,單憑中醫的望、聞、問、切,或者西醫的針劑、刀石、鐳射透射,根本無濟於事,只是隔靴搔癢一般,難以拔除根基。就算他親自來,也沒有十分把握,只看大亨的佛緣如何。」一路上電梯,我一路簡單地告訴她這些情況。
薩迦寺座落於藏地薩迦縣奔波山上,是藏傳佛教薩迦派的主寺。「薩迦」是藏語音譯,意思是「灰白土」。北宋熙寧六年,吐蕃貴族昆氏家族的後裔貢卻傑布,發現奔波山南側山坡的土呈現光澤白色,出現祥瑞之相,即出資建起薩迦寺,逐漸形成薩迦派。薩迦寺用象徵文殊菩薩的紅色、象徵觀音菩薩的白色,和象徵金剛手菩薩的青色來塗抹寺牆,所以又被稱為「花教」。
「藥菩薩」德吉上師則是中、印、尼三國知名的醫學大師,曾被聘為尼泊爾王宮的名譽御用國醫,五度赴歐美講解神秘的藏藥、藏醫,名聲傳遍全球。這次我之所以能把他請到港島來,幾位尼泊爾王室的朋友居功至偉。
雷娜精神一振:「太好了,藏藥文化博大精深,也許只有來自雪域高原的靈丹妙藥,才能對抗詭異的瓜地馬拉黑巫術吧?剛剛陳泰告知李慕珍的死訊,給我打擊不小,他一直負責義父在中醫方面的診療進展,想不到會出現這種意外……」
李慕珍今年四十歲,是港醫大唯一的單身而非鑽石王老五的男性。像他那樣的工作狂,普通女孩子也會敬而遠之,不敢招惹。同理,做為一個與世無爭、無欲無求的人,他與「遇害」這個詞語之間,似乎也很難扯上關係。
我們踏進四樓那個專業試驗室的時候,陳泰正帶著一隊警員做仔細的現場勘察。
李慕珍的死狀很奇怪,他坐在顯微鏡觀測台前的一把椅子上,身子微微後仰,一手握著圓珠筆,一手捏著近視眼鏡,像是觀測累了,暫時閉眼休憩似的。站在門口看,會令人產生「他在沉思」的錯覺。
陳泰身材偏瘦,喜歡瞇著眼睛看人,臉上的表情永遠都是陰轉多雲,很少見到笑容。當他迎上來跟我握手時,嘴角勉強地牽動了一下,算是「笑著」打招呼。
「什麼情況?」除了對我之外,雷娜極少廢話,惜字如金。
陳泰聳聳肩:「李慕珍死於一條蟲子,一條嵌在額頭上的、僅有三粒大米連接起來那種長度的蟲子。死者全身唯一的傷痕在額頭上,被那蟲子咬了一口後,全身都浮腫變黑了,具體的體內變化,還得做詳細解剖後才能得出系統的結論。我已經通知驗屍官過來,借用醫大的解剖室展開工作。阿天,我派人給你做筆錄,這是例行公事,別介意。」
他招呼了一名叫「阿榮」的警員負責給我做筆錄,自己一個人在八扇寬大的落地窗前反覆踱步,偶爾蹲下身去,凝神觀察著乳白色的大理石地面。
我先去了觀測台前,看到了那條仍然齧住李慕珍眉心的黑色小蟲。它的外形與普通的米蟲、菜青蟲相似,但毒性卻猛烈得驚人,一種墨色的黑暈,以傷口為中心放射狀鋪散開來。李慕珍的臉色本來是白中帶黃,屬於睡眠嚴重不足的標準夢遊者一類,但現在看他,簡直就是地道的非洲人面孔。
雷娜抱著胳膊連續倒吸了幾口涼氣,不發一言,駭然倒退。
「好毒。」我皺著眉搖頭。
一口咬中,傷者立斃。這小蟲的殺傷力,比起蛇類中的七步倒、草上飛、青竹梢勝逾百倍,我立刻聯想到江湖上那個最出名的擅長養毒、制毒、下毒的門派--蜀中唐門。千百年來,唯有那一家的門下弟子,才對世界上千奇百怪的毒蟲、毒藥感興趣,並矢志不移地為了研發出天下第一的毒藥而一代又一代前仆後繼。
「雷娜?」我叫了一聲。
她立刻會意,重重地頓足:「我出去打電話,看是不是他們在胡來?李慕珍是義父的專職醫生,向他動手,就等於挑戰雷氏在江湖上的權威。」
贅述一句,雷霄漢、雷震都是昔日江湖中,以「製造火器、鑽研火藥」成名的霹靂堂嫡派弟子,他們的父親和爺爺兩代,從清末民國起轉行經商,不再炫耀「霹靂堂雷家」這塊金字招牌,實際上是最明智之舉。一個家族企業,如果僅靠「一招鮮,吃遍天」這樣的獨木橋式經營手段存在,很可能一夕之間遭到致命打擊而被連根拔起。
霹靂堂雷家與蜀中唐門,向來是江湖上誓不兩立的對立派系,與雷家不同,辛亥革命之後,蜀中唐門所倚靠的袁系軍閥樹倒猢猻散,本來就人丁凋落的唐門本身也遭連累,一蹶不振。時至今日,雷氏如日中天,而唐門弟子卻流落到世界各地,連祖宗留下的招牌也保不住了。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骨血降(1):煉蠱師之死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194 |
驚悚/懸疑小說 |
$ 254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骨血降(1):煉蠱師之死
本書主題以二十一世紀瓜地馬拉黑巫術、香港華裔蠱術、西藏藏藥、波灣戰爭秘辛「大殺器──戰神」為核心的神秘文化小說。
二十年前,向天的父母向昆崙、金鉤月,被瓜地馬拉恐怖分子龍將軍殺害,向昆崙的好兄弟、大亨雷霄漢,也被黑巫術部落下了「骨血降」,身體受到控制,除非用中蠱者自己的親生子女的骨骼和血肉做藥引子,才能解除。
二十年後,向天從西藏請來藥菩薩,為大亨雷霄漢治療骨血降,但黑巫術部落人馬和龍將軍出現,為了爭奪威力驚人的武器「戰神」,在港島展開了一場生死激戰,龍將軍和麾下七虎將、華裔四大煉蠱師、藏藥高手藥菩薩、黑巫術部落新一代掌門人相繼登場。最終,向天擊敗龍將軍,化解了二十年前大亨與黑巫術部落的恩恩怨怨,為大亨解除了困擾半生的骨血降,自己也終於抱得美人歸。
作者簡介:
飛天,天蠍座,職業作家,已出版長篇小說《盜墓之王》、《佛醫古墓》、《法老王之咒》、《伏藏》、《敦煌密碼》等共計500餘萬字,短篇小說《錯手》、《股神末日》、《冷刃報恩行》、《觸不到的電子情人》等十幾篇,以擅長創作探險懸疑、神秘文化類小說而著名於簡體、電子、繁體圖書市場,寫作風格大開大闔,情節佈局匪夷所思,個人座右銘為「業精於勤而荒於嬉」。
章節試閱
1颱風夜
血案
「叮零零、叮零零」,電話鈴聲夾雜在窗外的暴風雨聲裏傳來,一下子將我從並不踏實的睡眠中徹底震醒。
我拿起電話,李慕珍那近乎歇斯底里的興奮叫聲衝耳而來:「阿天,阿天,我終於揭開了……我終於弄明白了,恭喜我吧,快恭喜我吧!兩千萬的獎金馬上就會落在我的錢包裏,而且全香港的大小醫院、幾萬名醫生們都會崇拜我、嫉妒我……」
啪的一聲,我打開臺燈,先看了看側面牆上的電子鐘,時針正指向凌晨三點鐘。
李慕珍是港醫大出了名的工作狂,向來沒有時間觀念,千家萬戶酣然入睡的時候,就是他據案鑽研、靈感如泉湧的工作...
血案
「叮零零、叮零零」,電話鈴聲夾雜在窗外的暴風雨聲裏傳來,一下子將我從並不踏實的睡眠中徹底震醒。
我拿起電話,李慕珍那近乎歇斯底里的興奮叫聲衝耳而來:「阿天,阿天,我終於揭開了……我終於弄明白了,恭喜我吧,快恭喜我吧!兩千萬的獎金馬上就會落在我的錢包裏,而且全香港的大小醫院、幾萬名醫生們都會崇拜我、嫉妒我……」
啪的一聲,我打開臺燈,先看了看側面牆上的電子鐘,時針正指向凌晨三點鐘。
李慕珍是港醫大出了名的工作狂,向來沒有時間觀念,千家萬戶酣然入睡的時候,就是他據案鑽研、靈感如泉湧的工作...
»看全部
目錄
第一部 死亡預兆 017
序 018
1颱風夜血案 020
2發生在眉睫之前的殺人事件 034
3全球華裔四大煉蠱師世家 047
4大亨肩頭的最後一副重擔 061
5落魄青龍與鐵拳部隊 074
6七虎將現身,青龍化骷髏 087
7戰神是什麼? 101
8蘇雪腳心的七星紅痣 113
9蘇門答臘島藥人 126
10蘇雪是大亨的女兒? 140
第二部 人間戰神 150
1波灣戰爭的最大變數 151
2煉蠱師沙猜之死 164
3覬覦青龍寶藏三年的飛車黨太子 178
4藥菩薩德吉上師與珠穆朗瑪峰冰蛇 191
5龍將軍終於動手了 204
序 018
1颱風夜血案 020
2發生在眉睫之前的殺人事件 034
3全球華裔四大煉蠱師世家 047
4大亨肩頭的最後一副重擔 061
5落魄青龍與鐵拳部隊 074
6七虎將現身,青龍化骷髏 087
7戰神是什麼? 101
8蘇雪腳心的七星紅痣 113
9蘇門答臘島藥人 126
10蘇雪是大亨的女兒? 140
第二部 人間戰神 150
1波灣戰爭的最大變數 151
2煉蠱師沙猜之死 164
3覬覦青龍寶藏三年的飛車黨太子 178
4藥菩薩德吉上師與珠穆朗瑪峰冰蛇 191
5龍將軍終於動手了 204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飛天
- 出版社: 樸實 出版日期:2011-04-07 ISBN/ISSN:978986630249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4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驚悚/懸疑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