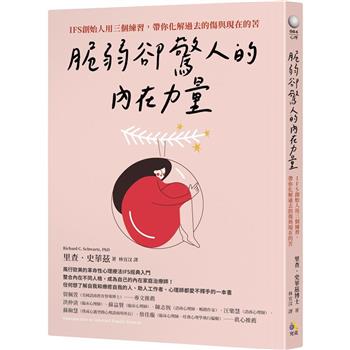本書講述一名敦煌莫高窟考古研究人員,在藏經洞發現了大量疑點,並據此推測敦煌絕不止一個藏經洞,因此引起神秘組織注意,進而被誘引進神秘、離奇的地底迷境,開始探險歷程。地底披掛濃重神秘感的廢棄基地、長波台、半截火車頭、潛艇、僧侶的屍骸、千佛洞、水底那爛陀寺,接踵刺激他的脆弱神經;而藏身暗處的純種突厥人後裔、日本人與中國考古隊在地底展開激烈暗戰,並將他捲入。主人翁歷經生死考驗,終於揭開真相。
作者簡介
公輸然
男,知名懸疑、歷史、探險小說作家,著名懸疑原創社團青銅文學創作社發起人。著有長篇小說《魯班書之血班母》、《南明寶藏》、《黑喇嘛》、《西域迷藏》;並先後在《今古傳奇》、《謎小說》、《懸疑志》等雜誌發表中短篇數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