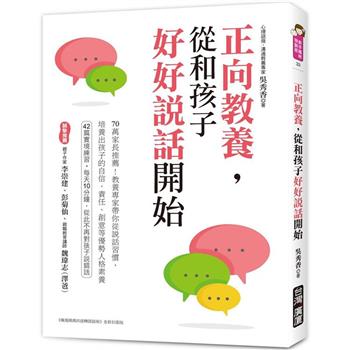第五十一回 程犯人釜魚漏網 施囚婦狡兔投羅
天地寥寥闊,江湖蕩蕩空,乾坤廣大盡包容。定盤打算,只不漏奸雄。 殺人番脫底,漁色巧成凶,安排凡事聽天公。要分孽鏡,情法果曾同!
右調〈南柯子〉
再說武城縣裡有一人,姓程,名謨,排行第三,原是市井人氏。弟兄六個,程大、程二俱早年亡故,只剩弟兄四人。獨程謨身長八尺,面大身肥,洗補網巾為業,兼做些鼠竊狗盜的營生,為人甚有義氣。他那竊取人家物件,也不甚麼瞞人。人有可惜他的,不與他一般見識;有怕他凶惡的,又不敢觸他的凶鋒。大酒塊肉,遇著有錢就買,沒錢就賒,賒買不來就白白的忍饑。鄰舍家倒是那大人家喜他,只是那同班輩的小戶甚是憎惡。
緊鄰有個廚子,名喚劉恭,也有八尺身軀,不甚胖壯,一面慘白鬍鬚。三個兒子,大的叫是劉智海,第二的是劉智江,第三的是劉智河。這個劉恭素性原是個歪人,又恃了有三個惡子,硬的妒,軟的欺,富的嫉忌,貧的笑話,尖嘴薄舌談論人的是非,數說人的家務,造言生事,眼內無人,手段又甚是不濟。人家凡經他做過一遭的,以後再叫別的廚子,別人也不敢去,他就說人搶他的主顧,領了兒子截打一個臭死。最可惡的,與人家做活,上完了菜,他必定要到席上同了賓客上坐。
一個蔡逢春中了舉,請眾鄉宦舉人喫酒。他完了道數,禿了頭,只戴了一頂網巾,穿了一件小褂,走到席前,朝了上面拱一拱手,道:「列位請了!這菜做的何如?也還喫得麼?」眾客甚是驚詫。內中有一位孟鄉宦,為人甚是灑落,見他這個舉動,問說:「你是廚長呀?這菜做得極好。請坐喫三鍾,何如?」劉恭道:「這個使得麼?」孟鄉宦道:「這有何傷?偺都是鄉親,怕怎麼的?」他便自己拉了一把椅子照席坐下,眾人愕然。孟鄉宦道:「管家,拿副鍾箸兒與廚長。」他便坦然竟喫,恨得蔡舉人牙頂生疼。客人散了酒席,一個帖子送到武城縣,二十個大板,一面大枷枷在十字街上,足足的枷了二十個日頭,從此纔把他這坐席的舊規壞了。
他的兒子都是另住,他與他的老婆另在一個路東朝西的門面房內,與程謨緊緊間壁。這個老婆天生天化,與劉恭放在天平秤兌,一些也沒有重輕。兩口子妄自尊大,把那一條巷裡的人家,他不論大家小戶,看得都是他的子輩孫輩。他門前路西牆根底下掃除了一搭子淨地,每日日西時分,放了一張矮桌,兩根腳凳設在上下,精精緻緻的兩碟小菜,兩碗熟菜,鮮紅綠豆水飯:雪白的麵餅,兩雙烏木箸,兩口子對坐了享用。臨晚,又是兩碟小菜,或是肉鮓,或是鯗魚,或是鹹鴨蛋,一壺燒酒,二人對飲,日以為常。夏用的衣服還也照常,唯是冬年的時候,他戴一頂絨帽,一頂狐狸皮帽套,一領插青布藍布裡棉道袍,一雙皂靴,撞了人趾高氣揚,作揖拱手,絕無上下。所以但是曉得他的,見了他的再沒有一個不厭惡痛絕。這程謨做些不明白的事件,他對了人敗壞他行止。人家不見些甚麼,本等不與程謨相干,那失盜之人也不疑到程謨身上,偏他對人對眾倡說必定是程謨偷盜。程謨一時沒有飯喫,要賒取些米麵,不是漢子,就是老婆,只除他兩口子不見就罷,教他看見,他必定要千方百計破了開去。
一日,一個糶米豆的過來,程謨叫住,與他議定了價錢,說過次日取錢。那糶糧的人已是應允,程謨往裡面取升,這劉恭的老婆對了那糶糧的人把嘴扭兩扭,把眼擠一擠,悄悄說:「他慣賒人的東西,不肯還人的錢價。要得緊了,還要打人。」程謨取出升來,那糶米豆的人變了卦,挑了擔子一溜風走了。程謨曉得是他破去,已是懷恨在心。過了半日:又有一個賣麵的過來,程謨叫住,又與他講過要賒,那賣麵的滿口應承。程謨進房取秤,又喜劉恭兩口子都又不在跟前,滿望賒成了麵要烙餅充饑。誰知那劉恭好好在屋裡坐著,聽見程謨賒麵,走出門前,正在那裡指手畫腳的破敗,程謨取秤出來撞了個滿面。賣麵的挑了擔就走,程謨叫他轉來,他說:「小本生意,自來不賒。」頭也不回的去了。程謨向劉恭說道:「你這兩個老畜生也可惡之極!我和你往日無仇,今世無冤,我和你是隔著一堵牆的緊鄰,我沒生意,一日不得飯喫,你升合不肯借我也自罷了,我向人賒升米喫,你老婆破了;我等了半日,再向人賒斤麵喫,你這賊老忘八羔子又破了我的!」
看官聽說!你想這劉恭兩個雌雄大蟲,豈是叫人數落,受人罵「老忘八羔子」的人?遂說:「沒廉恥的強賊!有本事的喫飯,為什麼要賒人的東西,又不還人的錢價?叫人上門上戶的囔叫,攪擾我緊鄰沒有體面!是我明白叫他不賒與你,你敢咬了我的雞巴!我還要攆了你去,不許你在我左邊居住哩!」程謨不忿,捏起盆大的拳頭,照著劉恭帶眼睛鼻子只一拳。誰知這劉恭甚不禁打,把個鼻子打偏在一邊,一隻眼睛烏珠打出掉在地上,鮮血迸流。劉恭的老婆上前救護,被程謨在胯子上一腳得跌了夠一丈多遠,睡在地上哼哼。程謨把劉恭像拖狗的一般拉倒路西牆根底下,拾起一塊棒椎樣的甕邊劈頭亂打,打得腦蓋五花迸裂,骨髓橫流。眾街坊一來懼程謨的凶勢,實是喜歡這兩個歪人一個打死,一個償命,清靜了這條街道。程謨見劉恭死停當了,對著眾人說道:「列位高鄰,我程謨償了劉恭的命,劉恭被我送了命,一霎時替列位除了這兩害,何如?」眾人說道:「你既一時性氣做了這事,你放心打官司。你的盤纏,我程嫂子的過活,你都別管,都在俺街里身上。」程謨趴倒地替眾人磕了頓頭,揚長跟了地方總甲去了。
眾人感他除了這劉恭的大害,審錄解審,每次都是街里上與他攢錢使用,還有常送東西與他監裡喫的。他的媳婦子雖是醜陋,卻不曾嫁人,亦不曾養漢,與人家看磨做活,受窮苦過。程謨駁了三招,問了死罪,坐在監中成了監霸,倒比做光棍的時候好過。
一年,巡按按臨東昌,武城縣將監內重犯僉了長解。押往東昌審錄。別個囚犯的長解偏偏都好,只有這程謨的長解叫是張雲,一個趙祿,在路上把這程謨千方百計的凌辱。一日五六頓喫飯,遇酒就飲,遇肉就喫,都叫程謨認錢;晚間宿下,把程謨繩纏鎖綁,腳鍊手杻不肯放鬆。程謨說道:「我又不是反賊強盜,不過是打殺了人,問了抵償,我待逃走不成?你一路喫酒喫肉,僱頭口,認宿錢,我絕不吝惜,你二位還待如何,只這般凌虐?我程謨遇文王施禮樂,遇桀紂動干戈,你休要趕盡殺絕了!」張雲、趙祿就道:「俺就將你趕盡殺絕,你敢怎麼樣的?」程謨說道:「誰敢怎麼樣的?只是和二位沒有仇,為甚麼二位和我作對的緊?」張雲對趙祿道:「且別與他說話,等審了錄回來,路上和他算帳!鼻涕往上流,倒發落起偺來了!」
到了東昌,按院掛了牌,定了日子審錄,張雲、趙祿把程謨帶到察院前伺候。程謨當著眾人就要脫了褲子屙屎。眾人說:「好不省事!這是甚麼所在?你就這裡屙屎!叫人怎麼存站?」程謨說:「你看爺們!我沒得不是個人麼?這二位公差他不依我往背淨處解手,我可怎麼樣的?」別的解子們都說張雲、趙祿的不是:「這是人命的犯人,你沒得不叫他屙屎?這叫他屙在這裡,甚麼道理?」張雲見眾人不然,同了趙祿,押了程謨到一個空闊所在解手。程謨看得旁邊沒有別人,只有二人在側,央張雲解了褲,蹲下屙完了屎,又央張雲與他結褲帶,他將長枷梢望著張雲鼻梁上儘力一砍,砍深二寸,鮮血上流,昏倒在地。趙祿上前扯他的鐵鎖,程謨就勢趕上,將手杻在趙祿太陽穴上一搗,搗了個碗大的窟窿,暈倒在地。程謨在牌坊石座上將杻磕開,褪出手來,將腳上的鐵鐐擰成兩截,提起杻來望著張雲、趙祿頭上每人狠力一下,腦髓流了一地,魂也沒還一還,竟灑手揚長往酆都去了。程謨手裡拿著磕下來的手杻做了兵器,又把那斷了的腳鐐開了出來,放開腳飛跑出城。
有人見兩個公差打死在地,一片長板丟棄在旁,報知了武城知縣。差人察驗,知是走了程謨,四下差人跟捉,哪有程謨的蹤影?只得稟知了按院,勒了嚴限拿人,番役都上了比較,搜捕的萬分嚴緊。有人說:「程謨的那個老婆,在刑房書手張瑞風家管碾子,只怕他知情也未見得。」三四個公人尋到那裡。其實張瑞風家把程謨的老婆叫將出來,眾人見了這個藍縷醜鬼的模樣,自然罷了。誰知合該有事,天意巧於弄人。張瑞風家抵死賴說沒有程謨的老婆在家,這些差人越發疑心起來。又兼這張瑞風衙門裡起他的綽號叫是「臭蟲」,人人都惱他的,眾人齊聲說道:「這是奉上司明文,怕他做甚?到他裡面翻去!」倒不曾搜著程謨的老婆,不端不正剛剛撞見一個三十以下的婦人,恰原來是那一年女監裡燒殺的小珍哥。
眾人看見,你看我,我看你,都說:「這不是晁源的小老婆小珍哥是誰?沒得偺見鬼了?」小珍哥一頭鑽進屋去,甚麼是肯出來?眾人圍住了房門,說道:「剛纔進去的那位嫂子,俺好面善,請出來俺見一見。」張瑞風的老婆在簾子裡面說道:「這是俺家的二房,臨清娶的,誰家的少女嫩婦許你這麼些漢子看?你拿程謨,沒得叫你看人家老婆來麼?」眾人道:「這說話的是張嫂子呀?俺剛纔見的那婦人,是監裡晁監生的娘子,眾人都認得是真。你叫他出來,俺再仔細認認,要果然不是他,等張師傅來家,俺眾人替他磕頭賠禮。他要再不饒,俺憑他稟了大爺,俺情願甘罪。你必欲不叫他出來,俺別的這裡守著,俺著一個去稟了大爺來要他。」張瑞風娘子道:「小珍哥托生了這八九年哩,如今又重新鑽出他來了?你列位好沒要緊!你不過說當家的沒在家,得空子看人家老婆呀!」眾人說:「這意思不好!私下幹不得!俺這裡守著,著一個稟大爺去!」
果然著了一個姓于名桂的番役跑到縣裡,稟道:「小的們打聽得程謨的老婆在刑房書辦張壽山家支使,小的們撲到那裡,張書辦沒在家,他家回說程謨的老婆沒在他家。小的們竟到他裡邊翻去,沒翻見程謨,只見一個媳婦子,通似那一年監裡燒殺的施氏。小的們待認他認,他鑽在房裡,必不肯出來。張書辦媳婦子發話說:小的們因他漢子不在家,乘空子看他老婆哩。」縣公問說:「這施氏是怎麼的?」于桂稟說:「這施氏是個娼婦,名叫小珍哥,從良嫁了晁鄉宦的公子晁監生。誣枉他嫡妻與僧道有姦,逼得嫡妻吊死了,問成絞罪。九年前女監裡失火,說是燒死了,如今撞見了這婦人通是他。小的們一個錯認罷了,沒得小的們四五個人都眼離了不成?」縣公問說:「那時燒死了,有屍沒有?」于桂說:「有屍。」縣公說:「屍放了幾日纔領出去?只怕屍領得早,到外邊又活了。」于桂道:「若是那個屍,沒有活的理。燒得通成灰了。」縣官問:「屍後來怎麼下落了?」于桂說:「晁鄉宦家領出去埋了。」縣官說:「晁鄉宦家見燒得這等,也不認得了。││叫張壽山來!」同房說:「他今日不曾來。」
縣官拔了兩枝籤,差了兩名快手,從院裡娼婦家尋得他來。快手也只說縣官叫他,不曾說因此事。張瑞風來到,縣官問說:「晁監生的妾小珍哥說是燒死了,如何現在你家?」張瑞風神色俱變,語言恍惚,左看右看,回說:「小珍哥燒殺了九年多了,沒得鬼在小的家裡?」縣官說:「奴才!你莫強辯!」差了于桂,叫拿了他來,叫張壽山跪在一旁伺候。待不多一會,將珍哥拿到。縣官問說:「這果然是小珍哥麼?」小珍哥不答應,只管看張壽山。張壽山說:「這是小的臨清娶的妾,姓李,怎是小珍哥?這人模樣相似的也多,就果真是小珍哥,這又過了九年,沒得還沒改了模樣?就認得這麼真?」于桂等眾人說道:「就只老相了些,模樣一些也沒改。」縣官教拿夾棍夾起。珍哥說:「你夾我怎麼呀?我說就是了。那年燒殺的不是我,是另一個老婆。我乘著失火,我就出去了。」縣官說:「你怎麼樣就得出去?」珍哥指著張瑞風道:「你只問他就是了。」
這縣官是個有見識的,只在珍哥口裡取了口辭,豈不真切?果被他哄了,叫上張瑞風審問。他支吾不說,套上夾棍,招稱:「九年前一個季典史,叫是季逢春,每日下監,見珍哥標緻,叫出他一個門館先生沈相公到監裡與小珍哥宿歇,又叫出一個家人媳婦到監服侍。一日,女監裡失了火,那家人媳婦燒殺了,小珍哥乘著救火人亂,季典史就乘空把他轉出去了,那燒殺的家人媳婦就頂了小珍哥的屍首,屍親領出去埋了。後來季典史沒了官回家,小珍哥不肯同去,留下小的家裡。這是實情。」小珍哥綽了張瑞風的口氣跟了回話,再不倒口。
縣官據了口辭,申了合干上司,行文到季典史原籍陝西寶雞縣,提取季典史並沈相公、燒死媳婦子的本夫。這季典吏家事極貧,年也甚老,哪有甚麼沈相公、家人娘子的夫主?本處官府追求不出,只得將季典史解到山東。季典史極力辯洗,經了多少問官,後經了一個本府軍聽同知纔問出真情,方與這季典史申了冤枉。審得張瑞風自從珍哥進監,他倚恃刑房書辦,垂涎珍哥姿色,便要謀姦。只因晁源見在,一懼晁源勢力,不敢下手;一因晁源餽送甚厚,不好負心。後晁源已死,又因晁源家人晁住時常進監與珍哥姦宿,張瑞風將晁住挾制毆打,將珍哥上匣凌虐,珍哥隨與張瑞風通姦情厚。珍哥在監內,晁源在日原有兩個丫頭並晁住媳婦在監服侍;晁源死了,晁源母晁宜人將丫頭媳婦俱叫出監去。張瑞風隨買了一個算卦的程捉鱉老婆在內與珍哥支使,買通了監裡的禁子劉思長、吳秀、何鯨,哄得程捉鱉老婆喫醉了酒,睡熟在珍哥炕上,放起火來將程捉鱉老婆燒死在內。珍哥戴了帽子,穿了坐馬,著了快鞋,張瑞風和三個禁子做了一路,羽翼了珍哥,乘著救火走出,藏在張瑞風家內。張瑞風要瞞人耳目,故意往臨清走了一遭,只說娶了一個妾。報了珍哥燒死,屍親領出葬埋。天網不疏,致被捉獲。申明了上司。
季典史完得官司,因年老辛苦,又缺盤費,又少人服侍,衣食不敷,得病身死。還虧了幾個舊時衙役攢了幾兩銀子與他盛歛,送了他棺木還鄉。張瑞風問了斬罪,三個禁子都問了徒罪,程捉鱉坐了知情,也問了絞罪。由縣解府,由府解道,張瑞風和珍哥各人六十板,程捉鱉和三個禁子每人四十板。過了兩日,張瑞風棒血攻心死了。又過了一日,程捉鱉也死了。
那日珍哥打得只剩了一口油氣,萬無生理,誰知他過了一月,復舊如初。晁夫人聞知此事,不勝駭異,也絕沒人去管他。有人叫晁夫人把程捉鱉的老婆掘了出來,晁夫人道:「人家多有捨義塚捨棺木的,既是埋了,況又不在自己地內,掘他怎麼?」珍哥這事傳了開去,做了山東的一件奇聞。珍哥此番入監,晁家斷了供給,張瑞風又被打死,只得仰給囚糧,苟延殘命,衣服藍縷,形容枯槁。誰知這八百兩銀子聘的美人,狼籍得也只和尋常囚犯一般!
第二年,按院按臨本縣,報了文冊,臨期送審。珍哥身邊一文也無,又沒有了往時的姿色可以動人憐愛,這路上的飯食頭口何以支持?審錄必定要打,打了如何將養?把一個生龍活虎倚了家主欺凌嫡室的心性也消磨得盡淨。無計可施,只得央了一個禁子走到晁家門上,尋見了晁鳳,叫他轉央晁夫人看晁源的情分,著個人照管審錄。晁夫人道:「我也只說這塊臭肉天老爺已是消滅了,誰想過了這麼幾年,重新又鑽出來臭這世界!我不往家裡攬這堆臭屎!我已是給他出過殯埋過他了,他又出世待怎麼!誰去照管他!晁鳳,你要房錢去,湊二兩銀子你送給他,叫他拿著來回盤纏。你再問他:『這往後也過不出好日子來了,還活著指望甚麼呢?乘著有奶奶,只怕還有人裝裹你;若再沒了奶奶,誰還認得你哩?這去審錄,說甚麼不打囚五十板子,這是活著好麼?』」
晁鳳問住房子的人家要了二兩銀,到了監裡,見了珍哥。穿著一條半新不舊的藍布褲,白布膝褲子,像地皮似的兩根泥條裹腳,青布鞋,上穿著一領藍補丁小布衫,黃瘦的臉,蓬著頭,見了晁鳳,哭得不知怎麼樣的,說:「我待怎麼?可也看死的你大爺分上!奶奶就下得這麼狠,通也就不理我一理兒!」晁鳳說:「你別怪奶奶。你幹出甚麼好事替奶奶掛牌匾哩?指望奶奶理你?那年燒殺的說是你,奶奶買的杉木合的材,買的墳地,請了僧人念的經,二叔還持服領齋。誰想都便宜了別人,後來又鑽出這麼等的!這是二兩銀子,奶奶叫送與你來回盤纏。奶奶說,往後的日子也沒有甚麼好過的了,叫你自己想哩。」
珍哥接了銀子只是哭,又問:「晁住這賊忘恩負義的強人在哪裡哩?」晁鳳說:「管墳上莊子的不是他麼?喫得像個肥賊是的。」珍哥哭著罵道:「我待不見那忘八羔子哩!事到其間,我也不昧陰了。你大爺在日我就和他好,如今就一點情分兒也沒了,影兒也不來傍傍!怕牢瘟染上他呀!」晁鳳道:「你可別怪他。從那一年惹了禍出來,奶奶說過,他再到這監裡來,奶奶待擰折他腿哩!」珍哥說:「他就這麼聽奶奶說?奶奶就每日的跟著他哩?你替我上覆奶奶,你說我只沒得甚麼補報奶奶,明日不發解,後日準起解呀,要是審錄打不殺回來,這天漸漸的冷上來了,是百的望奶奶扎括扎括我的衣裳,好歹只看著你大爺分上罷!」晁鳳長吁口氣道:「我說可只是你也看看大爺的分上纔好哩!」珍哥說:「我怎麼不看大爺的分上?」晁鳳說:「你坐監坐牢的已是不看分上了,又在監裡養漢,又弄出這麼事來,你親口說養著晁住哩!這是你看分上呀?」珍哥道:「這倒無傷。誰家娶娼的有不養漢的來?」晁鳳到家,回了前後的話。
果然次日武城縣將監內重囚逐名解出。小珍哥有了這二兩銀子,再搭上這隨身的寶貨,輕省到了東昌,伺候按院審錄。長解與他算計,把查盤推官的皂隸都使了銀子,批打時,好叫他用情。不料按院審到珍哥跟前,二目暴睜,雙眉直豎,把幾根黃鬚扎煞起來,用驚堂木在案上拍了兩下,怪聲叫道:「怎麼天下有這等尤物!還要留他!」拔下八枝籤,拿到丹墀下面,鴛鴦大板共是四十,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汪洋,只剩一口微氣。原差背了出來,與他貼了膏藥,僱了人夫,使門板抬了他回去。離縣還有五里,珍哥惡血攻心,發昏致命,頃刻身亡。差人稟了縣官,差捕衙相驗明白,取了無礙回文,准令屍親領葬。晁夫人聞知,差了晁鳳、晁書依還抬到真空寺裡,仍借了僧房,與他做衣裳和棺木,念經發送,埋在程捉鱉老婆身旁。
卻說珍哥自從晁源買到家中,前後裡外整整作業了一十四年,方纔這塊臭痞割得乾淨。可見為人切忌不可取那娼婦,不止喪了家私,還要污了名節,遺害無窮。晁源只知道挺了腳不管去了,還虧不盡送在這等一個嚴密所在,還作的那業無所不為。若不是天公收捕了他去,還不知作出甚麼稀奇古怪事來!真正:
醜是家中寶,俊得惹煩惱;再要娶娼根,必定做八老。
這晁源與珍哥的公案至此方休,後面再無別說。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醒世姻緣傳(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198 |
章回小說 |
$ 220 |
中國古典文學 |
$ 220 |
中國古典文學 |
$ 221 |
小說/文學 |
$ 225 |
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醒世姻緣傳(下)
《醒世姻緣傳》又名《惡姻緣》,是明末清初小說,共100回。作者以婚姻問題為題材,以因果報應的方式,用山東方言寫成,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由於作者觀察細緻,把社會各階級各色人物、官場和家庭生活,惟妙惟肖地如實刻繪出來,各具體態,在輕描淡寫之中,顯得詼諧幽默。
章節試閱
第五十一回 程犯人釜魚漏網 施囚婦狡兔投羅
天地寥寥闊,江湖蕩蕩空,乾坤廣大盡包容。定盤打算,只不漏奸雄。 殺人番脫底,漁色巧成凶,安排凡事聽天公。要分孽鏡,情法果曾同!
右調〈南柯子〉
再說武城縣裡有一人,姓程,名謨,排行第三,原是市井人氏。弟兄六個,程大、程二俱早年亡故,只剩弟兄四人。獨程謨身長八尺,面大身肥,洗補網巾為業,兼做些鼠竊狗盜的營生,為人甚有義氣。他那竊取人家物件,也不甚麼瞞人。人有可惜他的,不與他一般見識;有怕他凶惡的,又不敢觸他的凶鋒。大酒塊肉,遇著有錢就買,沒錢就賒,賒買...
天地寥寥闊,江湖蕩蕩空,乾坤廣大盡包容。定盤打算,只不漏奸雄。 殺人番脫底,漁色巧成凶,安排凡事聽天公。要分孽鏡,情法果曾同!
右調〈南柯子〉
再說武城縣裡有一人,姓程,名謨,排行第三,原是市井人氏。弟兄六個,程大、程二俱早年亡故,只剩弟兄四人。獨程謨身長八尺,面大身肥,洗補網巾為業,兼做些鼠竊狗盜的營生,為人甚有義氣。他那竊取人家物件,也不甚麼瞞人。人有可惜他的,不與他一般見識;有怕他凶惡的,又不敢觸他的凶鋒。大酒塊肉,遇著有錢就買,沒錢就賒,賒買...
»看全部
作者序
序言 五倫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夫婦處其中,俱應合重。但從古至今,能得幾個忠臣,能得幾個孝子,又能得幾個相敬相愛的兄弟,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倒只恩恩愛愛的夫妻比比皆是。約那不做忠臣,不做孝子,成不得好兄弟,做不來好朋友,都為溺在夫婦一倫去了!夫人之精神從兩用,夫婦情深,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的身上自然義短。把這幾倫的全副精神都移在閨房之內,夫婦之私,從那娘子們手中博換得還些恩愛,下些溫存,放些體貼,如此折了剛腸,成了繞指,這也是不枉了受他的享用,也不枉喪了自己的人品。可怪有一等人,攢了四處的...
»看全部
目錄
本書目次 下 冊
第五十一回 程犯人釜魚漏網 施囚婦狡兔投羅
第五十二回 名御史旌賢風世 悍妒婦恬惡乖倫
第五十三回 欺絕戶本婦盜財 逞英雄遭人綑打
第五十四回 狄生客中遇賢主 天爺秋裡殛凶人
第五十五回 狄員外饔餐食店 童奶奶慫恿庖人
第五十六回 狄員外納妾代庖 薛素姐毆夫生氣
第五十七回 孤兒將死遇恩人 凶老禱神逢惡報
第五十八回 多心婦屬垣著耳 淡嘴漢圈眼遊營
第五十九回 孝女于歸全四德 悍妻逞毒害雙親
第六十回 相妗子痛打甥婦 薛素姐監禁夫君
第六十一回 狄希陳飛星算命 鄧蒲風設計誆財
第...
第五十一回 程犯人釜魚漏網 施囚婦狡兔投羅
第五十二回 名御史旌賢風世 悍妒婦恬惡乖倫
第五十三回 欺絕戶本婦盜財 逞英雄遭人綑打
第五十四回 狄生客中遇賢主 天爺秋裡殛凶人
第五十五回 狄員外饔餐食店 童奶奶慫恿庖人
第五十六回 狄員外納妾代庖 薛素姐毆夫生氣
第五十七回 孤兒將死遇恩人 凶老禱神逢惡報
第五十八回 多心婦屬垣著耳 淡嘴漢圈眼遊營
第五十九回 孝女于歸全四德 悍妻逞毒害雙親
第六十回 相妗子痛打甥婦 薛素姐監禁夫君
第六十一回 狄希陳飛星算命 鄧蒲風設計誆財
第...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清)西周生
- 出版社: 台灣書房 出版日期:2012-03-20 ISBN/ISSN:978986631865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512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中國古典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