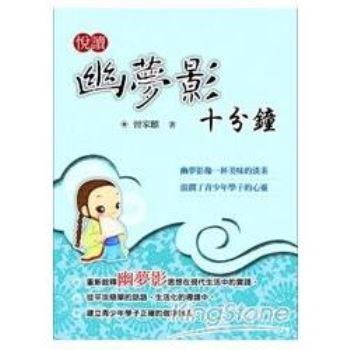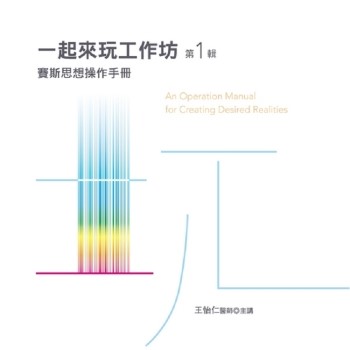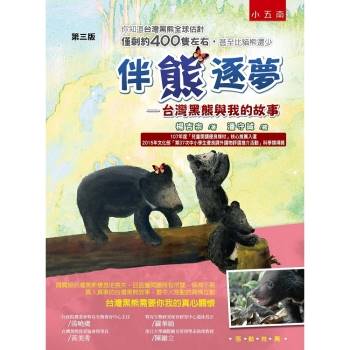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2012倫敦藝術獎(London Awards for Arts and Performance)最佳書籍決選入圍
★英國藝術文化委員會評為年度「最不該被忽視的小說」,讀者五顆星感動推薦!
★寫作才華媲美莎拉.華特斯和《蝴蝶夢》作者杜茉莉
★作家鍾文音 感動推薦
盛夏中變調的田園詩
慾望之前,有沒有純粹的證明?
一部關於愛,關於人性,關於「我是誰」的故事。
劍橋大學博士生史賓塞.李妥相信數學,相信它的恆久與純粹。在一九七六年不尋常的酷暑中,他隻身騎著單車來到陌生的山間農村,帶著一道攸關前途的未解證明。他用幫忙農活交換食宿,在一間農場寄住了下來。這個外來者言行拘謹,一被問話就緊張得結巴,不過還算是個好工人。村民無不納悶:堂堂的劍橋數學家,為什麼要來這窮鄉僻壤堆石牆、剪羊毛?
農場主人的女兒愛麗絲很快就與史賓塞親近起來,小女孩的純真友誼漸漸令他敞開心房,頻繁的農事鍛鍊也讓他煥然一新。然而,就在史賓塞漸漸融入農村,生平第一次彷彿找到歸屬的時候,深藏的祕密卻如土壤底層悶燒已久的火焰,揭開便一發不可收拾。在灼人的熱浪中,淳樸的田園似乎藏著晦暗,信任可以在流言蜚語中一夕崩壞,史賓塞覺得自己好像離解答愈來愈遠了……最終,他要證明的又是什麼?
這是一個關於愛,關於人性,關於「我是誰」的故事。作者優雅內斂的文字、看似簡單的安排,織就了最幽沉的扣問,最進退兩難的驗證。
作者簡介
凱瑟琳.霍爾(Catherine Hall)
一九七三年生於英國湖區。曾從事紀錄片製作,後成為自由投稿作家,並為人權及發展組織擔任編輯。她的第一本小說《我的愛,說不出口……》深受萬千讀者喜愛,並被讚譽為兼具莎拉.華特斯(Sarah Waters)和《蝴蝶夢》作者戴芙妮.杜茉莉(Daphne du Maurier)二人特長的作品。本書是她的第二本成功的小說。
譯者簡介
張琰
台大哲學系畢,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現為專業譯者。譯作領域廣泛,有《比利時的哀愁》、《西班牙情人》、《穿風信子藍的少女》、《愛情的盡頭》、《賈斯潘王子》、《萬物的尺度》、《蝴蝶法則》、《蜂鳥的女兒》、《12號公路女孩》、《悲喜邊緣的旅館》、《最後手稿》、《茱麗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