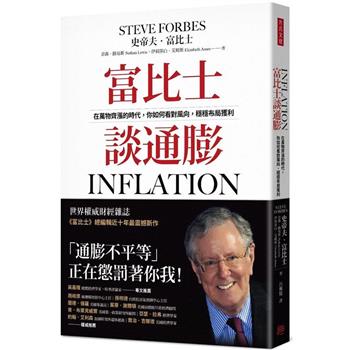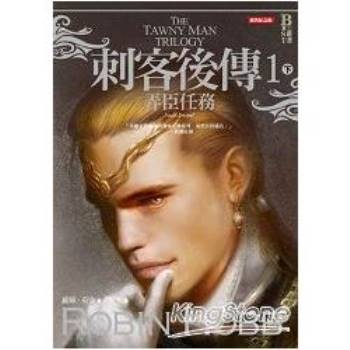記憶決定我是誰!
一趟驚奇的老年失智旅程,一齣勇敢的黑色幽默劇!
讓我們從中思考生而為人的意義……
本書榮獲亞馬遜網路書店 五顆星評價
2009年英國維康信託書獎 (Wellcome Trust Book Prize)
2010年歐威爾獎 (Orwell Prize)
數年前,身為作家及三個孩子的母親,安卓亞.吉利斯開始了一段苦悶的旅程──成為婆婆南絲的家庭看護。南絲罹患了阿茲海默症,已踏入中期階段。由於家庭人數擴增,她們舉家搬牽到寒冷的蘇格蘭北方,住進懸崖邊一棟維多利亞式大莊園。原本意欲尋求大自然的慰藉、激發小說的靈感,卻弄得一身灰頭土臉。南絲的病情也因遷移而惡化,從理性世界游離,進入失智的混沌現實之中。
本書是作者在冷冷荒野中一長串苦澀的生活日記,她一點一滴記錄南絲病情的每下愈況、所漸次遺失的能力,穿插業餘慧黠的調查與思考,深入揭發阿茲海默症進犯大腦的步步軌跡,不僅吐露照護阿茲海默症病人的心路歷程,更進一步探索人類大腦與意識組成,最後更碰觸到關於本我、靈魂以及「記憶決定了我們是誰」的核心問題。對於身處在此情境之中的家庭,這本書所提供的學習與領悟,將超過你所能想像!
本書特色
*失智症即將成為全球人口老化後的一個最重要的公共衛生與社會議題。目前據估算全世界有超過三千五百萬人患有失智症,而且這個數字每二十年就會增加一倍。由於失智症是一個殘酷而冗長的疾病,在患者接受失智症診斷後會有八到十年的漫長照護歷程,許多失智症照護者的故事都是血淚交織而成的。全世界的狀況都一樣:約七成以上的失智症患者都是在家中接受照料,其中六、七成以上都是由單一的照護者來擔負此一重任,而且絕大多數都是無酬的家庭照護者。他們直接承受著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與患者面對面無可躲藏、無法逃避的壓力,因此在照顧的工作上經常是充滿指責、爭吵而事倍功半、徒勞無功最後飽受挫折,甚至逃避面對照護的工作。《記憶的照護者》(Keeper)這本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產生。
*作者安卓亞.吉利斯以深厚的寫作功力,樸實幽默的筆觸,深刻記錄婆婆南絲罹患阿茲海默症的發病軌跡以及她個人的照護心路歷程,同時更整理了許多豐富的阿茲海默症相關神經科學資料,讓這本書兼具了優美浪漫的文學性與科學知識性。英文版問世之後即於2009年拿下英國維康信託書獎 (Wellcome Trust Book Prize),2010年更榮獲以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為名、特別設立獎勵「文學中的醫學」(medicine in literature)的歐威爾獎(Orwell Prize),獲得文學界、新聞界、醫學界一致的感動與好評!
*面對「失智世紀炸彈」(Dementia Time Bomb),我們將如何因應?不管您是失智症患者家屬、照護者、衛生福利政策的制定者、執行者或者醫護專業人員,這都是一本萬萬不能錯過的深刻好書,值得向所有關心失智症的朋友們誠摯推薦!
*生命潛能文化事業2011年度巨獻,生命學堂系列新書,全書內文再生紙印製,與您共同守護美麗地球、珍惜每一個生命!
作者簡介
安卓亞.吉利斯 (Andrea Gillies)(預留作者照片位置)
現居住於北蘇格蘭,從事寫作、文宣工作、旅行與參考書籍編輯,並為報紙撰寫專欄。二○○九年以《記憶的照護者》獲得獎金高達兩萬五千英鎊的維康信託獎(the Wellcome Trust Prize,此獎頒發給當年度關於健康或醫學傑出小說或非小說)。二○一○年更榮獲以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命名的歐威爾獎(Orwell Prize)。二○一一年百老匯出版社出版美國版。
譯者簡介
許桂綿
曾任出版社人文類叢書編輯,紐約佩斯大學出版研究所研究,譯有《樹的療癒能量》、《印加靈魂復元療法》、《印加大夢》、《雨林藥草居家療方》、《通靈工作坊》、《把孩子的快樂找回來》、《與慈悲的宇宙連結》、《男女大不同:職場輕鬆溝通》(合譯)等書(均由生命潛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