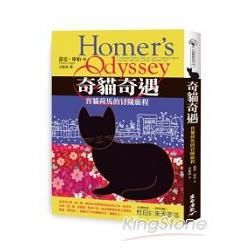名人推薦:
推薦序——苦難是能源活水
杜白
動物的世界是沒有邏輯的,牠們不會線性思考,牠們用圖像來連結,沉穩的過著每一個當下。
你問家裡的小狗小貓:「嘿!小伙子,你今天過得好不好?」牠們一定猛搖尾巴表示好,因為牠只抓得住你說的最後一個字──好。
牠們以生物本能的嘗試錯誤來學習成長,建立自己的資料庫,全部皆為是非題,是非、善惡、好壞、安危,沒有模糊的灰色地帶。
幾乎所有的狗都怕打雷,因為在牠們古老的記憶裡,轟天巨響使牠們從沉睡中驚醒,接下來就是傾盆大雨,淋得牠們又濕又冷,所以打雷等同於惡魔,生生世世永不忘懷。
貓害怕閃電、巨響與突然出現的物體。因為閃電之後就會轟隆巨響,巨響之後就會有啪哩啪啦的大雨,大雨中熟悉的世界頓然消失。
如果你懷著戲謔的心,在貓的面前,突然把傘撐開,牠們受到驚嚇之餘,一定會罵你:變態!
然而夜魔俠的盲眼貓荷馬,卻失掉了圖像連結的思考模式,這回造物者開的玩笑似乎太大些。
所幸,這個小小的失手之後,卻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牠免於被安樂死,找到手頭拮据、對牠卻又一見痴心的媽。
生命裡有無限的發展可能,需要的正是機運。對於荷馬這個病例,我的猜想如下:雖然眼珠子被摘除,卻還殘留許多視神經。就像有些人被摘除半邊大腦,留下的半邊居然可以發展成全大腦的功能。神經細胞是非常珍貴的,或許荷馬永不服輸的大腦就把這些殘存的視神經加工成為雷達或聲納系統,使得荷馬成為貓界中的蝙蝠,稍做探索練習,就可在熟悉而穩定的空間裡飛簷走壁,暢行無阻。
對於荷馬的本事,我絲毫不驚訝,只有佩服,佩服牠理直氣壯的活著。
狗貓有太多的特異功能,是人類無法全然理解的。
狗貓完全聽得懂我們說什麼,而我們卻不太懂牠們說什麼。我們總是對於牠們的心靈世界,充滿無限好奇。所有動物都用心靈來溝通,不若人類有不同語言的隔閡。時下國內外,就有許多動物溝通者,可以來滿足我們人類的偷窺慾。他(她)們其實就像一支智慧型手機,可以接收宇宙間密密麻麻經過設定的訊號。而所有動物包括人類生來就是一支智慧型手機,我們都是電力飽滿的生下來。長久以來總是小心的保持它外形亮麗,卻忘了幫它充電,當然就不通了。
葛雯‧庫柏小姐,因為收養荷馬而漸漸改善了她的人生,這種事例不勝枚舉,本來牠們就是造物者派來的助手。然而牠居然能像盲劍客一般擊退來犯的竊賊。這等本事實在罕見,也難怪被視為英雄。其實他們都是彼此的英雄,因為九一一的悲劇就發生在家附近。已經被迫撤離災區的庫柏小姐,千辛萬苦灰頭土臉,感動軍警放行,終於得以回來一家團聚。我深信荷馬這三口,至始都堅信主人必定會回來,因為她是牠們唯一的親人。
我們喜歡叫狗貓心肝寶貝,牠們又如何界定我們呢?既是衣食父母、食物主要來源、家人、又是佣人、寵物。不管是那一個,都是牠們所僅有,我們就是牠們的全世界。
貓願意接近人類,不只為了好奇、討好、打招呼。當牠跳上你的大腿上,或是擠進你的被窩裡,那是全然的信任。被牠們信任,那是無比的榮耀。情人、夫妻、手足、子女之間都比不上,因為我們不全懂牠們的心靈,牠們卻願意如此的付託,牠們給我們的愛,是沒有絲毫雜質的。
最近,導盲犬界的退役老兵歐哈拉(Ohara),透過動物溝通師說,牠很想來找我,溝通師很疑惑的回問牠現在的媽媽:「你說杜醫師?可是牠卻叫他『老杜』?」
當下,比中了樂透還爽!
推薦序——我愛貓
朱天衣
我終於有機會可以大聲說:「我愛貓!」
自許為動保義工以來,我一直提醒自己,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每一個生命都該被同等珍愛,但我心底深處清楚知道,貓族是我的罩門,營救狗及其他動物時是不忍、是責任,而遇見貓,則是上天給我的禮物。
和狗狗相處很直接、簡單,就像和男孩子共事一般,直來直往、不需多費心思;而貓族就像女孩般細膩,需要溫柔對待、小心呵護,所以我常以狗兒貓女稱呼身邊的動物同伴們。
所謂的溫柔呵護,倒不是指要耗費多大氣力,多半時候照顧貓要比狗省事許多,尤其在都會裡,光是蹓狗及犬吠聲,便足以讓你和鄰居有扯不清的糾葛;而貓,只要為牠準備一個貓砂盆,一個安全的室內空間就可以了,而且如果你太忙碌,沒時間陪伴自己的同伴動物,那麼頗能自處的貓族比較不會讓人心生罪惡感,你不必整天焦慮於家裡有個殷殷期盼你歸來的狗兒,狗族對人的倚賴,有時是可滿足人的成就感,但同時它也會是個負擔。
當然說這麼多,並不是鼓勵大家養貓不養狗,我反而想呼籲,狗兒是更需要人照看、更需要人認養的,因為現代的狗已沒有自主謀生的能力,不管在都會、郊區,甚至山野,已沒有獵物打食,牠們完全要靠人們餵食,或撿拾人們的殘羹剩餚,所以狗兒們是必須仰賴人才能生存的。
而貓族體形小,靠著狩獵來的老鼠、蜥蜴,或各式昆蟲便可填飽肚子(我便曾撿過流浪貓,在牠的糞便中發現一堆蚱蜢腿),所以相對來說,貓真的不至於到沒有人就存活不下去(幼貓除外)。因此,我們是否發現,當貓族並不需要幫助,卻又願意和人建立關係時,那不是更值得珍重?你曾想過牠要的是什麼嗎?我一再強調貓族的獨立自主,並不是要大家漠視牠們真正的需求,雖然當我們忽略這一部分時,貓女們仍能依牠的方式繼續存活,但損失的會是你,因為你將錯過一場與貓族細膩交心的機緣,那真的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事。
所以當我們回到《奇貓奇遇》時,你就會理解作者葛雯.庫柏花了這麼多筆墨寫下盲眼荷馬貓的故事,不是喃喃囈語,而是一段自我深層的探索,因為唯有你沉靜下來、柔軟下來,才可能進入貓族的世界,這與耙梳自己的心靈狀態是如此相似,也和進入寫作情境是如此雷同,所以當你願意和貓族深情相待時,你會打開生命的另一扇門,這門會通往哪兒、會經驗什麼樣的事,唯有親臨才會知曉。
狗兒對人的信賴,是把自己完全敞露在你面前:「看!我就是這個樣子,我就是這樣全心全意愛著你!」而貓女呢?也許多半時候,牠會盤踞在某個高點,冷冷地看著你:「你確定要愛我嗎?你不需要先了解我嗎?等你好好想清楚再決定吧!」貓族不是不在乎你的感情,也許她比狗兒更在乎,但她要的不是施捨,她要的是平等對待、她要的是更深層的心靈相通,她要的太多了,連自己都知道很難達到,以致於她只能冷漠以待。
當然我所說的是通例,如果你和貓女結緣是在牠幼兒期,在牠「人格」尚未定型前,那情況會不同,因為在這之中參雜了母親的角色,但若是在她成年後才相遇,那麼你一定要花更多的時間與心力,才能搏得她的認可,如葛雯的丈夫羅倫斯,和每一位貓女發展出不盡相同的情誼。
在我身邊也一直保持著近二十位貓女,牠們有的黏人黏得緊,隨時監控著你的舉動,一見稍有空檔,便會挨近身邊要你抱抱;也有的離群索居,一日三餐必要像玩躲貓貓似的,讓你尋遍每個角落抱她回來用餐,如果適值烈日或暴雨,我便會嘟嚷:「你真是不孝順,快把我弄到腦充血了。」還有的是連我都摸不到,永遠藏在貓屋為她準備的角落裡,八年了,我也只能尊重她的堅持。
面對這些吃同樣食糧卻養出百種性情的貓女們,我從沒覺得煩厭過,因為我永遠珍惜牠們的選擇,牠們可以不必、卻選擇了和我共度此生,牠們表達感情的方式是如此含蓄,有時幽微到難以辨識,但我始終知道,也會牢牢記住,牠們是這樣或長或短深情地走入我的生命。
序曲──擁抱人生的小貓咪
「告訴我,哦!繆思女神!
我想知道那位英雄的故事,他是多麼敏智巧謀,
他已飄泊遠行,闊拓見聞……」──〈奧德賽〉荷馬
我每一天忙完的時候,總是循著相同的路線回家。
「噹!」電梯聲響會先傳進那雙敏銳的耳朵,預告著我即將出現。直到手裡的鑰匙撞擊著家門的鎖孔時,我會聽見門的另一頭傳來爪子輕拍聲。我發現自己打開任何一扇門的時候──即便是其他人家的門,都會謹慎注意著別讓可能冒出來的毛球小惡魔一時翻滾至門外。那些爪子可不只是在地上探索,一秒鐘就能從門後直撲我的雙腳。一隻小黑貓全心撲上我的身體,像是踩著狐步舞(一種爵士舞)步伐攀上樹幹一樣。
他的爪子踩踏雖輕,但很尖銳的,我不想自己的衣服損壞,甚至透過去傷到底下的皮膚,因此會蹲下並愉快地先說:「嗨,荷馬小熊」(這是我在他還是隻小小貓時就取的暱稱;著眼於他那一身光澤烏黑、看似灰熊披掛全身的毛皮)。荷馬把我的動作視為默許,就跳上我的膝蓋,把他的前爪放在我的肩頭,再用他的鼻頭磨蹭我的鼻子,同時發出滿足的喵叫。那一連串短促、清脆的喵叫,聽來不比尋常,像極了小狗的尖叫聲。「嘿,小傢伙。」我說時,還搔揉著他的耳後。這令荷馬豁然開懷,當下不再滿足於只是鼻頭磨蹭,而是將自己的整張臉都貼上我的前額,再滑順至我的臉頰,然後如此上下廝磨。
不過,我如此盤蹲在常穿的高跟鞋上(因為我身高只有一百五十二公分,卻拒絕過矮子的生活),要忍受的不舒服感可比它的高度看來更驚人,所以我會抱起荷馬,再將他放在地上,然後起身進入我和丈夫勞倫斯同住的公寓。鑰匙、外套和包包都很快地歸回原位。如果你的家裡有三隻貓,要避免外出服沾滿貓毛的方法,就是習慣一回到家,立即換上家居服。因此,我馬上走進臥室,迅速換裝。
與此同時間,會有一團毛球黑影追尋我的腳步穿梭公寓,沿路跳躍著途經的個個家具。是荷馬。他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從地板起跳至椅子而後餐桌,再跳回地板,就像手機遊戲「小精靈跳方塊」加速版那樣。當我從客廳兼餐廳區進到了走廊時,荷馬會跳上邊桌頂端,不假思索就一躍斜穿過走廊,跳到書櫃的第三層,隨後稍停下來全神貫注等著,直到我穿越走廊而過。接著,他會往下跳到地板上,走在我前頭忽左忽右地前行;興致一來,他偶爾還會活繃地撲向我養的另外兩隻貓,直到他抵達通往臥室的門口。每一次他都準確地停留在相同的地點,但在短促得幾乎令人難以察覺之際,馬上又向左急轉穿越臥室,畫出一個無形的大寫L字。這時,他再跳上床鋪的頂端,因為我會坐在那裡脫鞋子,然後他會要爬上我的大腿,再來一次滿足的嗚喵呼嚕叫和雙頰廝磨。
這樣的行徑日復一日。唯一有所變化的是,當我換裝完,他開始仔細勘查公寓的路線。荷馬這個小動物,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嗜好。我們很難知道他每個星期會決定什麼新的計畫。
有一陣子,他的目標似乎是想要創世界紀錄,看看自己一天之內能夠從茶几上推下多少東西。勞倫斯和我都是作家,所以我們有著典型的作家起居環境:筆、便條紙、潦草手寫的紙片,再混雜著雜誌、平裝書、面紙盒、票根、墨鏡、火柴盒、口氣芳香錠、遙控器和外賣選菜單。某天當我們回家時,發現家裡茶几上所有的東西都被掃得一乾二淨,那些書、筆、遙控器……全都零亂地散落在地上,好似傑克遜.波洛(Jakson Pollock)的抽象派油畫作品。我們將東西一一歸位,還帶著一點愧疚的神色,覺得原本也該是時候整理那些雜堆。這行徑持續好幾個星期。我們不確定是哪一隻貓成為家裡的魅影清潔員。有一天晚上,我回家時逮到荷馬躁動不安,為著自己的成就興奮得抖動不已,毫無悔意,真相終於大白。
「或許他是在抗議那些雜物亂堆。」我向勞倫斯提議道,「隨處亂堆的雜物可能會混淆他。這樣他每次跳上桌子,桌面上的物件位置都變得不一樣。」
勞倫斯並不像我這樣,總是探求我們寵物心懷的動機。「我想,貓咪就是喜歡把東西推下桌。」這是他的答案。
我們還有一個因他而學的新習慣──隨手緊閉家裡衣櫃的滑門。一旦你想到接下來的畫面,保持這個習慣就顯得輕鬆許多:有隻小貓可能會將全身的力量垂掛在牛仔褲的兩條褲管(丹寧布料是一種極具韌性的好布料,很適合攀爬),然後,他開始推爬著上到櫃櫥頂端。在那上面有裝著舊照片的盒子、從沒打開過的生日與節慶禮物,還有柔軟的衣服堆可以做他們舒服的小窩。他會抓扒著要打開那些個禮物的外包裝,再弄出些許沙沙聲,玩得不亦樂乎。無論垃圾桶有多高,他都能一躍跳進去,再將桶子往身子所在的那一邊傾倒。只要毅力足夠,他能將捲成直筒的海報抓扒開成平攤模樣。他還能攀登書架,去到盡己所能到的書架高處,再丟擲下精裝書。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我們視聽區堆疊的錄音帶、CD和DVD。只要想像力夠,你知道的,一隻小貓可以無止盡地依循我們平常上班日的活動行徑,發發無傷大雅的淘氣、搞些小破壞。如果說我能從荷馬身上學到什麼寶貴的人生課題,說真的,無非就是一個人該找些值得進行的計畫,填滿自己的時間。
差不多就在最近,荷馬已經學會使用馬桶。為什麼他到了十二歲的年紀,突然決定再成功多學會這招把戲,我也說不上來。我聽過貓咪經由主人的訓練後,能夠使用人類的廁所,而不是動物專用的貓砂盆,但是我還沒聽過貓咪是自己去學會這種特殊技巧的。
起初我是在意外間發現了他最近學會的這項成果。有天早上我起得早,跌跌撞撞地走進浴室。打開燈之後,我發現……那上面有個什麼東西,結果是荷馬幾近完美平衡地坐在馬桶座上?!
「啊,真是對不起。」我因睡眼矇矓而下意識地脫口說出。直到離開浴室、還體貼地關上身後的浴室門時,我才想到,等一下……
「……我們的貓咪是個天才!」那天稍後,我跟勞倫斯滔滔不絕說起這件事。
「若是他自己學會按沖水鈕,他就真是個天才!」勞倫斯回答著。
這倒是真的:沖水的技巧,仍是超乎荷馬的理解。因此,我已經將這件事放在心上,而檢查馬桶就成了我也會不時查看的另一項目。當我晚上回到家時,總會看看家裡是否有翻轉的畫框、被打開撬起的櫥櫃,或是打翻了的小擺飾,因為我從不知道自己走進家門時會看見什麼情形──因為見到荷馬,總會伴隨著在眼前出現料想不到的景象,那都是他不諳此道而一個人搞出來的;所以,對於初次造訪我家的訪客,我都會儘量事先給他們心理準備。自從我和勞倫斯開始交往而不再外出約會新的對象的這些年,我的年紀也老到新朋友愈行減少,也就愈來愈不需要再做這些事。
不過,我記得有一次,當我新認識的男性朋友首次進我家門時,我沒能事先提及此事,因為我也沒想過會邀請那次的約會對象到我家做客。等到我們說好去我家時,我覺得再來談家裡的那些貓咪,好像蠻殺風景的,怕那些浪漫氛圍會消逝無蹤。
那期間剛好是荷馬特別迷戀於玩衛生棉條的日子。有一次他意外遇上一個機會,從此就著迷於這個可以滾來滾去的東西,還有上頭尾端的拉線。他實在太愛這玩意兒了,先弄清楚我存放它們的地方在浴室洗臉盆底下的櫃子之後,以一貫的耐心和準確無誤的方式,熟練於強行打開櫃子的任務,進而掠取放棉條的盒子。
等約會那天,當我與那位約會對象一起走進家門時,荷馬跑到門口歡迎我。他當下嘴裡叼著的就是棉條;一身黑色皮毛映襯白色棉條,鮮明得特別惹人側目,讓我感到一陣羞赧。他東轉西跳一會兒,顯出得意洋洋的歡欣,再接著迅速飛跑,一臉期待地盤坐在我的面前,那棉條就掛在他的下巴上,好似小狗叼著一根玩具骨頭。我的那位約會對象看來是嚇得不住往後退,只能勉強支吾地擠出幾個字。「這……什麼……是……」他這樣結結巴巴了一會兒,最終好不容易鎮定下來,「你的貓發生什麼事了嗎?」
我半蹲下來,然後荷馬開心地爬上我的大腿,再把盜取來的棉條扔在我的腳前。「他很好,」我回答著,「他只是沒了眼睛而已。」
那位約會對象聽見這話,難以置信。「沒有眼睛?」他問著。
「說到這個,他生下來的時候是有一雙眼睛的,」我解釋道,「但是就在他還只是個小貓的時候,不得不摘除那雙眼珠。」
※※※
依據動物收容所的估計,全美國三千八百萬個家庭中,豢養了約莫九千萬隻的貓咪;因而就某方面來說,荷馬是隻再普通不過的貓。他吃食、睡覺、把紙張弄皺成團球,還有半數的時間,他惹上的麻煩可比我制止他的多。除此之外,他就像任何一隻其他的貓咪,相當固執於什麼是他喜歡的、什麼又是他不喜歡的。在荷馬的世界裡,所謂的喜歡就是從罐頭裡倒出的新鮮鮪魚、攀爬任何能支撐他重量的物件、故作凶猛姿態地衝向他那兩位毫不知情的同伴姊妹(而且她們的體型都還大他許多許多唷);還有,趁著夕陽西下之前,在客廳裡陽光灑落的一隅打盹。至於不喜歡的就是,在所有家裡的貓咪中,最後才擠上「媽咪」身旁的沙發位置;貓砂盆沒有即刻清乾淨;被嚴拒進出我們公寓的陽台(一隻盲眼貓外加高台──想也知道會發生什麼意外),以及「不可以」這個詞。
只是,在我的心中,荷馬遠比現實生活中所表現的更顯不凡。我時常覺得,他的故事只能用史詩般的壯偉字眼來表述。他這隻貓的一生是──無父無母、小小年紀(出生兩個禮拜)就病重得摘除雙眼才能存活下來的挨餓流浪貓、確定能度過難關、恢復健康以後卻又無人認領回家。他是電影裡的「夜魔俠」、漫畫裡的「鋼鐵俠」那種等級的超級英雄。鋼鐵俠為了救一名盲人,意外中自己也失明了,但同時他獲得其他感官的超能力。荷馬也像夜魔俠,聽覺和嗅覺、還有僅在陌生房間內走動過一次即可搜索並成功越過所有障礙的能力,簡直是不可思議。
他可以嗅聞到三個房間以外的一小片鮪魚、可以騰空跳上約一公尺半,還能抓到飛舞中嗡嗡叫的蒼蠅。每次從椅背跳躍至桌上都毫不猶豫,那可是一不小心就會跌落深淵。每當他在走廊上追著球跑,很明顯都是勇敢之舉。只要他攀爬窗簾或是櫥櫃頂端、與新朋友首次相互熟悉、在看不見又無人可指引的周遭世界往前踏出一步……那都是勇往直前、無所畏懼的一個奇蹟。荷馬沒有導盲犬、沒有手杖,更無法用言語來確認眼前的事物外形與類別。我家的其他貓咪能夠看見窗外的景象,知道自己居所世界的範圍。但相對的,荷馬的世界是無邊無際,最終就是不可知的;他所身處的任何一個房間,就是一個世界,所以,他的世界等於是無可限量。他只很短暫地認知過時間與空間,因此,他的世界不受兩者所限。
一開始,荷馬會來我家是因為沒人要領養他。所以,我一直很訝異於那些第一次見到荷馬的人,甚至只是初次聽見關於他的事,就足以令人對他著迷,包括那些並不是特別喜歡貓的人。不論如何,他總是能成功變為話題引子。我最初領養他的時候,從未想過會有這種情形。想想那九千萬隻貓咪,代表著有九千萬個貓咪故事,然而,我家的貓咪在我心中永遠都是最特別與不凡的(即便這話聽來懷有偏見,讓人聽不下去)。在過去這十二年間,至少每個星期荷馬都會做出一件逗我開心的事、觸怒我的事,或是大出我驚奇的事……而他最令我意外的,莫過於我第一次透過別人的眼光再次重新看待他。
「哎唷,真可憐!」這通常就是人們一聽說荷馬在兩週年紀就摘除雙眼時所吐出的字眼。我會接著回應道:「只要你親眼見過荷馬,卻還能在這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角落,找到比他更快樂、更嬉鬧的貓,我就給你一百元美金。」然後,他們會問:「他要怎麼四處跑跳?」我就會回答:「用他的腳哇!就像任何一隻健康的貓一樣。」偶爾,荷馬特別熱衷於自己的玩耍時,我會聽到「碰」一聲!是他那小小的貓頭撞到了牆壁,或是忘記桌腳位置而碰撞上的聲音。這情景總是引得我發笑,但每次也會在那聲響的當下讓我的心涼了一半。我會笑出來是因為,若任何人目睹一隻貓在戲鬧得瘋癲中,往後仰倒沙發或是一頭衝向關閉的玻璃門時,都會忍不住咯咯地笑。然而我也會心痛,是因為樂觀來看,若是荷馬早一個星期被發現,他那雙受感染侵襲的眼睛,很可能就只是「嚴重感染」而非「無法治癒」。
但是當然,真要是這樣的話,荷馬也就根本不太可能進入我的生命中了。
※※※
踰越節是為了紀念上帝帶領摩西和以色列人離開埃及、脫離奴隸身分進入樂土。我慶祝這個節日時,最愛的是和大家一起雙腳舞踏,並大聲歡唱著「達因」之歌。「達因」這個字在希伯來文的意思是「我們已經滿足」。「達因」講的是上帝用以色列人為名所展現的種種奇蹟,同時堅信每當這樣一個奇蹟顯現於眾人面前後,「我們已經滿足」:如果上帝已經帶領我們出埃及,但沒有審判埃及人,「我們已經滿足」;如果上帝已經審判埃及人,但沒有為我們分開紅海,「我們已經滿足」;如果上帝已經為我們分開紅海,但沒有在沙漠中照顧我們的需求達四十年,「我們已經滿足」……
……如此推論下去。
過去十二年來,我都與荷馬一起生活,早已構築出自己的「達因」推論。如果荷馬已經能活過兩星期,「我心已經滿足」;如果荷馬就只能學會獨立找到自己的食缽和貓砂盆,「我心已經滿足」;如果荷馬就只能自我摸索到獨自在家裡穿梭於各個房間之間,「我心已經滿足」;如果荷馬最終學會如何跑、跳、玩耍和無懼於做出別人說他永遠做不到的事,「我心已經滿足」;如果荷馬只能陪伴我十個年頭,在這期間,每一天都逗得我開懷大笑,「我心已經滿足」。
此外,如果荷馬就只是我所知最忠誠、深情和勇敢的,並因此帶來歡欣、鼓舞人心……我想,這些都已經不只是「我心滿足」可以形容的了。
在看似失去希望的情況下,在任何明理的人都以為好事不可能來臨之時,卻還是莫名地出現了歡樂結局──也就是我們稱為奇蹟和美妙之事。我相信我們之中有為數不多的人,有幸能在日常生活中看見這樣的美妙之事。
正是這樣,這本書要獻給所有像我一樣的其他幸運者,同樣地,我也要獻給那些已經放棄相信奇蹟與英雄每天都會出現的人們;獻給愛貓人士,也獻給自認可以堅拒貓咪的人;獻給認為平凡與理想沒有差別的人,也獻給那些明白有時稍稍脫離所謂的「正常」其實能豐富自己生命的人。
我將荷馬──一隻奇蹟化身的貓的故事,獻給所有的人。
達因(我心已經滿足)!
媒體推薦:
〈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亞馬遜網路書店獨家專訪動物星球頻道〈貓咪一0一第二季〉特別報導全美知名媒體(〈今日美國〉、〈時人〉雜誌、〈多倫多太陽〉報、〈出版家〉週刊……)好評如潮
「感動人心……不可錯過。」 ──〈今日美國〉評價
「忍不住想讀完的一本書!」──〈多倫多太陽報〉評價
「溫暖人心,具娛樂性。」──〈時人〉雜誌寵物專頁報導佳評
「讀來令人歡心不已……可謂薇琪.麥蓉所著《圖書館裡的貓》後,另一部人貓之間的溫馨回憶錄,定能溫暖所有寵物愛好人士的內心。」──〈圖書館期刊〉紅星評價
「保證愛貓者一讀再讀!葛雯描述自己掙扎著職業進展與愛情生活的那部分,也能引發讀者的多方共鳴,譬如彷若《美味關係》中書所述二十多歲大女孩時期的回憶點滴;以及像是《馬利與我》關於各種與寵物相處磨合的故事,都可見於本書中。」──〈書單〉書評
「柔情又感人。」──〈出版家週刊〉佳評
「我很確定只要你認識了荷馬,很難不愛上他;書中的溫馨段落,也同樣能讓你感同身受。兩個不同族群的個體,有時也能產生獨特的連結。葛雯以她幽默、機智、坦率的文筆,寫出這隻超乎想像的小貓咪,必定能擄獲你心。」──《貓咪的九種情感生活》和《哭泣的大象》作者傑佛瑞‧麥森推薦
「故事生動、文采美妙,充滿柔情、真實的描寫……(與葛雯及荷馬)一起經歷這段人生,你的人生也將更為豐富。」──〈我愛貓〉雜誌佳評
「愛動物人士的必讀故事。」──美國德州菲烈德利斯堡當地報紙〈自由蘭斯星報〉佳評
「頌讚人與貓之間亦能深度連結的奇妙故事,《奇貓奇遇:盲貓荷馬的冒險旅程》是部能激發人心的故事,應該列於任何愛貓人士的最棒假期禮物清單內。」──〈貓科動物健康〉雜誌佳評
「只要瀏覽前言,就會一下子看完整本書,而且看完後才發現,自己好似才享受過熱呼呼的美味布朗尼蛋糕聖代……通常事後都證明荷馬是個英雄,有一次甚至在夜賊闖入葛雯家時,救了葛雯的命!」──〈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佳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