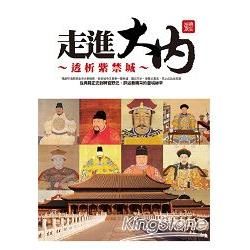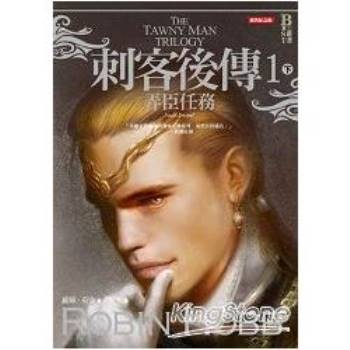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走進大內:透析紫禁城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39 |
中國歷史 |
$ 240 |
中國歷史 |
$ 288 |
中國史地總論 |
$ 288 |
中國歷史 |
$ 288 |
社會人文 |
$ 288 |
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走進大內:透析紫禁城
內容簡介
紫禁城是明清兩代五百年歷史的見證。紫禁城自明永樂十八年建成,至清宣統三年溥儀遜位,經歷了明清兩代四百九十一年的滄桑歲月,共有二十四位帝王在這裡御極,並實施對全國的統治權。在這座明清兩代的中心舞臺上,不知演出過多少幕歷史的悲喜劇——鄭和下西洋、土木之變、南宮復辟、于謙蒙難、明武宗荒淫、魏忠賢亂政、張居正改革、李自成進京、崇禎帝自縊、清統治者入主中原、康乾盛世、鴉片戰爭以來的種種屈辱,慈禧垂簾聽政,戊戌變法,清帝遜位……五百年間王朝的消長,中華民族的榮辱,世界潮流的衝擊,在這裡一一展示。紫禁城是一處濃縮這一切的地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張曉生
漢族 ,一九四七年生於河南林縣 ,祖籍山東肥城 。早年學習音樂 ,後學醫從醫 ,三十五歲才拿起筆 。主要著作 :《中國古代戰爭通覽》、《中國近代戰策輯要》、《中華古文明大圖集》、《中華佛文化圖典》、《兵家必爭之地》、《歷代兵詩窺要》、《野人小草集》、《我們沉睡在清晨》、《從奧林匹亞到萬里長城》、《衝動商旅》、《蜀道》、《統萬城》、《成才經》、《魯迅大辭典》(撰稿人之一)、《文藝鑒賞大觀》(主編)等 。
張曉生
漢族 ,一九四七年生於河南林縣 ,祖籍山東肥城 。早年學習音樂 ,後學醫從醫 ,三十五歲才拿起筆 。主要著作 :《中國古代戰爭通覽》、《中國近代戰策輯要》、《中華古文明大圖集》、《中華佛文化圖典》、《兵家必爭之地》、《歷代兵詩窺要》、《野人小草集》、《我們沉睡在清晨》、《從奧林匹亞到萬里長城》、《衝動商旅》、《蜀道》、《統萬城》、《成才經》、《魯迅大辭典》(撰稿人之一)、《文藝鑒賞大觀》(主編)等 。
目錄
序:帝宮鳥瞰——見皇房壯知天子尊
第一章:九五之尊——朕即國家天威叵測
第二章:乾綱獨斷——天下事重躬自斷制
第三章:大位傳承——有嫡立嫡無嫡立長
第四章:祭天祀祖——奉天承運祖宗家法
第五章:君王起居——窮奢極侈恣性縱欲
第六章:皇子教育——因其材力各俾造就
第七章:六宮粉黛——富貴已極終無意趣
第八章:太監制度——賤似蟲蟻皇家心腹
第九章:共和風雲——中華帝制壽終正寢
明朝皇帝大事掠影
清朝皇帝大事掠影
第一章:九五之尊——朕即國家天威叵測
第二章:乾綱獨斷——天下事重躬自斷制
第三章:大位傳承——有嫡立嫡無嫡立長
第四章:祭天祀祖——奉天承運祖宗家法
第五章:君王起居——窮奢極侈恣性縱欲
第六章:皇子教育——因其材力各俾造就
第七章:六宮粉黛——富貴已極終無意趣
第八章:太監制度——賤似蟲蟻皇家心腹
第九章:共和風雲——中華帝制壽終正寢
明朝皇帝大事掠影
清朝皇帝大事掠影
序
【寫在卷首】
人生確如白駒過隙,轉瞬已到了晚年。就在二十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風塵中幸遇知己,將我引進故宮西華門內武英殿行走,開始接觸到文物,而且多是出國列展的頂級文物。我這人野路子出身,幾乎沒受過任何完整的系統教育,尤其是文史教育。大概從三十年前拿起筆來舞文弄墨的那天起,就是在踉踉蹌蹌全無法度,難諧盡耳唯擅孤吹,被莫言謔稱「雙目炯炯,匪氣十足」,好像什麼也不在乎。哪裡敢什麼也不在乎,只在乎想在乎的東西而巳。譬如,對於見到的文物,就會情不自禁地心存敬意。
何謂文物?顧名思義:文化信物。無論來自祖宗遺傳,還是地下出土,都是歷史上確實存在、現在還能見到的東西。這對於想搞歷史研究的人,該是何等重要,怎麼去講,也不為過分。歷史又是甚麼?歷史是秦皇銳思漢帝窮神,也得是驪山之塵茂陵之草。記得在跟某些朋友聊天時,說過這樣的話:當您走進遍佈於神州各地的歷史博物館,切莫小覷那一件件火為精靈土為胎的陶瓷,那一尊尊古鏽斑斕的青銅器,那一片片燦若雲霞的絲綢,那一柄柄百煉鋒成的利刃,它們所展示的,不正是可以使您直接感觸到的我們這個文明古國的心靈歷史嗎?時代精神的火花,在這裡凝凍、積澱下來,傳留和感染著人們的思想、情感、觀念、意緒,經常使人一唱三歎,流連不已,要比看多少文獻都可靠。而在故宮幫助工作的五、六年間,每日有事沒事,徜徉在充滿歷史迴響的偌大的紫禁城內,抬頭不見低頭見,所見全是有意味的存在,就很容易心由境造。曾有感寫下一副對子——太息乾坤星移物換,歌吟歲月雨縱風橫,作為告別那裡時的贈言。
說到在故宮最大的收穫,還是對早已被高度抽象化了的中國皇權帝制這個概念,究竟本該是些什麼形態,似乎有所領悟。所以,我才認為,要想瞭解點什麼,現場感挺重要。有兩句老話:書到用時方恨少,覺知此事須躬親。其實,人要是比較聰明,臨時看書也來得及,但對什麼若無親身感受,滿腦子都是耳食之言,即別人對這是怎麼說的,那永遠都會是別人是怎麼說的,形不成屬於自己的學問。我確曾很羡慕在故宮上班的人,認為他們那差事不錯,琢磨過能否調進去。當然,想也白想,戎裝在身,不可能的事。再好的工作,也要看怎麼幹,如果不利用職務便利,上班就去那兒搬來搬去,登記造冊,雖說是工作需要,也可能只是為別人做點準備,自己啥也不知道。我於是將對這裡環境器物的印象筆記下來,翻拍一氣,免得日後忘卻。這麼說來,早就該寫這本書了,何以等到現在?沒別的原因,當年禁不住誘惑,幹別的去了。如今回過頭來,再想怎麼樣,筆頭都有些發澀。然而,我相信下過的工夫不會白費,且不說常感到這些東西餘溫尚存,正所謂死灰不可復燃乎,總把前程問火爐。最近翻揀有關筆記,發現只要認真梳理一下,也許還能搞出本有用的讀物。至於它有沒有用,我說了不算,讀者說了算。最後,解釋一下書名中的「大內」二字。「大內」,在這裡語義雙關:既是紫禁城昔日的別稱,又是指它所負載的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內涵。
人生確如白駒過隙,轉瞬已到了晚年。就在二十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風塵中幸遇知己,將我引進故宮西華門內武英殿行走,開始接觸到文物,而且多是出國列展的頂級文物。我這人野路子出身,幾乎沒受過任何完整的系統教育,尤其是文史教育。大概從三十年前拿起筆來舞文弄墨的那天起,就是在踉踉蹌蹌全無法度,難諧盡耳唯擅孤吹,被莫言謔稱「雙目炯炯,匪氣十足」,好像什麼也不在乎。哪裡敢什麼也不在乎,只在乎想在乎的東西而巳。譬如,對於見到的文物,就會情不自禁地心存敬意。
何謂文物?顧名思義:文化信物。無論來自祖宗遺傳,還是地下出土,都是歷史上確實存在、現在還能見到的東西。這對於想搞歷史研究的人,該是何等重要,怎麼去講,也不為過分。歷史又是甚麼?歷史是秦皇銳思漢帝窮神,也得是驪山之塵茂陵之草。記得在跟某些朋友聊天時,說過這樣的話:當您走進遍佈於神州各地的歷史博物館,切莫小覷那一件件火為精靈土為胎的陶瓷,那一尊尊古鏽斑斕的青銅器,那一片片燦若雲霞的絲綢,那一柄柄百煉鋒成的利刃,它們所展示的,不正是可以使您直接感觸到的我們這個文明古國的心靈歷史嗎?時代精神的火花,在這裡凝凍、積澱下來,傳留和感染著人們的思想、情感、觀念、意緒,經常使人一唱三歎,流連不已,要比看多少文獻都可靠。而在故宮幫助工作的五、六年間,每日有事沒事,徜徉在充滿歷史迴響的偌大的紫禁城內,抬頭不見低頭見,所見全是有意味的存在,就很容易心由境造。曾有感寫下一副對子——太息乾坤星移物換,歌吟歲月雨縱風橫,作為告別那裡時的贈言。
說到在故宮最大的收穫,還是對早已被高度抽象化了的中國皇權帝制這個概念,究竟本該是些什麼形態,似乎有所領悟。所以,我才認為,要想瞭解點什麼,現場感挺重要。有兩句老話:書到用時方恨少,覺知此事須躬親。其實,人要是比較聰明,臨時看書也來得及,但對什麼若無親身感受,滿腦子都是耳食之言,即別人對這是怎麼說的,那永遠都會是別人是怎麼說的,形不成屬於自己的學問。我確曾很羡慕在故宮上班的人,認為他們那差事不錯,琢磨過能否調進去。當然,想也白想,戎裝在身,不可能的事。再好的工作,也要看怎麼幹,如果不利用職務便利,上班就去那兒搬來搬去,登記造冊,雖說是工作需要,也可能只是為別人做點準備,自己啥也不知道。我於是將對這裡環境器物的印象筆記下來,翻拍一氣,免得日後忘卻。這麼說來,早就該寫這本書了,何以等到現在?沒別的原因,當年禁不住誘惑,幹別的去了。如今回過頭來,再想怎麼樣,筆頭都有些發澀。然而,我相信下過的工夫不會白費,且不說常感到這些東西餘溫尚存,正所謂死灰不可復燃乎,總把前程問火爐。最近翻揀有關筆記,發現只要認真梳理一下,也許還能搞出本有用的讀物。至於它有沒有用,我說了不算,讀者說了算。最後,解釋一下書名中的「大內」二字。「大內」,在這裡語義雙關:既是紫禁城昔日的別稱,又是指它所負載的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內涵。
張曉生記於二○一三年九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