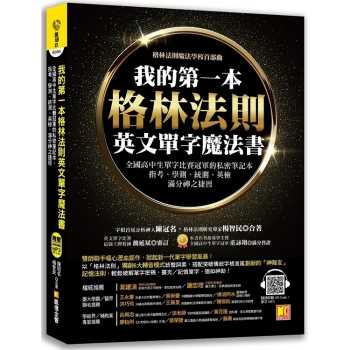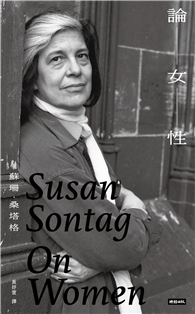【選詩】
陳令洋
藝術無關乎政治
藝術無關乎政治。所以請不要畫天空
因為當天空被煙囪染黑
總讓人想起政治
藝術無關乎政治。所以請不要畫山海
因為當海邊蓋起了飯店,山邊蓋起了劇場
總讓人想起政治
藝術無關乎政治。所以請不要畫家園
因為當家園被政府搗碎
總讓人想起政治
藝術無關乎政治。所以請不要畫動物
因為當小貓被人凌虐,小狗流浪街頭
總讓人想起政治
藝術無關乎政治。所以請不要畫人類
因為小孩總是被老師打、人總是要變老、有人總是沒飯吃、總是會有人殺人
這些總讓人想起政治
藝術無關乎政治。所以請不要畫抽象畫
因為當交錯紛亂的線條色塊,表現了我們的愛恨見聞思維願景
這些總讓人想起政治
如果藝術無關乎政治,請千萬不要將畫布塗黑、或者留白
因為當這裡沒有畫面,那裡完全沒有畫面
也總是讓人想起政治
【詩評】
另一個辛波絲卡
陳子謙
辛波絲卡在波蘭和華文世界,很可能面對著截然不同的讀者群:前者閱讀時或會想起魯熱維奇、米沃什等波蘭詩人,後者則多半忘不了舊譯的手勢,特別是陳黎、張芬齡夫婦的折射。台港的詩迷,往往熟讀他們合譯的《辛波絲卡詩選》(新版名為《辛波絲卡詩集》);至於中國大陸,多年前已有林洪亮、張振輝的兩個譯本,但迴響不大;去年陳黎夫婦在大陸出版了增訂本《萬物靜默如謎:辛波絲卡詩選》,迅即售出六萬冊,讀者熱烈如謎。我不禁好奇:林蔚昀會喚來那個我們早已熟悉的辛波絲卡嗎?
譯者也是編選者
小說和詩譯者的角色是不同的,前者譯好就夠了(這不是廢話嗎?),後者卻常常兼顧編選。陳黎夫婦以譯詩聞名,我認為其成功因素也包括了編選──他們選錄的詩作,往往較少文化隔膜,便於異地的讀者進入。讀林蔚昀的新譯本,我們也難免期待能重溫〈一見鍾情〉等陳黎夫婦譯過的經典。令人震驚的是,林蔚昀居然沒有重複陳氏台版的任何詩作,與大陸版《萬物靜默如謎:辛波絲卡詩選》也只有五首重複。依我看,這與其說是偶然,不如說是林蔚昀有意為華文讀者(特別是台灣讀者)帶來另一個辛波絲卡。
讀陳黎夫婦的譯本,總覺得辛波絲卡是個淡定的智慧老人,每每能抽離地俯望人間荒謬。讀林蔚昀的譯本,卻隱隱覺得辛波絲卡也有平常人的憂愁和恐懼,在實實在在的歷史環境中掙扎。死亡的陰影,在陳氏譯本中或只是偶一閃現,卻是林蔚昀譯筆下的主色。死亡可以是人類共有的壓力,但林蔚昀為辛波絲卡的死亡書寫重塑了歷史背景──原來她的表親、暗戀的男生都在二次大戰中喪生,男友則在執行軍事任務時失蹤。過往華文讀者對辛波絲卡的印象,多少是去地域、去歷史的,林蔚昀卻令我們感到:辛波絲卡也是個活生生的人,會笑,也會哭。
一張嘴就是一種滋味
我曾經以為,辛波絲卡的精華在於觀看的角度和鏡頭剪接,語言明朗,誰來譯都差不多。陳黎夫婦、林洪亮和張振輝的譯序,都不談翻譯過程的具體困難和取捨,難免令人以為辛波絲卡是容易翻譯的。林蔚昀卻在譯序中詳細探析辛波絲卡如何講究語言,如翻新諺語、自鑄新詞等,令我重估翻譯的難度。事實上,辛波絲卡的〈字彙〉也輾轉談過翻譯之難。這詩寫的大概是兩國間的政治和文化隔膜,我卻把它讀成翻譯的寓言──拿掉最準確的詞彙,我們還能聽到心裡的聲音嗎?即使譯文無法徹底移植原文的語感,怎麼譯,還是必須注意的關鍵。
總體來說,陳黎夫婦更追求凝煉,略帶文言腔調,難怪我們會讀到這樣的句子:「使之欲逃無路」、「始終很佳,/別無例外者」;又會讀到大量四字套語:「無庸置疑」、「獨一無二」、「無家可歸」、「如火如荼」、「一覽無遺」……比較之下,林蔚昀雖未有完全甩掉成語,但整體來說更加口語化──這其實更脗合我對辛波絲卡的一貫想像:這些日常生活的哲思,用口語說出來不是更合適嗎?至於哪個譯本更貼近原文的語感,就得留待兼通波蘭文和華文的識者來決定了。
林蔚昀翻譯的〈車站〉開首,便很見功夫:
我的缺席
準時抵達N市的車站
你已經被告知了
透過一封沒有寄出的信
你趕上在約定的時間
不前來
陳黎夫婦沒有譯過這詩,我們不妨對照其他譯本:林洪亮把頭兩句譯成「我沒有到達X城,/按照我原先的安排。」張振輝則譯成「火車正點到達N城,/但我卻沒有來。」這兩個版本都比較貼近日常的句子,卻沒有攫住這詩的悖論:「缺席」就像「在場」,看似「無」卻又像「有」。詩人不是「沒有到達」或「沒有來」,而是她的「缺席」「準時抵達」了。林蔚昀筆下的「缺席」,在辛波絲卡的原文中是放在句首的名詞nieprzyjazd,這詞性本身就給人「有」的實體化錯覺。因此,把「我的缺席/準時抵達」換成了「但我卻沒有來」或「我沒有到達」,看似自然,卻令詩意缺席了。
翻譯就像接吻,每張嘴的滋味都有點不同──可惜如此,也幸好如此。林蔚昀的辛波絲卡,還是我們以往熟悉的辛波絲卡嗎?是,也不是。就像〈僅只一次〉告訴我們的:
沒有一個白日會重複
也沒有兩個一模一樣的夜晚
或是兩個同樣的吻
兩道同樣的凝視
(本文為節選,完整版原刊香港明報)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衛生紙+21:藝術無關政治的圖書 |
 |
衛生紙+21:藝術無關政治 作者:鴻鴻 主編 出版社:黑眼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10-2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47 |
中文書 |
$ 148 |
現代詩 |
$ 151 |
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衛生紙+21:藝術無關政治
本期推出兩位波蘭偉大詩人辛波絲卡、魯熱維奇的專題,除了選詩,還有六位年輕詩人的讀詩筆記,香港詩評家陳子謙如此推崇林蔚昀從波蘭直譯的辛波絲卡:「過往華文讀者對辛波絲卡的印象,多少是去地域、去歷史的,林蔚昀卻令我們感到:辛波絲卡也是個活生生的人,會笑,也會哭。」
地域和歷史,也是《衛生紙+ 》從來不肯迴避的命題。21期「藝術無關政治」源自陳令洋的反諷詩作──如果藝術迴避了政治,那就什麼都不剩了。台灣對政府的公義抗爭、中國對邊境的侵凌欺壓、乃至遠方不遠的敘利亞內戰,衛生紙詩人一字排開,都不能無言。南京和北京詩人,在這裡發表他們難以在境內披露的詩;海外詩人,也把這裡當作文學的實驗場。
特別推薦廖育正的組詩〈廖人之家〉,藉著一個家族寓言,以眾多生動的場景,彰顯人類的各種暴力,語言與構思都深具創意。作者的另一篇〈真情水中刀痕〉,更是對詩人黃粱的重要評論。而年輕作者李璐的劇評,則是以《如夢之夢》的修改版本,作為台灣文化受中共保守意識影響的惡例,提出犀利質問。
封面由賴舒勤繪製,展現這位年輕詩人的另一才情。
作者簡介:
詩人,劇場及電影導演。現為黑眼睛跨劇團藝術總監、黑眼睛文化負責人。曾編導約30齣戲劇、歌劇、舞蹈、及詩的演出作品。擅長以實驗性的手法、批判性的觀點,詮釋當代的「冷僻經典」。近年來積極培育新銳導演、劇作家,鼓勵跨界創作與社會觀察,為台灣劇場界注入另一股嶄新的活水。
章節試閱
【選詩】
陳令洋
藝術無關乎政治
藝術無關乎政治。所以請不要畫天空
因為當天空被煙囪染黑
總讓人想起政治
藝術無關乎政治。所以請不要畫山海
因為當海邊蓋起了飯店,山邊蓋起了劇場
總讓人想起政治
藝術無關乎政治。所以請不要畫家園
因為當家園被政府搗碎
總讓人想起政治
藝術無關乎政治。所以請不要畫動物
因為當小貓被人凌虐,小狗流浪街頭
總讓人想起政治
藝術無關乎政治。所以請不要畫人類
因為小孩總是被老師打、人總是要變老、有人總是沒飯吃、總是會有人殺人
這些總讓人想起政治
藝術無關乎政治。所以請不要畫...
陳令洋
藝術無關乎政治
藝術無關乎政治。所以請不要畫天空
因為當天空被煙囪染黑
總讓人想起政治
藝術無關乎政治。所以請不要畫山海
因為當海邊蓋起了飯店,山邊蓋起了劇場
總讓人想起政治
藝術無關乎政治。所以請不要畫家園
因為當家園被政府搗碎
總讓人想起政治
藝術無關乎政治。所以請不要畫動物
因為當小貓被人凌虐,小狗流浪街頭
總讓人想起政治
藝術無關乎政治。所以請不要畫人類
因為小孩總是被老師打、人總是要變老、有人總是沒飯吃、總是會有人殺人
這些總讓人想起政治
藝術無關乎政治。所以請不要畫...
»看全部
目錄
林蔚昀 辛波絲卡詩選/筆記:陳子謙、蔡仁偉、eL
林蔚昀 魯熱維奇詩選/筆記:阿米、阿芒、袁紹珊
陳令洋 藝術無關乎政治
沈雨懸 不要在我家前面玩石頭
瞇 做什麼、在公義與仁愛路口、紅綠燈、價值、白忙人生
廖永來 驢、新疆、大埔徵收事件、照理說
許赫 野狼很忙、翻桌、信任危機、祖國認同不就是
阿芒 狂犬病一發不可收拾、大家都有鼻子、原來啊,媽媽咪呀
阿米 重要書-寫給兒童、一隻烏鴉的學習筆記、四季、帶電的靈魂
蔡仁偉 早餐店杯蓋題 等25首
熒惑 孩子不懂什麼是戰爭
徐徐 跨國、壁畫、果實、不要臉書、...
林蔚昀 魯熱維奇詩選/筆記:阿米、阿芒、袁紹珊
陳令洋 藝術無關乎政治
沈雨懸 不要在我家前面玩石頭
瞇 做什麼、在公義與仁愛路口、紅綠燈、價值、白忙人生
廖永來 驢、新疆、大埔徵收事件、照理說
許赫 野狼很忙、翻桌、信任危機、祖國認同不就是
阿芒 狂犬病一發不可收拾、大家都有鼻子、原來啊,媽媽咪呀
阿米 重要書-寫給兒童、一隻烏鴉的學習筆記、四季、帶電的靈魂
蔡仁偉 早餐店杯蓋題 等25首
熒惑 孩子不懂什麼是戰爭
徐徐 跨國、壁畫、果實、不要臉書、...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鴻鴻 主編
- 出版社: 黑眼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10-21 ISBN/ISSN:978986635934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