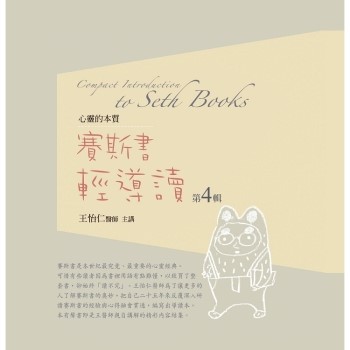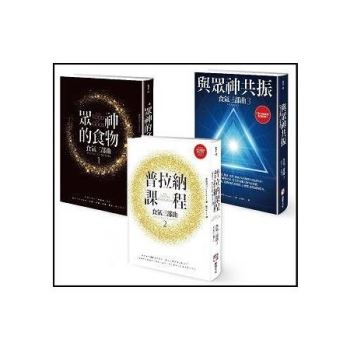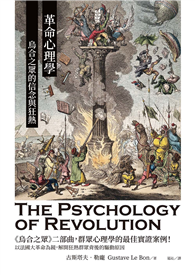【推薦序】
歌袂爽,詩袂爽 :幾幀布勒詩集小照張亦絢
我在咖啡店裡,讀一本談影子的書。裡面講到雕塑家澎庫西(Brâncuși),他給他的雕塑拍照,並且說:展示就好了,不需要評論。意思是,攝影就是展示,展示,就相當於評論。我喜歡這個想法。澎庫西與賈克梅蒂(Giacometti)完全不同,但每次我想到一個,就會想到另一個,並且都要再想一遍,在火車上,面對面地,看到某人死去的,那是賈克梅蒂。在這一切的背後,我還想著布勒的詩:
在〈貓的日常——給不在的爺爺〉裡,「如一座雕像的生存法則」的爺爺「一直都在」,不過那也是「是不是因為死亡太近╱我才一直看得見你」。這是首很奇怪的詩。一開始人貓就不太分明,又不是「穿長筒靴的貓」,貓怎麼會「還沒去上班呢╱就已經累了」——說它奇怪,一點不是覺得不好的意思。詩不奇怪無可觀,奇怪是被擊中的異感以及難以自拔的被挽留。陸穎魚寫過〈一個養女子的貓〉,貓與人角色倒錯或混生,似乎頗有傳統。要說貓是無意識中的「陰性共犯」仍覺不夠,鏡像是貓不是人,至少可說,此鏡更訴諸語言而非視覺的透析性。我很喜歡的〈貓咪呀——給浪貓與L〉,佳句甚多,但我覺得最美的,是結束兩句「貓咪呀,今天別走╱貓咪呀,明天別走」——「永遠」沒出現,要是比較不行的作者,就會殺出「永遠」兩字而落敗。疊句除了呼喚情緒惹人笑愛,後句還密告前句不宣的欲望,也讓人感到,面對無盡的分離,必須有種「鐵杵磨成繡花針」的恆心「磨」工與甜痛交織。
就像夏宇給葉青的〈強壯的日子〉詩意浩蕩,詩集中〈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致吾友葉青〉,布勒傾注的光熱,也令人過目難忘。「沒有誰的視線╱朝這裡望」——至少說了幾事:首先是「畫像」的政治性,畫像預示視線存在的假設是不能確定的,「無視」是有權對無權最有效的放逐。喬伊斯、梵谷與葉青,生前都曾活在「被隱形的人為洞穴」中,「無畫無像」的懲戒與束縛力,是三者「死亡前的死亡」。所謂一生,恰如不斷奮力的顯靈。這也寫出葉青以及歸隊為其同行與後繼者的對抗之所在。女同或同志的特殊性包含於其中,但也並非唯一。「畫我無畫像」只是起點,完成畫像未必能獨力改變規則,畫像蒙塵或被視若無睹仍有可能,寫詩因此是對視線治理持續的起義翻覆,也是危險的志業;儘管說,哀悼的完成,在使死者仍活在生者的世界,布勒的詩致葉青,個人與非個人的成份,重要性卻不分軒輊:
但我堅硬而巨大,極渴望被刺穿
據說被幹到射的經驗非常難得,非常
非常稀罕
我是等待被進入的那角色以古典跪姿
誰若進入了我,誰就無法避免重新認識他的虛無
我的同性戀是天生的,毫無疑問
啊!色情來了。「被幹到射」居於樞紐,以一般概念來說,自然會想到俗稱「潮吹」的「女性射精」,此處我們也不必避諱它在色情中的「神聖」地位。「我」也籠罩在此幻想中。「我是等待被進入的那角色以古典跪姿」,無論「被進入」或「古典跪姿」,都是極度陰性化位置的描述,然而這裡有一層響亮複義伴生,使其不是靜物化的被動與不能動,也就是說,這不是一個單純攻受方的「受」標記,「誰若進入了我」,同時是「性交合」與「幻想主體承接」,也就是「幹我與變成我」都是(進入了)我,也因此「虛無」以及「重新認識」是「我」也是下一位「來者」的命運。在這之後「我的同性戀是天生的,毫無疑問」也有意思。一方面,沒有這個宣敘,上述五行都會被吸收進異性戀而抹去同性戀;另方面,它也如調侃,意即「只要快感能夠自由多樣偏移」,只要框架會一變再變,只要向著未知開啟,就可「判定」為「天生的同性戀」,這就形成,凡有想像力的,都成了「天生的同性戀」。不是基因與解剖學的「天生」,而是語言與象徵能力的「天生」。回到「被幹到射」這個色情用語,誰可以「被幹到射」呢?答案是,所有的人。「幹」做為生理男性的獨佔性,是種文化建構;在合意性交的狀態中,「幹」與「被幹」總是難分的;採陰性位置中心,也可以說,只存在「被幹」與「被被幹」,爽總是雙向迴轉,沒有誰會因為生理,而沒有幻想與實作的快感交互位置。色情語的挪移並不易,布勒除了深得自白體在感官性中淘金之道,還有偷天換日的矯健,其搖擺力十足的暈染,在戳現語言幻覺的同時,鑲嵌了意念的新骨與新肉,此處我只點到為止,儘管此成績值得大書特書。
若說夏宇是「所有的挫敗都帶來狂喜」,布勒令我注意到的,反而是「所有的挫敗都不帶來狂喜」的新局——一種「歌袂爽」的特殊性。〈也沒關係啊〉寫到後來看似不完全悲傷,「再怎麼寶貝╱都可能長蟲」,蟲子後來「還學飛」,事實的悲劇,因為喜劇而更悲,然而作者並沒因找到突梯的形容就快樂起來,她沒那麼容易滿足分心,並從鬱卒的位置撤離:「我們不希罕罷了」——簡直莫名其妙!難道要希罕蟲?寶貝到,長蟲還寶貝?這個「莫名其妙」在常識上是不通的,但在詩裡,卻形成乖張與無理的魅力。不希罕的還是希罕,還是寶貝的那個什麼,當然不是蟲。全詩一再出現的「沒關係」,其實都「很有關係」。詩的餘味與低迴在這裡:因為餘情未了。睥睨一切的情人是不存在的,情人就是情人,情人都愛計較。夢裡詩裡都一樣。
雖然布勒也寫非常漂亮的警句如「可以打開不代表可以關上」,但在某時,詩人突然露出情人的苦樣,彷彿「我才不管詩了」,那種圖窮匕現,還是詩的——會乍然撥動我們的心痛。《致那些我深愛過的賤貨們》,詩集名擺明她「不在乎格調」——挫敗像親密,都牢記,這在「智慧小語」的觀點中,萬萬不可;但詩的使命也在不唱高調。咒詛是愛到盡頭又倒退著愛一遍,「愛兩次」之苦非常人性,「犯賤且犯禁」,最好是詩給了這種自由以及愛。袂爽是真的,只有如此,爽才會也是真的;因此我萬分慶幸,在這世上,有布勒寫詩。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致那些我深愛過的賤貨們的圖書 |
 |
致那些我深愛過的賤貨們 作者:布勒 出版社:黑眼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6-2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96 |
二手中文書 |
$ 281 |
中文書 |
$ 282 |
現代詩 |
$ 282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88 |
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致那些我深愛過的賤貨們
淵藪的海啊
我的愛深不可測
是他人的地獄
寫詩之人即為戀人,而戀人有時賤。
《致那些我深愛過的賤貨們》是布勒的第一部詩集,共收錄50首詩作。除了記錄詩的一瞬兩瞬,詩人也讓我們目睹,愛,可以如此性別,而痛苦與憂傷亦是。
本書以記憶為經,感官為緯,書寫女字邊的日常。當日常是荒謬劇場,小情小愛皆成展演,在此,欲望遂走成鋼索,孤獨是跌不死的深淵,唯有經歷愛的動盪與暴亂之後,才開始劫後餘生。
「若說夏宇是『所有的挫敗都帶來狂喜』,布勒令我注意到的,反而是『所有的挫敗都不帶來狂喜』的新局——一種『歌袂爽』的特殊性。」──張亦絢
「所謂賤貨:毋寧是指向在愛的動盪與暴亂中的每一個人。一本正經的調戲。因喜悅而脫口的親密挑釁。表裡不一的咒詛。線索:特權與苦難,留給所有的女字偏旁。若我的部首是陰性,我的歷史就從手牽手一起去廁所寫起,就是終其一生活在被強暴的恐懼底下直至老去,就是只被允許學習綿裡針、冷暴力,而血大抵只從下體與心裡流出來。」──布勒
作者簡介:
布勒,1981年生,長於花蓮,喜歡海邊。視動植物如家人,討厭噪音。
TOP
推薦序
【推薦序】
歌袂爽,詩袂爽 :幾幀布勒詩集小照張亦絢
我在咖啡店裡,讀一本談影子的書。裡面講到雕塑家澎庫西(Brâncuși),他給他的雕塑拍照,並且說:展示就好了,不需要評論。意思是,攝影就是展示,展示,就相當於評論。我喜歡這個想法。澎庫西與賈克梅蒂(Giacometti)完全不同,但每次我想到一個,就會想到另一個,並且都要再想一遍,在火車上,面對面地,看到某人死去的,那是賈克梅蒂。在這一切的背後,我還想著布勒的詩:
在〈貓的日常——給不在的爺爺〉裡,「如一座雕像的生存法則」的爺爺「一直都在」,不過那也是「是不是...
歌袂爽,詩袂爽 :幾幀布勒詩集小照張亦絢
我在咖啡店裡,讀一本談影子的書。裡面講到雕塑家澎庫西(Brâncuși),他給他的雕塑拍照,並且說:展示就好了,不需要評論。意思是,攝影就是展示,展示,就相當於評論。我喜歡這個想法。澎庫西與賈克梅蒂(Giacometti)完全不同,但每次我想到一個,就會想到另一個,並且都要再想一遍,在火車上,面對面地,看到某人死去的,那是賈克梅蒂。在這一切的背後,我還想著布勒的詩:
在〈貓的日常——給不在的爺爺〉裡,「如一座雕像的生存法則」的爺爺「一直都在」,不過那也是「是不是...
»看全部
TOP
目錄
[推薦序]歌袂爽,詩袂爽:幾幀布勒詩集小照 張亦絢
無愛演化生活
鬼的狂歡
不明
模糊
厭煩
鬼火
得不到
病
貓的日常──給不在的爺爺
將近
霧中風景一
霧中風景二
你喜歡的……
某種覆滅之前
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彌補──給親愛的Kuo
經過
無意同謀
尋常陪伴──當整個世界是鐵達尼號
欺騙──給L
青春──記校園霸凌
記憶
也沒關係啊
公園
該怎麼說的這些(童年往事)
辜負(妳這個賤貨)
斷裂一景
破滅
到底認不認命
教養
目的地──讀隱匿〈事情不是這樣的〉
提的概念
貓咪呀──給浪...
無愛演化生活
鬼的狂歡
不明
模糊
厭煩
鬼火
得不到
病
貓的日常──給不在的爺爺
將近
霧中風景一
霧中風景二
你喜歡的……
某種覆滅之前
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彌補──給親愛的Kuo
經過
無意同謀
尋常陪伴──當整個世界是鐵達尼號
欺騙──給L
青春──記校園霸凌
記憶
也沒關係啊
公園
該怎麼說的這些(童年往事)
辜負(妳這個賤貨)
斷裂一景
破滅
到底認不認命
教養
目的地──讀隱匿〈事情不是這樣的〉
提的概念
貓咪呀──給浪...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布勒
- 出版社: 黑眼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6-20 ISBN/ISSN:978986635966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開數:12.4*21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