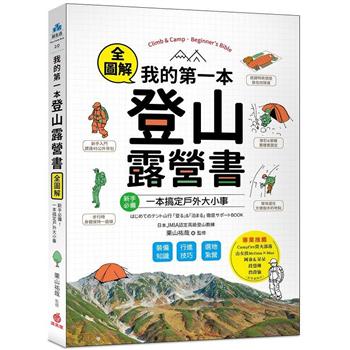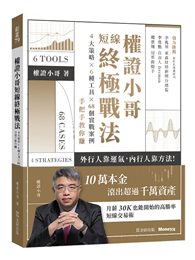前言
什麼事都有「預兆」或「前兆」。在能源和糧食市場中,「預兆」會呈現在自由市場所定的「價格」裡。全世界有六億噸的農作物,乃指全年產量約六億噸的小麥、玉米和稻米(帶殼米),再加上產量超過兩億噸的大豆,總數超過二十億噸。光是這些就已超過全球糧食總產量的一半,由此可知,全球人口依賴特定穀物作為糧食的程度。
目前,這個主要的穀物市場產生了變化。全球最具代表性的芝加哥穀物市場,作為主要糧食的小麥、玉米和大豆價格,自二○○六年十月之後高漲,到了二○○七年更創下自一九九六年以來的新高。穀物價格暴漲是什麼樣的「預兆」呢?
價格暴漲的不只是穀物。原油、鐵礦、非鐵礦物和煤炭在二○○六年就已創下數十年來的歷史新高,而穀物價格的暴漲只是上述情況的延續。筆者認為最近幾年能源價格暴漲並不是一種過渡期,而是從「廉價的資源時代」走向「昂貴的資源時代」的一種「平衡點的變化」。
這是因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動力,從人口不到八億的先進國家轉移到人口約有三十億、被稱為BRICs的開發中國家,即巴西(Brazil)、俄羅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國(China)。最大的原因是這些人口大國正式展開工業化,企圖以最快的速度迎頭趕上各先進國家。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快速成長,也使所得快速增加。所得增加改變了人們的飲食生活,除了量的改變之外,質也跟著變化,糧食需求大幅提升,使得原本可再生的資源,如農產品每年利用太陽能和水即可重新生產的部分糧食,最近也開始成為有限資源。生產糧食所需的水、土壤和地球環境愈來愈有限也是原因之一(關於這點,在文中將會詳細介紹)。
尤其因為糧食有限,世界各國就可能因為有限的糧食在三方面產生爭奪戰。首先就是國家之間的爭奪戰。一直以來被稱為「全球麵包盒」彈性供應世界各國糧食的美國,因國內市場擴大,無力維持出口,而經濟成長顯著的中國逐漸成為新的糧食進口大國。其次是市場之間的爭奪戰。隨著原油價格上漲,取代石油的生質燃料開始受到各國重視,導致能源市場和糧食市場之間相互競爭。
第三是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之間的爭奪戰,因為水和土地產生競爭。由於工業部門需要工業用水和用地,和工業相比,附加價值和生產能力較低的農業逐漸被逼至絕境。對於一直以來認為「只要付出高價就可以買到糧食」或「追求高品質、安全和安心的食物」的日本人而言,在爭奪糧食的世界,如果任由市場機制運作,將可能無法解決問題。此時此刻,綜合利用糧食自給率、根據WTO(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簽訂的多國協議、FTA(兩國協議)、農業技術、環境對策,以及人才培育等方法才是解決問題的當務之急。
筆者認為糧食價格暴漲乃是繼能源和礦物資源價格上漲而來,是為在不久的將來將發生糧食爭奪戰的前兆。價格暴漲的「前兆」在提醒我們什麼呢?筆者在寫作此書時,特別針對三點,第一,不只是從單一看法進行分析,而是盡可能從多方面、專業和歷史角度來看問題;第二,除過去的分析外,大膽進行「預測」;第三,提供應採取的因應之道和解決辦法。「預測」愈是大膽,與現狀的差異就愈明顯,解決的辦法也不再只是補救措施,也可是大膽創意。全文的結構除依照大綱書寫外,每節也可獨立閱讀。
糧食問題非常複雜,如只是像拼圖般拼湊片段的事實,很難了解「糧食爭奪」的全貌。
一般來說,要判斷將來會不會發生某件事,可依照判斷的方式是否根據合理、科學的理論和資料進行分析,還有會在何時發生、是否能夠鎖定發生的時間,區分為「預測」、「預想」、「天啟」(占卜)和「空想」四種類型。如果合理並可鎖定時間為「預測」;雖合理但無法鎖定時間為「預想」;雖可明白指出何時發生,但毫不合理為「天啟」(占卜);不合理也無法鎖定時間為「空想」。本書所採取的「預測」並不是包括樂觀、悲觀、遵循標準劇本所說的「這也可能,那也可能」,而是在描述可能發生的「風險(悲觀)劇本」。
本書之所以能夠出版,除得力於筆者所屬的丸紅經濟研究所同事,以及丸紅的經營幹部和糧食部門的先進,直接或間接提供的世界各地的資訊和意見,並透過外部的研究會,尤其是筆者擔任委員或臨時委員的社團法人國際農林合作協會(JAICAF)「糧食供需動向綜合檢討會」的服部信司委員長(東洋大學),和岩崎正典委員(伊藤宗桑氏)每年四次的基調報告,協助我透過實際的情況觀察市場。還有學生時代的老朋友農林水產省「糧食農業農村政策省議會綜合糧食分科會」的生源寺真一委員(東京大學大學院農學生命科學研究科教授),為我分析日本農業的現況和未來的展望。本書在進行市場分析時,和我上一本著作《資源膨脹》(日本經濟新聞社出版)一樣,都獲得大東文化大學經濟研究所蔣安教授的鼎力相助,提供資訊和意見。
還有,不可不提筆者在丸紅的上司,同時也是大學時的學長,小島正興先生(原丸紅專務)。小島先生在一九八○年代,日本農業面對自由化的壓力而開始改革時,擔任經團連農政問題懇談會米部會長,同時負責協調經常交惡的經濟界與農業界及行政間的橋樑,極受各方信賴。當時我有機會聆聽小島先生演講,並擔任部會長的「跟班」,前往日本眾多農業現場訪視。從這個角度來說,本書可說是小島先生的想法。除上述的各位先生外,本書在寫作的過程中得到各方協助,在此深表感謝。內容的文責當然盡歸筆者。
當然我要感謝在出版前一本《資源膨脹》之後,再度給我機會的經濟新聞出版社,尤其是對細谷合彥先生。雖應允盡早出版,但因筆者延遲使得工作進度大幅落後,在此致歉。本書在企畫和校正的所有過程中,都由細谷先生和我合力完成。最後我想對內人說一句「謝謝妳」。
二○○七年七月
柴田明夫
第二章 飽食時代及其陷阱──「爆食」中國的幾何級數衝擊
一 亞洲糧食情況的多樣化及其脆弱之處
消耗糧食的類型為「西洋型」還是「亞洲型」?
目前日本畜牧業的情況十分惡劣,除牛乳消費停滯外,穀物價格高漲導致飼料成本上揚,生產過剩的牛乳被酪農當作產業廢棄物處理。筆者曾獲全酪連(全國酪農協連絡會)邀請擔任研修會的講師,全酪連就是支援全國酪農專業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全國性組織,當然也舉辦促銷販賣牛乳的活動。然而相對於二○○三年約八百四十噸的牛乳產量,每人平均乳製品消費量僅不到七十公斤,僅就牛乳來看,全年消費量一直無法突破三十五至四十公斤。日本由於少子高齡化,人口減少,年輕人不喜歡喝牛乳的情況更為惡化。
反觀中國,牛乳在當地掀起一股熱潮。據大昌貿易行的趙慶先生表示,直到二十多年前,牛乳對中國的一般老百姓而言是非常昂貴的食物,只有病人才可以喝,而且需要醫生的診斷證明,大多數的家庭購買奶粉當作小孩或老人的營養輔助品。然而由於近年來驚人的經濟發展,以都會為中心的牛乳消費量大增,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推動和物流業之間的低溫運輸系統(將食物冷藏從產地運送至零售業者的方法)。據趙先生表示,這樣的結果使都會區的人均牛乳消費量從二○○○年的九點九四公斤倍增為二○○四年的十八點八三公斤。中國的糧食消費日後會發展到什麼地步?不!不只是中國,包括印度、印尼、泰國和越南等亞洲人口大國,同樣由於經濟發展使飲食生活更為豐富。
關於今後亞洲糧食消費類型變化的影響,有兩種發展的可能,一種是「西洋型」,另一種是「亞洲型」。以肉量消費量為例,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的糧食供需表可看出二○○三年日本人均肉類供給量為四十三公斤、美國為一百二十五公斤、法國為一百一十一公斤,在亞洲的中國為五十二公斤、台灣為七十七公斤、韓國為四十九公斤,明顯偏少,這就是「亞洲型」的糧食消費類型。如同戰後的日本曾流行「飲食西化」這句話般,亞洲各國的飲食習慣是否也會發展成「西化」,即「西洋型」,或是在某種程度就停止了呢?
儘管如此,中國和台灣的肉類消費量之所以出人意料的多,是因為日本的肉類消費量是以去骨的精肉為主來計算,而中國和台灣除了以豬肉為主外,整隻豬除了聲音不能吃什麼都能吃,所以極可能是以帶骨的肉塊來計算。此時必須將精肉換算為帶骨肉塊的百分之六十(因此中國變成三十一公斤,而台灣則變成四十六公斤,也就是所謂的「亞洲型」消費類型)。
無論如何,在展望二十一世紀全世界的糧食供需時,重要的關鍵字為「亞洲的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使亞洲糧食的消費多樣化,但因區域內的生產和供給缺乏彈性,大多數的糧食消費仍傾向依賴外國。一般來說亞洲的糧食消費有幾個特徵,首先是糙米的比重偏高。以印尼、泰國和越南為例,人均全年消費量為一百四十至一百八十公斤,一半以上的營養攝取來源依靠稻米。馬來西亞、菲律賓和中國也超過一百公斤,遠多於日本的六十公斤。全亞洲在一九九○年代每年消費七億噸左右的榖類,其中約有五億噸是稻米。
其次以國別來看,每個國家都有根深蒂固的飲食習慣。以印度為例,肉類的消費量每人每年平均為四公斤多,遠低於世界平均的三十二公斤。泰國的海鮮類消費量則為二十五公斤,比其他各國多。中國的榖類、肉類和蔬菜等的整體糧食消費量大。這些差異的產生除了有佛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等宗教因素外,還有身為島國或大陸的地理環境因素,以及屬於中華文化圈或其他文化圈的飲食文化差異。事實上,如同日本有以稻米、鮮魚和蔬菜為基礎的「和食」(日式飲食生活)飲食文化,韓國也有以「辛辣」為基礎的飲食文化,而中國和台灣則屬於利用食用油炒菜的豐富多樣中華料理。
然而在亞洲重要的是,九○年代以後快速工業化發展對飲食生活造成的影響。一般來說隨著經濟發展,農業會從原本依靠榖類生產的單一文化,轉變為以蔬菜和水果等經濟作物為主的結構,飲食生活的類型也會隨之改變,這類的農業生產和糧食消費多樣化的傾向在亞洲各國非常明顯。
其一是在傳統以稻米為主食的亞洲地區,由於肉類消費量增加,作為飼料的小麥和稻米等榖類消費量也快速增加。以韓國長期的糧食消費類型變化為例,六○年代除稻米外,根莖類小麥和豆類的生產和消費量增加,到了七○年代,則是蔬菜和水果產量增加。在這些產量逐年成長的農產品中,在蔬菜方面,以往被用來製作韓國飲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泡菜材料的白菜、白蘿蔔和辣椒,視為三大蔬菜。七○年代以後,傳統蔬菜的栽培停滯不前,取而代之的是高麗菜、萵苣、紅蘿蔔和洋蔥等,與新生活方式有關的蔬菜產量大增。在水果方面,傳統的香瓜種植逐漸減少,西瓜、橘子和蘋果等成為主要作物,這是因為都市近郊塑膠布溫室栽培等設施擴大所致。此外,七○年代以後的特徵是畜牧業擴大。豬的飼養頭數從七○年代的一百一十二萬頭增加到九○年代後期的六百五十萬頭,期間韓國的牛也從一百二十八萬頭增加到約兩百六十萬頭,雞也從兩千三百六十三萬隻增加到約八千六百萬隻。畜牧業發展同時也意味著飼料需求增加,尤其是韓國和日本,國內缺乏供給玉米和豆渣等必須的飼料用榖物基礎,必須依靠大量的進口飼料,也就是說飲食生活改善表示依賴進口的程度提高,突顯供給的問題。
支撐印度經濟發展的糧食生產及其未來
由於印度是繼中國之後興起的新興市場,因此備受矚目。印度經濟以一九九一年的國際收支危機為契機,更改為經濟自由化,一九九二年後發展至年成長率達百分之六的階段。總理曼莫漢辛格上台後,在第十一次五年計畫(二○○七年四月至二○一二年三月)中,提出平均百分之九的經濟成長目標,計畫在十年內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現在的七百美金增加一倍。擴大以稻米和小麥為中心的糧食生產,是支持經濟穩定成長的重要原因。諷刺的是,印度的經濟發展日後將大幅擴大糧食需求,極可能連累國際市場而引發新的供需問題。
印度的國土總面積(三億三千萬公頃)約半數為耕地,比例高於日本的百分之十二和中國的百分之十。農業部門的國內生產總值從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三十點三逐年下降,到了二○○三年降至百分之二十二左右。但二○○一年在總人口十億兩千七百萬人中,農村人口即占七億四千萬人(百分之七十二),農村的就業人口約四億人(約占就業人口的六成),和製造業及商業等其他部門的關係密切,因此農業的穩定生產對穩定經濟成長十分重要。尤其是印度大半的窮人都住在農村,提高農村雇用和所得是解決貧窮問題的關鍵。但印度農業的灌溉率只有大約四成,形同靠天吃飯,受天氣的影響極大、極不穩定。尤其是六月至九月間的雨季降雨集中,而且由於變化多端的降雨時間和降雨量,使農作物的產量變化極大,因此稱為「雨季的賭博」。
整體穀物產量每年約兩億噸,其中以印度東部為中心的稻米(精米)為八千萬至九千萬噸,超過四成,以西部為中心的小麥則在六千萬至七千萬噸左右,不到四成,雜糧約占百分之十五,其他豆類約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說稻米和小麥約占穀物產量的八成。二○○二年遭逢一百二十年來罕見的旱災,稻米的產量僅剩七千兩百七十萬噸,比前年減少兩千零四十萬噸,降低至九○年代前半期的水準。但自二○○三年以後,東部的稻米產地受惠於雨季,二○○三年的產量為八千七百萬噸,二○○四年則為八千六百萬噸(圖表2-1)。
至於小麥的產量,二○○三年因西部山區發生旱災,減少為六千五百一十萬噸,但二○○四年以後又恢復到七千兩百一十萬噸,這是因為當年氣候良好、土壤和水分適當,再加上各州沒有病蟲害發生,使產量得以恢復。然而後來連續兩年小麥減產,期末在庫量從二○○一年的兩千三百萬噸減少為二○○五年的兩百萬噸,驟減至十分之一以下。為了彌補國內小麥不足,相隔六年再度進口小麥。繼二○○六年五月自澳洲緊急進口五十萬噸後,二○○六年六月底印度財務省為解決國內小麥供給不足,抑制國內價格並增加庫存,將小麥的進口關稅從百分之五十降低至百分之五。根據美國農業部的報告指出,降低關稅的結果使得印度二○○六和○七年度的小麥進口量擴大為六百萬噸,期末在庫預估將小幅增加為三百萬噸。
印度之所以擴大糧食生產,是因為以旁遮普省等北印度為中心展開的「綠色革命」。以往的糧食增產主要是因為小麥的種植面積擴大,「綠色革命」以後由於高產品種(HYV, High Yielding Varieties)、整頓灌溉系統、使用化學肥料和殺蟲劑等農藥,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又因七○年代印度西部發展二期化稻作,使稻米和小麥產量大幅增加,其中又以普遍埋設水管、利用地下水灌溉開發的影響極大。隨著雨季的產量穩定,以往只能用作休閒或種植豆類等附加價值較低的作物的乾季,也能生產稻米和小麥。七○年代末期達到自給自足的目標,自八○年代起推動農業成長的主角變成搾油作物、蔬菜、水果和畜牧業。
到了九○年代,印度政府同意旁遮普省等生產過剩地區富有農民的要求,大幅提升購買穀物的價格。這個充滿政治色彩的漲價動作,九○年代前半在五方面引發一連串的效應。即提高農民生產穀物的意願;在公共配給制度(PDS,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下,提高窮人配給穀物的價格,以縮小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差距,使窮人的人均穀類消費量減少;突顯穀物「過剩」問題,無法負擔在庫成本的印度政府為解決這個問題,決定大量出口以稻米為中心的穀物。二○○○至二○○一年稻米和小麥的期末在庫量為四千七百萬噸左右,為降低在庫量,自九○年代中期起快速提高稻米出口量。以往印度僅以中東市場出口印度香米(高級香米),為小型的稻米出口國,但一九九四年突然以普通米為主出口四百二十萬噸,因此一躍成為僅次於泰國的稻米出口國。出口量在二○○一年達到六百三十萬噸,二○○○年以後,小麥的出口量也突然大增,二○○二至二○○三年間突破五百萬噸(圖表2-2)。然而,考量貧窮問題惡化的情況,穀物出口量暴增具有強烈「飢餓出口」的特色。
將來印度的糧食供給也可能自給自足嗎?預估印度在二○四○年將會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超過十五億人),國內糧食生產是否能夠滿足需求?要想知道這個答案,必須觀察每個人的糧食消費動向,尤其是作為飼料的穀物之間接需求動向。
尤其最近幾年,印度經濟快速成長,將來人均穀類需求極可能大幅增加。原因有三,其一是印度目前有三至四成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其中大多居住在農村,如果依照農村所得階級來觀察榖類消費量,每個月人均所得在五百六十盧比(約一千三百日圓)以上的階級,每年直接消費一百公斤的榖類。相對於這個數字,每個月收入不滿一百二十盧比(約二百八十日幣)的最低所得階級,全年僅消費一百一十六公斤;中等階級全年消費一百六十四公斤。在農村只要所得增加,直接消費榖類的數量就會增加,也就是說農村的直接消費仍未達飽和狀態,今後只要農村所得增加,榖類消費就會繼續增加。
其次是和其他開發中國家或先進國家相較,印度的人均榖類消費量極低。相對於世界各開發中國家和先進國家的每年人均榖類消費量三百至四百公斤,印度僅一百六十至一百八十公斤。一般來說,只要經濟發展,直接消費量就會增加,所得增加、直接消費量減少,取而代之的是飼料用穀類消費量增加,整體穀類消費量便大幅擴大。只要今後印度的經濟發展順利,穀類消費量也會大幅增加。
第三是隨著肉品消費量增加,將大幅提升穀類的間接需求。以下雖然是較早的資料,根據一九九四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的糧食供需表指出,印度的人均肉品消費量僅四點四公斤、中國為三十三公斤、日本為四十公斤、美國為一百一十八公斤。由於印度的人口規模較大,肉品消費量一旦增加,需求的量一定是極大的。相對於此,也有人認為由於大半印度人信奉印度教吃素,將來對畜產品的需求還是會比較低,雖然確實不能忽視飲食文化的影響,但印度人的肉品消費量之所以比較低,根據調查顯示與其說是宗教因素,毋寧說是所得水準的關係。
最近幾年印度除了根據國內穀物生產是否豐收進行有限制的進出口外,供需結構幾乎是自給自足,對國際市場造成的影響有限。然而近來由於經濟發展,印度穀物生產的方向不論在消費或生產面,都可能對國際市場造成極大的衝擊。
專用小麥的進口量也增加
隨著中國快速且持續的經濟發展,飲食生活從「量」到「質」的改變,其中變化最大的就是小麥市場。相對於多樣化的小麥需求,專用小麥的生產無法因應,導致進口量增加。
中國為全世界最大的小麥生產和消費國,據美國農業部農產需求報告指出,中國二○○六至二○○七年度小麥產量為一億三百五十萬噸,較前年的九千七百四十萬噸,產量規模占全世界小麥產量(五億九千兩百萬噸)的百分之十七,遠超過印度的百分之十一(六千八百萬噸)和美國的百分之八(四千九百三十萬噸),中國的小麥消費量預估為每年一億至一點一億噸,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十五至十六,但在過去的十五年內,中國的小麥市場在「量」和「質」方面都產生極大的改變,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是一九九○年前半的供給不足期。中國在一九九○年鄧小平的南巡演講後,出現經濟過熱,糧食供需緊迫,每年從美國進口一千萬噸以上的小麥。
第二為一九九○年後半的供給過剩時期。相對於中國大量進口小麥,當時看守世界研究中心(Worldwatch Institute)所長雷斯特布朗(Lester Brown)發表「誰來養活中國」的報告,對中國大量進口小麥將影響國際市場提出警告。中國因此大幅提高購買糧食的價格,促使農民增產,結果糧食生產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年連續四年達到約五億噸,期間小麥產量更是超過一億噸,在一九九七年創下一億兩千三百二十八萬噸的歷史新高。然而諷刺的是,國內因此出現過剩庫存,使中國搖身一變成為小麥純輸出國,市場出現「賣難買難」(品質差的賣不出去,買不到品質好的)的新問題。
為了因應這個問題,中國政府自一九九八年提出「適地適作」、「適地適策」來調整全國的小麥生產。具體的方法有以下幾點,第一,降低以低品質小麥為中心的收購價格,改種棉花或菜籽等較具經濟利益的產品;第二,將農地轉為工業用地或住宅用地,結果小麥產量在進入二○○○年後減少為一億噸,二○○三至二○○四年度更減少至八千六百五十萬噸,創下十四年來的新低。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原本三千萬公頃的小麥耕作面積快速減少,到了二○○四年規模縮小至自一九六九年以後三十五年來僅見的兩千一百五十萬公頃,小麥在庫量目前仍持續減少。原本超過一億噸、占全世界小麥在庫量(約兩億噸)半數的小麥在庫量,二○○五至二○○六年度期末減少至僅剩二○○一年的一半,及三千五百三十二萬噸,創下八○年代初期以來的新低。
第三點,二○○○年以後民眾對飲食的「質」的追求,以及所造成的專用小麥不足,原因在於飲食生活的變化。中國自九○年代後半起和六○年代後半的日本一樣,以都市為中心主食從米食轉變為麵包。通常主食轉變為麵包與都市化加速和女性參與社會有關,中國的小麥需求也從純硬質小麥(半硬質)和用來作月餅的軟質小麥,變成製作麵包、蛋糕和點心用的高筋麵粉、作通心粉用的粗麵粉和作蛋糕用的低筋麵粉的原料小麥等專用小麥。此外,傳統的饅頭、麵條和餃子等「蒸煮」食品,也需要更多良質的中筋麵粉。
一般來說歐美和日本等麵粉產業發達的國家,不同用途的麵粉種類就多達六十至七十種。據新華社Net Japan指出,中國不同用途的麵粉僅數十種,通常原產量僅占整體麵粉產量的百分之五,政府自一九九八年以後雖然開始重視「質」而非「量」,朝小麥食品構造多元化來調整生產,仍無法供應旺盛的需求。
中國的小麥貿易反應國內市場,最近開始進入專用小麥的純進口期。中國在二○○一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二○○二至二○○五年設定以百分之一的低關稅進口小麥配額(TRQ,Tariff Rate Quota),乃指配額內的進口課以較低關稅,超過的部分則課以較高關稅。協定中,具體的小麥關稅配額為二○○一年的七百八十八點四萬噸,二○○二年為八百四十六點八萬噸,繼二○○四和○五年的九百六十三點四萬噸,二○○六年也定為九百六十三點六萬噸,二○○五和○六年度的小麥進口僅一百三十萬噸,反應國內產量大增的實況,預估將較前年的六百七十五萬噸大幅減少(圖表2-7)。考量在庫量不斷減少,二○○六年再度增加小麥進口的可能性提高,美國一家穀物調查公司,即芝加哥顧問業者農業資源公司(Agresource)預估進口規模可達三百五十萬噸。國家小麥工程技術中心也指出,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全世界的小麥生產國,無不關注中國巨大的小麥市場,以生產配合中國市場的專用小麥為目標,今後一場中國的小麥進口戰將正式展開。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糧食爭奪戰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52 |
財政經濟 |
$ 280 |
應用科學 |
$ 882 |
科學科普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糧食爭奪戰
繼能源浩劫之後,糧食爭奪戰已在全球燃起烽火,
身為糧食生產小國,
我們有足夠的應變能力嗎?
繼「能源不足的問題」而來的糧食失衡問題,逐漸侵襲我們的生活。藉由本書瞭解糧食問題的嚴重性,與目前全世界將面臨的糧食困境,進而思考可供改善的政策,達到預防糧食恐慌的危機。
近年來,糧食失衡問題間接導致物價高漲,環境與氣候變化更影響了糧食供給的穩定性。然而,價格暴漲的不只是穀物。原油、鐵礦、非鐵礦物和煤炭在二○○六年就已創下數十年來的歷史新高,而穀物價格的暴漲只是上述情況的延續。最近幾年能源價格的暴漲,並不是一種過渡期,而是從「廉價的資源時代」走向「昂貴的資源時代」的一種「平衡點的變化」。
尤其因為糧食有限,世界各國就可能因為有限的糧食在三方面產生爭奪戰。首先就是國家之間的爭奪戰。美國一直以來彈性供應世界各國的糧食,但因國內市場擴大、漸漸無力維持出口,而經濟成長顯著的中國逐漸成為新的糧食進口大國。其次是市場之間的爭奪戰。隨著原油價格上漲,取代石油的生質燃料開始受到各國重視,導致能源市場和糧食市場之間相互競爭。第三是工業和農業之間的爭奪戰,由於工業所產生的附加價值高於農業產值,以致農業用水和用地,逐漸被逼至絕境。
對我們來說,糧食問題已不再遙不可及,而是隨時左右你我生活方式的民生議題,藉由本書通盤瞭解影響糧食供應的廣大範疇、認清癥結所在,進而思考解決之道。
章節試閱
前言 什麼事都有「預兆」或「前兆」。在能源和糧食市場中,「預兆」會呈現在自由市場所定的「價格」裡。全世界有六億噸的農作物,乃指全年產量約六億噸的小麥、玉米和稻米(帶殼米),再加上產量超過兩億噸的大豆,總數超過二十億噸。光是這些就已超過全球糧食總產量的一半,由此可知,全球人口依賴特定穀物作為糧食的程度。 目前,這個主要的穀物市場產生了變化。全球最具代表性的芝加哥穀物市場,作為主要糧食的小麥、玉米和大豆價格,自二○○六年十月之後高漲,到了二○○七年更創下自一九九六年以來的新高。穀物價格暴漲是什麼...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柴田明夫
- 出版社: 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09-08-27 ISBN/ISSN:978986636939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288頁
- 類別: 中文書> 科學> 應用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