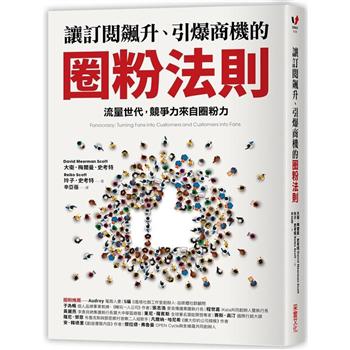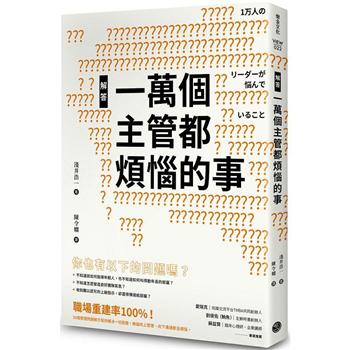我選擇直接衝撞方式,揹著相機走入城市,如野犬般,浪跡在人群街道間,
而這樣衝撞的能量越是強烈,反映在作品上也就越明顯……
日本攝影大師 森山大道 首部中文版作品
80年代傳奇攝影作品「野犬三部曲」第一部《犬的記憶》
進入大師世界的首要代表性自傳書籍。
2001年日文復刻再版;2004年英文精裝出版;2009年中文版感動上市
粗樸原始、強烈黑白照片風格,赤裸記錄城市人生風景。
影像中的青春感性和活力,表現人內在強韌的生命力,
感染力道十足,深刻打動了每一位城市人。
自喻為野犬的森山大道,自八○年代陸續寫就了《犬的記憶》、《犬的時光》、《犬的記憶──終章》等野犬三部曲,被譽為是進入大師世界的代表性自傳書籍。其中尤以《犬的記憶》一書為重,1982年首次出版;2001年復刻文庫版出版至今十餘刷;2004年出版英文精裝版。
與其說攝影是記錄,毋寧說攝影是記憶,一連串記憶積累的歷史過程。
同時也是時間的化石,更是光影的神話。
──森山大道
高職未畢業便離開制式教育的森山大道,強調街頭就是他的學校,靠自身學習成為攝影大家的過程令人傳誦。他以強烈黑白照片風格、擷取城市荒落一景,表現都市人孤獨冷漠但又契求與人建立聯繫的心情,感染力道十足,深刻打動了每一位城市人,被譽為是街拍大師。而他作品所呈現的青春感性和活力,表現人內在強韌的生命力,尤其受到當代日本及世界各地年輕人的喜愛及追隨。
「當我來到這個世界,邁出屬於我的人生時,其實我對於我之所以為我,還一點自信都沒有,而是逐漸才喚醒自己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自覺。才不久前,我的五感和第六感終於開始好好作用了,並且開始和那些促發了潛意識運作、也就是所謂的記憶的各式各樣的事物和事件產生了連繫,也讓我開始回溯這個所謂的我的個人歷史。
一九七一年我開始在青森縣拍攝流浪狗,當時我剛好從下榻的旅館走到大街上,一隻狗從我面前經過,這個機緣讓我拍下了它。從那時起,流浪狗就一直在心裡跟隨著我,這張照片讓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人們一想到我的作品,就會想到這張照片。」──森山大道
犬的記憶,既是這張感動大多數人的照片,也是自喻為野犬的森山大道的私人回憶。書中二十篇意味深長的文章,森山分享了他的生命經歷:他生活、工作之處,家人、朋友、感情,旅行所到之處,漫走於各個城市及鄉野之中……森山在記憶之中追索,在影像之中徘徊,透過文字挖掘出在影像中交錯的記憶與真實,以及帶給他的生命意義。
這些文字完美地契合了他所拍下充滿詩意的粗顆粒黑白照片。事實上閱讀森山的文字,也能讓人感到森山內在那份強韌的生命力。不加修飾的詞藻,赤裸裸呈現森山對於城市角落的敏銳觀察,那是一份昇華自人群中的能量,正如他所說:「我選擇直接衝撞方式,揹著相機走入城市,如野犬般,浪跡在人群街道間,而這樣衝撞的能量越是強烈,反映在作品上也就越直接明顯。」
作者簡介:
森山大道
1938年生於日本大阪,原只是一名默默無聞的平面設計師,後進入大阪岩宮武二攝影工作室擔任助理,為其攝影啟蒙階段。在照相館中偶然見到威廉‧克萊因的成名大作《紐約》,受到極大啟發;1961年決定轉赴東京,投靠細江英公門下從助理做起,並協助細江完成三島由紀夫攝影集《薔薇刑》。1964年獨立發展,以《相機每日》雜誌刊登的橫須賀美軍基地攝影作品初露頭角。
1968年首次出版攝影集《日本劇場寫真帖》,展現藝術家風格的強烈印記;1969年參與由攝影家中平卓馬及高梨豐,以及岡田隆彥(詩人)、多木浩二(評論家)共同創辦的《挑釁》雜誌,模糊、晃動、高反差、粗粒子,成為森山風格的明顯標記,並在日本廣告界形成一股狂熱模仿風潮。此一時期同時開始與作家寺山修司的合作關係。1970年出版《攝影再見》攝影集,作為自己該階段的總結。
70年代森山歷經自己生命中的整理期。作品風格轉而呈現失意、絶望,抑鬱黑色。為擺脫陰霾,森山受日本設計大師橫尾忠則之邀,遠赴紐約,游移在異國城市之中。
80年代,森山逐漸擺脫低迷,《光與影》表現森山昂首直視景物的鮮明意志,使日本評論家驚艷不已。媒體並以斗大標題報導:「森山大道終於回來了!」
90年代起,頻繁於日本海內外舉辦主題個展及大型回顧展,1999年舊金山當代藝術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等美國各城市巡迴展;2002年倫敦及紐約個展、2003法國卡地亞基金會大型回顧展;2004至2009年陸續在科隆、阿姆斯特丹、奧斯陸等城市受邀個展,及日本北海道各城市巡迴展覽。
攝影集及文集陸續出版數十本,包括《犬的記憶》三部曲、《遠野物語》、《新宿+森山大道》、《大阪+森山大道》、《寫真對話集》、《晝的學校、夜的學校》、《森山。新宿。荒木》、《另一個國度》等。
譯者簡介:
廖慧淑
東京外語專門學校日中翻譯科畢業,並於視丘攝影學院研修攝影。曾任《遠見》、《卓越》雜誌記者;《WA.SA.BI.日本四季之旅》、《AZ時尚旅遊》雜誌採訪編輯、日文編譯及攝影。目前為自由工作者,專職翻譯及攝影,譯作有《巴黎.家的私設計》、《這是一場從巴黎地鐵開始的小旅行》;攝影作品主要為音樂CD封面攝影、演唱會攝影及雜誌攝影。
章節試閱
※犬的記憶──陽光普照之處
我的哥哥名字叫做一道,虛歲二歲時離開人世。我跟哥哥是雙胞胎,當然我沒有任何關於哥哥的記憶,若說哥哥是森山家的翻版,那我就是哥哥的再翻版。因為我的名字是大道,是在哥哥名字的「一」字中,插入一個「人」,所以我存活下來了。
昭和十三年十月十日,接近中午的時刻,我們誕生於大阪府下池田町宇保(現在的池田市宇保町)的一家職工宿舍。根據母親的記憶,那天風和日麗。當時父親在一家總公司位於大阪的壽險公司上班。我們的出生地宇保位於郊外,周邊有很多樹木,屬於悽涼的住宅區,整天都會聽到某處傳來阪急電鐵寶塚線的鳴笛聲。
照理說我應該記不起當時的事,但不知為何,在我腦海中總是浮現某些影像。或許不該說那是既視感,因為在陽光普照的風景中,朦朧的影像總是不斷出現,很像是浮現在虛幻天空裡的蜃氣樓。
那年冬天,我們一家因為父親工作轉調,移居到廣島。聽說那時候我的身體好像非常虛弱,為了養生,雙親將我帶回故鄉托付給祖父母。祖父家位於島根縣的石見地方,是一處面向日本海的小村莊。我在那個海邊的村莊日漸懂事了。
那麼,偶爾浮現在眼前,如幻影般的光景,究竟從何處被喚醒呢?
池田町,現在的池田市,位於大阪平原的西北方。猪名川流經城鎮的盡頭,與兵庫縣西川市相連。從古時開始就是具有歷史的地方,比灘更早成為釀酒之地,因此池田也被稱為北攝的要衝。現今則是商業都市大阪的衛星城市,也殘留許多古時的商家及倉庫,既熱鬧又清靜。雖然我在這裡沒有幼兒時期的記憶,也沒有在某處與某人的共同記憶,然而不知為何,這裡卻令人懷念。緣因於此,在《朝日相機》雜誌第一回連載的「犬的記憶」專欄,我無論如何都想以此地為開端。
這裡不是我出生後成長的地方,也不是我的故鄉,更不用說也不熟悉。雖說有影像出現,但畢竟只是幻影。在我心中只留下「宇保」這個地名。然而在我記憶深處,朦朧輪廓、陽光普照之處,卻總是縈繞於心。
我並非想要追尋失去的時光。若我對池田這個地方沒有絲毫感傷的話,就無法產生望鄉之念。若無足以對照的過去,也無法將心情寄託於幻想,更不用說能夠對著幻影按下快門。更侈言,將過去與現在、或是將現在與過去重疊在一起檢驗記憶。本來所謂的記憶,就是呈現自己內心懷念的心情,而非再現個人的影像,以現在作為分水嶺,連結距離遙遠的時間點,跨越心中的領域。我能做的,僅有暫且先回到池田這個地方,將鏡頭面對著眼前的光景。這麼一來,突然傳至指尖的知覺,或許能夠喚醒記憶。懷著這樣的期待,我帶著相機,前往我的出生之地。
今年(一九八二年),一月中旬的某個週末,我在東京車站搭上「光號」(Hikari)。那天天氣晴朗,但午後非常寒冷。富士山看起來異常地美麗,前往大阪的電車裡,我逕自望向窗外,不可思議地,數十年後再度探訪的出生地,我卻沒有任何一點感慨,只是茫然地抽著菸。傍晚時刻,電車抵達大阪,我緊接著從人潮擁擠的阪急梅田站,轉乘寶塚線,十三、曾根、岡町、豐中等,令人懷念的站名逐漸出現,傷感也漸漸浮上心頭。不知是不是因為是週六的晚上,池田車站黑色人影熙熙攘攘。因感傷而濕潤的眼裡映現著街燈。我就像是一位旅人,探訪一處從未前往的地方,心情上也像是在測量遠近一樣,徘徊於時間與空間之中。我把相機背在肩上,重新收拾心情,姑且先朝著寒空中凝固不動星星的所在地前進。結果,那天夜晚,我就像是蟲一樣,從這個燈飛往下一個燈,只在車站周邊閒晃。因為天氣寒冷和多少有點疲累,想找個地方休息,我沒有拍下半張照片,為求溫暖,我很早就進入一家咖啡店休息。店裡的熱咖啡很好喝,我透過因暖氣而起霧的玻璃窗,觀望窗外忙碌的人們與車子,總算鬆了口氣,回到我自己。我想要探尋的記憶,對我來說,究竟是什麼呢?這才開始漫無邊際地思考了起來。
隔天星期天,我在梅田的新阪急飯店醒來。我想在出生地探尋假想記憶的想法,使得心情糾纏於某種鬱悶之中。雖然那天天氣晴朗,但是北風非常寒冷。我從飯店一路前往池田。在派出所問到往宇保町的路線,沿著鐵路線走了十五分鐘,進入城鎮。相隔四十三年,再度踏上的出生地,心情卻沒有特別的感慨。宇保町的中心地有一間古老、灰色調的神社,城鎮裡到處可見樹木,以及殘留的田地。關西地方特有、由矮樹籬笆圍繞的宅邸,與新建材、絢麗多彩的住宅,悄悄地併列一起,很安靜的地方。人影稀少,我從陽光普照的小巷,走進另一條小巷,眼裡又慢慢地浮現出那個幻影,於是,眼前實際的風景,漸漸地開始與腦中影像重疊。腦中縈繞著一種奇妙的錯覺,不管我看到什麼,都覺得這裡不是我的出生地。然而,阪急電車的警笛聲確實隨風傳來,同時也傳來焚火的味道。我再度察覺到自己捲入不可思議的時空中。重新整理心情,面對眼前的風景按下快門。其實不管拍哪裡都無所謂。移動著相機的觀景器,從陽光普照的地方,前往下一個向陽處,不知為何,我只記得自己在按下快門時,無力感油然而生。隨著情緒走動,卻無法將之與記憶對照。寒風中,頭頂上成群烏鴉飛舞,而噴射機穿越而過的聲響更顯得突出。我還是一樣搞不清楚時空,正午時分,就這麼緩慢地徘徊在宇保的路上。
我就像這樣,三天都在池田這個城鎮遊走,漫無邊際地拍下十幾卷底片,心情未獲釋然之際,我返回了東京。
這些影樣就像是X光片一樣,映射在我眼裡。是在哪一天看到的?是在夢中嗎?是晴天?陰天?是正片?還是負片?一切都無法判別。我只確定那是出現在陽光底下的景色。若是我在少年時期看到的任何東西,只要它存在記憶中,我就可以鮮明地記起那段影像,然後對自己說,那是實際發生的事……。
原風景,雖然我不想簡單的使用這樣的字眼,但是存在內心的幻景,某些部分就是像這個樣子。也說不定那是因為我得花費四十三年的時間,才能在我內心稍微顯現的烏托邦。現在日常生活中,從光與影的世界突然顯露的影像,或許就是因為感應到那個影像才會出現。至今我所拍的照片,還有現在開始為「犬的記憶」連載所拍的照片,都將以幻風景=原風景的基調繼續進行。
在出生地池田,宇保這個地名、雜草叢生路上,我自始至終都在想著這個問題。我又再度想起我是哥哥的再翻版,我與自己也不知道的分身、還有哥哥一道的存在,以及沒有記憶、出生時的秋日光景,再加上手裡拿著相機、茫然的自己,我就像是希臘神話中的阿麗雅德妮(Ariadne)轉動著線球到達那裡。那是我為了探尋陽光普照之處,三天微帶酸甜卻又苦澀的心靈之旅。
※我的寫真記──穿梭街頭
我的照片生平第一次印刷出來,是我成為自由攝影師不久後,刊登在那本《Photo Art》雜誌上,現在已經絶版了。因為在雜誌社有認識的人,雖然只登了一張照片在刊頭,但是因為這麼快就有工作,我覺得很高興。因為是第一次刊登在攝影雜誌,我興致勃勃地拍了二十卷底片交給他們,一直盼望書店快點販賣那本雜誌,發售的第一天,我就趕快跑去書店,翻開雜誌,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在上面,非常感動。我的照片在最前面,更何況還是印刷出來的,我有點自豪,覺得自己已經是專業攝影師,也有種預感覺得接下來會很順利。
但是接下來,完全沒有工作。雖然不覺得一開始當自由攝影師,馬上就會有工作進來。也不認為自己的名字很好賣,但是一直以來,看到細江先生的工作多到溢出來,因為落差實在太大,我覺得失敗了。
或許因為時機到了,從那時開始,攝影界開始出現華麗的樣貌,立木義浩《吐舌頭的天使》;篠山紀信《灼熱肉體》;橫須賀功光《Mode In》;高梨豐《辛苦了》;柳澤信《兩個城鎮的對話》;內藤正敏《日本的木乃伊》……幾乎都是與我同世代的攝影家們,一個接著一個,進駐、占據各本攝影雜誌,以新銳的姿態,開始鮮烈竄紅。總之,不管是照片,還是攝影界,持續流動,適逢轉換的年代。我雖然想要跳進時代的潮流,但是手上卻沒有任何東西足以讓我進入主流。所謂手上的東西,不是指具體的照片,而是指我必須要找出屬於我自己的礦脈。但是這種東西不是想要就有,也不是想找就會出現,我沒有辦法馬上進到主流。一直以來,拍照以及思考攝影相關事情的人,是另一個自己,所以無法看清現實,但是現在已經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沒有勇氣再背對眼前這條華麗的奔流,也不能再這麼悠閒自在,更不能再發呆下去。不知該說是幸運,還是不幸,我手邊沒有必須處理的工作,所以馬上就决定,「好,要開始認真做囉。」
於是,我首先做的事,就是全面否定我認為是主流的照片,為了區分哪個是主流,哪個是二流,花了一點時間。結果我把自己全部的作品都認定為二流,仔細一看這也不怎樣,總之全面否定。那麼照理說,我應該馬上就可以出門攝影才是,但是我手上連底片都沒有,而且就算想去某個遠處拍照也沒有資金。土門拳去了築豐,東松照明去了長崎,雖然我也想去遠地攝影,但看來不可能了。之後,我又想了三天三夜。腦袋裡總是出現東松先生所拍攝的照片影像。「啊!」我突然想到了。就在眼前的事,人常常會忽略掉,想了想,我結婚之後就移住到逗子市,而隔壁的城鎮就是橫須賀,也就是東松先生的那個名作《占領》系列的其中一個城鎮。那天晚上,透過想像我覺得自己已經拍到兩、三張名作。雖然軍事基地橫須賀就在附近,但是我竟然還沒去拍過,而縱然我想像中的畫面,馬上就跟東松先生拍過的照片重疊,但是那天夜裡,我决定了否定東松的作品,走出我自己的風格。心情就這樣直線上升。
年輕時候的想像,總是容易短線思考,但是也培養出直接了當的嗅覺與第六感。不是因為到了現在我才這樣說,我在那個時候有種直覺,覺得自己拍的橫須賀一定會被接受,而且還不光只是拍出好照片,絕對會成為不朽的東西。
我因為連底片也沒有,隔天早上就去東京,找一位擔任電影攝影助手的朋友,要了幾百英尺他們拍攝剩下的底片,花了一整個晚上,把底片裝進底片盒裡,然後隔天開始往返橫須賀。到鄰鎮的橫須賀,單程要三十日幣,從那天開始我每天都從妻子哪裡拿二百日幣,也就是交通費跟喝咖啡的錢。橫須賀的街角,很像我在小時候看到進駐軍的樣子,街道飄散著令人懷念的味道,我在第一天就喜歡上那裡。當時正處越南戰爭的最高潮,街道很荒亂,我常被地頭及擦鞋的人追趕,常會逃到ドブ板通(Dobuita Street)或是汐入的巷道裡,但是不知為何,追趕我的總是日本人。每當這個時候,我都會將相機藏起來,穿梭於橫須賀的巷道中。我不知道被拔起來多少卷底片,也曾經因為大腿被踢,跛了兩天。但是我覺得很有趣沒法停止拍照。我在橫須賀路上快攝,感受到生理上的快感。
我在美軍野戰背包裡隨身都會帶著《相機每日》雜誌,每當疲憊或是畏縮時,就會在路上將雜誌拿出來,翻開雜誌看其他人拍的照片,每次都覺得,拍得不怎麼樣,為自己增加勇氣。整整拍了兩個月之後,開始沖洗照片,雖然很想放大到四開的印相紙,但是相紙的費用太高,看來是不可能了。花了將近十天,冲洗出一百六十張、六開大小的照片。擔任細江先生的助手之後,第一次這麼認真沖洗照片。我迷上了乾燥之後自己拍的照片,現在想起來,覺得當時真可愛,覺得自己已經超越東松先生。我把當時攝影界的主流雜誌《相機每日》的全部照片,再一次重複翻看,將刊載的照片,與自己拍的照片相互比較。「好!」從全部沖洗出來的照片中,選出七十張。我知道有一位製作人,他能夠自由操作攝影界的流行,我在擔任細江先生助手時,曾經見過兩三次面,對方是叫我「細江君那裡的小朋友」的編輯。我從一開始就打算將照片拿給他看,在將照片拿去給他看之前,我好好的將照片放入箱子裡,綁上繩子,在上面寫著:「給相機每日,內附照片。主題:『橫須賀』,森山。」
我慎重地抱著那些照片,出發到許久未去的東京,辦完要事之後,到達每日新聞社所在地的有樂町,已經接近傍晚,夕陽西射。我看著眼前的新聞社,打了通電話到《相機每日》的編輯部。沒有事先連絡,突然打電話過去,我清楚地說我是細江先生的前助手,希望他們能看我的照片,請對方聯絡引領攝影界的負責人山岸章二先生。雖然只等了一會,但是那段時間我很緊張,胸口撲通撲通地跳。突然話機傳來口齒清晰的聲音,傳進耳裡,我就像是在夢中說話一樣。
「是,我是山岸。什麼,咦?是你啊!辭了細江那裡的工作?原來如此,什麼!帶了照片來了,喲,拍了什麼。啊?橫須賀?什麼啊,是拍基地啊,不太想看呢。什麼?現在已經在車站?好吧,那就拿來看看,馬上過來。」就掛了電話。好了,關鍵時刻來了。
每日新聞舊大樓位於有樂町站,隔一條道路的另一側,SOGO百貨公司前面。進入裡面以後,又舊又暗的建築物,電梯也是舊式的。我是第一次進入這棟大樓,當然不用說,到《相機每日》編輯部也是第一次。往雜亂的出版編輯室裡去,之前在細江事務所見過的山岸先生就在那。我用高昂的心情打了聲招呼,他笑了笑說:「是哪個,給我看。」接著就從我手上拿起箱子,快速地打開蓋子,拿出裡面的照片開始看。正確地來說,那不叫做看,而應該說是不斷地切換,就像是魔術師在切換撲克牌一樣,快速地切換。我花了二個月時間拍攝、十天沖洗、二天挑選的七十張照片,一分鐘都不到就切換完了。我呆呆地一邊看著那熟練的手法,看破了一切。一定是因為完全不有趣才會看得這麼快,變得頹喪起來。
山岸先生將看完的照片,原封不動交給坐在旁邊、年紀較長的人,之後就不知道去了什麼地方。那個年紀較長的人,跟山岸先生完全相反,一張一張仔細地看照片,我看到他充滿善意的動作,稍微出現了一點希望。大概是估計時間已經可以將照片看完,山岸先生回來問了那個年長的人說:「如何?」我把希望押在那位年長的人身上,「嗯?」左思右想了一下。我的所有夢想與自大,在那個時刻全都粉碎了。不管是身體還是心情,都像石頭一樣僵硬。山岸先生從那位年長的人手中接回照片說:「我覺得這個很有趣呢,」接著,就整理一下照片,拿在手裡,說了聲:「一起跟我來。」帶著我到一間排列著一堆桌子,很像會議室的寬廣房間,再次如機器一樣的速度分類照片。在細長的桌上排了大約二十張左右的照片。雖然我的心中想著,不會吧!不會吧!但是這次真的很期待,山岸先生推了兩張照片到我面前,問我:「喜歡哪一張?」又一邊像是變魔術一樣,快速移動照片。「好,就這樣!」看著我的臉笑了笑。結果,我在旁邊側視著一切,看似瞭解事態,其實卻又不然,當事情實際發生在面前時,我卻在發愣,瞬間,無法將心中所想之事,與映射在網膜的畫面相結合。對著茫然的我,山岸先生輕輕拍著我的肩膀,笑著說:「如何?九頁。刊載於八月號。」我只能不斷地向山岸致上最敬禮。
手舞足蹈,就是我在那個時候的情況。我生平第一次拿作品自我推銷,雖然說我本來就是朝著那個目標努力,但是為何一次就決定了呢。而且還是通過那個負責人山岸先生的手,刊登在《相機每日》上。我到底何時、如何從喜悅與興奮中醒來的?我已經記不起來。大概是因為在決定以前,我已經將所有的精力都用光了吧。
那一天對我來說,是在攝影界初露頭角的日子,也是山岸先生與我藉由照片相識的開始。之後經過很多年,到山岸先生前幾年過世為止的歲月,我要是沒有跟山岸先生邂逅的話,大概就沒有辦法繼續拍下去了吧。接受照顧,為什麼是這麼簡單的事呢。
(未完待續)
※犬的記憶──陽光普照之處
我的哥哥名字叫做一道,虛歲二歲時離開人世。我跟哥哥是雙胞胎,當然我沒有任何關於哥哥的記憶,若說哥哥是森山家的翻版,那我就是哥哥的再翻版。因為我的名字是大道,是在哥哥名字的「一」字中,插入一個「人」,所以我存活下來了。
昭和十三年十月十日,接近中午的時刻,我們誕生於大阪府下池田町宇保(現在的池田市宇保町)的一家職工宿舍。根據母親的記憶,那天風和日麗。當時父親在一家總公司位於大阪的壽險公司上班。我們的出生地宇保位於郊外,周邊有很多樹木,屬於悽涼的住宅區,整天都會聽到某處傳...
推薦序
導讀文章
關於森山大道/文‧沈昭良
「與其說攝影是記錄,毋寧說攝影是記憶,一連串記憶積累的歷史過程。同時也是時間的化石,更是光影的神話。」──森山大道
數十年來,一直以鮮明獨特的影像表現、強烈的民族風格、近乎苦行式的拍攝方式,遊走於世界各地城市;勇於開創的恣意與銳氣,即時回應時代與城市變遷,反覆梳理攝影與自我、時代、環境間關聯,影響諸多攝影創作者,而作品形式風格足以獨立成為攝影敘事論述,乃至曾於全球主要城市美術館舉行回顧展的攝影家,首推來自日本的森山大道絕不為過。
一九九九年,美國舊金山當代藝術博物館為森山大道舉辦了名為《彷徨之犬》的大型巡迴回顧展,森山攝影作品中那強烈而獨特的影像風格,廣受美國藝術界與媒體的普遍肯定。《美國藝術》甚至稱他是日本首位在美國一流藝術博物館舉辦完整回顧展的藝術家。《彷徨之犬》接著更巡展至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與日本協會畫廊。其後於二○○三年,法國卡地亞基金會同樣為他在巴黎舉辦大型回顧展。二○○八年,日本東京都攝影美術館為這位揚名全球的本國攝影家同時舉辦《夏威夷》個展及回顧展,同時出版關於森山大道作品的論文集。今年(二○○九)六月起至明年(二○一○年)三月止,森山更將伴循著記憶,史無前例地於北海道的札幌、夕張、美唄、東川町等地,大規模巡展北海道系列作品。
回顧森山在本書中,所陸續提及的幾個關鍵轉折和發展脈絡,森山可說在辭去細江英公的助理工作後,正式開啟他近乎壯遊式的,無悔開闊的攝影旅程。一九六九年三月,森山更在由中平卓馬、高梨豐等人發起的《挑釁》(Provoke)雜誌中嶄露頭角,模糊、晃動、脫焦、高反差和粗粒子,頓時成為森山作品風格的明顯標記,直接影響當時許多對攝影的形式與內容懷抱疑問的年輕攝影者。其後雖曾引發日本廣告業界一股令人尷尬的爭相模仿風潮,但森山已然在眾多追隨模仿者間,奠定其屹立不搖的根基。
綜觀森山大道的創作歷程,一九六八年集結出版的《日本劇場寫真帖》著實為森山烙下具作家風格的強力印記,惟七○年代的森山作品,普遍呈現失意、絕望和悲傷的抑鬱黑調。就連春暖和煦白花盛放的櫻花樹,不僅是在晦暗中綻放,枝葉也彷若乾枯血管般蔓延凋萎。長期關注森山作品的日本評論家,甚至懷疑森山是否會走上自殺一途。森山為擺脫這樣的陰霾,在整理完《攝影 再見》與《狩人》的出版原稿後,旋即遠赴紐約短暫停留,期間,除了歷訪藝術展館,森山游移在曼哈頓街頭的步履依舊晦澀沉重。
森山創作歷程中的另一個關鍵性壯遊,則是當《日本劇場寫真帖續集》(一九七八年)出版後,延續類似上述的質疑與探問,這次他選擇了北海道。
一九七八年晚春至初夏(五至七月),森山在友人的協助下,在位於札幌東部郊區的白石區租了一間公寓,開始他為期三個月的北海道行旅。由於是短期停留,森山只準備了一張小桌子和顯影底片所需的工具,同時以此處為基地,放射狀地往返於函館、小樽、旭川、萌留和網走等地。外出之餘,森山除了書寫攝影日誌與閱讀,陪伴他的幾乎就是失眠、長夜、低溫、土司和威士忌。
至於為何選擇遠赴北海道,除了森山希望藉由拍攝行為,檢視與驗證自我做為專業攝影家的意志與職能之外,尚含括森山深受明治初年,也是日本攝影發展黎明階段,由田本研造所攝之北海道作品的影響。由於這些攝影作品的拍攝動機,雖以調查、記錄和測量為主要目的,惟傑出的美學實踐,看在森山眼裡,實已超越攝影的資料性與記錄性意義。加上孩提時期的森山,即對津輕海峽那頭的北海道風情,懷抱著如異國般的嚮往,以及森山試圖讓自己身處在另一個陌生的環境,擺脫當時如同行屍走肉般的生活內容與氛圍等等複雜的緣由。
而這批迄今三十二年的珍貴底片,在森山緊接著進入下一個階段的創作後,並未能及時發表,也就這麼默默地在角落裡沉睡了三十餘年。直到二○○八年十二月,位於東京的Rat Hole Gallery為森山大道策劃了名為「北海道」的個展,這批作品才得以完整面貌公諸於世。
一九七○年代後半對森山大道而言,那段持續質疑,四處尋找自我與攝影關聯的蕭瑟歲月,從《攝影 再見》及《北海道》系列中,那股分別隱藏在抽象與具象之間,莫名漂浮的焦躁與無力感,對照現在的成熟穩健,應是既痛苦卻又甘醇甜美。綜覽《北海道》中諸如津輕海峽上的迷濛與浪濤,札幌市街的俯視擁塞,雜杳寂寥的市集,無亙綿延的濕原景緻,呼嘯疾駛的列車,車廂內濕黏的霧氣,女子青澀的回眸凝視……隱約望見那逐漸沒入荒原的纖瘦身影,拖行著探尋未知的步履,消逝在三十二年前的寒夜、北國。
直到一九八○年代,森山在精神上才逐漸擺脫低迷渾沌,《光與影》的付梓,更是重現森山昂首直視景物的鮮明意志,驚艷不已的日本評論家,甚至以斗大的標題宣示「森山大道終於回來了」。延續上述的脈絡,不難發現森山數十年來不同時期的作品中,緊密且及時回應他自身的生理與思想狀態。二○○九年四、五月間,為配合《光與影》攝影集的復刻發行,位於東京的BLD藝廊,重新推出「光與影」系列。由於展出內容與設計,獲得高度的評價與迴響,主辦單位甚至像演唱會般,以「安可」之名將展期延長了兩週。
至於其他各時期取材於城市街頭,諸如《日本劇場寫真帖》、《紐約》、《巴黎》、《布宜諾斯艾莉斯》、《新宿》、《東京》、《上海》、《夏威夷》等膾炙人口的攝影專題,也絕非只是即興式的街頭抓拍,而是含括森山與當下城市中的建築、景觀、人文、流行、氛圍等等對話的影像濃縮,內化後再藉由視覺形式所進行的深刻描寫。
二○○八年三月初,森山大道旋風式短暫停留台灣,謙卑有禮的應對,令所有接觸過他的人印象深刻。當然對這位才華洋溢、影像嗅覺敏銳,自喻為野犬般的街頭攝影家而言,寶島台灣自然是不可錯過的拍攝題材。他不免俗地登上台北一○一大樓的展望台,鳥瞰這個既陌生卻又似曾相識的國度與城市,隨即馬不停蹄地遊走在西門町、萬華、大稻埕、永康商圈的街頭巷弄間。其間,他不假思索地舉起相機鎖定、游移,狂躁如入無人之境。唯獨在龍山寺,森山如同台灣信眾一般,高舉整齊擺盤的玉蘭花虔誠禮佛,為即將歨入禮堂的女兒祈福,桀敖灑脫的浪子,頓時化為深情款款的慈父。
夜晚,則落腳在師大夜市附近的一處小咖啡館,那裡的內部陳設氛圍,近似陪伴他大半歲月的新宿黃金街酒吧商圈,更令他顯得輕鬆自在。混雜著裊裊炊煙與咖啡香氣,勾串著他的過往與追憶。直到午夜時分,野犬的身影,才兀自游移消逝在黝黯巷弄深處。
導讀文章關於森山大道/文‧沈昭良
「與其說攝影是記錄,毋寧說攝影是記憶,一連串記憶積累的歷史過程。同時也是時間的化石,更是光影的神話。」──森山大道
數十年來,一直以鮮明獨特的影像表現、強烈的民族風格、近乎苦行式的拍攝方式,遊走於世界各地城市;勇於開創的恣意與銳氣,即時回應時代與城市變遷,反覆梳理攝影與自我、時代、環境間關聯,影響諸多攝影創作者,而作品形式風格足以獨立成為攝影敘事論述,乃至曾於全球主要城市美術館舉行回顧展的攝影家,首推來自日本的森山大道絕不為過。
一九九九年,美國舊金山當代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