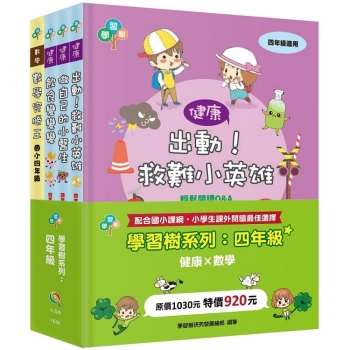【第一卷】幽冥一線
第一回•勞燕兮分飛
蘇州知府柳斜風,保持無所事事時的一貫姿態──昏睡,雖然外面的鼓被敲得「咚咚」山響,但習慣了的聲音傳入耳內,早已失去它的刺激性。
堂上的那張大椅其實坐著並不舒服,這種大椅純是為了威風,擺在那裡,椅子同人全是樣子,官兒樣子。除非你把兩隻腳也縮到椅子上去,或者你真的身長八尺,不然,是靠不到椅背的;如果你努力的靠到椅背,保證你的腰會特別酸。
坐這種椅子有個講究,坐在椅子上,兩手要扶住膝,背要挺直,全身唯一的支點放在臀部,目不斜視,不怒自威,正好和襯頭頂那塊匾上四個字「明鏡高懸」。不管內裡和不和襯,面子上總是要的。
柳斜風這位知府大人卻是向來不要面子的,人人知道蘇州知府柳大人是最實際的,只認錢,並不認面子,當然包括他自己的面子。所以他整個人斜斜地靠在椅子上,當然這樣子他的腳絕對無法安安穩穩地放在地上,他的腳架在桌子上,不,不能說桌子,因為知府衙門公堂正中擺的不會是桌子,那叫案,紫檀木的大案。
公堂上紫檀木的大案當然不是拿來放腳的,但柳斜風向來管不了那麼多,其他人也管不了那麼多,大家來到公堂之上自然不是為了管知府老爺的腳放在什麼地方。知府衙門的大堂是打官司的。
而且通常打到知府衙門的官司都不會太小,雞毛蒜皮的小事最好莫要麻煩柳大老爺的。這並不是因為知府大老爺公務煩忙,也不是因為大家體恤知府大人,而是因為實在是──太貴了。即便是三歲的孩子也知道,對著了位只認錢的大老爺打官司,怎麼可能不貴呢?
蘇州知府衙門破案的效率在全國各府衙若稱第二,便無人敢稱第一,自柳大人上任後,這裡從來沒有破不了的案子,但是,代價不菲。
打個比方:城東的李老爺兩年前丟了一頭牛,知府衙門的捕快半個時辰就在李麻子那間小破屋的後院找了回來。
可惜的是,那頭牛李老爺並沒能領回去,而是被柳大人斜著眼一瞪,就成了一頭「瘋牛」。這頭「瘋」了的雄壯耕牛被拉到西市在屠戶丘快手那裡,換到了兩片新鮮的黃牛肉,那李麻子還因為控制瘋牛有功,同他那七十多歲的老母分了兩條大大的後腿,至於其他的肉,大約是給柳大人下酒了。
更讓人意外的是,丘快手這位二把刀的獸醫居然很快就治好了「瘋牛」,拉到市集上又很快的賣了個好價錢。
花了五十兩銀子非但沒有整死李麻子,還白丟了一頭牛的李老爺,卻冤得欲哭無淚,真是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但那也是沒辦法的事,這位柳大人雖然很不像樣,卻有位非常像樣的爹,大儒柳至言。人人都知道,在渭南主持書院的柳大儒兩樣最多,一是書,一是學生,數萬卷的書,遍佈天下的學生。
據說,柳斜風應試時的主考陳尚書,就是柳至言的學生。又據說那柳斜風在試場整整睡了三天,卷子上一個字也沒寫,陳尚書雖然不敢把他取成頭名狀元,但放在三榜最後一名這種不打眼的位置,還是有能力做到的。
而把進士最後一名派到蘇州這個魚米之鄉來做知府,其中又有哪些貓膩(按:不可告人的黑幕)?那就不用再贅言了,凡長腦子的,都想得出。所以,即便蘇州府的這位「昏」官惹出再大的麻煩,上上下下都會有許多人義不容辭的挺身而出,替他鏟平,充分展示什麼叫做官官相護。
李老爺雖然很冤,可他那顆心總算是玲瓏剔透的,還不至於做些不長眼的事,既沒膽子與柳大人堅強的後盾抗爭,也強不過曾師爺口中那條三寸不爛之舌。便是打爛牙齒和血吞,那也是要吞的。
張狂與堅忍的個性總是具備在同一個人身上,尤其是有錢人。
柳大人還在睡,仰在公堂的大椅上睡,而且看上去睡得非常舒服。似乎正在做著什麼樣怪異的猗夢,歪起的一邊嘴角帶著一種痛苦的笑意。
衙役們依舊照足規矩壓低聲喝起堂威,柔和的「威武」聲中,驚堂木輕輕拍響。
驚堂木自然不是柳大人在睡夢中拍的,柳大人或許會在睡夢中做許多古怪的事,卻絕不會在睡夢中辦公。他的兩隻手只願意摸在美人身上。一塊爛木頭,他才不屑拍!
驚堂木是曾師爺拍的,曾師爺當然不例外的也是邵興師爺,同邵興府的女兒紅同樣醇的邵興師爺。女兒紅可以醇得讓人自口舌到腸胃一起放鬆,曾細雨更勝一籌,人如其名,醇得便如仲春時節的微微細雨,令人全身每個毛孔都感覺舒泰。
曾師爺做每件事都很細緻,就連拍一下驚堂木,那分寸都拿捏得恰到好處。「啪」的一聲,就如木炭在火盆中爆開,輕脆悅耳,絕不會驚擾到睡夢中的柳大人。
按照一般的程式,此時曾師爺應揚聲問:「何人擊鼓?」
可是今天狀況似乎有些不大一樣,尚未等曾師爺開口,一名男子已直撲進來,顧不得撕扯得稀爛的衣衫及腫得半天高的嘴唇,忍著痛大嚷:「王家同唐家打起來了,快請老爺去瞧瞧。」
蘇州知府衙門的辦事效率是驚人的,但今天效率又特別的高些,高得不能不讓人感慨,搶著看熱鬧當真是所有人的天性,尤其是在蘇州這個繁華得人人都能吃飽的地方。
一轉眼的工夫,捕頭李鐵已帶著四名捕快奔了出去,曾細雨一彈指,仍在昏睡的柳大人就被抬入了停在門口的大轎。
行到路上,面上仍帶著一貫微笑的曾細雨才低聲詢問:「袁里正,別急,慢慢說。」還不忘囑咐一句:「瞧你這嘴腫的,等會兒別忘了上點兒藥。」
那袁里正苦著臉,一口氣道:「王家的媳婦唐麗珍今兒早給人發現死在蓮香院的後巷裡。」歪著嘴,用手在脖子上比一下,「很深的一刀!那唐老爺一口咬定女兒是姑爺王正雲殺的,帶著傢伙上王家理論去了。您是知道的,王長天王老爺那『鬼刀王』的名聲可是響徹江南道的,一口刀可不是吹的,等閒誰敢惹他?但唐麗珍她爹唐百成是唐門嫡傳弟子,光是唐門的名兒聽著都讓人怕,這打起來怎麼得了?」
曾細雨心頭吃驚,面上卻不動聲色,拍拍袁里正肩頭:「不急!不急!屍首呢?」
袁里正手指前方:「唐家人抬走了,八成是擱去王家門口。」
曾細雨深吸一口氣:「王正雲呢?」
袁里正鼓著腮幫罵道:「那小子忒不是東西,事發時還睡在蓮香院紅袖的床上,唐家的人得信找去,連鞋都不及穿就跳上房頂逃了。」
曾細雨腹中冷哼一聲,心道:「這可有好戲看了。」
忽然一道急促而沙啞的聲音自轎中傳出:「快!快!跑快些,鬼刀王同唐門弟子打架,那一定好看得緊,要是沒讓老爺我看到好戲,打斷你們的腿!」
曾細雨不由笑出聲來,輕聲喝道:「還不快跑」
四個轎夫立刻如被鋼錐刺到屁股的驢子,腳不沾地,飛奔起來,兩旁閃過的蔥綠的樹影幾乎連成一線,不一會兒奔出閶門,來到閒春巷外。
王家的影園占據閒春巷的半邊,是蘇州城第二大園,只比拙政園小一些。巷口這時已擠得水洩不通,但是開道的大鑼一敲,人們也知道要讓出一條道來,因為兩家打架雖然熱鬧,但若加上柳大老爺那一定更有看頭。
巷口雖然是滿滿聳動的人頭,但巷內卻沒有半個閒雜人等。
殺氣自巷子深處激蕩出來,初春時節,雖然仍帶著些許寒意,但這裡迴旋的風卻夾著刺骨的痛,就連柔媚的陽光都被擋在了層層新芽的外面。石板路上細微的塵沙緩緩滾動,發出一種輕微的呻吟聲。
沒有人講話,只有刀與劍閃爍著藍瑩瑩的光。
捕頭李鐵抱著雙臂冷冷地站著,對於身邊劍拔弩張的兩家人視若無睹,只是冷冷地盯著仵作驗屍。
大轎輕輕的落在地上,轎簾打起,柳斜風兩肘支膝,雙手托腮,注目片刻,見兩家人只是相互怒視,卻是誰也不敢草率動手,心下無聊,一拍膝蓋,皺眉道:「這唱的是哪齣戲啊?我鑼鼓點兒都敲半天了,你們什麼時候開練?」
王長天身形高大,手中一口五六十斤的鬼頭刀橫在當胸,就似鐵塔般一動不動地定定直立,眼珠也是一動不動,對於這位柳大人的話充耳不聞。
唐百成的眉毛卻已輕輕挑起,手中泛著藍光的劍微微一擺,還劍入鞘,轉過頭來向著柳斜風抱拳:「大人既然來了,還請為在下主持公道。」言語雖然平和,卻說得咬牙切齒,目中的怒火竭力壓抑,仍是撐得目眥欲裂。
王長天冷「哼」一聲,鋼刀當胸,護住身後衣衫不整的兒子,厲聲道:「大人主持公道可以,但若冤枉小兒,老子這口刀可不答應。」
王正雲個子猶比乃父高出半頭,這時卻勾背縮肩,赤著一雙大腳,蒼白了面孔,躲在王長天身後微微發抖。
柳斜風吸吸鼻子,伸長脖子向停在邊上的屍首望一望。
仵作立刻直起腰來,輕輕走到轎旁,雙手呈上屍格。
柳斜風掃得一眼,似是並無心細看,轉手將屍格遞給站在轎旁的曾細雨,撇撇嘴抬頭道:「要公道也不用急在這會兒,好歹也是武林中人,有架不打,淨在這兒絮叨」打個哈欠,口中半陰不陽:「還真不怕丟了祖宗的臉?」
唐百成目中怒火噴射,再不搭話,身子倒拔而起,空中一個側轉,劍已離鞘,匹練般向王長天當胸刺出。
王長天暴喝一聲,鬼頭刀不避反迎,刀鋒過處,將唐百成的長劍震得歪過一旁,正是「鬼刀十八斬之劈風斬」。
鬼刀十八斬!王長天的成名刀法。當年他遠赴漠北學藝,同鬼頭蕭淒學得鬼刀十斬,回家後細加琢磨,自創八招,合成這鬼刀十八斬,在這江南道,博了個鬼刀王的名頭。
唐百成雙臂功力雖不及王長天,但唐門嫡傳弟子豈可小覷?手下經驗十分老到,右腕輕轉,劍鋒順勢斜削,身子一滑,自王長天腋下穿過,狹長的劍身蛇信般向王長天小腹刺去。
王長天的鬼刀十八斬本是漠北一派的功夫,剛猛固然有餘,但靈巧度著實不夠。偏偏唐門的招數最是陰狠毒辣,再加上劍鋒淬有劇毒,更是如虎添翼。
唐百成瘦小的身子滑似游魚,在王長天身周左穿右出,長劍專在王長天小腹攻擊,口中兀自喃喃咒罵,舌鋒之狠毒比之劍鋒不遑多讓。
王長天眼中瞧著陰藍的劍光,耳內聽著唐百成左一句「龜兒子」,右一句「斷子絕孫」,再加上王家十八代的祖先,直氣得火冒三丈,再不管唐百成耍什麼花巧,只使開鬼刀十八斬,一刀刀向唐百成猛劈過去。
這一發狠,果然陰風陣陣,唐百成立刻感到氣促,咬緊牙關力挺,口中那些惡毒言語也就說不出來。但他心中倒也並不緊張,知府大人面前,諒王長天還沒膽子真的殺了他。心中放鬆,手上長劍更是得心應手,仍是在王長天周身不住轉悠。
王長天雖然一把刀使得如開天劈地一般,但心中確有顧忌,倒不是因為知府的名頭,官府再如何強霸,為了王正雲這棵王家獨苗,大不了遠走天涯。
但這位柳斜風卻非同一般官員,因為他不止有一個不同一般的爹,還有一個不同一般的娘,睡美人于夢。于夢十六歲時就已聲名遠播,因為她的姐姐于知做了華山掌門,是華山派數百年來第一位女掌門。
于夢最喜歡的不是行走江湖,而是睡覺,她的看家本領就叫做「厭厭春睡手」,她很少醒著,許多事都在夢中做,包括殺人。于夢實在太愛睡覺了,出道剛剛兩年,一不小心睡到了大儒柳至言的床上,於是第二天就迷迷糊糊的成了柳夫人。
沒有人有膽子吵睡美人睡覺,只有她那寶貝兒子柳斜風,做娘的自然捨不得責罵兒子,但造成寶貝兒子吵她睡覺的原凶卻絕不會放過。她的方式一向簡單,就是睡到華山派大殿的正中,直到家姐于知帶同華山弟子將那原凶捉來,她才肯回到自家床上去睡。
現在替柳斜風抬轎子的霸橋四地龍,就是不小心打了柳斜風的驢子,結果自己變成了四頭健驢。
整整三十年,江湖上都公認睡美人是最難纏的人物,雖然她只是在睡覺。
王長天的鬼刀十八斬靠的就是一股如雷氣勢,這會子心中有所顧忌,不能盡情放開手腳,氣勢根本外強中乾,看似占了上風,實則處處受制。眼見唐百成長劍越來越順手,劍尖直點到面前,心頭暗想:唐百成雖然也不敢當著知府大人面前殺了他,但他劍上淬毒,就算劃開一點兒皮肉,也必然原氣大傷。
鬥得半刻,王長天終於心中發狠,手上鋼刀立刻快捷數倍,逼得唐百成連連後退,連攻數招後,一刀橫砍過去,鋼刀距唐百成脖子僅有三寸。
王長天忽然醒覺,心頭大叫不好,腕上力道急收,但已來不及,驀地小腿一麻,身子不由向下矮得幾分,刀鋒便也向下偏了幾寸,堪堪避開了要害,整整齊齊在唐百成的胸前劃開一道傷口,好在傷口不深,不過淺淺的一痕。
柳斜風在轎中直起腰來,輕輕拍掌,笑道:「好刀法!這一刀應是第『十六斬斷魂斬』第三式『幽冥一線』吧?本官可有看錯?」手指輕彈。
垂手立在旁邊的仵作立刻上前,扒開唐百成胸口的衣衫細看一回,直起身來道:「是!就是這一刀!同死者唐麗珍頸部刀傷一模一樣,確是王家家傳刀法幽冥一線。」
柳斜風吹個口哨:「你也算是老江湖了,怎麼還這麼血氣方剛?真經不起逗,說兩句就拼上老命了。那!有多少家底都能給你洩光了。一個字,笨!」
王長天頓時呆若木雞,手中的鋼刀落地,汗如雨下,喃喃念道「不會的,不會的,不會是雲兒殺的……」忽然轉過頭去,一把扯過王正雲,厲聲道:「說!人不是你殺的!說啊!」手臂青筋浮突,抓著王正雲的衣襟不住搖動。
王正雲面無人色,張著一雙驚恐的大眼,只是「啊啊」連聲,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捕頭李鐵面無表情地踏步過來,右手在王長天臂上一拂,左手已提開王正雲,直拖到柳斜風轎前,在他腿彎踢了一腳,王正雲「咚」地跪倒在地。
曾細雨展開手中屍格,斷斷續續地輕聲念道:「全身衣飾整齊,一刀弊命……傷口在頸中,長三寸六分,喉管切斷,全身無其他傷痕……」邊念邊行到屍首旁彎身瞧一瞧,伸手將唐麗珍胸前衣襟拉平,停得一下,又看著屍格皺皺眉:「右手指甲有紅色粉末?死亡時間應是昨夜三更左右。」抬頭再問仵作:「沒有其他了?」仵作搖頭。
捕快張三倌捧上一個托盤道:「死者手中握著半塊玉佩。」
曾細雨伸手取起,是半塊和闐白玉,玉質細潤,似乎是一個人形,一角有些些黑色。他眼睛一亮,脫口道:「好漂亮的唐飛天,可惜殘了。」將那佩舉到王正雲面前輕聲問:「認得嗎?」
王正雲「吶吶」連聲,一雙眼現出恐懼之色,張開嘴尚未發出聲音,站在他身後的唐百成已搶著道:「是王正雲的東西,這是他們訂婚時,咱家送的禮,那一角的黑色水銀沁是假不了的。」說著飛起一足踢在王正雲後腰,罵道:「果然是你這畜生。」說著又要上前撕打。
兩名捕快急忙上前將他攔住。
王正雲這時才叫出聲來:「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昨兒晚我一直都同紅袖在一起,我一直都同她在一起啊!大人,冤枉!」
唐百成一聽怒火更炙,指著他痛罵:「你這龜兒子,我女兒哪裡對不起你,結婚還不到兩年你就成天泡在妓院裡,你!你!你……」眼中狠惡之色閃過,手腕一翻已扣住一把毒針。
一少年男子飛撲上前,攔腰將他抱住,叫道:「爹,您別衝動,這兒柳大人自會還姐姐一個公道,可犯不著給王家把柄。」
唐百成深吸一口氣,一雙眼利刃般看向柳斜風。
柳斜風伸伸腰,揉揉後頸,懶懶地問:「還有半塊呢?」
張三倌提過一個包,躬身道:「在紅袖的屋子裡,還繫在王正雲腰帶上。」
柳斜風雙眼連眨,向著李鐵問:「李捕頭,紅袖呢?」
李鐵仍是雙臂抱在胸前,木然不動,卻有兩名捕快自後面人群中拉出一名女子,架到柳斜風轎前跪下。
那女子正是蓮香院的紅牌姑娘紅袖,本來花樣的女子,被這麼一折騰,哪裡還有人樣?只見紅袖內裡是粉紅的小肚兜,外面卻罩了件男子長衫,歪歪斜斜的裹著,鬢髮散亂,面上殘妝,東一搭西一搭糊成一團。
柳斜風眼中卻立刻充滿笑意,面上浮出一種憐惜之色,柔聲道:「嚇著了吧?沒事,別怕,唉!看這樣子昨晚一定沒睡好吧?」
紅袖面上微微一紅,垂首道:「妾身昨晚睡得挺好。」眼波向旁邊的王正雲一橫,嬌聲再道:「昨晚咱們二更就睡了,妾身累極了,一直睡到天亮才被吵醒,連夢都沒做一個。」微微側頭,眼尾媚光柔柔閃動。
柳斜風輕輕笑了,擺一擺手,轎簾落下,四名轎夫四隻大手在轎桿上一推,那轎子原地打轉,已倒過頭,鑼聲響起,眨眼工夫已出了巷口。
曾細雨輕輕嘆氣,望著王正雲不住搖頭。
王長天的眼淚終於滑出眼眶,怔怔地愣在當場,眼看著兩名捕快架著茫然失措的王正雲離去。
夜,悄悄降臨,溫柔的月牙含羞爬上絲絨樣的天幕。
柳斜風斜在一張貴妃榻上,這貴妃榻有著非常優雅的式樣,一邊兒有斜斜捲起的靠背,似貴妃一樣的美女慵懶地倚在上面,會有說不出的風情,圖畫中常有這樣的畫面,一般叫「美人春睡圖」。
可是,正倚在這張貴妃榻上的不是哪個美人,而是柳斜風,雖然他的樣子也很慵懶,但這畫面實在不敢恭維,好似一堆爛泥糊在了優雅的貴妃榻上,令人不忍卒睹,而這堆爛泥手上還抓著一隻酒瓶。
曾細雨就皺著眉看著他,過半晌,終於嘆道:「令尊令堂可謂人中龍鳳,怎麼會生出你這種兒子?什麼好處傳到你身上都大打折扣。」
柳斜風笑了,笑得非常開心的樣子:「我老子娘的事要你多嘴,倒是你在那唐麗珍身上摸了什麼東西?到現在還不拿出來瞧瞧,能讓你看上眼的東西總有些來頭。」
曾細雨長嘆一口氣:「怎麼一口咬定我在她身上拿東西,你哪隻眼瞧見了?」
柳斜風指指胸口:「心眼!你走過去看唐麗珍的屍體,卻並不對著屍格所寫核對,偏偏去整她的衣襟,唐麗珍衣衫整齊,可需你多事?」
曾細雨狠瞪他一眼,罵道:「小心眼!」伸手自懷中摸出一塊雞心佩來,臉上又露出笑來:「原來唐家喜歡唐玉,只可惜全家人都瘦得只剩一把骨,卻不似唐人那般肥肥的。嘖嘖,這塊雞心佩還真是不錯,可惜玉色灰了些。」
忽然轉過頭來問:「你還不去案發現場瞧瞧?」
柳斜風搖搖頭:「妓院的前門一向是沖洗得油光水滑,有時還灑著花瓣,但這後巷卻不是人去的地方,什麼阿咋物都從後巷倒出來,長年累月積得滿是黑泥,踩大力些會拔不起腳來。」
「所以你不去?」
「我怕弄髒鞋。」
曾細雨嘆一口氣:「看來王大少是死定了!」
柳斜風懶懶地也嘆一口氣,忽然又問:「那王家少奶奶用她美麗的小指甲在牆磚上刻了什麼字?」
「一個雨字少了一點兒。」曾細雨端起茶呷一口。
柳斜風又笑:「原來你已去過那條後巷了,這會子卻來蒙我。」
曾細雨撇撇嘴:「那種你都不去的地方,我怎麼會去?是張三倌報的。」輕笑一聲接著道:「其實那不是一個雨字,那應該是雲字的一半兒。」
柳斜風也笑起來:「這王大少真不簡單,一刀就把老婆的脖子砍斷了三分之一,他老婆輕功那樣好,為什麼不跑?」
曾細雨怪問:「你怎麼知道他老婆輕功好?」
柳斜風半抬起身來「嘿嘿」笑:「她身上沾得都是黑泥,可那雙小小繡花鞋子的鞋底卻乾淨得很,別說黑泥了,一星半點兒灰塵也沒有,所以她一定輕功極好,人家踏雪無痕,她踏黑泥無痕。」
曾細雨摸摸下巴沉吟到:「我怎麼就沒注意到她腳底沒有泥?」
柳斜風冷哼一聲:「你只注意她脖子上掛的玉佩。」
曾細雨咳一聲:「所以你不要去那妓院的後巷?因為人並不是在那裡被殺的?」
柳斜風懶懶地接話:「牆上的字大概也不是王家少奶奶自己刻的。」
曾細雨沉吟:「喉管被一刀砍斷的人確實沒辦法在牆上刻字,所以王家大少爺不是兇手,這是有人要嫁禍給他。兇手知道王正雲當晚住在蓮香院,所以殺了唐麗珍後將屍首搬到蓮香院後巷,拿著她的手指在牆上刻下那半個雲字,然後將王正雲那半塊玉佩塞在唐麗珍手中。」
柳斜風「啪啪」地拍起掌來,再喝一口酒:「真長進了,講得似模似樣。」
曾細雨信心大增,心頭激動,站起來踱兩步,忽道:「那我們為什麼還不把王大少放了呢?」
柳斜風四腳張開道:「關我什麼事?人好像不是我帶回來的。」
曾細雨搖搖頭:「可是大人你的酒錢已經沒了。」
柳斜風似被針扎到屁股,「騰」地跳起來:「十萬兩這麼快用完?」
曾細雨攤攤手:「虎丘那邊滑坡,轉眼就用光了。所以這蘇州城首富的兒子說什麼都得要再關幾天,不然這兩天你柳大老爺就得渴死。」
柳斜風搖搖手中的酒瓶,湊過嘴去,小心地輕啜一口,無限滿足地嘆氣:「對對對!至少得再關他五六七八天。」
「為什麼呢?」
「娶了老婆就不該再上妓院。」
「這話什麼人說的?」
「女人都這樣說!」
「是嗎?」
「沒錯!連浣花館的小楚兒都常常這樣說。」
曾細雨點頭:「雖然女人說的話通常聽不得,但這句總還是對的。」心中卻在盤算,「好不容易等著這麼個由頭,還管他王正雲是不是殺人兇手,沒把這蘇州首富扒掉三層皮,可不好意思善罷干休。」
柳斜風忽然傷感地望著窗外,喃喃道:「楚兒好久沒來看我了。」
曾細雨自鼻子中哼出聲來:「浣花館的姑娘鼻子忒靈,尤其是你那小楚兒。所以,你最好快快賺錢,憑楚兒的本事,十里外就能聞到銀子味兒。」
柳斜風搖著頭努力自貴妃榻上爬起來,心中似有萬般不甘。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斜風細雨不須歸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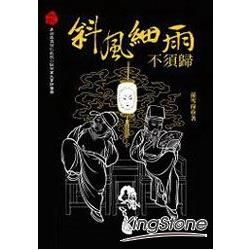 |
斜風細雨不須歸 作者:孫雪僮 出版社: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8-1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96 |
其他武俠小說 |
電子書 |
$ 210 |
小說 |
$ 246 |
武俠小說 |
$ 246 |
武俠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斜風細雨不須歸
抽絲剝繭,詭譎層疊
佳人才情,令人驚豔
名作家駱以軍、武俠評論名家林保淳、大陸知名作家張寶瑞 推薦
《斜風細雨不須歸》由三篇偵探武俠短篇集結而成。
懸疑、蹊蹺而離奇的故事安排,有古龍的詭思、有公案劇語言脈絡、有卜洛克推理角色經營。
柳斜風,一位又貪又色又愛酒的知府;
曾細語,一位笑裡藏刀的師爺,
如何破解江湖上如真似假的三道詭謎?
且看---
〈幽冥一線〉
他的妻子死了,會使「幽冥一線」劍法的,看似都有嫌疑。兇手呼之欲出之際,牽扯出劇毒「三日醉」的秘密,那三日醉之毒有得解嗎?
〈佳人如畫〉
鬼氣森森的寒山寺,魔女彷彿要從畫中走出;一眾和尚接二連三遇害,樁樁命案,癲狂的殺人魔是畫中佳人?
〈卿須憐我〉
一彎蘭舟上殺殺打打,情孽難捨,迷離的是岸邊景色、款款情意,以及看似無端上演卻不動聲色的一齣齣好戲。
本書特色
第四屆溫世仁武俠小說百萬大賞評審獎 作品
作者簡介:
孫雪僮
年齡:可大可小,化妝的時候取決於化妝的技術,不化妝的時候取決於穿什麼衣服。反正又不是相親,用不著合八字是吧?
性別:女,這點從來沒引起懷疑。
籍貫:祖籍東北(不會說東北話),出生在西北(話倒是會說,架就不會打),在東南方混跡十幾年(沒找到地方落戶)。
喜好:游泳(比速度基本不行,比定力那就罕逢敵手,要比嗎?請跟出版社聯絡)。睡覺(這跟屬相有關,應歸類為先天因素)。
作品:還在寫,只要大家喜歡,我打字的速度還是挺快的。粗製濫造?當然不會,雖然不做質量管理很多年了,但品質意識紮根很深。
第四屆溫世仁武俠小說百萬大賞 評審獎得主
章節試閱
【第一卷】幽冥一線第一回•勞燕兮分飛蘇州知府柳斜風,保持無所事事時的一貫姿態──昏睡,雖然外面的鼓被敲得「咚咚」山響,但習慣了的聲音傳入耳內,早已失去它的刺激性。堂上的那張大椅其實坐著並不舒服,這種大椅純是為了威風,擺在那裡,椅子同人全是樣子,官兒樣子。除非你把兩隻腳也縮到椅子上去,或者你真的身長八尺,不然,是靠不到椅背的;如果你努力的靠到椅背,保證你的腰會特別酸。坐這種椅子有個講究,坐在椅子上,兩手要扶住膝,背要挺直,全身唯一的支點放在臀部,目不斜視,不怒自威,正好和襯頭頂那塊匾上四個字「明鏡...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孫雪僮
- 出版社: 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8-10 ISBN/ISSN:9789866375163
- 語言:繁體中文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武俠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