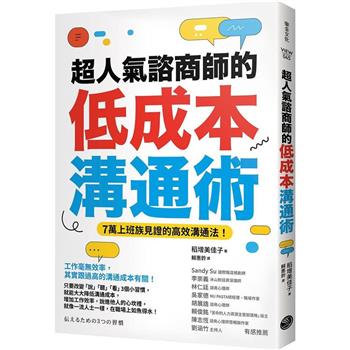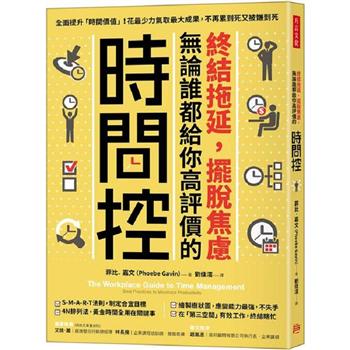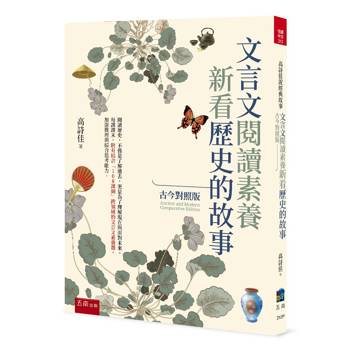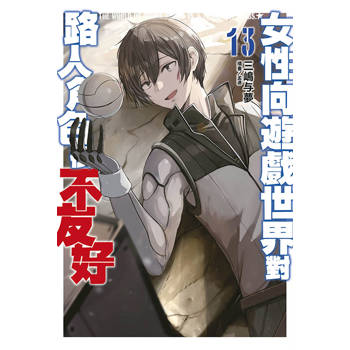【歷久靡新的都會經典∕徵婚啟事20年紀念版】
屏風表演班舞台劇《徵婚啟事》原著小說(1993、1998、2002三度搬演,2009將展開環島巡演)
導演陳國富改編電影《徵婚啟事》(劉若英以此片獲亞太影展最佳女主角)
★收錄20年紀念版新序<我祝你們幸福>
「我們見面的那一天,風很大,我目睹一顆流星的殞落。他走近我時,手上抱著摩托車鋼盔,嘴上啣一根菸……」——第五個男人
「我至今不清楚,自己究竟不喜歡他血色太黑的嘴唇還是無法自拔的憂鬱症。我自己有時候也不快樂,但是他的憂鬱中似乎含有太多的自虐。」——第二十三個男人
「我試探性地問:會不會和我這種人結婚?沒想到他居然說:同居可不可以?」——第二十八個男人
「生無悔,死無懼,不需經濟基礎,對離異無挫折感,願先友後婚,非介紹所,無誠勿試。」
這是一名女性與42位男性徵婚的記錄。
二十年前,作家陳玉慧在劇場與文字間尋找一種新的形式與觀念,在報上刊載了一則徵婚啟事,邂逅了107位男人和1名女士,開啟一場報導式的無形劇場,而演員共通點便是寂寞單身。《徵婚啟事》記錄作者與其中42名男子徵婚的過程,以極具創意的形式呈現最真實的人性與情感。在邊緣與主流之間探索,作者看見了男人的寂寞;而從她的書裡,或許我們也看見自己和整座城市的寂寞。
作者簡介
陳玉慧
在台北讀中文系,去巴黎學戲劇表演,到紐約外外百老匯當導演,後來留在德國擔任《聯合報》駐歐特派員。法國國家社會科學研究院文學及歷史系碩士。曾獲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香港浸會大學「紅樓夢獎」決審團獎,及台灣新聞評議會主辦的傑出新聞人員獎等。當過演員和編劇,也導演過許多膾炙人口的大戲,如與明華園合作之《戲螞蟻》。去過許多戰爭和國際新聞的現場,訪問過無數國際領袖與菁英,多年來不定期為德語媒體《南德日報》及《法蘭克福廣訊報》撰稿。被舞蹈家林懷民譽為當代最動人的散文家,文學評論家陳芳明稱以台灣的「世界之窗」,著名德國作家史諦曼(Tilman Spengler)認為是「德國文壇最值得期待的新進作家」。暢銷作品《徵婚啟事》曾改編成舞台劇及電影,轟動一時;而影射台灣百年歷史的長篇《海神家族》已在德國出版,且將搬上國家戲劇院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