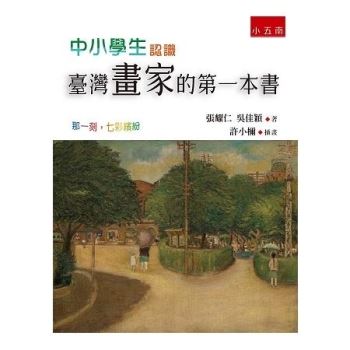【輯一.被困住的時光】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塔羅牌
很多年後,他逐漸相信:當事物不可逆轉地變得貧乏、扁薄、失去原先於各凹凸稜角閃閃發光的神性,那只是整個世界退縮回那個不再紛亂流動、蹦跳竄走的靜物幻燈片。
他父親從遠方攝下,寄回來給他們的那些幻燈片。
那是一個過度曝光的世界:枯旱荒野中一棵巨大的樹,乍看眼花,覺得樹頂重疊蒙覆著一片色彩妖異的葉片,瞪視細部才發現,那全不是葉子,在每一枝椏分杈處,每一像絕望手指朝天撐張的這棵枯死之樹的每一根白色的尖細末端,全棲息著一隻一隻的鳥。也就是說,單在這株樹梢上,便窩聚著上千隻的鳥群。
幻燈片裡的世界是在地球另一端的非洲。他父親是台灣當年派往非洲邦交國教導對方農民水稻耕作技術的農耕隊裡的一員。那些幻燈片更多的被攝對象,是一臉茫然,臉、手臂、腿……黑到不能再黑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強光下塵土飛揚的茅草屋、牛頭骨、蒼蠅覆滿的一盆甘薯……
他們總在山裡空無傢俱的屋裡,黑暗中一家人圍著看那無聲的、粉末狀、強光飽和從機器噴出的、投影在壁牆上變得高矗甚至有某種神聖性的,父親寄來的幻燈片。
他九歲那年父親過世。那些從幻燈片裡被叫喚出來的白光幻影,成了他父親留在他記憶中的某種空洞、漂浮、純淨的,「活著的時光」。那之後的,他一腳踩進的真實世界,就和這島國上所有經歷過那繁榮、瘋狂、縱慾、躁鬱、綜藝……年代,以至於眼翳上皆沾上一層油彩的一整代人所曾見識過的感官爆炸場景無有二致。他國二那年,他們的健康教育老師(一個國字臉的,深受學生愛戴,上十四、十五那兩章可以用一種對大人的尊重態度,毫不曖昧遮掩地詳盡向他們細細解說男女性器官的男老師)殺了他們的英文老師(一個甜美得像蝴蝶般的大姊姊),並將她的屍體肢解、剁碎、煮熟。當然是情殺。檢察官和刑警們押著那男老師到掩埋(其實是任意棄置)屍塊的校園後方的一片田隴上拾撿那女老師的碎骸時,這鄉下學校的管理階層竟完全沒禁阻那些好奇學生們,圍在現場旁觀著大人們用長鋁夾一塊一塊撿起那些爬滿蛆的肉塊(可能是女老師的某一片肝臟、某一塊臗骨或耳朵什麼的),放進黑膠垃圾袋中。
父親過世之後,家計靠母親在工地扛水泥撐起,作為家中唯一的男孩,有一段漫長時光特別難熬。記憶中他父親高大而英俊,埋入墓穴裡的屍身像百合花一般潔白。但成為孤雁的母親,可能為了能有更多工地的粗活可接(這是他長大後才回頭去體諒理解),總置身在那些粗鄙醜惡的工頭和男工間喝酒。在那工地特有的水泥腥味,那些比他父親黑壯的身體群蒸騰而出的汗臭味之間,還有一種他那年紀無法理解卻如幼豹憤怒屈辱以對的生殖氣味。那在更難以言喻的複式時光領會後,他或能艱難描摹出母親比他們任何一人更要悲慟絕望。因之不僅是為了養家而將身體的女性質地放棄被保護形式,且因消沉、孤獨,因他來不及長大頂替父親空缺的那家中男主人位置,母親在衰老壞毀之前,便徹底沒入那顏色污濁的底層之海。
因為貧窮,他和同齡之人有著完全不同的少年時光。
因為發育較慢,個子遠不及班上那些少年抽長及壯突的速度,他長期被一個日後回想起來心智和意志皆遠不及他的陰暗傢伙盯上並霸凌。很長的一段記憶是他用大灶堆柴升火煮全家人的晚餐。他用法西斯的方式管理一群豬隻,餵牠們吃ㄆㄨㄣ,清洗牠們的糞便,以木棒痛擊牠們。有一次這些豬隻們發動了一場半像遊戲半像謀殺的集體行動:其中一隻帶頭者將他拱上背脊,然後像足球隊員三角短傳那樣,力道柔軟地將他在不同豬隻間的脊梁間彈甩著。那時他既恐懼(牠們要殺了我?)卻又充滿少年承受未曾經歷之愛撫那樣輕飄飄且無比幸福。最後一隻豬把他拱摔在牠們的糞便堆中。
在人人危言聳聽,臉色暗沉口耳相傳那個「金融海嘯」、「大蕭條年代」來臨之前,他曾那麼努力讓自己進入那座大教堂般,萬事萬物俱閃閃發光的嶄新世界。有人說這是人類歷史以來最富有的三十年。他名下的財產,有一間內湖捷運站旁房價最高時上喊逼近兩千萬元的大廈公寓(雖然他仍要繳十年以上的房貸),有一輛百萬元左右的馬自達RV車,有股票、海外基金、保險……雖然戶頭裡的存款不到十萬元,但嚴格說可算符合坊間那些理財書籍說的全面性理財形式。他不到四十歲,所擁有的絕非同齡時的他父親所能夢想。
事情發生在那萬事萬物皆褪色晦黯,如古早狐仙故事鈔票變回榕樹葉、金子變成硬土疙瘩、金漆馬車變回南瓜的灰撲撲辰光。有一天他竟然在公司附近一處騎樓看見許久不曾出現之大排長龍人群隊伍:原來人人推著一輛腳踏車,等著店鋪裡一位彷彿他中學時代懷舊黑白照片的老師傅,蹲著把一輛腳踏車暗紅色內胎剝出,放在水盆裡測試破孔處,並用銼刀磨平該處、等著糊上強力膠將補胎皮黏上……。世界再一次像他父親那些發著白光、無聲但美麗的幻燈片飄浮遠去,只剩下暗影疲憊沾滿油污的凡胎濁骨……
那天,他按朋友的介紹,到一位據說靈驗無比的塔羅牌老師工作室算命。對方要他洗牌抽牌時他便確定這只是一場蕭條年代討生活的某種騙術罷了。他抽到一張「高塔」。牌面上似乎畫著天頂有雷霆閃光將一座中世紀鐘樓擊毀。他恍神不經意地聽著那陰性氣質的年輕人用華麗空洞的詞藻編排著他的命運。有一瞬間他突生異想:如果這抽翻的一張一張牌,上頭是他父親當年遠從非洲寄回的那些幻燈片:那些枯樹頂梢上的群鳥,那些比黑夜還純淨之黑的男孩女孩,那些熾白強光下的荒原、濁黃的河流、鮮豔的花朵……?是否更貼近他想以簡御繁,以隱喻描述這個父不在的真實世界的渴望?
那天的晚間新聞他竟看見電視上特寫的照片不正是那位替他算命(並且告訴他他將遭遇的一切苦厄都是此生要學習的「功課」)的塔羅老師嗎?他們說他只是個十六歲的國中輟學生,曾裝神弄鬼騙了那位因貪瀆而官司纏身的前總統。他曾替他卜算,據說當時那位擅於以漫天飛花般華麗語言錯幻織編各式烏托邦、魔境、倒影之城的權力巫師,抽中的是「死神」牌,但另有一說是「戰車」牌,於是記者們或輕佻地以好萊塢電影情節《神鬼交鋒》的橋段嘲弄這場荒謬降格喜劇,或一本正經分析兩種不同牌面所暗示的未來命運……
但那天夜裡,他滿臉淚水地從一個充滿懷念、悲傷的夢中醒來。在那個夢裡,他又變回小男孩模樣,趴在他這座大廈公寓的窗邊向外望,眼下的整座城市已變成一片廢墟,文明繁華已不再。遠方原該是一○一大樓的那高矗地標變成了一座塔羅牌上畫的塔樓,月光下散放著銀色光輝。他無比清楚看見他的父親被關在那塔頂,目光灼灼看著他。然後,既像撫慰又像擔憂,朝他伸出雙手,那手臂像不斷抽長的海芋花莖,穿透那整座曾繁榮又衰敗的城市上空,穿透多少個他淚水往肚裡流的艱難孤寂時光,伸到他面前,撫摸著他的雙頰。
【輯二.晃走的城市】夜遊神
搬進城裡已好幾年。奇妙的是勾動我想起此事,恰是因這些天乍暖還涼,忽豔陽光照一如盛夏,忽又陰霾蕭索的天色。春雨綿綿,我打傘糊里糊塗走在人行磚上,皮鞋的縫綻竟然進水。
那正是那時搬離鄉下,住進城裡公寓時的氣候。街景樹影像吸水過飽的水彩畫紙。其實塵土不興,空氣中充滿著一種一整年只有這段時光才有,行道樹們從葉片、樹木、樹皮整體騷動不能安靜的氣味。
偶然在朋友的文章瞥見提到我,寫道:「……城裡來的朋友」如何如何,一個回神,才想起自己確實已是「城裡人」了。
那是怎樣的一回事呢?孩子讀了城裡的小學(這也是當初遷就學區而倉卒搬家的原因);每禮拜總有幾天時間一到,便拎著大袋小袋垃圾,從公寓四樓奔下,混身在巷子裡各拎一藍膠袋的主婦、少年、老人和印尼幫傭越南幫傭們,擠向停在定點的垃圾車,像籃球禁區身體卡位的拔起投射一樣(有時用勾射),把胖鼓鼓的一袋廢物扔進那金屬輾壓攪碎的怪獸之嘴……
偶爾可以在哄小獸上床後,騎著妻的淑女腳踏車出門,穿過夜色中閃黃燈的和平東路,在擠滿叼著酒瓶的老外和濃妝辣妹的pub入口騎樓鎖車,到樓上的「漫畫王」和我的漫畫達人朋友討教,現場想到啥特殊畫風啥有點意思的,直接從櫃架上整落抽出……
偶爾有多年好友從南部上來,可以夜間出門喝兩杯,然後像想像中的日本惡漢作家醉醺醺地搭短距計程車回家,在寂靜闃黑中掏出鑰匙插進鎖孔……
「住在城裡」,或意味著,可以,在某一神祕瞬刻,發現只有自己一人,走在空盪盪的夜間街道上。
有時或遇一二頭髮漿結如灰麻繩的流浪漢,一身行囊保特瓶罐塑膠袋布陣四周,縮睡在郵局自動提款機的騎樓凹影裡。
也有過一次經過一間燈光妖幻像廣告運鏡的光潔7-eleven門口,一個理著美國海軍平頭的女孩,醉醺醺,滿臉淚水,罵著三字經,吆喝著收銀檯裡,穿紅罩衫制服,也是剃平頭,但白白淨淨小圓框眼鏡和尚臉的另一個女孩出來。自動門賓蹦賓蹦開了又關。我發現除了我作為第三者遠遠旁觀,整間發光的便利商店及外頭地磚上還殘餘燒烤店潑出海產污水腥味的走廊,俱空無一人。那使得罵人的和低頭不睬的兩人,像在小劇場舞台上一樣悲哀又純淨。
也有過一次,和友人喝酒畢,約半夜兩三點,暈恍恍快步走在冷風撲面的城市馬路上,一些夜班計程車像巡游魚缸底沙的鼠魚,緩緩跟在我身後,直到我揮揮手才換檔加速離去。經過一座電話亭,暗影裡一個風姿綽約的女人,噴著煙,躁鬱地撥號。然後,用撕破喉嚨讓整條街聽見的音量,對著聽筒大吼:「蕭×強,你欠我錢。我操你媽的××--」我吃了一驚,酒整個嚇醒,甚至還丟臉地在電話亭邊顛絆了一下。女人掛上電話,把一整口煙用最大肺活量吞吸進丹田,然後和這狀態非常不協調地對我嫣然一笑。
幾年前,曾幫一位導演發展一個劇本的故事大綱(當然後來這個劇本是流產了),他的男主角是一個在某次重大災難痛失摯愛之人後,便得了失眠症的憂鬱傢伙。為了要處理這樣一個睡不著之人,如何打發那一個個在城市裡不眠的漫漫長夜,我想了許多「一個百無聊賴在入夜城市可能的活動」:跑去fight club當人肉沙包;在百貨公司樓下空蕪的投幣式投籃機百無聊賴地投籃;找工具撬開自動販賣機挖裡面的易開罐飲料;翻進小學校園把教室所有的椅子以一種支點平衡的方式倒立在每一張課桌上;甚至(為了視覺效果)放火燒路邊的某一個鋁皮垃圾桶;天亮前跑去一間全聚擠著菲傭的教堂,淚流滿面和她們一起跪著祈禱……
這些那些。
後來我發現那全是移植於某一些小說或電影之閱讀(譬如卜洛克的小說?或年輕時讀的安部公房《燃燒的地圖》?),關於一個夜間城市的樣貌,或是一座城市的靜夜之夢。一個酒精中毒的流浪漢,在街角撿到了一個有著天使心腸的混身惡臭的女孩(或是失憶症的女孩?或是被人蛇用毒品控制的阻街女郎?或是一個殺了她父親而心智崩潰的女流浪漢?)……或者,如那位導演在原故事構想中,作為救贖者的女主角(她治好了那男人的失眠症):一個嗜睡症患者,一個整天待在擠滿那些LV、Prada、Gucci、香奈兒、Hermes動物皮革氣味之名牌包墳塚的五、六坪大小二手包店的女孩。到了夜間,她就像仙度娜拉關上鐵捲門,為了心愛的真品(對,該死的超A仿冒品)盛裝到夜店當公主……
這些其實不是我搬進城裡後,在夜間遊蕩時可能看見的。有一陣子我非常好奇一個奇幻景觀:那是我每週一、三、五黃昏帶小孩去上英文班後所見,在新生南路、信義路交叉口那一帶街區,無論是往鼎泰豐金石堂那一方向的騎樓,或是斜對角一間隔著一間櫥窗裡停放著不同廠牌休旅車的展售場景,總是在黑壓壓的人群中,魔幻不真地走著兩兩一雙,美麗高得像機器人的俄羅斯少女。這些女孩,牝鹿般的小頭顱和身形的比例,不可思議地全是日系漫畫裡的九頭身,臉孔精緻立體得讓人目奪神搖。肌膚似雪。耳垂、肩膀下巴、脖子……每一處細節的弧形皆優美如一個瘋魔燒瓷家手下的極品瓷瓶。她們是從哪冒出來的呢?我被弄得迷惑不已。以我的直覺,這些女孩身上的氣氛,絕無一絲絲所謂「金絲貓大舉侵台」那種跨國妓女的風塵味,也無一絲絲混pub的老外或美語班打工老外的調調。她們甚至帶著一種科幻電影裡,來自未來更進化人造人的器質性和疏離氛圍。我甚至想像:這些高、眼珠像綠寶石稜切折光一樣的美麗魔物,在維修的輸送帶上,那漂亮頭顱下的切口,露出的是一叢叢發出金黃光澤的金屬管線……
【輯五.像一句詩那麼短】黎礎寧
黎礎寧自殺這件事給我極大的震撼。我家並未接第四台,星光幫第一代爆紅的時候,我是過了許久才因友人S激凸推薦,上Vlog點播了楊宗緯和蕭敬騰的鑽石與白銀歌喉對決。二班我則從頭到尾錯過。說來我這樣年紀的中年男子被家計與生活瑣事包圍之疲憊與世故,著實不是星光幫此等節目製作單位預設的觀眾群。
今年農曆年過後,我為了把手上拖延漫漶的長篇收尾,和妻商量每週有三天跑去新竹、桃園、宜蘭、台中的一些小旅館「閉關」寫稿。於是奇幻的,在某幾個孤獨沮喪、寫不出任何東西的週末夜晚,我是在一間一間窄小、晦暗、陳舊,燈光昏黃且地毯且附著一種揮之不去霉騷味的小旅館裡,坐在床上吸著菸,瞪著電視機裡的「星光三班」那不可思議,近乎我們這時代這島嶼之史詩的飆歌、對決PK、落單之挫敗者和既是同伴又是敵手的倖存諸人含淚擁抱……
有時我一人在那些旅館裡看得熱淚漫面。我當然知道那些現場即興的催淚戲劇性是製作單位設計的遊戲軌跡。但三班的這一批孩子們實在太像一群美麗頸弧奮力揮翅的白鳥了。他們那麼純粹柔弱,卻又那麼努力。有幾次的PK對決,靈魂意志將這些不過才二十出頭年輕男孩女孩的歌喉飆高到無比巨大莊嚴的境域。偶爾幾次其中一、二人會宛如神明降臨、渾身發光宰制整個舞台。那讓我目瞪口呆。雖然大部分時刻,他們會像這樣年紀孩子應該的表現:失誤、抵抗不了巨大壓力、垮掉、失敗、淚灑現場……。但我實在太喜歡這群孩子了,從徐佳瑩、林芯儀、黎礎寧、黃靖倫、美猴王潘嗣敬、舞神歐巴馬、簡鳳君、小侯佩岑林雨宣,乃至PK賽爆發冒出來的原子小金剛……
黎礎寧是這其中最能召喚我久已結繭之柔弱粉絲情感的一位。我一直以為她會是最後的冠軍。她本身像是一把豪華昂貴、音質醇厚音域無比寬廣的薩克斯風,優雅迴旋在比這個比賽高許多海拔的稀薄上空。當然比賽的後段,聚焦全在被諸神寵愛背後像垂著天使羽翼的創作天才徐佳瑩與具有強大靈魂意志你感覺她將這歌唱大賽拉至聖壇獻祭、生死相搏之境的林芯儀,兩人之間的駭麗對決。黎礎寧似乎就早早退出戰局,進入一種每次登場,只在享受演唱,而非比賽的醚醉狀態。
在那些窄小黯黑的小旅館房間裡,從那個發光的小框格中,有一種我這年紀不可能再有的年輕純質像水母或深海烏賊的透明生命在湧動著,他們其實比我們這些大人堅忍、見怪不怪,面對挫折、傷害或屈辱,更有創造力將之優雅帶過。有一場比賽,黎礎寧在短時間內學義大利文,和一位台北愛樂菲律賓裔男高音飆唱歌劇(那次林芯儀亦是在瘋狂特訓後和台灣一個頂尖愛爾蘭踢踏舞團表演踢踏舞),我看得瞠目結舌,似乎一場神祕的測試,「看妳們的極限可以,可以推到多高?」但大人們給他們的獎勵實在太吝嗇微薄了。他們各自在那樣高強度的擠壓中,展演了二十多歲靈魂所能摺藏的,不可思議的華麗、精緻、像神贈予的美好品質。那比我們這個社會的政治人物、媒體名嘴、白痴八點檔、打嘴砲綜藝大哥……所給一整世代深層靈魂的觸動、提升、正面能量,多得太多了。但似乎比賽結束後,拉斯維加斯的布景舞台,不,野台戲的竹竿篷架拆一拆,曲終人散,蜃影幻夢,大人們趕著下一批罐頭偶像的生產線機關開模,另一場嘉年華,另一個無需進入真實的虛擬巨星遊戲又開始。
那樣的開啟了封印的瓶塞,將某一群人內在如神燈巨人的神祕壯麗可能召喚出來,最後卻草草捏掉、棄置的浪費、沉慟、與虛無之慨,幾乎存在這島國每一領域。從棒球、籃球、奧運金牌希望、電影、小說、藝術……似乎在某一時期,你總會無比驚豔僥倖看見一、兩個毛色發光的秀異天才,他們也按著各領域世界級的極限規格在操練自己。每一個將這些年輕孩子從尋常人的形貌抽拔拉胚成神蹟(譬如黎礎寧在唱西班牙文藝術歌曲的那一刻)的高速運轉、強壓、撕裂張力,以及他們承受這些極限操演時脊椎發出嘎嘎聲響的戲劇性,幾乎都可以紀錄片拍攝下來變成盪氣迴腸、催人熱淚之史詩。但為什麼之後常常什麼也不算數,所有人皆嘻嘻哈哈咭咭呱呱朝著浸在尋常平庸光度的生活裡奔跑過去呢?為什麼我們總會在許多年後,唏噓感傷地遇見那些毛色灰黯的,變成修路工人或便當小販的職棒明星,變成寫廣告文案糊口的天才小說家,變成毒蟲的實力派演員,變成負債者的電影導演?
我在那些髒臭小旅館,為著電視小框格裡那些發著光的「神的孩子」們的極限演出而熱淚盈眶時,有什麼地方出了差錯?事物本身展演的方式被我偏斜了某個細節而錯誤的理解?幾年前極著迷的一個日本綜藝節目《超級變變變》,那個競賽或表演或嘉年華或裝扮秀遊戲的設計形式,其成立的戲劇核心或精神性的什麼總讓我百思不解:一組一組的參賽者(可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小學生、拉麵店或美髮店同仁、業餘藝人、廢材大學生)在極短的時間,表演一件「模仿真實但其實不是真實」的事物。但這鴻光一瞬的表演,往往需要這群業餘表演者反覆操練好幾個月以磨合默契及流暢感。透過布景、道具、懸吊、同伴間躲在舞台死角的扛舉協助,他們專注又來勁地表演模仿尋常生活的事物:飛鳥、風中搖擺的晾曬衣物、自動販賣機、海灘剛孵出之小海龜、奧運各項運動剪輯的廣告……種種種種。有的表演真是讓人佩服不已。這些業餘演出者,在每一集節目得獎後的興奮大叫大跳、互相擁抱、淚水弄得扮妝的顏料糊掉……但是之後並沒有人因此而成為職業演員哪。
我後來想:也許「星光三班」的那些孩子們,原初被設定的(或我們真正在消費的),本就不是他們的歌喉舞藝能否到達一巨星之境。而是像電影《登峰造擊》的那個拳擊女孩。我們要他們演出的,本就是挫敗本身。對挫敗的恐懼、哀憫與尊嚴。他們如在夢中地把「與挫敗鬥爭」這件事,集體表現到不可思議之深刻輝煌。但節目結束後,他們是角色而非演員。下一齣續集大人們會找來一批新的演員重演一次他們經歷過的事。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中文現代文學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現代散文 |
$ 252 |
現代散文 |
$ 25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
這是一些發生在《西夏旅館》之前,之後,或之外的──
故事、夢境、另一個流浪者晃走於灰灰惘惘昨日之城的記憶荒墟。
我總是被那些人的故事迷得搔首撓腮,
可惜目的地總太早就到,
像我們這時代聽故事的宿命,那樣硬生生被截斷……
這是作家駱以軍的雜文集,漂浮著小說的幽魂黯影;或更是一部錯過之書、失物之書,撩撥對於青春無憂昔時太容易獲得的珍寵、太輕恣揮霍的情感至今風華盡褪的懊惱與惆悵,並記錄夢和信仰的傾斜,如將墜未墜的星塵──那些追憶之瞬都太逼似超現實世界的漫遊旅程,確實可能一去不復返了。那不只意味著「事物不可逆轉地變得貧乏、扁薄、失去原先於各凹凸稜角閃閃發光的神性」,也是更困難的新冒險即將展開之天啟──只是物質與肉身皆日漸貧弱匱缺,失落愛的靈魂則更顯形單影隻。
作者簡介:
駱以軍
文化中文系文藝創作組、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畢業。曾獲台灣省巡迴文藝營創作獎小說獎、全國大專青年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推薦獎、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台北文學獎……等。曾出版小說《西夏旅館》、《我愛羅》、《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降生十二星座》、《我們》、《遠方》、《遣悲懷》、《月球姓氏》、《第三個舞者》、《妻夢狗》、《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紅字團》。
章節試閱
【輯一.被困住的時光】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塔羅牌
很多年後,他逐漸相信:當事物不可逆轉地變得貧乏、扁薄、失去原先於各凹凸稜角閃閃發光的神性,那只是整個世界退縮回那個不再紛亂流動、蹦跳竄走的靜物幻燈片。
他父親從遠方攝下,寄回來給他們的那些幻燈片。
那是一個過度曝光的世界:枯旱荒野中一棵巨大的樹,乍看眼花,覺得樹頂重疊蒙覆著一片色彩妖異的葉片,瞪視細部才發現,那全不是葉子,在每一枝椏分杈處,每一像絕望手指朝天撐張的這棵枯死之樹的每一根白色的尖細末端,全棲息著一隻一隻的鳥。也就是說,單在這株樹梢上,便窩...
很多年後,他逐漸相信:當事物不可逆轉地變得貧乏、扁薄、失去原先於各凹凸稜角閃閃發光的神性,那只是整個世界退縮回那個不再紛亂流動、蹦跳竄走的靜物幻燈片。
他父親從遠方攝下,寄回來給他們的那些幻燈片。
那是一個過度曝光的世界:枯旱荒野中一棵巨大的樹,乍看眼花,覺得樹頂重疊蒙覆著一片色彩妖異的葉片,瞪視細部才發現,那全不是葉子,在每一枝椏分杈處,每一像絕望手指朝天撐張的這棵枯死之樹的每一根白色的尖細末端,全棲息著一隻一隻的鳥。也就是說,單在這株樹梢上,便窩...
»看全部
作者序
【代序】孤獨的至福
多年不見的哥們約在路邊人行道擺開小桌椅的海產店喝啤酒。F說起這兩年多來迷上了爬山,是專業登山客的那種爬山喔,百岳中的玉山、雪山、南湖大山、北大武山、中央尖山、大霸尖山……幾乎都挑戰過了。座間諸人皆已各自成家,聊起小孩經也不再是奶粉尿片,而到了小學安親班英文班才藝班的階段,唯獨F君猶孤家寡人。幾年前聚會F當時迷飆車,網路上買了一輛改裝中古BMW,整修起來花了五、六萬,四十歲歐吉桑入夜和年輕車友在二高幾處熱門路段風馳電掣軋車暴走。現又變成登山狂人。似乎我們皆在時間流河中混濁、衰老,只...
多年不見的哥們約在路邊人行道擺開小桌椅的海產店喝啤酒。F說起這兩年多來迷上了爬山,是專業登山客的那種爬山喔,百岳中的玉山、雪山、南湖大山、北大武山、中央尖山、大霸尖山……幾乎都挑戰過了。座間諸人皆已各自成家,聊起小孩經也不再是奶粉尿片,而到了小學安親班英文班才藝班的階段,唯獨F君猶孤家寡人。幾年前聚會F當時迷飆車,網路上買了一輛改裝中古BMW,整修起來花了五、六萬,四十歲歐吉桑入夜和年輕車友在二高幾處熱門路段風馳電掣軋車暴走。現又變成登山狂人。似乎我們皆在時間流河中混濁、衰老,只...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駱以軍
- 出版社: INK印刻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9-07-30 ISBN/ISSN:986637705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72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