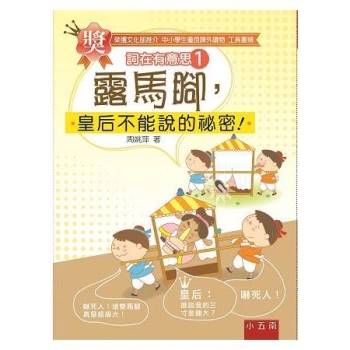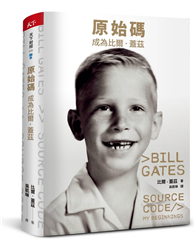風物依舊,新世界不新,好像舊世界的延伸,只是沒有了家。——高爾泰
一個理想主義者對尊嚴、美學與自由的追求
美學名家高爾泰生死歌哭之作
2007年獲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當代漢語貢獻獎」
被譽為當代散文最美的收穫之一
你很久沒有看見這樣一部作品了。文字可以如此簡單又無比優雅,情感可以如此清簡又無比飽滿。原來故事可以這樣講,原來歷史可以這樣看,不用吶喊,不用悲泣,卻讓你懂得!從內心裡真正懂得。
《尋找家園》共三卷--
第一卷【夢裡家山】,從一個孩子的眼睛,看一個角落裡的一段歷史。江南小城,抗戰逃難,深山小村,戰後還鄉,政權易手,「土地改革」、「鎮反運動」……為了孩子的安全,父母安排他外出上學。孩子在外想家,故園家破人亡。
第二卷【流沙墜簡】,寫一個大學生在「肅反運動」中,因「思想問題」被審查,畢業後分配西北,被打成右派,送往戈壁灘上一個關押著三千多人的右派集中營「勞動教養」。不到三年,已有兩千多人死亡。他偶然倖存,得以回到社會,成家立業。文革中又被揪舉,再次家破人亡。
第三卷【天蒼地茫】,寫「新時期」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命運。「平反」、「歸隊」以後,因違反「四項基本原則」,被「清除清神污染」,禁止教書和出書。後來又被國家科委授予「有突出貢獻的國家級專家」稱號。再後來又以「反革命宣傳」被捕入獄,出獄後逃出中國。
高爾泰說:「除了活著,還有更多。更多之一,是意義的追尋。」又說「在這資訊滔滔,文字滾滾,每天的印刷品像潮水一樣漫過市場貨架爆滿的日子裡,我一再囑咐自己,要寫得慢些,再慢些。少些,再少些。」他的文字清麗,飽滿而沉重,書中有控訴、有寬容,也有對現實的詰問與超越歷史的思考,使人看見潔白底下的黑暗,以及黑暗底下真正的潔白。面對歷史與過往,高爾泰選擇了寬恕,但對於現世,他卻以剛直的秉性,發出了「絕不妥協」的強音!
作者簡介:
高爾泰
1935年生,江蘇師範學院畢業,57年被打成右派,押送勞改教養。62年解除勞教,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66年再次被打成右派,到五七幹校勞動。78年「平反」,先後到蘭州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出版《論美》。83年《論美》被禁售毀版。84年到四川師大,86年出版《美是自由的象徵》,上暢銷書榜,國家科學委原會授予「有突出貢獻的國家級專家」稱號。88-89年與王元化、王若水編輯出版《新啟蒙》創刊,至第四期被禁,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在南京大學教授任上被捕。出獄後流亡海外至今。2004年,《尋找家園》前兩卷審查刪節本由廣州花城出版社版,上暢銷書榜。2007年,獲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當代漢語貢獻獎」。
章節試閱
〈夢裡家山 〉 回到故鄉,極目四望,恍惚中竟不知身在何處。兒時家山,早已經不存在了,變成了我心靈中的一個虛無縹緲的夢境……
我的故鄉高淳,位於江蘇省西南端與安徽省交界的地方,恰好是「吳頭楚尾」。地勢東高西低。東部是茅山山脈和天目山山脈的銜接處,山高林茂,俗稱「山鄉」;西部為丹陽湖、石臼湖、小南湖三湖所環繞,溪河交錯,葦岸無窮,俗稱「圩鄉」。最早的縣治固城始建於公元前五四一年,比楚威王築石頭城置金陵邑(前三三三年)還早二百來年,可稱古邑。
到我出生的時候,固城早已荒廢,縣治淳溪鎮也只是一個僅數千戶人家的小鎮。鎮上只有一條三米多寬、青石板鋪面的彎曲小街,俗稱老街。兩旁店鋪係明清建築群,樓宇式雙層磚木結構,挑檐、斗栱、垛牆、橫桁鏤窗。油漆剝落幾盡,裸露著灰色的木頭。在街上走,有一種憂鬱的感覺。還有一條「半邊街」,另一邊是水市,是這一帶歷來盛產的大米、魚蝦、竹木、桐油、土布、野禽、羽扇、茶葉、菸葉、苧麻等等的集散地,每天晌午前後,都有一陣子熱鬧。正如我父親高竹園先生在一首詩中所說,「水陸兩楹市聲喧」。一到傍晚時分,復又歸於寂寥。
淳溪鎮位於小南湖西岸,沒有城牆,但有城門。出東門就是湖,越過葦岸邊大片大片的野菱菰蒲白蘆紅蓼,可以望見湖上帆影點點。天氣好的時候,還可以望見湖那邊隱隱約約的一髮青山。這裡那裡,時不時的,會有成群的野鴨、茭雞或水鴿子突然飛起又很快落下。南面是一條河,叫淳溪河。沿河綠楊如煙,煙樹中白牆青瓦的老式民居夾雜著銀灰色的草屋,淒迷沉靜。
河上有一座七孔石橋,叫襟湖橋,橋欄上的石獅很生動。橋頭有一寺塔,叫聚星閣,第一層石頭門樓,第二第三層皆六角形木結構,飛檐十二,凌空欲去,更生動。二者都是始建於明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年)的古建築,保存完好。解放後,襟湖橋已改造為汽車可以通行的公路橋,聚星閣也已拆除。那鐵鑄的寶瓶形塔頂有烏篷船那麼粗,落地後無法運走,一直橫在那裡。大躍進時砸碎,餵土高爐餵了很久。
位於淳溪鎮東面的小南湖,又叫固城湖。由於中生代燕山運動後期的地層斷裂,小南湖東岸的原始湖岸線幾成一條直線(它現在已被圍湖造田弄彎了)。直線那邊,平行地、但不均勻地分布著馬鞍山和十里長山的山脈,這些山脈到湖邊上就斷了,成為懸岩峭壁。主峰大遊山由砂岩、火成岩及石英砂岩組成,海拔一八七公尺,林深石黑。八年抗戰時期,日軍占領了淳溪鎮,我們全家逃難,就躲在大遊山中。
所有這些山脈,全都被森林覆蓋。山上幾乎全是松樹,山下則是毛竹和雜樹,主要是橡樹、楓樹、棗樹、棠梨樹和毛栗子樹。棠梨極酸,沒法吃。橡子極澀,也沒法吃,但是很好玩。各棵樹上剛落下的橡子,形狀花紋都不同,帽蓋也迥異,有的像栗子,有的像包緊的松球,有的像打開的松球,有的像很小的倒毛雞。剝出來光彩潤澤,不亞於泉水裡的雨花石。有一陣子,姊姊們愛收集各色橡子,我也跟著揀,揀了還要給取名字,大頭、海頭、阿扁、阿細、羊羊、馬公之類。可惜放在匣子裡面,很快會乾枯褪色,幾天後再打開時,全都變成了晦暗的土黃色。
好在樹林裡有趣的東西很多。即使灌木的叢莽,也都是無盡藏的寶庫,那裡面有覆盆子、漿果、草莓、甜心草……。我喜歡一種淡紫色的小花叫蜜糖罐,摘下一朵,花托處會滲出一滴乳白色的液汁。你吸一下,小苦微甜,有股子清香。野生動物很多,有時聞得見狐狸或者野狗的氣味,知道牠就在附近,但是看不見。我能看得見的,都是些小傢伙,野雞雛兒之類,一個個絨球一般,嘰嘰叫著跑得很快,一忽兒就不見了……。有些山裡的孩子,捉得到麂子、獐子、獾,我捉不到,但是知道牠們的存在,就感覺到野風拂拂,生活更加有趣。
不過這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世界,現在已經沒有了。現在高淳的地貌,已經完全改觀。在圩鄉,由於圍湖造田,八十多平方公里的小南湖只剩下大半,二百六十多平方公里的石臼湖只剩下小半,三千多平方公里的丹陽湖整個兒變成了田野。由於人口爆炸,淳溪鎮的面積擴大了至少十倍,把附近的許多村莊都吞沒了。一排排五、六層整齊劃一、互相擠得很緊的公寓樓,代替了昔日小院橫斜的老式民房。街道拓展得很寬闊,河被兩邊夾緊,變得很狹。水泥築成的碼頭上人擠人運輸繁忙。河上機動船團團冒煙突突作響。下水道很多,河水濃稠腥臭,漂浮著油污垃圾。河上已經有兩座公路橋了,從橋上望出去,即使在夏天,也難得看到一點兒綠色。固城湖湖管會和江蘇省漁業廳投放的三十多個網箱裡,頻頻有魚兒全部死光的記錄。
山鄉的變化更大。大躍進全民煉鋼時,樹木都被砍伐一空,所有的山全部光禿。水土流失嚴重,以致許多地方幾乎寸草不生。七九年開始重新造林,但可以造林的面積已經很小。許多原先是森林的地方,這時已變成農田和村莊。原有的村莊迅猛膨脹,同時又增加了許多新的村莊。從因競相開採石頭而襤褸不堪的山上望出去,村連村店連店,廠礦企業處處冒煙,一派城郊景象。特別新房屋都是紅磚砌成的,蓋房頂的材料,也用方形的紅色平瓦,代替了從前那種半圓形青灰色小瓦,望上去特別扎眼。縱橫交錯凹凸不平的公路和土路上,以及因水質汙染而渾濁不堪的河道上,卡車、小型拖拉機、三輪摩托和機動船擁擠吵鬧,捲起陣陣黃埃,噴出團團黑煙。
回到故鄉,極目四望,恍惚中竟不知身在何處。兒時家山,早已經不存在了,變成了我心靈中的一個虛無縹緲的夢境。
〈夢裡家山 〉 回到故鄉,極目四望,恍惚中竟不知身在何處。兒時家山,早已經不存在了,變成了我心靈中的一個虛無縹緲的夢境……
我的故鄉高淳,位於江蘇省西南端與安徽省交界的地方,恰好是「吳頭楚尾」。地勢東高西低。東部是茅山山脈和天目山山脈的銜接處,山高林茂,俗稱「山鄉」;西部為丹陽湖、石臼湖、小南湖三湖所環繞,溪河交錯,葦岸無窮,俗稱「圩鄉」。最早的縣治固城始建於公元前五四一年,比楚威王築石頭城置金陵邑(前三三三年)還早二百來年,可稱古邑。
到我出生的時候,固城早已荒廢,縣治淳溪鎮也只是一個僅數千戶人...
作者序
這是一本在流亡中寫作的書。
飄泊天涯,謀生不易,斷斷續續,寫了十來年。
十來年沒過過生日。七十歲那天,很偶然地,在桑塔菲附近的高山上度過。寥寥長風,莽莽奇景,感到是最好的慶祝。和小雨談起一些往事,我說,假如我現在是一個嬰兒,或者是一個嬰兒的病危的母親,對於自己的、或自己死後孩子所面臨的如此人生,一定會感到無比地恐懼。現在都過來了,能不感激命運?
何況除了活著,還有更多。更多之一,是意義的追尋,化作了文字。早年冒這個險,是因為心靈的需要。窒息感迫使我用手指在牆上挖洞,以透一點兒新鮮空氣。空虛感迫使我盜竊黨產,想偷回一點兒被奪去的自我。機會很少,「作品」更少。字跡是贓物罪證,保存比寫作更難。少而往往失去,常不得不從頭來起。能有些許殘餘,都是命運的恩賜。
但是,這只是我個人的幸運。許多比我優秀的人們,已經消失在風沙荒漠裡面。屍骨無存,遑論文字?遑論意義?從他們終止的地方開始,才是我對於命運之神的最好答謝。但是走到這一步,腳下已沒了路。坦克當前,鐵窗斷後,一切又回到零度。
流亡十幾年,飄泊無定據。海洋郡日夜海風松濤,煩透了古典主義的寧靜。偶住紐約,受不住鋼骨水泥森林裡那份現代主義的機械、效率、和結構性的剛硬冷峻。拉斯維加斯紅塵滾滾,白天黑夜理性非理性大街上和高樓裡都很難分清。無數流動交織的邊緣,疊現出後現代主義模糊的面影。但是解構的語境,解不開「輕」的沉重。總是在尋找意義,看到的卻只有霓虹。煙花萬重後面,是荒涼無邊的太空。
十幾年來,眼看著人類失去好幾百種語言,地球失去好幾萬種生物,新世紀與第三波恐怖主義同來;眼看著同情心,愛和被愛的需要,對自由、正義和更高生命價值的渴望等等,也在和森林草原冰川礦脈等等同步萎縮;眼看著專制政權黑幫化,知識分子寵物化,文藝學術商業化,生化核彈普及化;眼看著歐盟要賣武器給中國,北大清華學生們敲鑼打鼓為「九一一」歡呼;善良溫柔的阿拉伯婦女為了捍衛自己的石刑、面罩、和無權地位,而爭當人肉炸彈……我只有 驚訝。
瞪著驚訝的眼睛(顯出智力的限度),看世事如魔幻小說。看自己的過去,也覺得像是夢遊。在黨的無微不至的關懷下,我的全部經驗、知識和觀點,都局限在一個狹小閉塞的範圍。沒有書籍,沒有資訊,沒有朋友,獨鑽牛角。在許多我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如因果律,質量不滅定律,歷史不會倒退,真理只有一個,正義必定戰勝邪惡等等一再被證明是不正確的以後,還在以天下為己任舍我其誰,還在「以為真理在手,不由別人分說」,非夢遊而何?無知是內在的黑暗,引導我在外在的黑暗中摸索,非夢遊而何?
夢醒時分,我知道了什麼叫做混沌。知道了我藉以呼吸的「有序」,很可能是自欺欺人的童話。在核恐怖平衡的鋼絲繩上,隨著無數人類從未經驗的事物如反物質、隱秩序、基因工程和所謂「文明的衝突」等等進入「視野」,我發現自己由於定向思維的宿疾,腦子生鏽,又感到呼吸困難。
寫作《尋找家園》,又像是在牆上挖洞。這次是混沌無序之牆,一種歷史中的自然。從洞中維度,我回望前塵。血腥污泥深處,浸潤著薔薇色的天空。碑碣沉沉,花影朦朧,藍火在荒沙裡流動……不知道是無序中的夢境?還是看不見的命運之手?畢竟,我之所以四十多年來沒有窒息而死,之所以燒焦了一半的樹上能留下這若干細果,都無非因為,能如此這般作夢。真已似幻,夢或非夢?我依然只能,聽從心靈的呼聲。
聽從心靈的呼聲,是不問收穫的耕耘。不問不是不想,凡事不可強求。現在和同齡人溝通都難,遑論與E世代新新人類?遑論從難友們終止的地方開始?在這網路眼花繚亂,聲、光、色、影像飛旋,「文化消費」市場貨架爆滿的年代,在這資訊滔滔,文字滾滾,每天的印刷品像潮水一樣漫過市場的日子裡,我一再囑咐自己,要寫得慢些,再慢些。少些,再少些。
想不到《尋找家園》前兩卷能在大陸出版。想不到雖然經過審查刪節,還能得到那麼多陌生的知音。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知音。「自由鳥永不老去」「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孩子」……都是莫大鼓勵。最使我感動的,是余世存的兩句話:「原來高爾泰就是我呀,或者說我們都是高爾泰。」奴隸沒有祖國,我早已無分天涯。集體使我恐懼,我寧肯選擇孤獨。在流亡十幾年之後,聽到遙遠故土新生代的這些話語,好像又復活了一個,已經失去的祖國。
那些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生態,家破人亡顛沛流離的命運,曾使我經常有一種在敵國作俘虜的感覺。這種感覺在超高溫下凝固,超低溫下凍結,乾硬如鐵,支撐著我們的脊梁和膝蓋,使我們得以在非人的處境中活得稍微像個人。但是像個人樣,也就是同非人的處境——我們的生存條件或者說祖國的疏離。
有一次我到出生地高淳看望姊姊。兒時家山,已完全變樣。在那個安置拆遷戶的公寓樓裡,她指著鄰家堆滿破爛雜物的陽台上一個曬太陽的老人,告訴我那就是五八年監管「階級敵人」的民兵隊長,直接虐殺我父親的凶手。可能睡著了,歪在椅背上一動不動。看不清帽沿子底下陰影中的臉,只看見胸前補丁累累的棉大衣上一灘亮晶晶的涎水,和垂在椅子扶手外面的枯瘦如柴的手。但是僅僅這些,已足以使我對這個人的幾十年的仇恨,一下子失去支點——同時,我也就更遠地飄離了,那片浸透了血與淚的厚土。
偷越國境,只是外在流亡的開始。在那之前很久,我已經在內在流亡的途中,把一切都看作了異鄉。有人說我出國前後,文風判若兩人,從激烈到平淡,表明叛逆者經由流亡,學會了寬容與妥協。這是誤解。寬容妥協是強者的特權,弱者如我輩,一無所有,不是可以學得來的。是在無窮盡的流亡生活中所體驗到的無窮盡的無力感、疏離感,或者說異鄉人感(也都和混沌無序有關),讓我滌除了許多歷史的亢奮,學會了比較冷靜的觀看和書寫。
能夠完成這本書,要感謝國際作家議會的幫助,更離不開妻子小雨的支持。我是一個生存能力極差的人,在國內混不到安全,在國外混不到飯吃。寫作稿費極低,是消費不起的奢侈。如果沒有她長期付出精神和體力的雙重透支,為我承受著種種難以想像的生存壓力,我根本就沒有可能坐下來寫書。如果沒有她每天下班回來給我看稿子刪掉許多躁氣、火氣、「沒味兒」和「小家子氣」,我要寫也絕對寫不到現在這個樣子。正如我們所尊敬的作家李銳所說,這是我們共同的作品。現在能一字不改地在印刻出版三卷足本,我深深感恩。
這是一本在流亡中寫作的書。
飄泊天涯,謀生不易,斷斷續續,寫了十來年。
十來年沒過過生日。七十歲那天,很偶然地,在桑塔菲附近的高山上度過。寥寥長風,莽莽奇景,感到是最好的慶祝。和小雨談起一些往事,我說,假如我現在是一個嬰兒,或者是一個嬰兒的病危的母親,對於自己的、或自己死後孩子所面臨的如此人生,一定會感到無比地恐懼。現在都過來了,能不感激命運?
何況除了活著,還有更多。更多之一,是意義的追尋,化作了文字。早年冒這個險,是因為心靈的需要。窒息感迫使我用手指在牆上挖洞,以透一點兒新鮮空氣。空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