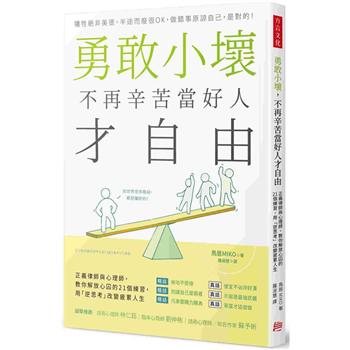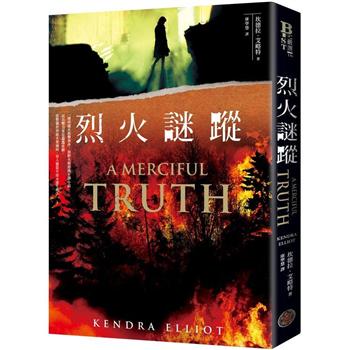風語 不是風的語言 而是風的聲音
將人物放置在大時代的風雲際會 讓人性於驚濤駭浪展開無窮的可能
一個驚世駭俗的數學奇人、天才破譯家
一段考驗智力、更考驗人性的大時代風雲際會
世上再沒有比這更殘酷的職業!
人類卑鄙的陰謀,一個天才爲葬送另一個天才而設計的屠宰場!
揭開中國破譯密碼「黑室」的真面目!
當今中國身價最高的作家、茅盾文學獎得主--麥家,繼《暗算》《解密》《風聲》狂銷數百萬冊後,2010年最具野心的長篇小說,開啟中國「懸疑解密小說」風潮,同名作品改編,電視劇《暗算》、電影《風聲》引爆大型諜戰影劇熱潮,以500萬天價版稅震動華人文壇的麥家,自認《風語》一書是他傾注心血最多、寫得最用力的諜戰小說巨作!
戰爭最殘酷的,不是家破人亡的痛苦,而是對人性的凌遲!
這是一場破譯密碼的戰爭,一群天才的競技,人世間最高級的智力搏殺!
他可以輕易破解數字底下的複雜密碼,卻逃不過隱藏在虛情假意背後的陷阱。
*
「桃樹下埋著少女,梨樹下住著寡婦,香樟樹上掛著死人的衣衫。一九三八年的中國,每一棵樹都是向天國報喪送信的道士,每一片夜色都是人鬼同行的窮途末路。……」一九三八年對日抗戰期間,繼上海失守、南京淪陷後,武漢軍情亦告急,節節敗退的國民黨政府在死守武漢的同時,也做好退守重慶的準備,於是,重慶成了各方間諜活躍的場域。就在這個時候,陳家鵠,一個曠世的數學天才,帶著滿腔熱血與心愛的日籍妻子自美返國,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卻是他不幸和災難的開始,他的天才反成了關押他的牢籠!
為了破譯敵方密碼,陳家鵠成為各方拉攏的對象,日本特務追殺他,八路軍藉同鄉身分接近他,國民黨更是無所不用其極,曉以大義、威逼利誘,甚至不惜陰謀陷害他的日籍妻子!錯綜糾葛的明爭暗鬥下,陳家鵠與妻子身不由己地落入時代的羅網:間諜無所不在,真情假意難分,親情與友情全不可信,愛情成為一把利刃,所有的善意都可能是一樁陰謀詭計。誰是敵人?誰是同志?是救了陳家鵠夫妻倆一命的八路軍?妻兒慘死於日本轟炸下而心懷怨恨的兄長?還是日籍妻子的美國友人?一切的一切,彷彿待破解的密碼,暗藏殺機!同時一步步將他導引到一個再無法回頭的人間煉獄……
作者簡介:
麥家
1964年生於浙江富陽,畢業於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無線電系、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從軍17年,歷任軍校學員、技術偵察員、宣傳幹事、處長等職,後轉任成都電視台電視劇部編劇,現為杭州市文聯專業作家。作品開啟中國懸疑解密小說風潮,根據其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暗算》獲得極廣大迴響,風靡一時,電影《風聲》更躋身2009年十大賣座影片。著有長篇小說《解密》、《暗算》、《風聲》,小說集《紫密黑密》、《地下的天空》、《讓蒙面人說話》、《充滿愛情和悽楚的故事》,隨筆集《捕風者說》、《人生中途》,中篇小說《陳華南筆記本》,短篇小說《兩位富陽姑娘》等。作品曾獲茅盾文學獎、國家圖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人民文學》年度最佳長篇小說獎、中國小說學會中國長篇小說排行榜第一名及新加坡華語文學獎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再現麥家式的意志 /北京晚報.劉春燕(2010-05-03)
麥家新作《風語》尚未出爐,其動靜已經一波連著一波。〝五百萬〞版稅引發廣泛爭議,也引出麥家自己的辯白,他一直強調出版方應該看完稿再說。日前《風語》的版權如期被北京精典博維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拿下,而今年的《人民文學》雜誌也做出舉措,從四月開始連載這部長達80萬字的“諜戰”新作,預計將以十期的規模連載完畢--這對作為中國最權威、級別最高的文學雜誌《人民文學》來說,無疑也是第一次。
《人民文學》雜誌主編、評論家李敬澤認為,“麥家的《風語》肯定是2010年最值得關注的長篇小說之一。麥家在當代雜誌發展史上創造了兩個第一。第一次是此前的《風聲》作為長篇的單行本全文連載,第二次就是眼前這部長篇新作《風語》的多期全文連載。這是一部麥家超越自我的作品,也是其雄心勃勃的集大成之作。”在還未刊發的第5期連載的編者按中,李敬澤如此評價麥家的小說:“麥家的小說被指為‘諜戰’小說,引領風氣,儼然成了一個類型。儘管‘類型’在傳統的文學思維中一向備受疑忌,但有力地確立一個類型,其實是很難的……但麥家又是反類型的,他作品的意涵遠非‘諜戰’所能框限,麥家一切作品的真正支點,始終是‘力’。一種生命強力,或者叫做‘意志’。麥家的文學意義在於他對‘意志’的深入追究和不斷發現……對意志的想象恰恰是我們文學中一個薄弱區域。”
評論家謝有順表示,他非常樂於見到《人民文學》能這樣高格調地定位麥家的新長篇,“麥家作為諜戰小說和諜戰影視熱的肇始人,他的《風語》達到的高度,將預示著這類小說行將走向終結。它幾乎用盡了麥家所有的力量,尤其是他塑造的人物形象,飽滿、尖銳,並有著當代文學人物少有的價值光輝,這樣的人物立在那裏,就如同那洪水中的石頭,沉實、有重量。我相信,洪水終會過去,但這樣的石頭會留下來。”
精典博維老總陳黎明認為,像《人民文學》這樣老牌的經典文學雜誌以及李敬澤等評論家的意見,再一次證明了我們對麥家作品及其市場價值判斷的準確性。至於最終版稅,陳黎明以〝不願以此為炒作〞拒絕透露。
七種密碼玩個遍 挑戰讀者智商 /杭州日報(2010-06-18)
■獨家訪問
麥家最新長篇小說《風語》已經在《人民文學》上連載了三期,引起的連鎖反應是這份文學期刊的銷量以每月1.5萬本的數量遞增。而世界盃過後,《風語》的第一卷也將正式上市與讀者見面。
獨立書評版選擇在這個時候採訪麥家,想跟他聊聊這本即將面世的新作背後的創作故事。他將見面的地點定在了植物園的新書房。
隱在植物園中寫《風語》
沿著植物園的主幹道往裏走,在某條岔路的盡頭,隱約可見一排灰磚墻平房,麥家的書房便隱在其中。
不得不說,他很會挑地方。這個季節的植物園滿眼的綠意,遊客卻不會太多,有一份難得的清靜,適合創作。而他隱在此間寫作這一件事,又與其特情小說中一貫的神秘色彩頗為搭調,很容易讓人想到《暗算》中的701單位又或者是《風語》中的黑室。
門半掩著,入眼即是一張大書桌,背面的墻做成了兩個大書架。桌上既沒有厚厚的書稿,也沒有成堆的書籍,只有一個竹質收納筐和滿是煙蒂的煙灰缸,還有一臺筆記本。《風語》的文稿應該都在這臺電腦中吧。
便裝、拖鞋,泡上一杯茶,點燃一根煙,斜靠在椅子上,麥家便以這樣休閒的姿勢說起創作近況。
顯然,他對這處去年年底找到的地方也挺滿意。除了沒有幹擾外,出門跑步也方便,而這對一個長時間從事高強度寫作的人來說是極其重要的。
每天早晨,快走或慢跑三四公裏是麥家的必修課。植物園周邊的地形,譬如哪裏有山雞出沒,哪個時辰松鼠會出來覓食,早就被他摸得一清二楚。
在這樣的環境裏,文思定當如泉湧,小說以每天幾千字的速度在推進吧。可這個問題還真不好說,“因為腦袋會有一團糨糊的時候”。麥家的最新卡殼記錄是“近3個小時內寫了27個字”。
寫《風語》的日子常常失眠
《風語》大抵也是講了一個與破譯密碼有關的黑室故事。與以往作品不同的是,麥家試圖通過這次寫作,在一個狹隘密閉的空間裏,融合進一個時代的風雲際會,情節更加大開大合。他自稱創作《風語》是“一次瘋狂的寫作”。為此,他曾在去年9月大病一場,又在今年4月腰傷復發,再次入院。
究竟可以瘋狂到什麼地步?
每天長達10多個小時連續寫作,直到淩晨2點上床睡覺時,大腦仍處於極度亢奮狀態。因此,在創作《風語》期間失眠,那是家常便飯。他隨手打開了桌上的收納筐,裏面放著來自三個不同國家的安眠藥。
這還是其次,麥家說最主要的原因是《風語》龐大的文字量,“大概有三卷本,劇本36集,兩個加起來總字數超過200萬”。
其實,早在去年9月,《風語》就已經有了60萬字的初步框架,進行同名電視劇劇本改編時又觸發了一些新的想法。於是從今年年初著手修改,目前的總文字量已突破90萬字。到最後,這個故事究竟會有多長,麥家自己心裏也沒譜。
已先睹為快的讀者,想必對第一部第三章中軍統幹員陸從駿查內賊時用的方法印象深刻。即讓嫌疑人逐個進木桶洗澡,通過秘密觀察他們在洗澡時的行為來排除嫌疑對象。
這一段就屬於修改時的新增情節,靈感源於麥家“曾經聽說過的一個真實事件”。而增加此情節的目的很簡單:增加趣味性。在他看來,一部長篇小說,總要間或設置一些趣味點,讓讀者覺得好看,能繼續讀下去。
可與《風語》主人公比拼智商
寫作過程雖然壓力很大,但從讀者和專家對已刊出部分的反饋來看,《風語》的反響還不錯。但麥家還是留了一手,真正閱讀此書的快感,只有等新書上市時才能充分體會到。
書中,在故事裏出現的每道密碼破譯題,都會以圖表的形式再現。也就是說,麥家在紙上向讀者發起了智力挑戰,在他揭曉謎底前,讀者可以自行與數學天才陳家鵠(《風語》的男主角)一較高下。
“我試圖把整個密碼的發展史都濃縮在《風語》中。原始密碼、替代密碼、移位密碼、語言密碼、書本密碼、數字密碼和數學密碼這七種基本類型,通通都有涉及。”換句話說,只要看完《風語》,就基本知道密碼是怎麼回事了。
對曾有過短暫低保密度特情工作經歷的麥家來說,設計密碼並不算太難。比如,《風語》中陳家鵠寫給妻子惠子的信中,末尾那串意為閨房情話“親愛的,我的上頭和下頭都非常想你啊”的數字密碼1231116971612,屬於入門級別,他用了半小時來設計。而最復雜最難破譯的一道密碼,將會出現在第二卷中。這段情節大概有1500字,差不多是電腦文檔上的一頁半,卻花了他整整12天時間。
開機陣容超強 這次比智力拒絕酷刑 /北京娛樂信報.王大鳴.責任編輯王婉瑩(2010-03-17)
昨日,總投資近3500萬的電視劇《風語》在杭州舉行了開機發佈會,這部根據麥家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由胡軍、郭曉冬、孫寧、馮恩鶴等主演,劉江導演,麥家親自擔任編劇。麥加表示,這次一定會用智鬥抓住觀眾,而胡軍、馮恩鶴這兩個剛剛爆紅的大反派則再次聯手在劇中出任反派人物。
麥家揭秘《風語》寫得最用功
今年麥家的《風語》、《風聲》、《刀尖上的行走》三部電視劇接連開機,而在三部劇中《風語》的陣容最為強大,麥家傾注的心血也最多。他表示:“三個戲都是自己小說改的,都是自己的孩子。但從個人感情講,《風語》小說寫得最用功,劇本改得也最謹慎,希望這部戲能像《暗算》一樣成功。”
與〝聽風〞故事不同
《風語》的故事之前被有些媒體誤解成和《暗算》裏的“聽風”差不多,其實完全不同,麥家介紹,《風語》的故事是取材于真實歷史,首次解密了國民黨在抗戰時期設立的神秘部門“黑室”。在故事中,陳家鵠是一個留洋日美的數學家,娶了一個日本妻子,日本軍方千萬百計想將他為己用。但是陳家鵠拒絕與敵人合作,曆盡艱險回國後,他先加入了國民黨的“黑室”,在目睹了國民黨的種種作為後又毅然去了延安。
麥家說:“密碼機構本身就很神秘,像一個鐵桶陣,如果說《風聲》是地下黨想方設法從鐵桶陣裏把情報傳遞出來,那麼《風語》就是共產黨如何進入鐵桶陣,把具有特殊才能的陳家鵠吸引到延安。日本人得不到陳家鵠,就設計除掉他,用了各種殘酷手段,比如把他母親暗殺了,看你陳家鵠在出殯這天出來不出來。不出來,過幾天再把你父親也殺了,看你出不出來。國民黨一方也同樣,害怕陳家鵠的日本妻子會泄密,就誣陷她與人通姦,是日本間諜,千方百計讓陳家鵠死心留在‘黑室’。而共產黨為了爭取陳家鵠,不惜動用了周恩來埋藏在‘黑室’的王牌……圍繞著陳家鵠,幾方展開了激烈爭奪。”
要比智力拒絕酷刑
麥家表示,《風語》將完全靠智力吸引觀眾,而不是像電影版《風聲》,用身體上的刺激吸引觀眾。他認為:“《風聲》票房不錯,但故事沒講好,我想讓觀眾智力緊張,而不是身體緊張,《風聲》有點恐怖,把觀眾吸引在酷刑這個點,且關鍵環節不合理。”有了這樣的遺憾,麥家希望這次在《風語》裏強調人的智力比拼,是上兵伐謀的境界,而不是血淋淋的打鬥。同時,麥家也建議刪掉影視劇作品上打上的“麥家作品”字樣,“如果是小說這麼說沒問題,改編成影視劇後,就不是我一個人的作品了,是我們所有人共同的結晶”。
演員暢談
胡軍演壞人不會招人恨
《風語》的主演昨天全部來到杭州,郭曉冬將扮演男主角密碼專家陳家鵠,胡軍扮演反一號、國民黨破譯密碼機構“黑室”負責人陸叢俊,孫寧則扮演地下黨員林蓉蓉。《風語》劇組還邀請了《潛伏》中吳站長的扮演者馮恩鶴出演軍統特務頭子杜先生,將《十月圍城》、《潛伏》中的反一號一起集結在《風語》,非常受關注。
胡軍扮演的陸叢俊有點像《十月圍城》裏的閻孝國,他對於自己的信仰極為專一,即使是錯的也要堅持。這個角色表面非常冷靜,內心狡詐,胡軍認為比閻孝國更有魅力,可以在電視劇裏慢慢展開,是一件很過癮的事,“演完這個劇,觀眾不會恨這個‘壞人’,反而會由恨轉而更愛我。”
馮恩鶴反派演得太多
馮恩鶴則透露已經確定參加電視劇版《風聲》的拍攝,現在又參演《風語》,感到非常榮幸,“從《潛伏》後片約倒沒以前多,但請我演反面人物的太多了,沒什麼正面的了,參加這個戲完全是因劇本好,《風聲》、《風語》同時演,我希望兩個‘孩子’都好。”
郭曉冬挑戰“雨人”
在麥家的心裏,陳家鵠要比《暗算》中王寶強扮演的阿炳更難演,“一個盲人很有吸引力,也很有噱頭。而陳家鵠不問政治,不關心戰爭,只是想為國效力,是一個很文雅、喜怒不形於色、高知識含量的人,經歷遠比阿炳、黃依依、顧曉夢、李寧玉這些人物複雜。陳家鵠絕對不是阿炳,他更像達斯汀·霍夫曼扮演的雨人,目測能力、記憶力非常強。我寫陳家鵠用了七分力,而陸叢俊只用了三分力。”
麥家也坦率地表示他以前不認識郭曉冬,有點擔心他能否表現出陳家鵠的複雜內心感受,“我敢打保票,只要郭曉冬演好了陳家鵠,他絕對就是國內的一線大明星。”郭曉冬自己則坦言這個角色非常有挑戰性。
不學《風聲》玩酷刑 麥家揭秘《風語》中的“智力”看點 /浙江在線.徐史韻(2010-03-16)
由中視傳媒、東方星空文化基金、浙江影視集團、皓翰影業、北京藝博影視等聯合攝製的電視劇《風語》將於3月28日在上海正式開機。今天,《風語》在杭州召開了盛大的發佈會,該劇編劇麥家,導演劉江,以及主演胡軍、郭曉冬、孫甯、馮恩鶴均出席。
浙江在線杭州3月16日訊(記者 徐史韻) 由中視傳媒、東方星空文化基金、浙江影視集團、皓翰影業、北京藝博影視等聯合攝製的電視劇《風語》將於3月28日在上海正式開機。今天,《風語》在杭州召開了盛大的發佈會,該劇編劇麥家,導演劉江,以及主演胡軍、郭曉冬、孫甯、馮恩鶴均出席。
作爲今年第一部拍攝的麥家劇,麥家對《風語》寄予了很大希望,他表示《風語》是自己最看重的一部戲,希望能用“智力的緊張”來吸引觀衆,而不是像電影版《風聲》用“身體的緊張”來吸引觀衆。
首次揭露神秘“黑室”
國民黨在抗戰時期設立的“黑室”是一個神秘的部門,目前還沒有影視作品揭秘過。麥家告訴記者:“密碼機構本身就很神秘,就像一個鐵桶陣,如果說電影《風聲》是地下黨想方設法從鐵桶陣裏把情報傳遞出來,那麽《風語》就是共產黨如何進入鐵桶陣,把陳家鵠吸引到延安。”
另外,《風語》的背景遠比《風聲》更複雜。“因爲日本人得不到陳家鵠,就設計除掉他,日本人也打不進‘黑室’,就用了各種殘酷手段,比如把他母親暗殺了,看你陳家鵠在出殯這天出來不出來。不出來,好,過幾天再把你父親也殺了,看你出不出來。而國民黨害怕陳家鵠的日本妻子會泄密,就誣陷她與人通姦、是日本間諜,千方百計讓陳家鵠死心留在‘黑室’。共產黨爲了爭取陳家鵠,不惜動用了周恩來埋藏在‘黑室’的王牌,可以說圍繞著陳家鵠在‘黑室’的去留,幾方展開了激烈爭奪。”
對於《風語》的成績預期,麥家顯得信心十足。“故事會非常好看”,他告訴記者。
比拼智力 拒絕酷刑
電視劇《暗算》、電影《風聲》都是外界一致認爲麥家比較成功的作品,但是麥家自己卻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來,《暗算》在柳雲龍的導演下,色調、故事節奏都很好,堪稱上乘;而《風聲》雖然票房不錯,故事卻沒有講好。“我想讓觀衆智力緊張,而不是身體緊張。《風聲》是有點恐怖,卻把觀衆吸引在酷刑這個點。”
關鍵環節的不合理也是麥家否定《風聲》的原因之一,對此他舉了個例子:“張涵予用唐山皮影戲傳遞情報是不合理的,情報是固定的,唱腔也是固定的,你要想把兩者結合,只能改唱腔,而醫院的護士不是專業戲曲人員,倉促之間她能記得清楚?”
所以在電視劇《風語》裏,麥家突出強調的將會是人與人智力的比拼,“這是‘上兵伐謀’的境界,而不是血淋淋的打鬥。”
名人推薦:再現麥家式的意志 /北京晚報.劉春燕(2010-05-03)
麥家新作《風語》尚未出爐,其動靜已經一波連著一波。〝五百萬〞版稅引發廣泛爭議,也引出麥家自己的辯白,他一直強調出版方應該看完稿再說。日前《風語》的版權如期被北京精典博維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拿下,而今年的《人民文學》雜誌也做出舉措,從四月開始連載這部長達80萬字的“諜戰”新作,預計將以十期的規模連載完畢--這對作為中國最權威、級別最高的文學雜誌《人民文學》來說,無疑也是第一次。
《人民文學》雜誌主編、評論家李敬澤認為,“麥家的《風語》肯定是...
章節試閱
*一*
天剛下過一場與隆隆雷聲並不相稱的小雨。
雷聲把街上的忙人和閒人都提前趕回了家,平時嘈雜的大街在越來越暗的天幕下,顯得越來越空洞、平靜。但沒有下足的雨卻使空氣中更多了一份溽熱、黏稠、潮濕,仿佛伸手摸得著,抓得住。他穿了一身對這種天氣而言明顯是太熱的軍裝,默默地穿過狼藉的市街,拐入一條幽靜的小巷。在進入小巷之前,他不經意地看見一隻褐色小鳥在灰暗的天空中一掠而過,短促得讓他懷疑不是一隻鳥,而是一顆流彈。
小巷窄又深長,一眼望去,空空的,了無人影。有幾棵高大、蒼勁的桉樹和泡桐,從兩邊的高牆內伸出來,把灰暗的天空遮掩得更加昏暗。雷聲從高遠的天空中傳來,沈悶、乏力,更像是遠處的炮聲。一陣風過,樹葉發出沙沙沙的響聲,幾片落葉迎著他飄落。他下意識地躲開它們,仿佛飄落的是被炮彈炸落的飛沙走石。這是一九三八年六月的一個傍晚,他的記憶深處烙著太多有關戰爭的陰影,他需要不斷提醒自己,此刻他在重慶,這裏已經成爲陪都,也許是全中國最安全的地方。想到他能先於他人來這裏,並且幾天前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輾轉來到這裏,他就覺得自己真是幸運至極。
自鬼子在杭州金山衛登陸後,他和妻子相繼離別了上海。他妻子帶著孩子一直躲在湖南鄉下,他則隨部隊撤退、撤退。從上海到南京,到安慶、九江、武漢、宜昌、酆都,沿著長江一路西撤,最後到了重慶。
撤退也可以叫逃跑,他們不停地逃跑,逃跑。
哪有這樣打仗的?人死得比螞蟻還要多,卻寸土不保,打一仗丟一個地方。他曾在鎮江郊外親歷了一場狙擊戰,回顧起來總想到一個詞:潰不成軍。那一天,生和死對他來說只隔著一張薄薄的紙,最後能夠死裏逃生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他撿回了一條命,卻沒有絲毫慶倖的感覺。他覺得這場戰爭勝負已定,沒有懸念,南京必將失守,國人的江山和命運將不可避免地墜入可恥又可怕的黑暗中……傾巢之下,豈有完卵?國破家亡,在劫難逃,僥倖不死只能是加倍地痛飲苦水而已。想不到時隔半年,他還能過上這種日子,每天穿著周正的軍裝出入國家最高的軍事部門,有權有職,有吃有喝,生死無慮,下班有車坐,回家居然還能回到愛人身邊,享受家的溫暖和男女之樂。
現在,他正走在回家的路上,腳下踩著日久無人清掃的落葉。他覺得難以相信,這條幽暗、狹長、安靜、骯髒的巷子深處,竟有一間屋子,是他的家。
若不是橫生枝節,不要五分鐘他即可回到家。但事情說來就來,阻斷了他回家的路。一輛黑色小車,比他晚一分鐘駛入小巷,車輪嘩嘩地輾過落葉,小心翼翼地朝他駛來,越來越近,近到一定程度,又似乎減慢了速度,勻速跟著他。
他注意到後面有車駛來,回頭看了看,見是一輛高級小車,禮貌地往一邊靠了靠,繼續往前走,步子卻在不緊不慢中稍稍放慢了。他在等待車子追上來,超過他。
車子理解了他的好意,鳴了一下喇叭,提速衝上來,卻沒有超過他駛去,而是緊急又霸道地停在跟前,擋住了他的去路。不等車子停穩,四扇車門中的三扇被同時推開,鑽出三個蒙面的持槍漢子,惡狼般撲上來,刹那間已將他牢牢架住。其中一人把冷硬的槍口抵在他後腰上,小聲地喝道:
「別出聲,跟我們走。」
「你們要幹什麽……」他接受過的專業訓練,使他在這樣的緊急時刻,還能夠保持冷靜。
「少廢話,快上車!」
「你們抓人要問問我是誰,」他對自己表現出來的冷靜比較滿意,「你們抓錯人了。」
「錯不了,就是你。」另外一個蒙面人,有點黑老大的感覺,得意地對他說,「你姓陸是不是?陸上校嘛,我們抓的就是你!」說著迅速用早備在手上的毛巾塞住了他的嘴巴。
他嗚嗚地叫,似乎在說:你們是什麽人?
黑老大不理會,推他一把,「上車,老實一點。」
他不肯走,掙扎。但越掙扎,架押他的兩個人就越發用力,幾乎令他動彈不得。他感覺到其中一人十分孔武且粗暴,雙手像老虎鉗子一樣厲害、無情。一隻手生生地揪住他的頭髮,另一隻手在他臀部發力,猛的一頂一托,他的雙腳頓時離地,人像一個包裹一樣被塞進了車門。
嘭!嘭!嘭!
車門以最快的速度關閉,引擎以最大的功率怒吼。車子狂奔而去,捲起一地落葉,紛紛追著車子撲去,又紛紛散落在地。沒有誰看見剛才發生的一切,除了一隻當時正在圍牆上遊走的狸花貓。這必定是一隻野貓,在隆隆的雷聲中無處安身,慌張地遊弋於牆頭,它對著飛速遠去的黑色車影,叫了兩聲:喵、喵。
*二*
是什麽人綁架了他? 他們爲什麽要綁架他? 他到底是個什麽人,值得別人如此鋌而走險?
最後一個問題,不妨借用他首座的話來說。首座姓杜,人稱杜先生,聽上去好像是個大知識份子,其實是個玩刀子出身的人,統領著一群像刀子一樣危險又嗜血成性的人,包括他。他稱杜先生爲首座,後者稱他爲賢弟。幾天後,兩人首度相逢,問答如下——
「首座怎麽會選擇我?」
「當然是因爲我瞭解你。」
「可首座您並不瞭解我。」
杜先生笑道:「我怎麽不瞭解你?知汝者莫如我。需要我證明一下嗎?」說著,不疾不緩,從容有力地背誦道,「賢弟陸姓,單名一個濤字,十九歲就讀南京高等軍事學院,成績優異,畢業被保薦到德國海德堡軍事學校學習軍事偵察,同行六人,惟你畢業,令人刮目。鑒於此,歸國後委以重任,直升素有‘國軍第一師’美稱的第八十八師偵察科長。翌年調入國防部二廳二處,升任處座,時年二十五歲,乃國防部第一年少處座。同年十二月,你與蘇州女子秦氏喜結良緣,次年令郎陸維出世。盧溝橋事變前,你一直任上海警備司令部情報處長。上海淪陷後,你一度轉入地下工作,任軍統上海站站長,爲營救抗日將士建有奇功。今年年初,由杜(月笙)老闆舉薦,委員長欽點你赴武漢大本營任應急處處長,幹得好啊。武漢軍情告急,遷都事宜擺上日程,三個月前你又得重任,作爲國民軍事委員會第七辦公室特派員,爲即將遷都事宜趕赴山城。幾個月來,你盡職盡責,爲遷都大業建功卓著。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應該是你目前全部的履歷。」
那天陽光明媚,但陸濤上校眼前一片黑暗,因爲他戴著黑色的眼罩,什麽也看不見。他在黑暗中誇張地鼓了鼓掌,道:「先生真是博聞強記,我陸某佩服至極。」
杜先生看看車窗外明媚的陽光,親自爲他摘下了眼罩,笑道:「不該你給我鼓掌,該我爲你鼓掌,你的才能,你的忠誠,你的理想,都將爲你贏得最大的回報。你的前途光明一片啊,就像這陽光,明媚動人。」
陸上校眯著眼看著眩目的陽光,不知由來地感歎道:「先生的美言,令我受寵若驚。」
杜先生爽朗地笑道:「如果說剛才說的這些事確實讓您覺得‘受寵’,那麽您不會介意我們再來點‘若驚’吧。當然,您放心,只是讓您‘若驚’,不必擔心安全問題。」
那天陸上校頭上還包著紗布,傷口不時隱隱作痛,他撫摸著傷口說:「我發現自從與先生相處後,我老是心跳不止。看來我是注定要陪你玩下去了,人生百態變化無常,什麽滋味都得嘗嘗啊,那我也不妨嘗嘗這‘若驚’的滋味吧。」
「不要說玩,」杜先生伸手指了指他的傷口說,「這不該是玩的代價。」
「先生不但知道我的過去,也知道我的未來,莫非還知道我這傷的來歷?」
「你被人綁架了,事發在幾天前你下班回家的路上。」
「那麽先生也一定知道是什麽人綁架了我?」
「這個嘛,你不久也會知道的,無需我贅言。」
準確地說,這場對話是在陸上校被綁架後的第五天下午進行的,地點是在杜先生鋥亮的黑色福特轎車上。大約半個小時後,陸濤上校將再次看到五天前綁架他的三個人,加上他們的同夥:一個長得很有些姿色的年輕女子。
*三*
五天前,三個傢夥把陸上校塞進汽車後,就給他蒙了頭罩,捆了手,然後帶他兜圈子。兜了一圈又一圈。幾個回合兜下來,他傻了,東西南北不分,城裏郊外難辨。當車子開進一個院子,他聽聞四周很安靜,以爲是到了很遠的山上,其實就在他們單位附近。
院子古色古香,青石黛瓦,高牆深築,假山花徑,古木參天,看上去有種大戶人家的驕傲和威嚴。敵機已經多次光顧這個山城,街上殘垣斷壁四處可見,然而這裏秩序井然,幽然如初,有一種惟我獨尊的自負,仿佛眼前的戰爭跟它無關。
門是沈重的鐵門,深灰色,很厚實,子彈是絕對穿不透的,只有炮彈才可能摧毀。迎門有一大一小、一高一矮兩棟樓屋,呈直角佈局;大的三層,小的只有一層,牆體都是青色的石條,堅固如碉堡。
他們把他關在那棟小樓盡頭的一間屋裏,門外沒有安排人看守,卻有一隻人高馬大的狼狗,毛色黑亮,伸著長長的紅舌頭,對著門呼呼地喘氣。黑色的頭罩讓他失去了眼前的世界,但耳朵分明是更加勤勞了,靈敏了,他幾乎從狼狗的喘氣聲中,分辨出狼狗的大小和品種。這是一隻德國巴伐利亞狼犬,他以前在上海當軍統站站長時曾用過一隻,他知道牠除了靈敏的嗅覺外還有良好的聽覺,可以分辨一個人的噴嚏聲。塞在嘴巴裏的毛巾讓他口幹舌燥,眼冒金星,但他還是儘量用鼻子哼起了小調,目的是爲了讓門外的狼狗熟悉他的聲音,以便在夜裏可能逃跑時對他放鬆警覺。
要逃跑,當然得首先解除頭罩和捆綁。手被反剪在背後,麻繩一公分粗。是先解除頭罩還是先解開麻繩?他選擇了頭罩。因爲他迫切想知道,自己被關在什麽地方——如果是一間插翅難飛的鐵屋子,即便解了麻繩也無濟於事。而且,頭罩只是籠統地套在頭上,口子敞開著,要弄下來似乎並不難。他準備找個地方去解決頭罩,黑暗中碰倒了一張椅子,引得外面的狼狗一陣狂吠。
狂吠安定下來時,他已經知道怎麽來解決頭罩了,他把椅子移到牆邊,扶手頂著拐角,椅子基本上像長在牆體上一樣穩當。此時,椅子的一隻腳已經變得十分聽話,遠比他捆著的手聽話,他跪倒在地上,把頭低下來,通過頭的移動,調整方向,讓椅子腳鈎住頭罩的口子。這一步很關鍵,對他來說卻並不難,他很快做到了。接下來的事情是個簡單的機械運動,大概連門外的狼狗都能完成,更不可能難倒他。就這樣,他輕而易舉地把頭罩從頭上卸下來,讓椅子去戴它了。
卸掉頭罩,卻沒有給他帶來一絲快樂。他馬上發現,關押他的這間屋子似乎是一間專業的禁閉室,室內除了一張椅子和一只馬桶外空無一物,窗戶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圓洞,狹小,而且加了四根鐵柵欄,欄間距也許可以讓一隻貓自由出入,一個人是無論如何出入不了的。
窗洞裏盛著一團朦朧的白光,預示著夜色即將降臨。他的目光從窗洞裏退出來,耷拉下來,最後落在黑乎乎的馬桶上。他知道,這不能幫他任何忙的,它是象徵,是暗示,是威脅。想到自己有可能要使用它,他就抑制不住地煩躁起來,上去狠狠地踢了它一腳。結果,又引得狼狗一陣示威。
狗叫能給他帶來好運。當狼狗的吠叫再次安定下來時,他已經在爲可能的逃生努力了。原來馬桶的拎手是根不細的鐵絲,鐵絲頭略有刃口,只要有充足的時間,他有信心用它來磨斷該死的麻繩。手自由了,鐵絲和椅子都可以成爲他的武器。他自幼習武出身,二十歲入軍統,接受過種種逃生和克敵訓練,只要給他機會,即便赤手空拳,對付幾個綁匪和一隻狼狗他是有信心的。他想象著等他磨斷了繩子後可能出現的逃生機會,心裏頓時熱烈並緊張起來。
但是,沒有機會。
不一會兒,有人來了,先是狼狗欣喜的支吾聲,然後是兩個人的腳步聲,然後是放肆的開鎖聲,然後是雪亮的燈光(開關在門外),然後是吱呀一聲,門開了。
進來的是一女一男。女人年輕,漂亮,神氣活現,像隻剛下了蛋的母雞,進門就咯咯地叫。她發現他頭上的罩子已經套在椅子腳上了,衝他放肆地冷笑道:「身手不凡嘛,不愧是漂過洋鍍過金的。」
他還在適應突來的亮光,沒有搭理她。
男人矮壯,圓臉蛋,圓肚子,像只木桶。他邁著方步徑直走到牆角,從椅子腳上抽出頭罩,把玩著,說了一句日語。女人翻譯:「聽不懂吧,他問你,如果我們再遲來一會兒,你會不會把繩子也解了?」
他適應了光亮,嗚嗚叫,要求對方拔掉口裏的毛巾。
女人看看男人,男人點點頭,她就上前一把揪掉了毛巾,喝道:「放老實點兒,不要叫,叫也沒用。」
男人拍一下她的肩,示意她退後,同時用一種類似口吃的語調和生澀、可笑的口音指責她:「你對我們陸上校這麽凶幹什麽,他是我用四輪大轎請來的大救星,是來幫我做事的,知不知道?」
女人諾諾地退後。
陸上校想說話,卻仿佛也口吃了,張了幾次口都沒有出聲,好像毛巾還在嘴裏。男人顯然對這種感受很有經驗,依舊用那種類似口吃的語調和生澀、可笑的口音安慰他:「有話慢慢說,陸上校,都是我的失職啊,讓你受這麽大委屈。」說罷,對外面吆喝一聲,一個小年輕便送來剪刀。
男人接過剪刀,熟練地給上校鬆了綁,並請他去隔壁屋裏坐。陸上校不走,因爲他要說話。他終於可以說話了,但似乎還不能說高難度的話,只能重復。他說的是嘴巴被堵之前說過的一句老話:「你們是什麽人,你們要幹什麽?」
男人呵呵笑,不語。女人有點自以爲是,又走上前來,漫不經心地說:「什麽人?我嘛,翻譯。他嘛,自然是我的主人哦,山田君。山田君要找你問點事情。小事情,都是你張口就來的小問題。走吧,山田君請你去隔壁屋裏坐呢,你也需要喝點水吧,那邊有。」
陸上校瞪她一眼:「聽口音,不像個小日本,怎麽,當上漢奸了?」
女人氣得揮手要動粗,山田一把抓住她的手,用日語訓了一句,回頭又綻開笑顔請上校去隔壁屋。上校開步往外走,發現走廊上除了一隻虎視眈眈的狼狗和剛才送剪刀的小年輕外,還有一個腰間明顯別槍的中年人,人高馬大,神色陰鬱冷漠,有股子深藏不露的殺氣。鬼知道周圍還有什麽人?上校思忖著,停在走廊上。
女人湊上前,對著他後腦勺說:「快走。別看他現在對你這麽好,如果你不滿足他,他就會用這把剪刀剪斷你的脖子。」
山田一邊嘰嘰咕咕地說著,一邊帶頭走進隔壁屋。女人推著他往前走,一邊翻譯著:「我的主人說,他希望跟你交個朋友。」
上校走進屋,看到辦公桌上放著香菸和茶杯,茶杯冒著熱氣,似乎等著他去喝。屋子的另一邊,靠窗的那一頭,擺著一張大台桌,桌上擺放著一盞煤油燈和一些刀具、皮鞭等刑具,分明是在警告他:敬酒不吃要吃罰酒的。
山田邁著像山雞一樣的步子,慢吞吞走到桌前,款款入座,順手把香菸和茶杯往對面的空椅子方向推了推,示意陸上校坐下。
「過去坐吧,」女人推了他一把,「放聰明點兒,有話好好說,說了你就走人,還可以帶走一堆錢。」
上校過去坐下,問山田:「你想知道什麽?」一邊喝了一口水。
「我知道你抽菸的,」山田抽出一根菸,遞給他,「抽根菸吧,壓壓驚。」
上校接過菸,又丟回桌上,「這是你們的菸,我不抽,我抽自己的。」他從身上摸出一根菸,點燃,吸一口,又問山田,「你想知道什麽?」
山田說,女人譯:「你知道些什麽?」
上校把弄著水杯,笑道:「我知道的多著呢,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變之陰陽五行,數之九流三教,乃至飛禽走獸,柴米油鹽,我多少都知道一些。」
「你說的這些,我們不感興趣。」女人搶白,她顯然沒把自己當做翻譯。
「那你們還問我幹什麽?」
「問你的當然是我們感興趣的,」山田笑嘻嘻地說,「比如你鎖在鐵櫃子裏的X—13密件的內容,我們就很感興趣。」
「什麽密件?對不起,聞所未聞。」
「X—13密件!」女人咄咄逼人地警告他,「我們知道你手上有這個密件,說,是什麽內容?」
「我要說不知道呢?」上校反問她。
「那說明你不識相,要我們動刀子見你的血!」
「見了血還不說呢?」
「那只有死路一條!」
「我以爲像你這樣活著還不如死。」
「我怎麽了?我現在可以叫你死,也可以叫你生不如死。」
「你已經生不如死了,人模狗樣,一條母狗而已。」
兩人唇槍舌劍,置山田不顧。山田倒也好,任憑他們吵,不置一詞。直到看女人受了辱,要發作,才出面壓住了女人,笑嘻嘻地對上校說了一大通,要求女人翻譯。女人不情願地收起性子,有氣無力地翻譯道:「山田君說了,你好像不想跟他交朋友,這樣不好,對大家都不好。告訴你吧,不要考驗他的耐心。你沒長眼睛嗎?外面有兩個人等著進來呢,你最好不要見到他們,他們比那隻狼狗還要凶。」
上校冷笑道:「請你告訴你的山田君,我什麽也不知道,他不需要忍著性子對我笑,讓他把真面目拿出來吧。你們有功夫耗,我還沒有性子陪你們囉唆呢。」
山田聽罷,拉下臉問女人:「他說什麽?他剛才說什麽?」看樣子他其實是聽懂了的,只不過不想直接發作,要過渡一下。聽了女人翻譯後,他覺得應該發作了,轉身從台子上操起一把尖刀,對上校怒吼一聲,把刀子釘在他面前,拂袖而去。
女人對上校說:「你完了,準備吃苦頭吧。」言畢朝外面喊,「來人!」
兩個打手應聲而現。女人吩咐他們:「動手吧,交給你們了。」
兩人一齊撲上來,粗暴地將上校按倒在椅子上,要捆綁他。上校想反抗,力不從心,那個大塊頭膂力過人,一舉一動都壓制著他。他斷定,此人就是下午把他扔上車的那個傢夥,這是一個高人,內功氣力都在自己數倍之上。轉眼間,上校已被捆綁在椅子上,像隻任宰的豬,無效地掙扎著。
女人從牆上取下鞭子,遞給大個子,卻對上校說:「現在說還來得及。」
上校的目光落在鞭子上,默默吸了口氣,準備受刑。
女人一個眼色,大個子手上的鞭子呼的一聲飛過來。上校本能地一扭身,連椅子帶人翻倒了,同時也躲開了鞭子。緊接著又一鞭子追過去,這一回已無處可躲,鞭子抽在背上,上校忍不住慘叫一聲。
女人說:「我再說一遍,現在說還來得及,別不識相!」
上校怒目圓睜,看著她,猛然朝她吐出一朵口水。那口水居然像子彈一樣,遠遠飛過去,正正地擊中她的臉頰,可見身手不凡,是有功夫的!女人的反應比中彈還恐懼,她本能地彈跳起來,尖聲高叫:「給我打,狠狠打!打死他!」她捂著臉跑走了,像有人摸了她的下身一樣。
*一*
天剛下過一場與隆隆雷聲並不相稱的小雨。
雷聲把街上的忙人和閒人都提前趕回了家,平時嘈雜的大街在越來越暗的天幕下,顯得越來越空洞、平靜。但沒有下足的雨卻使空氣中更多了一份溽熱、黏稠、潮濕,仿佛伸手摸得著,抓得住。他穿了一身對這種天氣而言明顯是太熱的軍裝,默默地穿過狼藉的市街,拐入一條幽靜的小巷。在進入小巷之前,他不經意地看見一隻褐色小鳥在灰暗的天空中一掠而過,短促得讓他懷疑不是一隻鳥,而是一顆流彈。
小巷窄又深長,一眼望去,空空的,了無人影。有幾棵高大、蒼勁的桉樹和泡桐,從兩邊的高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