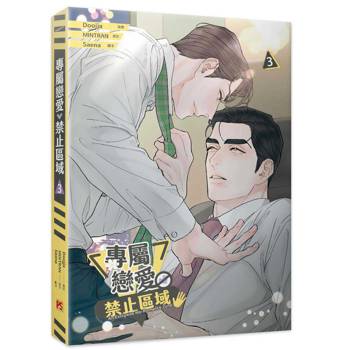推薦序
純真之光與暗影
看過《我是許涼涼》之後,我以為要採訪的對象會是一個優美時尚的資深熟女,一個善體人意的職業女性。直到見面才發覺,骨架纖細,有著一雙大眼睛的李維菁,當她靜悄悄地出現在身邊時,其實更像個研究所學生。
「我的生活很單純。也許就是因為自己的生活太簡單了,所以很愛聽別人的故事,常常在別人生活裡瑣碎的細節,我都能夠牢牢記住。」李維菁不諱言,《我是許涼涼》敘述一段相差十二歲,女大男小的姊弟戀,是刻意選擇了一個現代都會生活中最時髦的話題做為核心,這樣的題材雖然不算大膽,但是在李維菁綿密細膩的滔滔雄辯下,把一個三十八歲的氣質女生欲愛卻得不到愛的心情,描寫得讓人感動,也讓人心疼。
因為太真了,讓我這個同樣寫過小說的人,都忍不住有對號入座的質疑,將作者形塑成一個世故與天真揉和,冷靜與多情相偎的旖旎女性。是否在作者的真實生活裡,也是如此繽紛豐富?
「我對視覺非常敏銳。對人的印象,常常不是集中在他的長相,而是他身上衣著的顏色,他的手指頭,他的配飾,他的姿態。想要依賴語言與文字去了解一個人,其實很虛偽。」
李維菁一語道破了現實世界的殘酷。同樣身為職業女性,我認同她所了解的殘酷是我們每天必須面臨的生活挑戰;但是同樣以文字做為遣懷或抵抗人間炎涼的創作者,最終相不相信這世界還保留一種叫做「純真」的東西?
「你白天遇到鬼的機率有多高?」李維菁回答:「純真只是一種概念。它像植入腦裡的晶片,持續地反覆辯證。純真就像是一種程式,在演算的過程中,會不斷更換設定條件,每一次拆解或移除、加減,都會更改程式的演繹,也就改變了定義。」
在《我是許涼涼》中,華麗地展演了這一場繁瑣推理的愛情方程式。三十八歲的女人與二十六歲的男人,因為靈魂的相似而牽引碰撞,在愛情的火焰中燃燒,而餘燼是什麼?
「小時候我也相信某種光的存在,那是最漂亮的顏色,疆界的消失,人與人之間的融合。因此我對藝術特別感興趣,那些遐想與創造、璀璨與朦朧……,但是當我真正從事現代藝術的採訪報導工作之後,見識到了這些藝術家的真相,心就老了。那時候我就在思考,我要不要長大?要不要投入?」
彷彿美好的真實只存在於年輕,於是我們發掘了共同的記憶,同樣迷戀美國老牌男星葛雷.格萊畢克,法國女星凱瑟琳.丹尼芙,以及童年時最喜歡整理媽媽的珠寶盒,將一個個閃閃發光的項鍊、珠寶、戒指、拿出來羅列整齊,再依序置入收藏。甚至,連針線包都成為最親暱的伴侶,將眾人置之不理紛亂纏繞的線圈與死結,用縫衣針一筆一筆細細地挑開,鬆綁,展延出俐落筆直的線條,重新恢復原狀。
年輕象徵某種純真嗎?我說了關於一個女人教導她的兒子將來長大以後「娶妻要娶德」的故事,結果兒子在讀幼稚園時,就懂得選擇那個認真聰明又溫柔聽話但是長相抱歉的女孩子做為好朋友,而不是另一個全身名牌古怪精靈總是故意作對的漂亮妹妹。
當我欣慰於小男生早熟到瞭解伴侶的意義是「互相照顧與陪伴」時,李維菁說出了她更犀利的見解:「這是權力的分配。連小男生都懂得選擇最有利於自己的條件。」
難道這就是許涼涼注定面對的悲劇?在第一章裡,男人的母親陰影不斷,男人總是刻意錯開母親與情人相遇的機會,男人滿嘴推辭與謊言,男人畏愛著他的母親。許涼涼,一個睿智溫柔又懂得時尚品味,具備強烈的社會敏感度卻又嚮往真愛的女性,雖然年紀大了一點,卻超越不了男人的母親,而陷入了不利於己的階級位置,成為輩分更上位者宰制的工具。
「母親跟所有年長者,在上位者一樣,是所有資源的來源,他們掌握權力的控制。就像小孩撒嬌跟母親要錢,學生用功博取老師給予好成績,下屬努力工作渴望得到長官的嘉許,所有想要邁向菁英之路的人,都會選擇最有利於自己的方式,求得認同;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公式。」
所以許涼涼會說:「美麗的、明亮的、活躍的、多彩的、富有的、生殖力旺盛的、家族顯赫的、強壯的、富饒的、資源豐富的、無所畏懼的、充滿信心的,終究會獲得一切。」
原來一切早已經分配好了,這個時代從來沒有像過篩子,篩得少數人出類拔萃,多數人流離失所;這是一個完全自動化的標籤時代,上流與下流永遠不會融合,那些消泯疆界的最純粹的包容性極其廣大的關於「光」的想像,從來就不存在。
「其實我小的時候就已經知道這些階級的律法了,但我當時以為愛情是唯一可以打破這牢固階層使之崩潰決堤的唯一可能。」故事中的許涼涼如此解讀人性。真實生活裡的李維菁,為筆下人物做了更透澈的形容,她認為許涼涼不是耽溺於愛情,她執著的是「虛妄」;「知道而不理解,是許涼涼面對社會眼光的狀態。在第八章裡,我做了非常多的論述,許涼涼看不清楚現實,她不懂什麼是界限,她也不明白在人際關係的收放自如是什麼樣的境界。其實,這些也是我胸中塊壘經常纏繞的疑問。」
誰懂得?除了張愛玲的小說人物白流蘇在未傾之城牆下向范柳原調情時能義無反顧地說出:「我懂得!我懂得!」之外,那些年長者在上位者也不見得有足夠的智慧來解惑,他們只是主宰了權力的分配,他們就是王。權力的分配來自群眾力量,因此必須要先有組織,也就是同儕,小圈圈。這種狡黠靈巧的政治智慧,又豈是借筆抒懷的青青子衿悠悠我輩之心?
「小學時我總是被排擠,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永遠被摒除於圈圈之外,沒有任何理由。那些天生的公主們,在任何環境下都能迅速結合某種群組城邦,一旦有了勢力,立刻展開權力的掌握與分配。我看盡同學的嘴臉與老師的眼光,讓我更不相信語言與文字的意義,直想拆穿所有的虛偽。」
我想到了我的童年,因為單親家庭的背景,我被貼上了標籤,那時候,我也在圈圈外面,看著圈圈裡的人歡樂地跳高踢毽子,玩躲貓貓,每一次的冷空氣都在我加入團隊之後降臨,上課鈴聲也總是在氣氛凍結後的三分鐘內響起。
生命中的大圈圈小圈圈,都像雨水激起的漣漪一樣交錯於淺擱的湖泊,李維菁是撐傘駐足於湖邊的人,她冷眼旁觀人情冷暖,卻也在雨中淋得滿身濕濘。
「其實,你愈不相信語言與文字,不相信愛情,或是質疑某種純真的降臨,就代表你愈恐懼;愈是恐懼這一切,也就愈顯得你多麼想得到它。」
我們都在心裡豢養著一個童稚的自己,縱使歷經了成人社會的洗禮,小女孩偶爾還是會跳躍出記憶質疑,這世界有沒有因為你們的長大而變好?慧黠的李維菁說,我們不要這麼嚴肅的訪問了,不如一起去買買化妝品,看些亮晶晶的東西。我多麼贊同她的提議啊!詩人艾略特用《荒原》陳述二十世紀文明的虛無與沉淪,李維菁用高度細緻的文字在《我是許涼涼》中書寫了二十一世紀的孤獨處境。所有的哲學都是這樣開始的:四月是最殘酷的月分,死地裡生出紫丁香,揉合慾望與回憶,讓春雨滋潤遲鈍的根芽。
當春雨降臨的時候,說一聲朋友會不會太奢侈?我覺得我認識許涼涼好久了。
【2010.10月號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朱國珍專訪李維菁
序
少女革命與鬼故事 楊澤
A.
法國人羅蘭.巴特說過這樣妙語:「上帝存不存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本來就不應該,同時發明愛情與死亡……
B.
延伸巴特,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說:「上帝存不存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本來就不應該,同時發明愛情與城市……
C.
《聖經》說,愛比死更堅強。
的確,如果沒有死的有限性,人何以證明愛的無限性?
沒有瞬間與永恆的辯證,人又如何證成愛情「瞬間永恆」的真理?
日本漫畫《美少女戰士》中的女主角月光仙子,武器、配備雖然十分陽春,單靠純愛的力量卻能一再擊退邪惡勢力。倒過來,倘若沒有邪惡勢力的威脅,月光仙子又何以成其純愛、真愛的象徵?
D.
也許有人會質疑,愛情到底是一種發現,還是一種發明?
我們是不是應該,反過來這樣說:就像人類先發現愛情,才發現死亡,人類先發明了城市,然後才發明了愛情。
的確,愛與死已變成了,流行文化的一道方程式,而城市正是這道方程式,得以展開歷史辯證的偉大舞台。
E.
延伸巴特,我們是不是應該這樣說:「上帝存不存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愛情存不存在……
F.
二十年前,因緣際會,有這麼一座我們身居其中的城市,開始與資本主義大談戀愛,因而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消費時代。
在這個城市,產生了各式各樣的風潮或革命,譬如,寵物革命、宅男革命、少女革命,也因此促成了各式各樣,寵物學、宅男學、少女學的論述的誕生。
談到女人從家庭出走,在城市獲得解放,這早已是眾人耳熟能詳女性歷史的主流。進入城市前,女人原來處於權力關係的邊緣,只因為資本主義——城市文明的初戀情人——導致城市興起,帶動了消費革命,女人遂得以在日常生活的實踐過程中,找到新的自我。
G.
回頭看去,二十年前的少女革命其實與消費革命密不可分。
跨國百貨公司紛紛崛起,身體的商品化、時尚化益發受到強調,加上女性主義論述的成功發酵,「姊妹向前走」,少女不單成為新的消費主體,也是新的文化英雄,一時之間,如果套用晚明理學的說法,「滿街都是聖人」——在我們當年的消費城市帝國裡,也似乎,滿街都是美少女戰士。
H.
回頭看去,城市少女當年所經歷的,不只是向外走,也是向內走的一段過程。
向外走也正是一種向內走。向外,頭角崢嶸的城市少女經歷了,與世界的摩擦和碰撞,在校園與職場、家庭與百貨公司之間,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拉扯關係;向內,從集體過渡到個體,既純真且世故的城市少女反覆推敲思考,暗自演繹出一個又一個,既浮華且昇華、既保守且爆破的角色造型。
形形色色的城市少女,不管是打扮休閒隨性,舉止落落大方,抑或是穿著整齊套裝,儀態有所矜持,三三兩兩,她們在街道和巷弄之間出沒徘徊,行走著且窺視著這座城市。
我們可以這樣說,她們自成一個族群,卻從來也不願意,輕易的在城市中認出彼此。
I.
二十年後,當讀者看到李維菁一系列標榜為少女學的短篇故事,不禁會興起滄海桑田、往事並不如煙的似曾相識之感。
就如咖啡館、小酒館、pub當年還猶是新生事物,如今,連便利商店都賣起咖啡和紅酒,看在五年級、六年級的眼裡,別有一種況味。pub裡仍然是酒促美眉與塔羅牌,揉揉眼睛,卻是景物依舊、人事全非。當年鬧得轟烈的小少女、革命少女們,如今都已成了拒絕老去的老少女,美其名曰熟女與輕熟女。
借故事人物之口,李維菁說:人近中年,胸中的少女始終不肯走。
可她並不準備回頭是岸。
J.
李維菁寫城市的pub,寫其中的男歡女愛;她寫陰性的細節,唇蜜、彩色指甲、離子燙、單眼皮及雙眼皮。李維菁也寫不倫,姐弟戀、老少配;她寫感情的出軌,不太直接寫第三者,雖然在她的世界裡,第三者似乎無所不在。
李維菁和她的故事人物,駱以軍說「她的許涼涼們」,都是城市遊魂。李維菁說:她知道自己是鬼,別人卻不知道,她恍恍地在人世中漫遊,無恃無靠,但是也無所渴求,留在這裡就是只剩一雙貪婪的眼睛愛戀世上花花綠綠,五光十色。
李維菁自言,有雙天生滄桑的冷眼,敏於觀察世上的眾生相。如果你以為,她就是長期以來,文化理論千呼萬喚、萬眾期待的「女漫遊者」(fluneuse),那你就錯了。
K.
對照上一代女作家的冷眼,筆下人物往往表現出悲苦淒涼,卻又言語尖峭的特質,李維菁和她的「許涼涼們」(李維菁的命名不無反諷之意),她們的內心卻擁有另一種熱情的鬼火。
李維菁的人物總與世界隔著一層薄膜。談到新一代城市少女,不管是老少女還是小少女,她們的扮演是個頗複雜的題目,無法以幾句話說明白。如果一定要說,「甜」是個關鍵字,「可愛」或「裝可愛」是另一個。
「甜」是那種,在服飾之上之下,自然流露出的很特別的「自愛」。這份「自愛」,我在別的地方說過,既是高度自戀、「自閉」的,卻又極其渴望被他人凝視。說穿了,美麗的衣服、身上的配件配備,不只是孔雀開屏般,都會文明的「奇觀」(spectacle),更是一層量身打造,薄薄的玻璃罩。只是在這些城市少女身上,這層擁有童話色彩的玻璃罩,似乎變成了某種入口即化的糖衣。
李維菁的人物打扮擁有更多細節的趣味性,她們靈活地活在這個消費城市中,不至於像契訶夫式的「套中人」那般僵硬。但這些城市少女的「可愛」並不單純,與其說「可愛」,不如說「裝可愛」。所謂「可愛力量大」:可愛所以力量大,其實就在於它不是可愛,而是裝可愛,因而有一種隱藏的攻擊性,比上一代的「錦衣華服,嚴陣以待」,更具攻守自如的靈活性。
這些美少女戰士們也許不再活在父權的陰影下,卻因為渴望愛情,永遠活在 她們的對象物與欲望物,她們的愛人的凝視與回望之中。
L.
不像過去的三毛,李本人並不是那種離開熟悉環境,四處漂泊的吉普賽人。
借故事人物之口,她告訴我們:她每天在固定時間起床,走固定巷弄,搭固定捷運路線去工作,到固定的咖啡廳,坐固定角落,點固定的餐。
但如果你以為,她是那種以擁有「自己的房間」為滿足,或者那種點一杯咖啡,坐在咖啡館寫作一整天的上一代女作家,你就錯了。
李維菁跨界,但你也可以說,她不跨界(她的不跨界就是跨界)。她是那種,把城市當作天涯海角來流浪,在少女江湖打滾了很久,熟悉各種密碼、律法與遊戲規則的新人類。她長期在職場工作,對於資本主義的消費市場或人肉市場,一點也並不陌生。在這點上,就像在愛情上,她是個老江湖。
M.
李維菁並不特立獨行,她從來不是那種,在群體中大放異彩、馬上帶走你目光的城市少女。反過來,她似乎是那種怪怪的,坐在邊上看著眾人的女孩。她也渴望注視,或者說,她在內心是偷偷地、強烈地渴望著。當你注意到她時,你會被她的氣質,和她看人、看世界的獨特態度所吸引。直到你回過神來,你才恍然,她早已朝你的方向,從容地眨了好幾眼。
西諺有云:好女孩上天堂,壞女孩走四方。那麼怪女孩呢?她們會有她們的心思、她們的鬼計,只是,她們把那些心思、鬼計全部用在她們的愛情,她們的男人身上了。
在「單眼皮」這類短篇中,李維菁公布了她的性別策略,可算是城市少女學的一個高明套招。敘述者將世界上的男人輕易分成單眼皮和雙眼皮兩種,前者重義,後者情深;她說「單眼皮的眼睛有神、有力,冷靜之下有種抑制的熱情」,而雙眼皮「情感氾濫太過閃爍」,誰會喜歡一個雙眼皮比自己更深的男人呢?何況,電視命理節目也都說,雙眼皮男多情,單眼皮好,冷靜理智。敘述者的對應策略因此是,單眼皮做好情人,雙眼皮做好兄弟。
雖然故事幾經轉折,敘述者最後發現,雙眼皮固然情深,單眼皮固然義重,卻都不是為了她。結局雖帶有黑色喜劇的幽默與苦澀,至少對我這個讀者而言,卻另有一番啟示。城市少女深諳情愛的法則,知道愛情的脆弱與短暫,因此往往設下好幾道防線。第一道防線,可以是死黨、哥兒們,可以是妹妹或美眉,萬萬就不能是情人。
這樣的性別策略還有其他的好處。它讓李維菁,在情與理之間多了偌大的迴旋空間,也讓她有了與男性讀者作者,平起平坐,甚至一決雌雄的機會。
N.
李維菁其實不可能滿足於少女學的。時間的流逝,身旁充滿拒絕離開的幽靈或回憶,壓迫她一定要去問那些終極的大問題,譬如:愛情到底存不存在?愛是否比死更堅強?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李維菁,迫於時間的壓力,開始坐下來寫出她的第一篇故事。可以確定的是,從一開始,她就以過來人或「女鬼」的姿態出現。她的第一道防線早已潰堤,第二道、第三道也都守不住,她卻未輕言放棄。但,寫作絕不是她的最後防線,因為我們看見,她在作品中死去活來,從人變鬼、從鬼變人,隨時準備作反撲。
這點上,李維菁便不單是個老江湖了。我們甚至在她身上嗅到了,那麼一點女浮士德的氣味。像浮士德一樣,她一開始就告訴我們,她死了。的確,有好幾次,她愛得要死要活,她徹底垮了下來。但,野草燒不盡,只要一點休息生養,只要春風一點撩撥,她馬上又變得,像浮士德般,情不自禁、身不由己了起來。死了還要愛,還要愛得益發兇猛,益發情深義重。
O.
就像漫畫中的美少女戰士,李維菁既是不死的少女的精靈,也是不死的愛的精靈。
專屬於少女的那份「自愛」,那種自我的戲劇化,在她的兩部份量較重的小中篇,被推到了頂。我說的是,「我是許涼涼」及「普通的生活」,二者都是寫老少配,前者女大男十二歲,後者男大女二十歲。
老實說,這些並不是什麼獨特的城市傳奇,但眾人往往以八卦心態看待它,其實卻又視若無睹。李維菁以第一人稱觀點,以無比嚴肅的姿態去處理,這種日本人稱為「純愛」的不倫戀,更重要的,去面對內心,那個始終不肯走的少女,那一點始終在城市荒原中明滅閃爍的鬼火。
P.
而這也是李維菁與過去、與世界的對決。上一代女作家以寫作為職志,常擺出類女巫的姿態,透過標榜文字的鍊金術或某種超越性,追求自我救贖。李維菁卻化身故事中人,說出這樣的話:我常覺得我無知,無知到無法滄桑……我如此孱弱又這樣帶種。
她又傾向於揭開愛情的夢幻性,兩部小中篇皆見有關階級的大量討論。譬如,底下這樣一段自白:「其實我小的時候就已經知道這些階級的律法了,但我當時以為愛情是唯一可以打破這牢固階層使之崩潰決堤的唯一可能。但,其實什麼都是早被階級化規定好的。這世界,早就規定好了,哪些人會被愛,而哪些人不會被愛。」
這些有關情慾律法與世界律法的討論,似乎構成了某種階級跨界。李維菁卻誠實的告訴我們,這是因為:在現實情慾世界的律法中,我如今也成為卑賤弱勢者,一個中年、平胸、不美麗、不有錢、沒有事業地位的人,一無所有的女人。
Q.
既痴且頹,李維菁和她的敘述者分身,在〈普通的生活〉結尾,勇敢地打開了愛的黑盒子。
這次,她沒看見自己或愛情的倒影,沒看見小愛,她看見了別的東西。她說:「上帝,我跟你說話,你聽好。打從出生的那一刻我便命定是個不合時宜的存在,終其一生虛度流年,投注對虛妄的執著,人世一切的進程我全不自覺地擦身而過終至於流失,孑然一身讓記憶纏繞。」她又說:「我也必須對你坦承,多數的時候我根本不相信你的存在,懷疑痛苦的時候我卻又質疑詛咒你……」
在長達數千言的喃喃獨白裡,她展現果敢的知性與感性,探討宇宙萬物,及人世的現實存在與循環。她與上帝平起平坐,變得雄辯滔滔,而上帝啞口無言,似乎只是另一個不負責任的老男人。她宣稱,她已破解上帝的密碼或造假,而她的老男人J並不知道:
J我,還有那成千上萬的你與我,都是宇宙星砂塵埃碎片,然而儘管這些灰燼在碰撞之際,也曾經分享過那樣相同的虛妄與迷離,相同的感受,靈犀撞擊發生閃電一般的震撼與火光,那樣哀愁壯麗。執著成那樣濃烈的,已經不能說是曾經了。
那不可能是回憶。
那不可能是他方,那是此時此刻。
J以為在他方的,其實是此時此刻。
李維菁早不復是她自稱的「女鬼」,那個盤據在她胸中、趕也趕不走的少女。她已經把自己提升到「幽冥界女王」的層次。祝福李維菁,以及所有同她一起走過,那個少女革命時代的台北少女們。


 2011/02/27
2011/02/27 2011/02/07
2011/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