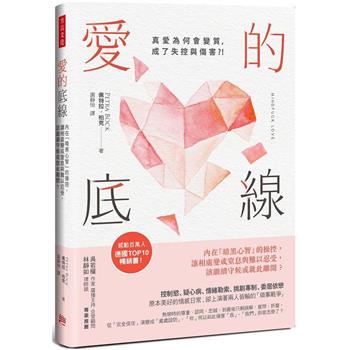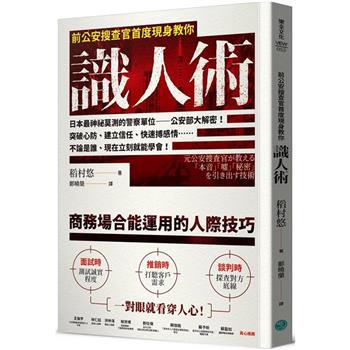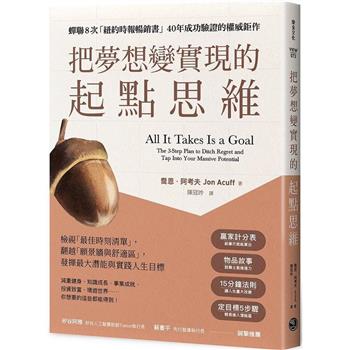給臺灣讀者的話:
很榮幸有機會能夠介紹我的好友唐諾.E.威斯雷克的作品《紙謎線索》給臺灣的讀者。讀了以下我的短文就知道,這本書問世的過程曠日費時而且十分曲折,一直等到我的好友過世之後,美國與世界各地的讀者才得以接觸到這本書。
臺灣讀者相當喜愛我自己的作品,能在臺灣找到敞開心胸接受馬修.史卡得、柏尼.羅登拔、以及我筆下其他角色的讀者群,令我覺得十分幸運。期待各位會同樣地歡迎唐諾.威斯雷克的書,《紙謎線索》是對他不熟悉的讀者們的最佳入門之作。─勞倫斯.卜洛克
追憶《紙謎線索》 勞倫斯.卜洛克
一九六三年春天的某日,郵差送來了一份三百多頁的手稿複寫本。送達的地址是紐約州托拿萬達市埃博靈道四十八號,當時我跟老婆、女兒在這裡剛住滿一年不久。那時老婆懷孕了─我們的次女後來在國殤日 1出生─我寫作產量很高,收入頗豐,除了幫幾家出版社寫情色小說、為推理雜誌寫短篇,偶爾還用專寫醫學作品的筆名出版講述個別性生活史的小說。我住的房子不錯、環境優美,儘管那段婚姻也許已經註定要完蛋,但我還沒有意識到這點。唯一缺少的是其他作家朋友;住在紐約市時有作家朋友,如魚得水,回到水牛城便覺得有所失落。
出現在我信箱裡的手稿,是我的摯友唐諾.威斯雷克寄來的。搬到托拿萬達之前,我和老唐的住處隔了好長一段地鐵;他跟妻子和兩個兒子住在卡納西 2,距離十四街地鐵線的最後一站將近一公里,而我和妻女則住在中央公園西大道四四四號,當時該地址是棟豪華的大樓,不過所屬的地段連「邊緣社區」都稱不上 3。我們搬家的時候,威斯雷克一家也準備遷移到紐澤西英國城的一棟透天房屋。雖然托拿萬達和英國城之間的書信往返相當頻繁,但感覺就是不一樣了。
我收到的那份稿子,是老唐剛剛完成的書稿;寄達的那天跟其他日子大同小異,唯一的不同是我胸口疼痛。我還不到二十五歲,不太可能發生心肌梗塞,可是偶爾胸腔左側會覺得悶悶的,這讓我很擔心,事實上我也打了電話給醫師,安排好隔天去看病。(我就別吊各位胃口了:我沒有毛病,幾十年過去了才終於恍然大悟,那些症狀、以及那陣子其他顯示我將死的種種跡象,幾乎可以肯定是由於家父意外猝逝的緣故。)
重點是:老唐的書稿寄達,我在吃完晚飯,把孩子哄睡了,開始閱讀書稿。然後老婆去睡了,我熬夜繼續閱讀,過了一陣子,我忘記自己「有心臟病」,一直讀到大約黎明時,把整本書讀完了。就在這期間我意識到,我那寫了幾本推理小說、科幻作品、以及一些軟性情色作品的好友老唐,剛剛完成了一本了不起的小說。
然後,大家都知道的,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我不知道老唐有什麼樣的期望,我自己是料想會有人出版這本書,得到強力推薦的書評,一般大眾的反應也不錯。印象中我當時並不認為《紙謎線索》會讓老唐口袋飽飽,不過這是將近五十年前的事情,而我們這群人大概沒有一個把寫作當作致富之道。大約一年前(二○○七),我去老唐在卡納西的公寓樓上坐,他向我透露,覺得自己以寫作為業,算是熬出頭,前途也穩定了。「我想,」他小心翼翼地說,彷彿不願把這些話說出口:「假如我繼續像之前那樣寫,一年賺個一萬應該不成問題。」
我沒有預見的是(我想老唐八成也沒有),他的經紀人竟然找不到人出版《紙謎線索》。
不過事情就是這樣,但回頭來看,並不難理解原因。當時代理老唐的亨利.莫理森年紀比他還輕,而且主要是經手通俗小說。更重要的是,亨利的上司是史考特.梅瑞狄斯,在有點水準的文藝圈中,名聲比池塘底的汙泥還要爛上好幾級。
亨利很努力,到處送出書稿,大部分讀過的編輯都覺得很棒,許多人的回應都表達出「要是我能出版就好了」的意思。然而他們對本書的熱誠就僅止於那樣的話語,每個人都把《紙謎線索》退回原處。
原因是,這本書說穿了不過是部頗長的小說,內容並沒有跟時事掛勾的議題可供行銷,作者的出版史也根本派不上用場。(藍燈書屋曾經為老唐出了好幾本精裝推理小說,藍燈是出版社業界的龍頭之一,但在純文學的世界裡,這並不等於「有口碑」,至少一九六三年時不算。)其中一本《The Mercenaries》(目前由大案公司 4以老唐原先定的書名《The Cutie》重新推出)曾入圍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愛倫坡獎最佳新人作品。聽起來很厲害吧?現在也許是這樣的,不過半世紀前,這個獎的聲譽並沒有那麼高。那年頭,愛倫坡獎這玩意除了美國推理作家協會之外,才沒有人在意個屁;要不是還有一小群推理作家和人數稍多一點的推理讀者捧場,推理作品跟諧星羅德尼.丹傑非爾德 5一樣,都「沒人看得起」。
話說回來,當年出版業還沒有那麼商業化,出版商可以冒險出書,甚至願意出版明知會賠錢的作品,只因為覺得應該讓社會大眾有這本書可讀。因此,到現在我還百思不解為何當時沒有人願意買下這部作品的版權。藍燈書屋為什麼不願意出版呢?光是為了讓作者開心、讓他在推理界之外添增一點純文學的光輝也好啊。
不管了。總之,那部書稿就像假錢或卡匹史川諾的春燕一樣,不斷回頭 6,而最後亨利再也無處可送稿子了。
許多年後─應該是一九七○年代後期了吧─亨利告訴老唐,也許能幫他找到人出版《紙謎線索》。這時他早已跟史考特.梅瑞狄斯分道揚鑣,老唐在推理界的地位已經大幅提高,而且推理作品在文學界的身分也沒有以前那麼像拖油瓶般爹不疼娘不愛 7了。
老唐對我說了這件事,又說他重讀稿子後,認為這本書已經錯過問世的時機,有許多方面跟不上時代,不適合出版了。
我可不確定真的是這樣;在我看來,這本小說的價值足以雋永流傳。不過,我自一九六三年之後不曾再讀過這本書,有什麼資格說話呢?
(差不多寫到這裡,我想我應該附帶說明:亨利絲毫不記得這一切。他不記得這本小說,也不記得他曾經賣不出老唐的書,更別說是十五年後還想再試一次了。「這是我賣不出版權的書?」他說:「唉唷,我怎麼可能記得那種事情啊?」咳,這就是記憶啊!)
二○○八年的最後一天,老唐突然去世。才過了幾天,美國推理作家協會就有人請我為會訊《三級謀殺》寫一篇追悼他的文章。我在文中提到老唐是個縱橫各種文體的作家,也講到要不是有某些障礙,他的寫作之路說不定就會轉往不同的方向。我正是在此談到了《紙謎線索》,提到如果當時這本書的銷路沒那麼慘,老唐可能會寫出什麼樣的作品?
這篇文章我用電子郵件寄了一份給老唐的遺孀愛比,告訴她也許會有人讀完文章後想要找出《紙謎線索》,她要有所準備。結果並沒有人前來詢問,不過這是愛比首次得知這本書的存在;她在老唐浩瀚的檔案中翻到這份書稿的複寫本時,便認出來了,問我想不想讀讀看?
老實說,那複寫本真是殘破不堪。我想,我們這些還記得複寫紙的老一輩大概所剩無幾了,我得承認,我可一點都不會懷念它。我有好幾年都離不開它,只要打字打到頁尾,就得拿一張複寫紙,夾在一張高級打字紙和一張便宜的馬尼拉紙中間─我們把那便宜貨叫做「第二張」,然後再把這份「紙三明治」塞進打字機。許多年之後,影印的價錢變便宜,我才能夠不用複寫紙,然後再過幾年,我連打字機都能丟掉了。如今,我們用網路傳輸文件,幾乎都可以不用紙了;電子書發明後,也不需要印刷;還有─停。
總之那複寫本殘破不堪,有幾頁撕破了,用透明膠帶黏起來;有些撕破了卻沒補。而且老唐跟大多數作家一樣,有時會把同一張複寫紙使用過度,因此有幾頁比其他更難以辨識。不過,上帝呀,確實就是那本書,完整無缺,字跡還夠清楚,可以讀得出它正是我四十五年前讀過的書稿,依然是我記憶中的小說巨作。
然後呢?
我首先意識到的是,書稿必須拿去掃描。以它目前的情況,閱讀起來非常不方便,更何況紙張太脆弱了,翻個幾次就會瓦解;影印的話,字跡反而更不清楚。掃描似乎是最好的答案,於是我試著做了,但要不是我的掃描器不行,就是我本人的技術不足,無法達成任務。
於是我想到了查爾斯.阿爾戴。我知道他是老唐的忠實讀者,知道他在大案出版社一定很樂於重新推出一些老唐早期的作品,心想他正是《紙謎線索》最理想的出版商。
而且由大案公司出版,在我看來並不算太撈過界。《紙謎線索》符合奧圖.潘茲勒 8對「推理作品」的這個定義:犯罪行為、或可能發生的犯罪行為是故事中的元素,不過這本書比較接近存在主義小說而非通俗小說。我得說一下,本書是講一個巡迴劇團的演員,被戴綠帽的丈夫捉姦在床、打得半死,結果得了持續性的失憶症,人生毀於一旦。《紙謎線索》是男主角拚命掙扎著要找回從前生活,卻註定失敗的故事。
這算推理作品嗎?也許不算,但無論如何絕對是本黑色小說。更何況本書不只背景設在一九六○年代,也是當時寫的,如同大案出版社大力推出的許多作品一樣。因此,我在愛比.威斯雷克授權之下聯絡了查爾斯。我想我至少能夠拐得他把這本書掃描起來。
查爾斯非常喜歡,把出版這本書視為大事,並同意在他的出版清單上添增它的位置。《紙謎線索》的試讀風評絕佳;關於這本書我覺得只需這麼說就夠了,因為各位可以自己去讀,我也希望你們會這麼做。
不過,要知道,我還是不禁會臆測幾件事。
首先,我不得不猜想老友會怎麼看待這一切。各位應該記得,他曾告訴經紀人不必找人出版《紙謎線索》,說它跟時代脫節得太厲害了,寧可就這樣不要出版。假如它超過二十年前就已經跟時代脫節,時至今日,就比較不脫節了嗎?
答案可以說是「對」。也許多歷經這段時間反而對本書有利:經過了二十年,它從「過氣小說」變成了「時代小說」。
話說回來,這畢竟是他的書,而他決定不出版了之後,並沒有機會推翻原先的決定。我想,他見到這本書終於獲得應有的認同、讓一般大眾得以閱讀,應該會很開心,但這終究只是我的猜想罷了。再說這個問題根本討論不出個所以然,不是嗎?假如人類真的死後有知,我實在無法想像靈魂會花一大堆力氣去管塵世間的人在做什麼、著作是否有人在讀。
(更何況,出版《紙謎線索》絕對讓老唐的鬼魂不得安寧的程度,絕對比不上另一個出版他遺作的計畫。以前─很久很久以前─老唐跟我合作寫了三部軟性情色小說,輪流寫不同章節,好玩極了。地下出版社 9二○一○年年底將推出三部合訂本,書名是《野貓與蜜糖》(Hellcats and Honeygirls)。老唐知道這件事會高興嗎?拜託,連我都不知道自己高不高興了。)
我還臆測了什麼呢?這個嘛,我再次猜想,不知道《紙謎線索》如果在寫作完成時就出版,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發展?我不想揣測出版後它的評價可能如何,也不想推斷它會不會入圍普立茲獎、美國國家圖書獎,或是我們必須接受它的銷售量可能很小但還算過得去,書評不錯卻不怎麼驚天動地。怎麼說呢,可能會叫好不叫座吧。
這樣對老唐的寫作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很想說,不會有什麼作用,因為像老唐這樣寫作態度嚴謹的人,並不會因為是否賣座而勉強寫他不喜歡的題材,也不會因此而放棄他喜歡的題材,而會寫出他天生命定該寫的作品。我們作家大多是這樣沒錯,至少在意識中是這麼想。
可是真正耕耘寫作時,有太大的部分是在深層潛意識中進行。成功會招致更多成功,而成功的動力會產生新的點子。我相信,假如《紙謎線索》當初真的出版了,接著會出現更多黑暗的存在主義傑作。我知道這一點,不單是因為作家差不多都是這樣的,也由於老唐其他作品的演進過程中可看得到這樣的模式。
不用說,他一直都是以趣味推理作品聞名。我們很容易忽略掉,唐諾.E.威斯雷克最初的幾本小說都是扎扎實實的硬派推理作品,而且他在推出第一本趣味推理小說《沒命逃亡的傻瓜》(The Fugitive Pigeon)前,已經出版了五本硬派小說(外加以李察.史達克為筆名出版的五本帕克系列小說)。
《沒命逃亡的傻瓜》比之前那些作品都賣座,也有較多書評注意到它。然後下一本書《忙碌的屍體》(The Busy Body)又是一本趣味推理小說,不但很賣座,更改編成電影。於是,老唐就這樣成了趣味推理小說作家。他依舊會寫硬派小說,以及其他不易歸類的作品,但《沒命逃亡的傻瓜》卻引導了他的寫作生涯,固定了他的寫作方向。
他是否無論如何都還是會寫出趣味作品?這個嘛,大概吧。如同大多數的人,他有光明歡笑的一面,也有黑暗陰鬱的一面,而在作品中抒發這兩面則是他成就自我的最佳方式。不過,早期的趣味作品很成功,鼓勵他的內在產生更多好笑的點子,一路走來從未間斷。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還有一個相反的例子:六○年代中期,老唐寫了三、四個現代短篇小說。小說中並沒有犯罪或推理元素,而是探討現代的男女關係。(我上次讀這些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我懷疑這些小說已經從世上消失,所以大部分的內容我已經忘記,只記得是描寫在感情路上跌跌撞撞的情侶,角色生動鮮明、認同感強,故事也很有趣。)
他會寫這些作品,並不是因為他覺得寫短篇小說有什麼特別的意義。那個時候就跟今日一樣,寫短篇小說都沒什麼用。他會寫,是因為靈感來了,吸引住他的注意力,況且短篇小說只需花幾天而非幾個月的時間,幹麼不寫寫看呢?
於是他便寫了,結果卻是一場空。有幾個雜誌的編輯雖然喜歡,可是沒有喜歡到願意花錢買版權的程度。於是事情就到此為止。
「那些故事寫起來很有趣,」當時老唐是這麼告訴我的:「假如我有其他點子,一定會繼續寫,可是我已經寫出來的沒人要,所以我心中產生靈感的那部分就說:老子不幹了。」
說真的,在這邊猜想如果情況不同,老唐可能會寫出什麼樣的作品,其實沒什麼意義。就我而言,光是他實際上寫出來的作品,就已經讓我很高興了─更高興的是《紙謎線索》總算將重見天日。─原載《Mystery Scene》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