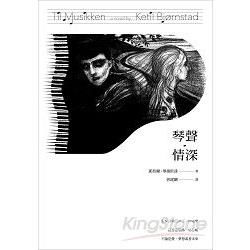音樂於我已成了一份迷戀,這份迷戀將一切吞噬,不論是愛、夢想或者未來
與音樂緊緊相扣 刻畫出人生的悲喜、慾望和恐懼
極具音樂天賦的阿克索受母親啟蒙而開始習琴。十六歲的夏日,全家人到河邊戲水野餐時碰上意外,他阻止父親被捲入漩渦中,卻使母親遭激流沖走失去生命。這讓他深陷孤立與絕望,音樂成了他唯一的救贖。
他無心向學,將所有時間用於練琴,全心投入鋼琴大賽。同儕間競爭激烈,卻又只有彼此才能理解對方,因而只能互相激勵。美少女安雅的天分和氣質深深吸引阿克索,使他跌入這埸終將失控的戀情之中。
安雅的完美演出,讓同場較勁的阿克索惶惶不安,當他終於精湛地彈至尾聲,原本悄然無聲的觀眾席上卻爆出一陣騷動,讓他的琴聲彷彿碎裂的水晶,冷冽銳利地刺痛他的雙手,與他的未來……而安雅是如霧般的迷夢,伸手彷若可及,抓住的卻只是冰冷的空氣。
即使如此,他還是決定,賭上一生,踏著荊棘前行……
得獎記錄
★本書榮獲二○○八年法國「讀者大獎」(The 2008 French Prix des Lecteurs)
本書特色
★挪威當代小說家、詩人以及鋼琴大師凱特爾.畢揚斯達全球第一本中文版長篇小說。
★本書生動刻畫了一群青少年之間強烈的情感世界,沒有《交響情人夢》的浪漫,而學琴之路卻同樣艱苦,他們大膽向彼此伸出援手,亦觸及了他們在攀向藝術頂峰時,不時在內心自問的人生難題:想主宰音樂這門高深的藝術,卻又不想付出個人苦痛為代價,這豈能兩全?
★凱特爾.畢揚斯達特別為此書創作《赤楊叢之歌》雙CD,成為閱讀本書最佳配樂選擇。
名人推薦
★推薦人李茶(樂評人) 、陳志林(極光音樂董事長)、焦元溥(樂評人)、蘇重(樂評人)推薦
冷靜細心的筆觸,搭配敏銳且富詩意的想像與鋪陳,畢揚斯達寫祈願也寫現實,有情卻也無情,說了藝術與夢想之難得,青春與世途之滄桑。但正因如此,我們需要文學,需要音樂,需要將振落的羽毛記憶成悠揚的歌曲—即使不能高飛,也要永遠保持望向天空的勇氣。——樂評人 焦元溥
那些愛與死亡、慾望與失落、在黑白鍵間飛梭流逝的春分與驚蟄,《琴聲.情深》不僅是一本描繪年輕音樂家的成長小說,更像是凱特爾.畢揚斯達向所有天生敏銳的藝術家,在創作出偉大作品(無論他是否一生寂寂無聞)之前所受的磨難致敬。——樂評人 李茶
挪威鋼琴家/詩人/小說家畢揚斯達的音樂,經常是深邃而細緻的,像是在寧靜的水面之下,隱藏著難以預測的礁石與暗流,波紋水流,撞擊聚散之間,彷彿音樂家用某種神祕的方式,觀照著自身意識深處的震盪。多年來,一直想要拜讀他的文學創作,希望多打開幾扇窗口,能夠對理解欣賞他的音樂作品,增添不同視角。他的小說,以少年鋼琴家 溫丁作為主角的《琴聲.情深》中文譯本問世,令身為樂迷的我雀躍不已。——樂評人 蘇重
媒體讚譽:
本書凸顯出青年同儕間複雜糾葛的競合。畢揚斯達文思敏銳,巧妙地寫出了成長過程中情感上的扭曲,文字間不時流露柔韌的戲劇張力和心理洞悉。──Henry Hitchings(英國作家、書評家),英國《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
引人入勝的故事,有愛情,有死亡,有慾望,也有失落。這是一部與古典音樂緊緊相扣的小說,作者自己就是一位當代鋼琴大師。文字跌盪起伏,時而停滯,時而流洩,一如故事中所呈現的古典曲目。──Tone Sutterud(挪威文化評論家、記者),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畢揚斯達乃文化界之奇葩。──英國《衛報》(Guardian)
寫的極美,且令人震懾。──丹麥《日德蘭郵報》(Jyllands-Posten)
一部雄偉、壯麗的小說。──法國《觀點週刋》(Le Point)
一部全面、情感深沉的小說。──德國,公視二台(ZDF)
微妙、扣人心弦的故事。──德國,《時代週刋》(Die Zeit)
本書是畢揚斯達的顛峰之作,讀者一閱讀就沉醉其中,非得要讀完才肯放下。──Ole Jacob Hoel(挪威書評家),挪威媒體Adresseavisen
極少挪威作家能像畢揚斯達一樣,以如此強烈的情感刻畫出人生的悲喜、慾望和恐懼。──Steinar Sivertsen(挪威批評家、記者),挪威《斯塔萬格晚報》(Stavanger Aftenbl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