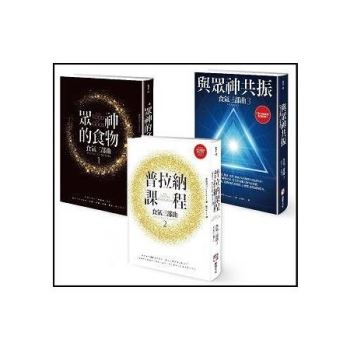問題的根源在於心。我們的心,就是答案!
33則心靈故事,點出了每個人都擁有「根本心」,這顆心的力量何其廣大,只要將一切難題託付給它,解脫的窗口自然在眼前開啟,而窗外將盡是一片金色陽光。
◎ 一個出家人只因偷了三顆穀子而需投身為牛,五百個強盜謹遵佛陀的言教,竟成為五百位菩薩?
◎ 為了讓病重的師父痊癒而必須殺生,該承受什麼樣的業力?
◎ 備受主人細心呵護的樹,因懂得感恩而救了全家人的性命?
◎ 小小一顆餃子居然蘊涵了「無為而為」的道理?
◎ 狐狸究竟說了什麼話,竟讓蜈蚣忘了該怎麼走路?
大行大禪師被尊稱為韓國最具德行的禪宗大師,童年的磨難,使她不斷向內探尋真實的本性,因此她所傳授的教誨,都是基於親身體驗,更能貼近人心,毫無隔閡。
大行大禪師深感眾生並沒有察覺到自己的天賦,以致一切行為和思想無法和真諦相契合,一直為苦惱所縛,無法自拔。她藉由一則則平凡而簡短的寓言故事,將故事中的主角化身為我們所熟知的角色,諸如動物、修行人、夫妻、父母和子女等等,巧妙地釋放出深刻的佛法底蘊和智慧,時而幽默、時而嚴肅、時而不著痕跡,輕鬆且適時的解答了你我都可能面臨的難題,以及眾生本為一體的道理。
書中附上十數幅筆觸優美、具有濃濃禪味的插圖,以及啟發人心的智慧之語,每一句都讓我們感受到生命流動之美,以及無限寬廣的力量。
作者簡介:
大行大禪師 Daehaeng Kun Sunim
1927年出生於韓國首爾,年輕時便有所證悟,並花了數十年光陰實踐畢生所學。
多年來,大行大禪師處處感懷眾生所受之苦,意識到這些苦都源自眾生的無明。有鑑於此,大行大禪師開始化導眾生,放下所有束縛他們發揮天賦的障礙,以明覺之心勇敢邁進。
大行禪師強調所有眾生都具備光明自性,都秉持佛陀的智慧與大能,因此,原本只教導比丘和數位比丘尼的大行大禪師,立志以這個「治心之道」,讓所有一切眾生,不論男女老少、貧富貴賤、士農工商,都能夠透過修行而證悟了道。為行此大願,大行大禪師於1972年成立了「一心禪院」,作為四眾弟子修行之所,教導他們如何更有尊嚴、更勇敢、更超脫地面對人生。即便是到了今天,大行大禪師仍然謹遵初衷,以此為化導眾生之不二法門。
譯者簡介:
劉宜霖
新加坡人,在新加坡接受基本教育。土木工程系畢業後,在建築業待了近八年。
2002年因緣際會下,到泰國合艾大智大學附屬語言中心教英文。2006年秋季,就讀於台灣國立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兼修一年梵文。目前正在寫論文:《釋上成下觀法師《六祖壇經》之英譯策略》。
皈依二十年,2002年開始接觸內觀修行法門。
章節試閱
擁有二對父母的男人
大約一千多年前,韓國心羅王朝住著一對夫婦,他們是一名貴族的僕人,因此所生的孩子自然也成為這名貴族的僕役。一天,忽然下起傾盆大雨,僕人的父親趕緊到田裡去查看,確保稻田沒有被大雨沖走。但當他去勘查堤防時,卻不幸被湍急的大水襲捲而溺斃。
想到僕人服侍自己這麼多年,這名貴族便把其中一畝大約兩千平方公尺的田地送給了僕人的孩子。有了這畝田,這個孩子就不需要再為他人勞役了。然而出乎貴族的意料,這個孩子依舊不辭辛勞地為他服務,一直把他的母親照料得妥妥貼貼。
幾個月後,一位修行人為寺廟化緣路過該地,這孩子見到修行人後,竟然把整畝田地都供養給他。孩子的母親想說服他:「你的前途該怎麼辦呢?這畝田地是你能夠過著安定生活的唯一機會啊!」
孩子回答說:「我是因為父親的犧牲才得到這畝田的,因此我認為這畝田的運用,必須對父親有利益才行。」他的母親雖然有點不安,但很有智慧的她知道,基於兒子的慈悲和德行,老天一定會眷顧他,因此也就放心了。然而,奇怪的是,三天後,這孩子就突然往生了。
至於那位接受供養的修行人,也不是等閒的出家人,而是一位已經證悟色界及無色界禪的聖者。這位聖者因為這個孩子的善行而深受感動,希望他能有一個光明的未來。然而,受限於當時的世俗體制,僕人的孩子,一輩子就只能夠當下人。這位出家人雖然是聖者,卻也無計可施。然而,聖者以出世間能力,讓這個孩子脫離原有的色身,重新投胎。
接著,聖者又出現在一位渴望得到子嗣的顯爵夢中,並告訴這位姓金的顯爵說:「毛良村一個名為大成的孩子,今天往生了,他很快便會投生成為你的孩子。好好把他扶養長大,因為這孩子將會成為一位德高望重的領導者。」
這位顯爵一連三夜都做了同一個夢。由於夢境怪異,讓他相當好奇,因此便派遣一名下屬去調查聖者在夢中對他所提之人。這名下屬的回報令他震撼不已 果然,在偏僻的毛良村,最近真的有一位名叫大成的孩子死去了。
數個月後,當這名顯要的夫人懷了身孕時,他一點兒也不覺得驚訝。孩子生下來後,他們將他取名為「金大成」,用心栽培他,後來,金大成成為心羅王朝的宰相,為韓國建造了二個最著名的寺廟「佛國寺」和「石窟庵」。在他睿智的統領之下,心羅王朝歷經了一段相當長的太平盛世。
金大成對自己的二對父母滿懷感恩之情,並在後來迎請了過去生的父母,以及這一世的父母一起共享天年;為這一世的父母建造了佛國寺,又為過去生的父母建造了「石窟庵」。
世事變幻無常,即便片刻時間,所有人事物也將隨之改變。只要你跨前一步,前一剎那便隨之而逝。而那一剎那,即名為「過去」。只要能理解在我們向前邁進的當下,一切也隨之生起變化,那麼你就會理解放下與不執著的重要。而無常,即是佛法之根本,是真諦,亦名為道。
你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本來就無不同之處;你的兄弟姊妹,亦如我的兄弟姊妹。無量劫來,我們以不同的角色輪迴相聚,這一生的父母也不是你唯一的父母,因此任何眾生都有可能是你前生的父母,甚至是兄弟姐妹。
蚯蚓湯
一個小寺廟的老師父病得很嚴重,身體很虛弱,不久後,甚至連坐起來都覺得困難。寺廟雖也有幾位法師在那裡修行念書,但畢竟坐落在貧困的深山之中,老師父的徒弟們很擔憂,因為他們能夠提供給師父的藥物實在有限。其中一位較資深的弟子只好把問題仰賴佛陀的慈悲加持,並繼續觀察。後來,他忽然有了解答:他記得多年前曾聽聞人在生重病時,若能夠用一點用蚯蚓熬的肉湯,對恢復體力相當有幫助。對於這個說法,他是從一位住在深山多年的老人口中聽來的。這位老人還熟諳許多怪方法,但都相當的神效。
大徒弟心裡這麼想:「如果蚯蚓湯能夠讓師父復原,我就去做,即便因此得下地獄,也在所不辭。」他大約收集了上百條蚯蚓,洗淨後煮成一大鍋,熬煮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他將蚯蚓湯過濾,然後把湯水倒在一個大罐子裡。當他在熬湯時,心裡還是憶念著那些蚯蚓:「這樣對待你們,實在情非得已,但你們可以讓我的師父復原。」為了報答蚯蚓的恩情,這位弟子便以本心做如是想:「你心即是我心,本為一體。我相信你們必將輪迴到較高的六道之中。我衷心的感恩你們。」
然而,當其他的徒弟知道這件事後,都難以置信:「什麼!難道你忘了持守殺戒嗎?難道你不知道你將會遭受的果報嗎?」然而這位徒弟依然不為所動:「師兄弟們,如果有任何的惡報,我願獨自承擔。無論如何,這鍋蚯蚓湯將同時解救我們的師父和這些蚯蚓;當牠們進入師父的肉身,必將與師父融為一體,仰仗師父的智慧而得以提升。你們想想看,這些蚯蚓要歷經多少千年的歲月才有如此的機緣,遇到這樣的聖者,經歷如此高深莫測的思維和境界啊!因此,在讓師父康復的同時,也解救了這些蚯蚓的慧命,可謂二者同時得救!」
當老師父喝完所有的湯水之後,身體終於康復,病情也穩定了。他把徒弟叫到跟前,問道:「那鍋湯水實在營養豐富,讓我恢復甚多。但是說來奇怪,這湯水到底使用什麼熬出來的?」
徒弟回說:「喔,我在森林裡找到了一棵古樹,摘了許多嫩葉回來,熬煮了許久才熬出來的。」
老師父瞇著眼睛看了看徒弟,咯咯笑了出來,然後又對他微笑。因為這個年輕的法師,那些蚯蚓才得以輪迴到更高的六道之中。
你認為戒律該如何持守呢?你是否在持戒的同時,只著重於表相功夫,但心裡卻無限掙扎拉扯呢?從不可見的實相中徹底了解物質層面的表相,你就能夠了悟持戒的真正意義,做到不持而持了。換句話說,心法和色法本來就不可區分;把二者融為一體,才是正確的持戒。
我們被教導不殺生,只因每一生命體都和你我一樣珍貴,他們所經歷的痛苦和你我所經歷的痛苦是一樣的。若你能夠了解箇中道理,就不會鄙視任何一種眾生而粗暴地對待他們。如果你是因為父母之病或子女之病而買了一隻雞,就等於你間接殺了那隻雞。然而,衷心地把你的信念建立在你的基礎主人空之上,意即你和雞本來就是一體。要知道:「你心我心本來無二」,然後把這個意念建構在你的基礎上。因為你把雞的精神注入到自己的心中,你毀壞的只是雞的色身生命,而不是牠的慧命。實際上,你是在幫牠消除無明。但儘管如此,你千萬不要在沒有需求的情況下把牠們宰殺來吃。並不是任何一種殺生都是被允許的;更甚者的是殘暴的蓄意謀殺。
擁有二對父母的男人 大約一千多年前,韓國心羅王朝住著一對夫婦,他們是一名貴族的僕人,因此所生的孩子自然也成為這名貴族的僕役。一天,忽然下起傾盆大雨,僕人的父親趕緊到田裡去查看,確保稻田沒有被大雨沖走。但當他去勘查堤防時,卻不幸被湍急的大水襲捲而溺斃。 想到僕人服侍自己這麼多年,這名貴族便把其中一畝大約兩千平方公尺的田地送給了僕人的孩子。有了這畝田,這個孩子就不需要再為他人勞役了。然而出乎貴族的意料,這個孩子依舊不辭辛勞地為他服務,一直把他的母親照料得妥妥貼貼。 幾個月後,一位修行人為寺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