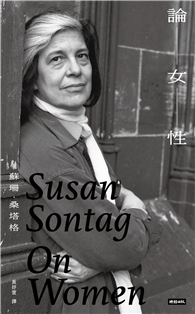欣聞《雪域求法記》即將在台灣發行出版,真真感到高興。感謝台灣橡樹林出版社及北京三聯書店的鼎力支持和辛勤工作,並在此致廣大台灣讀者吉祥如意,福慧增長。
今天,藏傳佛教正在廣向世界傳播,各地均有藏密各派大德宏法,世界發生了巨變,佛教亦在向前發展。七十年前,我曾披荊跋涉的荒漠古道,或許今日已不再存,但那些往事足跡卻依然伴隨著記憶,如此的鮮活清晰。
藏傳佛教具有悠久的歷史和舉世聞名的經典而著稱於世。她導源於第七世紀,那是中國的盛唐時代,並直接師承了印度佛教,故在經論方面、修行方面、制度方面均具其獨特的風格,對於整個佛教的宏揚發展,起著深遠的影響。自佛教開始傳入西藏,密教學說已發展到與中觀、唯識不可分離的階段,在西藏丹珠爾大藏經中,存有不少的密教論典,是龍樹、提婆菩薩等所著。而且印度晚期佛教聖人如月稱的中觀論、獅子賢解脫軍的現觀論、法稱的量釋論、金洲的唯識論、德光的戒律論,均在印度佛教衰亡之前傳入了西藏。加之西藏代有聖人,如寧瑪派創始人蓮花生大士、噶當派創始人阿底峽尊者、格魯巴創始人宗喀巴大師、薩迦派創始人貢曲甲布、噶舉派創始人瑪巴及米拉熱巴、菊南派創始人米交多杰及達惹那他等,這些先聖們無不解行並勝,學貫梵藏,闡幽探微,發前人之所未發,且能加以融會貫通,是那爛陀寺而後最能通達三藏者。
筆者自幼醉心佛教,少受庭訓,尤慕玄奘法顯之高行,乃弱冠隻身赴藏,訪求密法,親承大德教授。旅藏十餘年,有入寶山之感,不僅學到了經論,獲得了格西學位,還先後從一百多位德高望重的大德接受了六百多次密教各派的傳法灌頂,朝拜了薩迦寺和咱曰山,殊勝因緣不可勝述。
本期長居西藏繼續深學和工作,不意世事無常、因緣變化而離藏,後移美國深居。如今我已93歲,佛法加被,依然健朗,每日頌經修法,不離禪室,有時也講經授徒,圓滿六度四攝,上證菩提。
在此《雪域求法記》在台灣出版發行之際,衷心祈望藏傳佛教這一無上珍寶,能弘揚四海,饒益一切有情!
願世界和平,人民永久安樂!
邢肅芝
2009年5月於洛杉磯
本書緣起
一九九八年八月的一天,我們來到美國洛杉磯郊外一所宅子,拜訪隱居在此的邢肅芝老先生。在此之前,我們早就聽說這位老先生精通漢藏佛教,是一位修道有成的高人,一生充滿了神奇不凡的經歷。這便是此書的緣起。
邢肅芝老先生雖年過八旬,但身體康健,思維敏捷,記憶力十分驚人。我們初次的交談從邢老在西藏的經歷開始。講到半個多世紀前的往事,老人家取出了一本厚厚的相簿,他告訴我們,這裡面的照片全部是他自己拍攝的,記錄著自一九三七年從他進入西藏開始,入藏沿途的所見所聞,以及在西藏十三年的求法和探險中所遭遇的各種人物。相簿的封面已然褪色,一翻開,一幀幀微微發黃的黑白照片按照年代的順序排列著。從這些照片,邢老向我們展開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道出一段段傳奇的經歷。
以後的三年,在整理這部口述自傳的過程中,我們始終為能有這樣的一次難逢的機緣而慶幸。在近現代史上,邢肅芝老先生雖不是一位著名的大人物,但他的一生始終處在歷史的風口浪尖上,是一位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大動盪年代中,親身參與了漢藏兩地錯綜複雜的歷史演變的樞紐人物。他出生於一九一六年,九歲皈依佛門,少年時便接受了嚴格正規的佛學教育,十六歲時進入四川重慶漢藏教理院學習西藏語文,同時成為中國佛學會會長、近代佛教界的泰斗太虛大師的秘書,負責整理太虛大師的演講。一九三七年他隻身赴西藏,訪求藏傳佛教密法,決心將西藏密法取回漢地,做一名現代的唐玄奘。入藏途中,他遍訪康藏地區的高僧大德,在四川甘孜自治州之德格縣學習藏傳密教薩迦派密法三百餘種;隨後,他渡過金沙江進入西藏,沿途得到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四川軍閥劉文輝、昌都藏軍司令索康劄薩和軍糧官阿沛.阿旺晉美的贊助和支持。抵達拉薩後,進入哲蚌寺學習藏傳佛教五部大論,曾拜多位著名活佛為師,包括達賴喇嘛的教經師領蒼活佛。經過七年的刻苦學習及辯經,於一九四五年通過在西藏攝政王面前舉行的辯經考試,成為第一個獲得藏傳佛教最高學位──拉然巴格西的漢人,歷史上獲得這一學位的漢人僅有兩位。其間他四處參訪高僧大德,先後從師於一百多位藏傳佛教各派的活佛,接受密法灌頂六百多個。一九四四年藏曆鐵猴年的二月,他前往藏南咱日山藏傳佛教祖師蓮花生大師的道場朝拜考察,其經歷驚心動魄,成為進入此山而得以生還的唯一漢人。一九四五年,他攜帶著大量藏傳佛教密典滿載而歸,回到了重慶;此外,他隨身還攜帶著一封促成他一生重大轉折的文件──西藏攝政王達龍扎活佛委託他帶給蔣介石的一封親筆信。
歷史的現象與演變離不開因緣二字,世上的萬事萬物無一不是因緣和合而生,這是佛教世界觀的基本思想。細觀大千世界,芸芸眾生,每個人在偶然的衝動中,或在他人的影響下,或經深思熟慮後所做的每一項決定,往往形成事物發展的因,而外在的影響,各種客觀條件的聚合則是促成事物的緣,因緣的結合與離散形成萬事萬法的始與終,主導著每個人一生的命運,而這些無數個人因緣與命運的匯合,又形成了演變歷史的大事因緣,主導著社會變革的軌跡。對於邢老來說,冥冥之中因緣奇妙的結合,促成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轉折,使他從一個近代漢藏關係發展歷史的單純見證人變成為主動的參與者。在這次命運的轉折中,他本人對發展漢藏民族關係的強烈使命感成為轉折的因;而攝政王的親筆信、與蔣介石的會面、太虛大師的鼓勵和影響、國民黨政府處理西藏問題人才的短缺等種種因素的聚集則是緣;因緣和合,促成了他的入世參政,成為國民政府的官員,落實「教育治藏」政策的關鍵人物。一九四五年他再次返回西藏,此時他具有其他人無法具備的雙重身份:既是一位漢人喇嘛,西藏三大寺的格西;又是一位奉蔣介石之命入藏發展教育的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專門委員,教育部委任的國立拉薩小學校長。拉然巴格西的身份使他得到西藏噶廈政府、僧侶們和上層貴族的尊重和信任,能夠與西藏的政府官員和把握權力與資源的貴族階層建立良好的私人關係,完成連中央政府都難以做到的事情。而他的官員身份,則使他能夠直達中央政府,獲得在西藏發展教育事業所需的各種資源,成功地完成他的使命。
一九四九年七月,西藏噶廈政府乘國民黨軍隊在國共戰場上節節敗退之際,發動了震驚中外的「驅漢事件」。在這次事件中,邢老再次以他的特殊身份,參與中央政府駐藏辦事處與西藏地方政府的談判,努力協調漢藏之間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最後成功地組織了中央政府全體駐藏人員平安地撤離西藏。一九五○年他移居香港,開始講經說法,並將藏傳佛教的重要經典、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略論》翻譯成漢文。一九五九年,他應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邀請赴美國講授藏學,並定居美國至今。幾十年來,不論是化外為僧,還是入世參政,他始終保持著一個佛教徒的信仰,從未放棄佛法的修行。據說他的禪定功夫高深,在密法的修持上獲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對往事驚人的準確記憶,對各種人物和事件的敏銳觀察,以及對歷史變革內在軌跡的分析與體悟,給我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在多次的訪談中,邢老向我們展現出那種只有修行有成的人才能具有的定力和一種洞徹人心的能力,常常在我們還沒有開口提問之前,他似乎就已經知道了我們的問題。這種神奇的力量令人折服,卻又難以言喻。
邢老一生橫跨漢藏兩地,涵蓋僧俗二界,獨特的多重身份,使他的經歷具有極其豐富的歷史內涵。在地域空間上,他曾是漢地的法師和西藏的喇嘛,在漢藏兩地的寺廟中各自生活多年,對於兩地佛學思想與制度上的演變、交流與互動,瞭解得細緻深入,而且善於研究比較,有自己的見解與心得。對於西藏三大寺的體制、喇嘛的學經過程、密法的傳承和傳授、寺廟的生活等這些令現代人最感興趣而又知之甚少的部分,他的描述十分細緻動人,極富歷史動感。此外,對於舊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官吏制度,西藏貴族階層的生活方式和彼此間的明爭暗鬥,漢藏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外國勢力對西藏的滲透,國民黨政府治藏政策的得失等各個層面,他都提供了大量真實的細節性記述,足以彌補正史的不足。
邢老又是一位具有冒險精神的探險家,一生經歷險情無數。難得可貴的是,他在每一次的考察探險中,對所見所聞都做了詳細的筆記,拍攝了大量的照片,並盡可能地收集各種相關的歷史資料。邢老在他的家中曾向我們展示了當年入藏途中的遊記手稿,和在四川、西藏、雲南各處考察探險時的原始日記,以及他所收集的西藏早年發行的銀票和郵票、西藏和印度邊境的通行證、地方政府簽發的馬牌等等。他所拍攝的近千張照片,內容包羅萬象,其中有世上僅存的一張年幼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入主布達拉宮前在拉薩郊外休息的照片,漢藏雙方的軍隊為解決大金寺武裝衝突事件的談判會議現場,西藏寺廟中高僧活佛們日常起居的情形,大願節時的跳神儀式,藏南咱日山內「野人」部落生活實錄,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官員們的留影,拉薩小學的學生生活素描,甚至連三大寺中「武僧」的訓練場面都被拍攝了下來。這些照片儘管已經年久變色,畫面卻仍顯清晰生動,尤其是與口述記錄、遊記手稿相互參照時,給人以強烈而又逼真的觸摸鮮活歷史的感覺。
從一九九八年開始,我們先後對邢老進行了二十多次的採訪,錄成四十多卷錄音帶。將錄音初步整理成文字後,再根據整理情況摘錄出一些需要補充的細節問題,進一步採訪,經過多次反覆的挖掘和追憶,做最大限度的補充。聲音記錄轉換成文本後,我們再參照相關的歷史文獻,對口述文字與原有的遊記、日記及大量的珍貴照片進行合理的穿插編排,使得口述記錄能夠與歷史文獻達到相得益彰的互證效果。
邢老的經歷所涵蓋的時空廣闊,人物眾多,尤其是涉及佛學及藏傳密教的部分,需要參證大量的文獻,才能達到真實的復原當時佛教活動的歷史面貌的目的。往往為了一項細節的查證,要經過洛杉磯—北京之間橫跨太平洋的數次聯絡,三年內點點滴滴的工作持續不斷,直至各項因緣具足,方才功德圓滿,使這部口述自傳得以問世。我們希望這本書能為近代政治史、社會史、宗教史、民俗學、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提供一份真實可靠的歷史紀錄。這也是邢肅芝老先生的心願。
張健飛 楊念群
二○○○年四月初稿於北京
二○○○年六月定稿於洛杉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