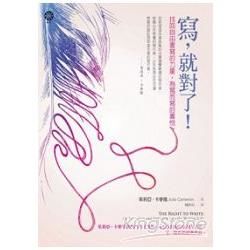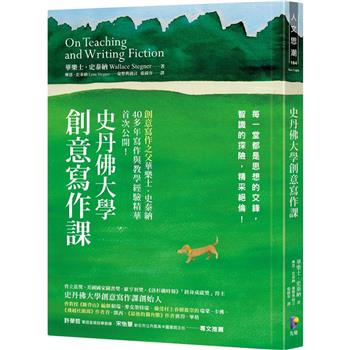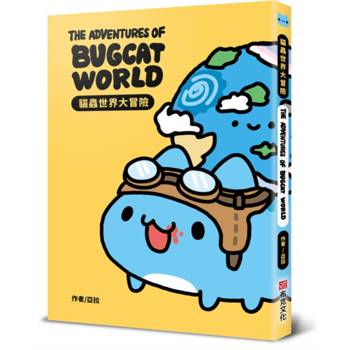茱莉亞‧卡麥隆繼暢銷書《創作,是心靈療癒的旅程》之後,又一精彩的經典作品。「我希望這本書能幫助治療遍體鱗傷的寫作者、鼓舞心存畏懼的寫作者,以及慫恿站在河邊想要把腳趾頭伸進水裡的寫作者。」──茱莉亞‧卡麥隆
親愛的茱莉亞:是你鼓勵我提筆寫作,雖然我覺得妳瘋了,但我還是寫了。隨信附上我剛出版的童書。
親愛的茱莉亞:教書教了三十年之後,我終於找到自己寫作的初衷了。我熱愛寫作!但願我沒讓自己等那麼久。請告訴其他學生要相信妳,並從此時此刻開始寫作。
曾經,書寫是每個人的本能,就像呼吸一般。隨著時間推移,我們受困在世人對作家狹隘的定義中,陷入對寫作的負面迷思裡,認為當作家注定是孤獨的、一輩子窮困潦倒、我們寫的文字沒有人要看、出版的書沒有人會買。於是我們在寫作之路上走得跌跌撞撞、茫然迷惑、信心盡失,最後遍體鱗傷,漸漸忘了寫作最原始的本質──寫作不是為了給誰看;不是為了得到掌聲;不是為了名利雙收;不是為了得到「作家」的頭銜。我們寫作,純粹是享受為寫而寫的喜悅,讓腦中的想法躍然紙上,透過文字跟自己對話。
本書作者茱莉亞‧卡麥隆從自己的寫作經驗出發,帶領讀者省思寫作的真諦是什麼?我們不需等到有時間、有靈感、有舒適的房間、合適的題材,才能好好坐下來寫作,這只是逃避寫作的藉口。對於寫作,你大可如天真的孩子般,腦海裡有任何奇思妙想,提起筆就寫,想到什麼寫什麼。你的文字不需經過旁人的指點過目,你就是文字的主人,你的靈感獨一無二。一段時間後你會有驚人的發現:那些你所寫下的隻字片語,竟是如此動人!那一個又一個你所創造的文字異想世界,精彩得讓你流連忘返!恭喜你,你重新找回文字的療癒力量。
寫作就是這麼一回事,抛開「我想寫,但是……」的疑慮和不安,旁人多事的提醒糾正,寫得快樂比寫得好更重要。寫,就對了!
作者簡介:
茱莉亞‧卡麥隆(Julia Cameron)
茱莉亞‧卡麥隆兼具小說家、劇作家、作曲家、詩人等多重身分,在電影及電視圈頗負盛名。至今已出版數十本著作,寫作題材廣泛,包括詩集、小說和非小說類。
《創意,是心靈療癒的旅程》(2010年橡樹林出版)是卡麥隆最受歡迎、最經典,以討論創意為主題的暢銷書。但在此之前,她曾投注十年時間不斷寫作,卻在創作之路上挫折不斷,最後只得仰賴酒精來支撐自己的意志力。儘管如此,卡麥隆仍不曾放棄,她憑著對創作的熱愛,重新回歸創作最本然的初衷,不斷向內省視自己的心,終於找到將靈感化為真實作品的方法,並獲得百萬讀者的正面肯定。
卡麥隆開設了名為「藝術家之路」課程,成功帶領許多在創作之路上遭遇瓶頸的作家、演員、舞者、導演、作曲家等等,和內在的自我對話,重新開啟了創意的泉源。甚至許多嚮往創作卻不知該如何開始的人,在運用了她的方法後,也大膽的在創作之路上盡情揮灑自己的想法。她的暢銷代表作有《創作,是心靈療癒的旅程》、《潛能尋寶遊戲》及《寫,就對了!》。
譯者簡介:
賴許刈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創意寫作碩士(M. Phil in Creative Writing)。編書也譯書的文字工作者,編輯作品多為歐美小說,翻譯作品則涵蓋各種類型。個人信箱:aneditor@pixnet.net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譯後記:一寫,就渾然忘我
賴許刈
曾經,寫作是我的核心,當作家是我的夢想。這世上如有一件能讓我廢寢忘食之事,那便是寫作。然而,我卻走上了一段一直與文字有關卻又離文字越來越遠的路途──學生時期得文學獎、零星作品刊在報紙副刊、拿了個創意寫作的學位、進入出版業當編輯,也翻譯了一些書籍,但始終沒有成為作家,對文字工作的怨念還越來越深。
還記得,得文學獎時,一位學弟看到消息,對我說:「妳那麼無聊喔?」那是熱愛文字的我第一次意識到,在旁人眼裡,寫作是無聊的事,寫作的人是無聊的人;寫作還寫到得獎,那真是無聊界的冠軍。
文學獎軼事還有一樁。當時的男友與我相隔兩地,投稿參加文學獎這件事,我是直到得獎之後才告訴他。那位有眼無珠的男友一聽便鐵口直斷說:「沒得獎。」我則一派淡定地告知他:「我得的是首獎。」他的反應是一聲摻雜著驚訝與不屑的:「蛤?!」
念創作所時,則曾有位非常失禮的同學對我說:「除非妳很有名,不然妳寫的這些東西,不會有人要看的。」
到了進出版社擔任編輯之後,我開始跳脫出單純文字的世界,打開了看見市場的眼界。基於工作所需,也自然而然更加多面向地看見一本書除了文字以外的全貌。但久而久之,在種種無法對外人道的職場辛酸磨蝕之下,我越來越把那些看也看不完的文字視為負荷沉重的工作量。漸漸地,情況演變成上班時咬牙切齒地忍耐,下班後則不想再閱讀任何文字。
這時候,我又碰到一個失禮的外行人,他問我:「你們這些當編輯的人為什麼要當編輯?是因為當不成作家嗎?你們的總編很有名嗎?在社會上有地位嗎?」還記得,我曾經在雜誌上讀到一篇女星賴雅妍的專訪,文中說她在女二號的迷宮裡卡關數年沒能當上女主角。讀著那篇專訪,我心想:人家好歹是個女二號,編輯在文字產業中扮演的角色又算什麼呢?
如此這般,從學校到職場一路走來,文字之路上其實充滿龐雜的負面訊息、對自己的懷疑與否定、必須壓抑下來的抗拒感,乃至於不知能如何取得平靜、找回熱忱的失衡心理。這種狀態年復一年地因循苟且下去──直至我翻譯到這本書。
翻譯的過程中,這本書的理念不斷衝擊著我。在出版社工作,我們的思維是市場導向的。我們揣摩著讀者要什麼、市場缺什麼、外界的潮流是什麼。此書的思維卻恰恰相反,在作者茱莉亞•卡麥隆眼裡,從市場出發不但是本末倒置的,而且可能造成你永遠寫不出一件作品的第一個字。卡麥隆主張從自己出發,她在書中逐步破除讓人遲遲不下筆的種種迷思,到了全書的最後一篇,她義憤填膺地提出「寫作的權利」,主張推翻「作家」這個字眼,推翻「專業作家v.s.業餘愛好者」的等級之分,甚或階級觀念。換言之,她要講的其實是,就算「成為作家」、「寫出暢銷書」、「寫出經典」這些前提都不成立,你還是大可以熱愛文字。
除了迷思的破除與觀念的建立,卡麥隆也提出了一套訓練寫作的具體方法,其中之一是她在在推崇、極力推廣的「晨間隨筆」──每天早晨寫三頁隨筆,看到什麼寫什麼,想到什麼寫什麼,沒有所謂的「寫不好」,也絲毫不要去顧慮這些隨筆最後能不能發展成像樣的作品。我體認到,這個被卡麥隆稱之為「晨間隨筆」的寫作訓練,是要訓練你義無反顧地拿起筆來寫下去。
我還體認到,這個「寫作的權利」,其實可以擴大為「實現夢想的權利」──是不是必須把接下來的每一步都構思好,是不是必須要有「功成名就」這個前提,才能開始實現夢想?是不是一定要成為一個什麼「家」,才能去做你熱愛的事情?
譯完這本書,我看待寫作或文字的心態,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曾經,寫作是我的核心。之所以活得再不快樂都沒有瘋也沒有去死,正因我有這個核心。是後來,外界的雜音使我自己不斷地否定掉這個核心。但如果我是那麼熱愛寫作,如果我一寫就渾然忘我,為什麼要管他人怎麼看?為什麼要管能不能寫出個所以然來?那每一個「一寫就渾然忘我」的當下,不就是熱情之所在?不就是活在夢想中、活出夢想來嗎?
譯完這本書,我看待懷抱「出書夢」而耕耘不輟的人,也有了不一樣的眼光。以往,我從市場的角度無情且不耐地審視他們的作品「賣點」何在。現在,我看見他們的認真與執著,我看見他們朝夢想飛蛾撲火的衝勁,我對他們「不成功也絕對無法放棄」的精神肅然起敬。
無論終點是什麼、下一站是哪裡,在這條漫長、曲折而迷離的文字之路上,就我的心態而言,此書是一個轉捩點。它整治了我的病根,讓我意識到種種迫使我離自己越來越遠的因素,也讓我在面對既有的文字工作時有了煥然一新的心情,最重要的是──它賦予我義無反顧投入熱愛之事的權利。
名人推薦:譯後記:一寫,就渾然忘我
賴許刈
曾經,寫作是我的核心,當作家是我的夢想。這世上如有一件能讓我廢寢忘食之事,那便是寫作。然而,我卻走上了一段一直與文字有關卻又離文字越來越遠的路途──學生時期得文學獎、零星作品刊在報紙副刊、拿了個創意寫作的學位、進入出版業當編輯,也翻譯了一些書籍,但始終沒有成為作家,對文字工作的怨念還越來越深。
還記得,得文學獎時,一位學弟看到消息,對我說:「妳那麼無聊喔?」那是熱愛文字的我第一次意識到,在旁人眼裡,寫作是無聊的事,寫作的人是無聊的人;寫作還...
章節試閱
1.開始
我坐在一張松木桌前,面向東邊的基督聖血山。視線所及,馬槽空空如也,需要再加水進去;一道白色籬笆當中開了一扇藍色小門,小門的藍是知更鳥蛋那種藍;陶土材質的鳥兒戲水盆上有幾尊裝飾雕像已經被撞掉了;鮮黃色的澆花水管擱在那裡,我都用它來為馬槽和戲水盆注水;一畦菜圃生長過盛,一只水桶就躺在旁邊;我的小狗麥斯威爾沐浴在早春的陽光下,像個在冷颼颼的天氣裡還樂觀地跑到海灘上做日光浴的人。等暖和一點,等那條黃色的水管解凍,我就會把馬槽注滿。等做完暖身動作,我就會告訴你關於讓自己下筆寫作,我知道些什麼。
第一個訣竅,亦即我現在正在運用的訣竅,就是「從這裡開始」。你在哪裡,就從哪裡開始。有心情寫是一種奢侈,是一個福分,但卻不是必要條件。寫作就像呼吸,是一件有可能學好的事情,但重點是無論如何都要去做。
寫作就像呼吸。我相信這點。我相信我們都是與生俱來的寫作者。我們生來就有語言的天分。生下來不出幾個月,我們就開始會為我們的世界賦予名稱。當我們賦予事物名稱之時,我們會產生某種滿足感,某種掌握了所有權的感覺。文字賦予我們力量。
蹣跚學步、牙牙學語時,首先我們學會用手去抓,接著我們學會用語言去掌握。我們學會的每一個字都是一項所得,都是一小塊讓我們更富有的金子。我們學到一個新字,一遍一遍地說,就像在光線下一遍遍地把玩一塊貴重的金子。孩提時期,我們囤積文字,我們津津有味地品嘗文字。文字賦予我們所有權:我們為世界命名,世界就變成我們的。
孩提時期,我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驚人速度學會新的詞彙。文字讓我們行使操控權:「媽咪,我要去!」或者「媽咪,不要走!」小孩子很明確、很直接,不會拐彎抹角。他們的文字很自我、很有力,飽含個人意志與企圖,充滿熱情與決心。小孩子相信文字的力量。
如果文字給了我們力量,我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失去掌控文字的力量?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些人自認擅長文字,甚至嘗試成為作者,其他人卻只是剛好必須用到文字,不敢妄想躋身作者之列?
據我的推測,對多數人而言,這種區別是從學校開始的。學校是我們被告知「你擅長文字」的地方。在諸如某份北歐地理報告之類的作業上,老師一絲不苟的字跡斜斜地寫在第一頁右上角:「寫得好。」
寫得好──這是什麼意思?在學校,那通常意味著思緒清晰、條理分明,文筆夠通順,舉證歷歷。那可能也意味著我們用上了老師教的東西,例如「主題句」和「起承轉合」。那往往並不意味著文字有弦外之音、創新的用詞與造句、天馬行空浮想聯翩的段落一切一個年輕詩人或小說家可能具有、想要發揮但在學校作業的規範底下派不上用場的天分。
那種文字倘若出現在學校作業上會怎麼樣?往往也會換來一行評語,只不過這回是負面的:「這裡有點離題了。」「請扣緊題旨。」會花時間與心思來欣賞文字不合乎作文範例的老師太罕見了,就彷彿我們在學院的高牆裡處於嚴格控制飲食的狀態:「這裡不要加那麼多胡椒。」
不要加那麼多胡椒。不要這麼煽情。拜託,不要這麼有人性。學術上,我們傾向於寫沒有個性、沒有熱情的刻板文章,語調甚至要有點堂而皇之,就彷彿文字只能來自於最崇高的主題,理性主義的精華液在字裡行間涓滴成流。
在寫作受到禁止的國家或處境中,文字肩負著保有隱私的使命。監獄中,人們把訊息刻在石頭上、泥土裡。荒島上,訊息被塞進瓶子裡送進大海。當溝通被迫成為不可能的任務時,人類渴望溝通的意志就會抬頭,使得人們冒死也要一試。
這是健康的。
當今文化中,某種不那麼健康的現象正在上演。寫作並未受到禁止,只是不被鼓勵。現成的賀卡都幫我們寫好了,我們直接買上面的賀詞最接近我們心意的卡片。學校訓練我們如何表達想要表達的意思,而所謂的如何,包括正確的拼字、主題句、避免離題,邏輯成為最高指導原則,情感被拒於千里之外。在這樣的調教之下,寫作成為一個不人性化的活動。我們總是塗塗抹抹,把可能不切題的細節修改掉。我們被訓練要懷疑自己,要在自我表達這方面對自己嚴格把關。
其結果是我們多數人寫作時都太小心翼翼了。我們努力要做「對」。我們努力要顯得學識淵博。我們很努力。完畢。當我們不那麼努力,當我們容許自己在紙頁上優游,寫作才會是行雲流水。對我而言,寫作就像一套好的睡衣──舒服。但在我們的文化中,寫作往往被設計成一套軍裝。我們要我們的句子排成整齊的隊伍踏著正步前進,就像寄宿學校裡循規蹈矩的學童。
把學校燒掉吧。或許留下書本,但要強迫老師告訴你他所隱瞞的真相:他愛讀愛寫的是什麼?什麼樣的文字帶給他充滿罪惡感的享受?寫作就該是充滿罪惡感的享受。文字就該有魅力,讓你無法抗拒,非得用它來描述有趣得不能不拿來一寫的事物。還有,忘掉那些崇高的主題吧。
我不寫崇高的主題,也從來沒寫過。六年級的時候,我為了吸引彼得.孟迪,寫了我的第一個(極)短篇故事。彼得是聖若瑟小學克勞波許女士班上新來的轉學生。他從密蘇里州搬到北邊來,帶來了南方口音和栗色頭髮。他的髮色有著圖珀洛蜂蜜的色澤,他的長相就像他嗓音裡透著的南方風情一般迷人。我想讓彼得當我的男朋友。我想讓他注意到我。於是乎,我對他發動文字攻勢。
二十年後,在他選擇了佩姬.康若伊而沒選擇我的很久很久之後,彼得告訴我,我的文字抓住了他的心:「妳太厲害,我嚇到了。」
彼得或許因此畏縮了,但在藉由紙筆追求他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更大的追求對象,我發現了以文字去追求一切的快感。
寫作很像是在一個燠熱的夏日行駛在一條鄉間公路上,地平線那頭有個神奇的光點,起伏不定、閃閃爍爍,你朝著它前進,踩油門加速抵達那裡。但當你抵達的時候,「那裡」消失了。你抬起頭來,又看到了它,還是在遠處閃閃發光。你朝它而寫。我猜有些人會說這是一種得不到回報的愛或無法滿足的貪求。我認為那是某種更好的東西。
我認為那是一種期待。我認為那是在低迴玩味。我認為那是透過嗅聞來品嘗一道佳肴的香氣。我不需要吃過剛出爐的麵包就足以愛上它。那股香氣就很美味,就已經像抹上奶油和手工杏仁果醬的厚片吐司般令人心滿意足。
大腦享受寫作,享受賦予事物名稱的活動,享受聯想和識別的過程。選擇文字就像挑蘋果──這一顆看起來很可口。
※ ※ ※
寫作這個活動本身,以寫好來為目標前進,就是一種純粹的快感,一個純粹的過程,像把弓拉滿般令人興奮。瞄準那個能精確表達地平線彼端閃爍著什麼的句子,命中創意的紅心。這些句子值得追求,但這份追求本身,你眼角瞥見的東西,也一樣有它的價值。寫得好,我很高興。但單單是在寫的時候,我就很高興了。完畢。
當我開始寫這篇文章時,天空還是蔚藍無雲。寫完的時候,外面已經風雲變色。肥厚的烏雲吐出狂暴的雨,強勁的風攪亂盎然的春意。我不需要幫馬槽注水,雨水已經把這件工作做好。我的小麥斯威爾跑進家裡縮在我腳邊。這一天,就像這篇文章般,從某處開始,接著發展成完全不同的東西。
迦比爾告訴我們:「你所在之處,就是起點。」這句話絕對適用於寫作。你所在之處就是對的地方,不需要矯正什麼,不需要綁緊靈魂的鞋帶,從一個更高的地方開始。你在哪裡,就從哪裡開始。
把寫作交給它自己,它自有一套路數,就像天氣自有它的一套劇本、形式,以及塑造這一天的力量。正如一場好雨洗淨空氣,一個好的寫作天也能洗淨胸臆。單純地放手一寫真的沒什麼不對。而要這麼做的辦法就是下筆去寫,從你所在之處開始。
下筆輔助工具
開始
這個工具要讓你直接跳進水裡。拿三張信紙規格的白紙,從第一頁的上方開始寫三頁,描述你此刻覺得如何、現在感受到什麼。無論是身體上、情緒上、還是心理上,就從這裡寫起。寫任何一切閃過你腦海的東西。
這是一個形式不拘的練習。你不可能會做錯。盡情地瑣碎、批評、牢騷、害怕。興奮、大膽、擔心、快樂都可以。無論你此刻如何,現在是什麼就寫什麼。寫在當下。感受自己當下的思緒與情緒。手不停地寫,單純地在紙頁上優游。一旦寫完三頁,就停下來。
3.讓自己去聽
關於寫作,我所學到最簡單也最聰明的一件事,就是方向感的重要性。寫作不是要把點子「想出來」,而是要把點子「記下來」。每當我竭力要「想出」一些什麼時,寫作就變成一件我必須掙扎著達成的任務。寫作變得高高在上,甚至是高不可攀,我無法企及。當我設法要想出一些什麼時,我絞盡腦汁。相反地,當我只是集中精神要把一些什麼記下來時,我有一種專注的感覺,但沒有絞盡腦汁的感受。
另一個看待這件事的方式,是把寫作當成一門聽寫的藝術,而不是口授的藝術。當我去傾聽,並單純地只是把我聽到的寫下來,點子就不是我要發明的東西,而是我要謄錄的東西。相反地,當我寫得很掙扎時,那是因為我試圖要在紙頁上說些什麼,而非聽些什麼。
一旦寫作成為一個傾聽的活動,而非發表言論的活動,很大一部分的自我就會從這當中抽離。我不再有意識地想著「我」所寫出來的句子,而是為這些彷彿是自己想要被寫下來的句子感到驚豔不已、興味盎然。寫作不是人為操縱的,而是自然顯現的,對任何讓文字經由他被寫下來的作者而言都是如此。就像任何一位讀者一樣,我們這些當作者的也很期待發現接下來是什麼。
當重點在於我們自己想說的東西時,寫作就會背負著憂慮,我們擔心讀者能不能「看懂」,亦即看不看得出來我們是多麼的才氣縱橫。當寫作是立足於將自然浮現的思緒記下來時,事情就比較不關乎我們的才氣,而比較關乎我們的準確度。我們願意多麼仔細去聆聽?我們願意放掉多少主控權,讓創造力透過我們施展出來,而不是我們為了自己想要達到的目的,試圖去發揮創造力?
我們可以「想出一個情節」或者「寫下一個情節」。我們可以「想點東西來寫」,或者把剛好正在想的東西寫下來。我們可以要求自己寫得好,或者我們可以舒舒服服、自由自在地寫下想要透過我們被寫出來的文字,無論好的、壞的,還是不好不壞的。
我們多數人其實都只想寫得好,這就是為什麼寫作這個活動讓我們絞盡腦汁。我們試圖要讓寫作一口氣兼任兩份工作:和人們溝通,同時讓人們讚賞。在這樣的雙重任務之下,難怪我們的文字負擔沉重、疲於應付。
所有談論寫作的作家當中,我讀過最誠實、最不為自己服務、最不將自己神化的,要屬亨利.米勒(Henry Miller)了。米勒的建言是:
「培養你對人生的興趣,從人事物到文學與音樂,這世界是如此豐富,活靈活現地充滿著可貴的珍寶、美麗的靈魂和有趣的人們。忘掉你自己吧!」
當我們「忘掉自己」,寫作就變得輕而易舉。我們不再像個士兵般僵硬地站在那裡,讓整個自我滲透到每一個「我」字當中。當我們忘掉自己,當我們把「寫得好」放下,安心地只是當一個作者,我們就能開始體驗到文字透過我們被寫下來的經歷。我們從充滿自我意識的作者這個崗位退休,成為別的角色,充當自我表達的媒介。當我們只是媒介,只是那個說故事的人,而不是故事的焦點,我們往往會寫得非常好,但不管寫得好不好,我們肯定寫得更得心應手。
下筆輔助工具
讓自己去聽
這個工具鼓勵你去聽,鼓勵你不要再把寫作看得這麼嚴肅,嚴肅到令人畏懼的地步。假裝你坐在一棵大樹下,背靠著樹幹。在這棵樹的另一邊,有個說故事的人也靠著樹幹坐在那裡。拿一張紙,在上面寫下一到五的編號。告訴那個說故事的人五件你想聽到來龍去脈的事。
4.時間的謊言
「如果我有一年的空檔,我就會寫一部小說。」
或許你會。或許你不會。無論何時,不斷耳提面命地告訴自己「現在就寫」,這往往是突破寫作瓶頸的不二法門,能讓你下筆有如溜上了油的溜滑梯般一路順暢。把寫作當成一件大事便容易讓寫作變成一件難事,隨興而寫則會讓寫作成為一件有可能的事。這個道理套用在「時間」的課題上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關於寫作,最大的迷思之一,就是我們必須要有大把不受干擾的時間才能好好寫。拿我自己來說,我從來不曾享有這樣彷彿一捲絲綢般的時間。我的人生,乃至於我在這一生當中從事的所有工作,多少都有點像在縫一塊拼布棉被,而不是在展開一匹無窮無盡、尊貴高雅的絲綢。
我們必須要有時間──要有更多的時間──才能寫的迷思,是一個阻撓我們善用既有時間的迷思。如果我們永遠都在嚮往「更多的」時間,我們就是在把已經得手的時間打折扣。
就在此刻,我有外地訪客要來訪,有飯要煮,有馬要餵,還有我的狗兒們實在需要散個長步。我或許可以又或許沒辦法去散個長步,但我會去做其他所有的事情──就在我寫完文章之後。多年下來,身為單親媽媽、全職老師及全職小說家,教會我搶時間寫東西,而不是等著有時間的時候到來。「搶時間」就是我現在正在做的。「搶時間」很有效。
對我們多數人而言,「沒時間」這個理由的誘人之處以及隱含的意思是「沒時間傾聽自己的思緒」。換言之,我們想像倘若有了時間,就會讓自己比較膚淺的那一面靜下來,去傾聽內在較為深沉的那個靈感之泉的聲音。再一次地,這是一個讓我們為自己開脫的迷思──如果我等到有時間再來傾聽,我現在就不用去聽了;今天我不需要有空為試圖浮出水面的靈感負責。
身為一個老師,我常常聽到「擋在我和一部曠世巨著之間的障礙,就是我沒有一整年的空檔」這種話。從這個角度看來,對於「有很多時間」的執迷便成為了寫作的瓶頸。多數學生或絕大多數的人們,都不可能有幸獲贈一整年的空檔。而沒有了那一年的空檔,我們就不能「真正地」從事寫作,是嗎?
或許事實不然。
「如果我有時間」的自我欺騙為我們大開方便之門,讓我們可以輕易忽略「作品需要被寫下來,而且寫作是由一次一個句子所構成」的事實。句子有可能在轉瞬之間構成。搶來足夠的片刻,搶來足夠的句子,一部小說就誕生了──即使沒有大把奢侈的時間。
律師史考特.杜羅(Scott Turow)是在每天通勤的電車上寫出他那部令人欲罷不能的小說《我無罪》(Presumed Innocent)。我的學生毛琳在一邊照顧她的男嬰、一邊忙於設計工作的情況下,寫出九齣劇情長片的電影劇本。另一個學生麥可,則是在攻讀碩士學位期間利用「閒暇之餘」完成了一整本書。這些人都是藉由搶時間寫作來達成目標,而不是枯等「找得到」時間的時候。
當我們懂得利用時間,便不論何時何地都能寫。一旦練就了「一古腦兒栽進去」的本事──為了培養這種本事,我教學生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寫整整三頁的速記──不論何時何地,你都能一古腦兒栽進去。等著看牙的時候、在飛機上的時候、在車站眼看別人要搭的車都來了而你還在等的時候、在會議與會議之間的空檔、午休時間、下午茶時間、在美髮沙龍、在瓦斯爐前等著洋蔥煎熟的時候……
一旦是出於對寫作純粹的熱愛而寫,我們就永遠有足夠的時間。但這時間是搶來的,就好像一對戀人在匆忙間趕緊吻一下彼此那樣。一回,有個冰雪聰明的女子告訴我:「再忙的大人物都能擠出時間給妳,如果他為妳神魂顛倒的話。但如果他找不到時間,那就是他不愛妳。」當我們熱愛寫作,我們就會為寫作找到時間。
所以,找到寫作時間的祕訣在於出於熱愛而寫,而非以完成一個作品為目標而寫。不要試圖寫出完美的作品,寫就對了。不要試圖寫出一部皇皇巨著,開始動筆就對了。沒錯,想到要擠出時間來完成一部小說,實在令人卻步。但如果只是要找到時間完成一個段落,或甚至一個句子,事情就沒那麼嚇人了。而段落是由句子組成的,小說則是段落組成的。
安妮的工作是為報紙寫稿,她永遠在等著有時間的時候要為了自己高興而寫。這聽起來就像在說時間是張一百美元的大鈔,哪天她運氣好就會在街上踩到。
我告訴她:「不要等有時間的時候,積極一點,搶時間寫!」
一開始,安妮發現她每天能搶到十五分鐘的時間。接著,她發現她每天能搶到兩段十五分鐘的時間。不久之後,她每週能搶到兩段數小時的時間。彷彿一個意外的豔遇般,安妮突然之間就能「為自己高興而寫」了。寫作的樂趣漸漸在她心裡蕩漾開來,她冷不防地就有了時間。
艾倫是個作文老師,一直渴望成為小說家。年復一年,他都告訴自己等他有機會休一整年長假,他的小說就會有眉目了。一天,他犯了個錯誤:把這個念頭告訴我。
我問他:「為什麼現在不可以?現在就開始寫,等你休長假的時候再來修改。」
艾倫辯白道:「我沒時間啊。我要教作文。我得坐在那裡,看著我的學生寫。」他聽起來滿腹的苦澀與惆悵。
「那就在他們寫作文的時候寫你的小說呀。別再把這件事想成一個了不起的大計畫。只要趁學生在寫的時候,你也寫個隻字片語就好了。」
艾倫又辯白道:「我只有一些模糊的想法,不知道這些想法要發展成什麼東西。」
「那就追隨其中一個想法,看看它要帶你去哪裡。」
「追隨其中一個想法!如果它帶我走進死胡同呢?我可沒時間從頭來過。」
「寫作的世界中沒有死胡同,沒有真正的死胡同。」我安撫他道。艾倫無話可說了,而且他知道自己無話可說了。
艾倫有時間寫。我們都有時間寫。從我們決定寫不好就寫不好吧,就讓我們勇於追隨一個可能成不了氣候的想法、隨手寫下隻字片語、只為了寫而寫、管它結果是否完美無瑕的那一刻起,我們就有了時間。
對時間的執迷,其實是對完美的執迷。我們想要有足夠的時間寫出完美的作品。我們希望在寫的時候底下有個安全網,這個安全網保證我們不是在愚蠢地浪費時間做一件可能得不到回報的事情。
我慫恿艾倫:「就從晨間隨筆開始,讓自己攤開紙、提起筆,寫三頁隨便什麼東西。這能訓練你的雷達,激發你的創造力。」
「我很懷疑。」艾倫告訴我。
「你儘管懷疑,但還是要去試。」我用手肘蹭他一下。
懷疑沒關係。晨間隨筆成功地點燃了引信,不出幾週,艾倫就在和學生們比賽看誰寫得快了。一次一句,一次一頁,他寫了起來。他甚至追隨起曾經被他認為是死胡同的想法了。
「我也覺得自己現在是一個比較好的老師。」他告訴我。
我並不意外。沒有什麼能比「愛」溝通得更清楚,而艾倫對寫作的熱愛將他像一盞明燈般點燃,讓他的學生可以看這盞明燈前進。
當我們讓自己為了熱愛而寫,當我們搶幾分鐘時間來當成禮物送給自己,我們的生活就變得更甜美,我們的性情也變得更可愛。我們不再是個充滿嫉妒的旁觀者,只會站在場外喃喃自語地說:「我也想……可是……」
「如果我住在佛羅里達,那我就能找到時間寫……」
「如果我的存款多一點,那我就能找到時間寫……」
我們告訴自己的這些關於時間與寫作的謊言,都和嫉妒脫不了關係。我們抱持著童話故事般的虛幻想法,以為有些人的生活比較簡單、資金比較充裕、比我們有更好的寫作條件。
蘿拉負責教幼稚園的資優生。她的生活要忙著規劃課程、批改作業,還要和家長打交道。但在這一切事務當中,蘿拉騰出時間來每天寫三頁的晨間隨筆,下午還能在晚餐之前的夾縫時間裡寫點東西。某些週末,她額外利用星期六多寫一點。前兩個冬天,她還到附近的社區大學上冬季寫作班。
蘿拉回憶道:「以前我也曾抱怨自己都沒時間寫東西。我想寫,我覺得不寫不甘心,但我又很安於當時的現狀。一開始,要撥出時間寫東西感覺起來還滿可怕的,但後來一切都改觀了。我現在不只有時間寫,似乎還有時間做其他所有事情。老實說,我覺得我以前很憂鬱,寫作把我的憂鬱治好了。這有可能嗎?」
「寫作能扭轉乾坤。」我告訴蘿拉。
「我知道妳一向這麼說,但以前我從來不相信,現在我相信了。」她答道。
在生活中利用時間來寫作,就能讓我們的生活有時間。當我們描述周遭環境時,我們便會開始品味周遭的一切。就連最匆忙、最混亂的生活,也會開始呈現出受到珍惜的樣子。
下筆輔助工具
時間的謊言
我們常說:「我沒時間寫。」但我們其實有時間,雖然只有一點點。這個工具幫助你打破沒有時間的幻覺。買五張明信片和五張郵票,寫上五個你關心但沒花時間聯絡的人的地址。設定鬧鐘,限時十五分鐘。每張明信片花兩到三分鐘,寫下給你朋友的問候,貼上郵票寄出去。
1.開始
我坐在一張松木桌前,面向東邊的基督聖血山。視線所及,馬槽空空如也,需要再加水進去;一道白色籬笆當中開了一扇藍色小門,小門的藍是知更鳥蛋那種藍;陶土材質的鳥兒戲水盆上有幾尊裝飾雕像已經被撞掉了;鮮黃色的澆花水管擱在那裡,我都用它來為馬槽和戲水盆注水;一畦菜圃生長過盛,一只水桶就躺在旁邊;我的小狗麥斯威爾沐浴在早春的陽光下,像個在冷颼颼的天氣裡還樂觀地跑到海灘上做日光浴的人。等暖和一點,等那條黃色的水管解凍,我就會把馬槽注滿。等做完暖身動作,我就會告訴你關於讓自己下筆寫作,我知道些什麼。
第...
目錄
【譯後記】一寫,就渾然忘我
【前言】
開始
讓自己去寫
讓自己去聽
時間的謊言
軌道
壞文章
寫作生涯
心情
字裡行間
惡人牆
珍視自身經驗
具體化
身體經驗
井
打草稿
寂寞
見證
何不在路上就做了?
連結
成為開放的管道
整合
資格
地點
幸福
成功
真誠
脆弱
日常
嗓音
現場與後製
走跳
練習與修行
自保
聲音
我想寫,但是……
駕車遨遊
根基
靈異經驗
小手段
風險
磨咕
栽進去
寫作的權利
【譯後記】一寫,就渾然忘我
【前言】
開始
讓自己去寫
讓自己去聽
時間的謊言
軌道
壞文章
寫作生涯
心情
字裡行間
惡人牆
珍視自身經驗
具體化
身體經驗
井
打草稿
寂寞
見證
何不在路上就做了?
連結
成為開放的管道
整合
資格
地點
幸福
成功
真誠
脆弱
日常
嗓音
現場與後製
走跳
練習與修行
自保
聲音
我想寫,但是……
駕車遨遊
根基
靈異經驗
小手段
風險
磨咕
栽進去
寫作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