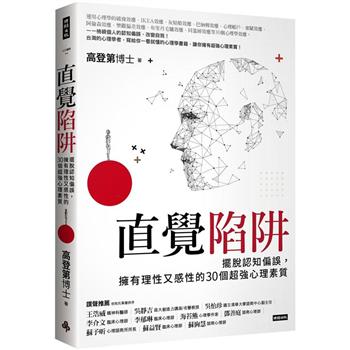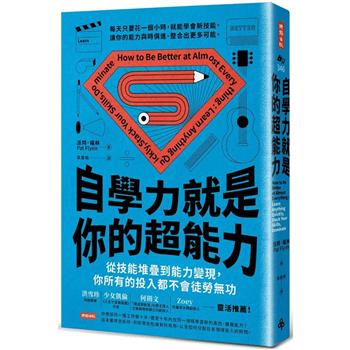新的豆腐︱為修訂、增訂、重排而寫 林海音
二十年前,我有一個﹁計畫編書﹂的構想,那就是以﹁中國﹂為主題,編輯一套中國的文、史、物之書,第一本就是﹁中國豆腐﹂。從策畫、邀稿到編輯,也煞費苦心;先安排內容,因為這不是一本豆腐食譜或豆腐歷史、豆腐坊如何做豆腐的書,要請什麼人寫什麼稿。這種點題式的邀稿方法,沒想到得到所有受邀者的支持,他們按時寄來了我特邀請譯寫的文章,如樂蘅軍的﹁古典文學中的豆腐﹂、朱介凡的﹁豆腐諺語﹂、子敏的﹁茶話豆腐﹂、伍稼青的﹁古籍中的豆腐﹂、彭歌的﹁海外吃豆腐﹂、篠田統的﹁豆腐考﹂、傅培梅的﹁兩種別致的豆腐菜﹂……等,共收了三十多篇好文章及我的兩個女兒祖麗訪問豆腐的製作、價值寫成﹁豆腐的身價﹂,祖美是傅培梅的弟子,她就搜集了百十道豆腐菜,寫成簡易的菜單。
我當時很怕寫來的文章或有內容重複之處,比如說大家都知道,中國豆腐起源於紀元前二世紀淮南王劉安發明之說最為普遍,如果大家的文章開頭點題都談及此,豈不讓我編起來麻煩。但是可愛可敬的作家們,居然各寫其豆腐,沒有一家是重複的。而且作家們都對於這樣點題的寫法表示讚許;他們挖空了心思想出他們心目中的豆腐,可以說,這使他們的靈感之泉流出了光潤圓滑的汁液,凝聚成一篇篇不同的﹁豆腐塊﹂。他們寫得高興,我也編得興起。當時大家所寫的,大多是散文、專文、回憶、家鄉豆腐等。雖然當時有人誤以為這是一本純豆腐食譜,其實豆腐菜單只佔全書的五分之一,這本書的文學意義高過菜單的實用,它實在是一本有思想和感情的﹁中國豆腐﹂啊,所以出版後頗受讀者的喜愛,也確實行銷一時。
自從我們娘兒仨︵ㄙㄚ︶編輯出版了﹁中國豆腐﹂,起了一點影響作用,即發現各報的副刊,不時刊出有關豆腐的文章,我看了也擇優剪存,預備再版時加入。接著我又繼續策畫編輯﹁中國竹﹂、﹁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中國兒歌﹂等,它們都在近十年來陸續出版了。雖然打著﹁中國﹂的旗號,內容可是都各有其學術的、具參考價值的、可讀的性質,也是我傾全力策畫、邀稿、找資料、編輯印製的。每本書出來都使我如釋重負。那時常有人問我:﹁底下要編的是﹃中國﹄什麼?﹂我笑笑回答說:﹁在我的構想中,還有一本﹃中國姨太太﹄呢!﹂大家聽了都驚異的笑了,﹁快編,我們要看。﹂但是十年以來,我事務繁雜,光是搜集資料,自己連策畫都力不從心了。而且說實在的,早先心目中已定好一位最佳撰稿人好友高陽,他卻故去了,要不然光是有清一代的﹁姨太太﹂,他就能瀟灑自如的寫上數萬言哪!而我自己對於民初以來的各型姨太太,也能寫出一些來吧!姨太太,本是﹁中國﹂特產,在中國文、史、物中,幾千年來,有她一大塊天地哪!
以﹁中國﹂為首已出版書籍中,除了﹁中國豆腐﹂是三十二開以外,其他都是二十五開本。所以我最近正在努力於本書的改版工作,改成二十五開本,以和其他﹁中國﹂書取其一致,不要顯得它矮了半截兒。而且文字的修訂、文章的增訂,都在這次一併作業了。在分類方面,我也重新安排,使之成為五種豆腐,即:
散文豆腐
考據豆腐
家鄉豆腐
海外吃豆腐
豆腐菜單
書中的三十多篇長短文,幾乎都是名家之作,豆腐菜單也是經過傅培梅女士審查︵它們是由祖美、祖麗姊兒倆搜集編寫的︶。二十年前的豆腐和現在雖沒什麼大改變,仍是那麼白嫩、那麼大方、那麼光潤,只是它的身價卻漲了十倍,也由板豆腐變成盒裝的機器豆腐。豆腐是每個中國人的食品,不管是家居飯桌上或豪華餐廳的酒席上,都少不了它!寫到這兒,我竟心酸的想起二十年前搬離要拆改的木屋進入高樓大廈居住時,最後的那天凌晨,仍是二十多年來在睡夢中阿婆的那一聲:
﹁買豆腐︱豆乾炸哦︱﹂把我從夢中喊醒了,張眼望窗外,天亮了,正是:
豆腐一聲天下白!
我可有二十年沒聽到這親切的聲音了,怎不令我心酸酸呢!
在我給新的﹁中國豆腐﹂增訂時,有一篇文章是我要特別提出說明的。
一九七六年的七月,我收到一本三百多頁圖文並茂的英文大書,書名:「豆腐之書──人類的食品」(The Book of TOFU-Food for mankind,作者Willian Shurtleff),贈者是郭偉諾(Thomas Gwinner)。他是西德人,德國海德堡大學中文系畢業,是德國學術交流協會的獎學金學生,來臺做為語文學家張席珍的學生,那時正在寫碩士論文,就是「中國豆腐」,後來他的博士論文則是「中國歷史的餐飲文學」。據張席珍先生說,我編的「中國豆腐」,也給了他一些影響和參考。後來我看「中副」有一篇他的作品,題名是:「中國文學中的豆腐」,寫成一篇五千字文章,可見其用心之深。而這本英文大書,則是他到日本京都收集資料寫成的,當時這位年輕學子才二十出頭,他雖是德國人,英文很好,又學的是中文。何凡和林良都記得他,何凡說曾跟他在報館打桌球,林良則知道的更多,說郭偉諾打球手執橫板,他有時也和球友們喝喝啤酒。張席珍則說他返德後也偶然來臺,這次有兩年沒來了,可見他和國語界諸同仁是好友。
這本英文書的封底是以這樣的詞句做為中國豆腐的認知和賞識:
豆腐︱前程更遠大的傳統食物
•中國在兩千多年前就發明了製造豆腐的方法。今天在日本一國就有三萬八千多家店鋪製售豆腐。豆腐在亞洲人民家庭食單上,已經佔據一席重要地位。
•現在美國人也愛吃豆腐,因為這種古老而富蛋白質的東方食品,正是尋覓既營養又價廉食物的西方人士的目的物。
•豆腐獲得大自然充足的養分,價廉物美,可說是對於世界吃緊的食物供應問題,給予革命性的紓解。
在我新編﹁中國豆腐﹂中,原已有美國人、日本人、韓國人所寫的豆腐文章,今又加上德國人的,故再綴數言表示我的欣喜。
八十二年五月二十日
原序 何凡
沒有耶穌基督就有豆腐︵見篠田統﹁豆腐考﹂︶了,所以豆腐是中國人的飲食文明的結晶之一。到了二十世紀,豆腐在中國食譜上應用更廣泛,製法更精緻,證明豆腐是禁得起時間的考驗的,沒有其他食物可以取代。豆腐在中國食物中有這樣超越的地位,也許和它的雅俗共賞、老少咸宜,及不嫌貧愛富有關係吧?
家裡有時來親友便餐,海音的最後的主菜常常是一味﹁二元豆腐﹂︵一元豆腐,一元鴨血︶,熱騰騰、麻辣辣、香噴噴,由那兩隻厚敦敦、軟綿綿的在我家廚房裡工作了三十多年的手端上來的時候,大家一聲歡呼,眾匙齊下,頃刻間就碗底朝天。
豆腐與青菜配搭,一向被國人視為維繫節儉美德,並保持健康營養的食品。如果配上雞、火腿、冬菇等高級食物,豆腐又成為豪華菜式。中國人的飲食文明博大精緻,在吃不過來的時候,選擇的機會較多,不免人人有忌食的東西,但是不吃豆腐的人恐怕不多。我小時候冬天愛吃凍豆腐︵那時沒有冰箱,只有等待大自然的轉變︶,這東西像海綿,本身沒有味道,以吸收他物之味為味,牙齒咬下去,滷汁就滋在口腔裡,十分有趣。來臺以後,為了配合逐漸衰退的牙齒,一碗肉末燒豆腐,配上亮晶晶的蓬萊米飯,比塞牙的雞肉、牛肉還對胃口。
由於大家都喜歡吃豆腐,觸動了海音編﹁中國豆腐﹂的靈感。這是一本綜合介紹豆腐的書,除了簡單的菜單以外,還包括關於豆腐的考證、散文、諺語、詩歌、傳說、專訪等等。看了這本書,可以先對中國豆腐了解個八九不離十。等到引起了興趣,再按書後菜單製作食用,則心裡明白,嘴裡享受,可以成為﹁豆腐專家﹂了。
海音這一構想得到親友的支持,女兒祖美、祖麗並且樂於為媽媽幫忙,於是在七月底發出徵稿信件,請大家湊湊熱鬧。在赤日炎炎的時候,高親貴友揮汗寫稿,正好趕上她秋涼編輯。稿子來源遠到美國、日本、韓國,作者也是東方人、西方人都有。雖不能說已集吃豆腐之大成,但是搜羅也夠廣泛的了。
有幾位作者,還寫了不止一篇。像梁容若先生的﹁豆腐的滋味﹂,是他二十年前在﹁中副﹂刊出的一篇作品,當海音把發黃的剪報寄給他,請求准予轉載的時候,梁先生自動的又寫了一篇,因為二十年來,他對豆腐有更多的話要說。海音請朱介凡先生在諺語中找豆腐的資料,他又加上一道朱老太太的﹁抓豆腐﹂。孫如陵先生也在百忙中把﹁豆腐革命﹂和﹁金鉤掛玉牌﹂兩文,親自用蠅頭小楷抄錄寄來。樂蘅軍小姐正在研究中國通俗小說,她由於在通俗小說中找豆腐,有了一些有趣的發現和心得︵見樂小姐原函︶,可以說是意外的收穫了。談豆腐就不能忘記一生提倡素食的李石曾先生,因此海音訪問九十三歲的李老先生。他是當年在巴黎辦豆腐公司的三元老︵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中僅存的一位。他所談的豆腐出國的資料,是以前沒有發表過的。又聽說梁寒操先生有詠豆腐詩,經海音寫信向梁先生求來,才知道豆腐有﹁劉小姐﹂這麼一個奇怪的綽號。也可以看出豆腐所到之處都可以適合當地人的口味。書中轉載的文章,都得原載報刊及原作者的同意,但陸德枋先生的﹁豆腐•節婦•傳麻婆﹂及康德夫人的﹁談豆腐﹂兩文,因﹁中副﹂已找不到通訊處,稿酬也就只好暫存了。
親家莊尚嚴先生病中揮毫,為書題名,為本書增色不少。
長女祖美是傅培梅女士的學生,對烹飪有興趣,對此書構想亦有貢獻。赴美後因臨產關係,只擔負拉稿工作。次女祖麗出訪新舊豆腐製作工作,兼助編校,因為這是她的本行工作,做來還算順手。
﹁中國豆腐﹂的資料、文章和菜單的收集,到此並不算完備,例如莊親家說的﹁江豆腐﹂,是清末民初的名菜,但是現在已自食譜中消失,亦不詳其製法,將來如果有人補充,仍舊應當補入。如果這本書獲得讀者的喜愛,願意提供更多的資料,再出一本續集,也是可能的。
這一個暑假,我看她們娘兒仨為這本書忙碌,也插不上幫忙之手。直到現在書排好了,還缺一篇序。廚房沒有我的份兒,補序總還可以,至此這種﹁家庭工業﹂的成品,總算條件具備,這也是慶祝中華民國六十年舍下的一個小貢獻吧!
六十年十月二日
豆腐頌 林海音
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豆腐。作湯作菜,配葷配素,無不適宜。苦辣酸甜,隨意所欲,﹁它潔白,是視覺上的美;它柔軟,是觸覺上的美;它淡香,是味覺上的美。﹂女作家孟瑤說:﹁它可以和各種佳肴同烹,吸收眾長,集美味於一身;它也可以自成一格,卻更具有一種令人難忘的吸引力。﹂
豆腐可和各種鮮豔的顏色、奇異的香味相配合,能使櫻桃更紅,木耳更黑,菠菜更綠。它和火腿、鰣魚、竹筍、蘑菇、牛尾、羊雜、雞血、豬腦等沒有不結緣的。當你忙碌或食慾不振的時候,做一味香椿拌豆腐,或是皮蛋拌豆腐、小蔥拌豆腐佐餐,都十分可口。時間允許,做一味麻辣燙三者兼備的好麻婆豆腐,或煎得兩面焦黃的家常豆腐,或毛豆燒豆腐,綠的碧綠,白的潔白,只顏色就令人醉倒了。假如就一碗蒸得鬆鬆軟軟的白米飯,只此一味,不令人百嘗不厭麼?它像孫大聖,七十二變,卻傲然保持著本體。
江蘇有句諺語:﹁吃肉不如吃豆腐,又省錢又滋補。﹂豆腐的蛋白質含量是牛肉和豬肉的一半,但是價錢卻便宜多了,豆腐的脂肪是植物性的,和肉類所含的動物性脂肪不同,吃了不會引起血管硬化或心臟病等毛病,難怪有許多人說豆腐是﹁植物肉﹂了。又因為它含極少量碳水化合物,所以也適宜減肥的人吃。豆腐中的鈣質含量和牛奶相同,特別適合孕婦和發育中的嬰幼兒吃。
慈禧太后駐顏有術,每天都要吞珠食玉。據民間傳說御廚房有蒸鍋四十九口,每口鍋裡放著鑲著珍珠的豆腐,四十九天可以蒸爛。四十九口鍋輪番蒸,慈禧太后就每天可以吃到一味潤膚養顏的﹁珍珠豆腐﹂了。
豆腐的做法是先把黃豆泡在水裡四至八小時,氣溫越高,泡的時間越短,泡夠時間放入石磨中去磨,磨好後濾去豆渣,剩下來的就是豆漿。然後把豆漿加熱至沸騰,再加凝固劑。一般都是用鹽滷或石膏做凝固劑,石膏的成分是硫酸鈣,鹽滷中主要成分是氯化鎂和硫酸鎂。加入凝固劑後,再入壓榨箱壓去水分就是豆腐。美國黃豆協會臺灣辦事處,每年有經費部分補助臺灣的豆腐製造商到日本考察。在日本,製豆腐簡直成了一門藝術。
近兩年市面上出現了用兩層塑膠袋包裝,經過高溫消毒的機器豆腐,不過銷路並不十分好,一般主婦還是喜歡新鮮的豆腐。豆腐店做豆腐都是從傍晚開始,天亮前做好。大清早又開始造第二批供午市需求︵豆腐工人下午休息︶。人人都買得起豆腐,在臺灣,一方豆腐只賣新臺幣一元五角。去年臺灣人共吃了五億公斤豆腐︱平均每人二十三公斤。臺灣每年產黃豆六萬公噸,進口六十二萬五千公噸,大部分來自美國,其中百分之十用來做豆腐,其餘的多用來榨油。
豆腐是漢文帝時代︵公元前一百六十年左右︶淮南王劉安發明。宋時,豆腐漸見普及,在江南,亦成為普通的食品。但除開特殊的情形外,尚未成為士大夫的食品,只有下層階級用來佐膳。清代開始,豆腐擴及於上層家庭,有時且調理成帝王專用的高級豆腐。宋犖七十二歲做江寧巡撫,剛巧康熙皇帝南巡。在蘇州覲見時,康熙見他年老,對他說:﹁朕有日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可令御廚太監傳授與巡撫廚子,為後半世受用。﹂
﹁隨息居飲食譜﹂對豆腐有如下的說明:
豆腐一名菽乳,甘涼清熱,潤燥生津,解毒補中,寬腸降濁,處處能造,貧富攸宜……以青黃大豆清泉細磨生榨取漿,入鍋點成後,軟而活者勝,其漿煮熟未點者為腐漿,清肺補胃,潤燥化痰。漿面凝結之衣,揭起晾乾為腐皮,充饑入饌,最宜老人。點成不壓,則尤軟,為腐花,亦曰腐腦。榨乾所造者有千層,亦名百頁,有腐乾,皆為常肴,可葷可素……由腐乾而再造為腐乳,陳久愈佳,最宜病人,其用皂礬者名青腐乳,亦曰臭腐乳,疳膨黃病便瀉者宜之。
不同時代,豆腐的名稱亦異。古語叫大豆做菽,﹁爾雅﹂稱為戎菽。豆腐又叫菽乳,還有﹁黎祁﹂或﹁來其﹂兩個名稱可能是印度或西域系統的語言,直到唐代,都是指乳酪、乳腐等凍奶食品來說,後來才變成豆腐的別名。﹁清異錄﹂說﹁邑人呼豆腐為小宰羊﹂,可能是因為豆腐普遍成為肉類的廉價代用品。
豆腐在中國社會中,是貧苦老實和勤勞的象徵。章回小說與舊劇中,也常喜歡安排一對孤苦無依的老婆老頭以磨豆腐為生,如﹁天雷報﹂裡面的張元秀。豆腐也圍繞著我國的語文,﹁豆腐西施﹂是說美貌的貧家女,﹁豆腐官﹂是廉潔的官,因為俸給微薄,只可以吃豆腐。
發揮豆腐烹調技巧最有名的人要算是成都北門順河街的麻婆了。麻婆娘家姓溫,排行第七,小名巧巧,美麗出眾,偏是老天捉狹,在她臉上撒下一些白麻子,但仍不減她的美貌。她十七歲那年,嫁給順記木材行四掌櫃陳志灝。光緒二十七年,四掌櫃不幸翻船。一月之間,健美的巧巧就形銷骨立。小姑淑華看她孤苦伶仃,加上十年相依的感情,不捨得留下她的四嫂自行出嫁。姑嫂倆為了生活,不得不面對現實,打開門戶。
姑嫂都能裁會剪,僅僅添了一張案板,裁縫店就立刻開張。不到半年,生意冷淡下來。好在四掌櫃在生時,那些常來他們店子歇腳的油擔子,看她們打開店鋪,每天又來歇腳,有些帶點米,有些帶點菜,沒有帶米帶菜的就在隔壁買點羊肉豆腐,其餘的人在油簍內舀點油,生火的生火,淘米的淘米,洗菜切菜,只等巧巧來上鍋一燒,就可飽餐一頓了。大家故意省下一口,就夠姑嫂早晚兩餐有餘。這些誠摯的情誼,不但鼓舞了巧巧枯萎的心情,更使她練出一手專燒豆腐的絕技。
巧巧做的臊子豆腐,經過眾口宣揚,名傳遐邇,凡是認得女掌櫃的總是想方設法,前來攀親敘舊,目的僅在想嘗嘗她做的豆腐。來者是客,怎好一個一個往外推。於是巧巧開店當爐起來,嫂嫂剁肉燒菜,小姑擦桌洗碗,那是光緒三十年。她們每天忙上十四小時,年復一年,由於操勞過度,姑嫂先後去世,而麻婆豆腐卻成了四川出色的名菜!
很少人有吃膩了豆腐的經驗。作家梁容若回憶生長在沙土綿延的地方,從小見慣了田裡種的大豆,豆子出產多,豆子的加工品自然也多。豆腐是天天見、滿街賣的東西。見慣看膩,無色無香,再加上家鄉豆腐常有的滷水苦澀味兒,所以他從小就不喜歡豆腐。
到抗日時期,一個兵荒馬亂的殘冬深夜,平漢路的火車把他甩在一個荒涼小站上。又饑又渴,寒風刺骨,突然聽到賣豆腐腦的聲音。梁容若擠在人堆裡,一連吃了三碗。韭菜花的鮮味兒、麻油的芳香、熱湯的清醇,吃下去直像豬八戒吞了人參果,遍體通泰,有說不出的熨貼,心想:﹁行年二十,才知道了豆腐的價值。﹂
他回憶說:北平的砂鍋豆腐、奶湯豆腐、臭豆腐,杭州的魚頭豆腐和醬豆腐,鎮江的乳豆腐,我都領教過,留有深刻的印象。有一次還在北平的功德林吃過一次豆腐全席,那是一個佛教館子,因為要居士們戒葷,又怕他們饞嘴,就用豆腐做成大肉大魚的種種形式,雖然矯揉造作,從豆腐的貢獻想,真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了。
作家子敏說:﹁我對豆腐有一股溫情,它甚至影響到我的處世態度。跟人相處,你不能蠻橫的要求對方的心情﹃必須﹄永遠是春天。朋友難免有心情壞的時候,難免失言、失態、失禮、失約。那時候,只有像豆腐那樣﹃柔軟﹄的寬厚心情,才能容忍對方一時的過失。朋友相交,夫妻相處,如果沒有﹃豆腐修養﹄,很可能造成終身的遺憾。
豆腐原是很平民化的食品。對我,它不只是這樣,它是含有深遠哲學意味的食品。它是平民的,但並不平凡,我們的﹃中國豆腐﹄!﹂
海音按:此篇係應中文﹁讀者文摘﹂之邀,摘錄﹁中國豆腐﹂一書中各家作品菁華編寫的。
六十四年六月
散文豆腐豆腐的滋味 梁容若
生長在沙土綿延的地方,從小見慣了種大豆,豆子出產多,豆子的加工品自然也多。豆腐是天天見、滿街賣的東西。油條就豆腐,豆腐拌辣子,蹲到擔子上就吃,賣油條的,買雞蛋的,背鋤的老王,打更的張三,誰也吃得起。見慣看膩,賤就不好,無色無香,再加上家鄉豆腐常有的滷水苦澀味兒,所以我從小就不喜歡吃豆腐。七、八歲的時候,聞到磨豆腐的氣味就要發嘔。菜裡有了炸豆腐,一定要一塊一塊的揀出來。這種偏憎不知道被大人們申斥過多少次。從小學裡知道了豆腐的營養價值,加上吃飯的禮貌訓練,暴殄天物的禁條,使我不敢再在菜裡揀出豆腐。可是碰到它的時候,也只是勉強下嚥,絕不主動地找豆腐吃。
是一個兵荒馬亂的殘冬深夜,平漢路的火車把我們甩在一個荒涼的小站上。又饑又渴,寒風刺骨,在喔喔的雞聲裡聽到賣老豆腐︵豆腐腦︶的聲音。大家搶著下車,你爭我奪。我也擠在人堆裡,一連吃了三碗。韭菜花的鮮味兒,麻油的芳香,熱湯的清醇,吃下去真像豬八戒吞了人參果,遍體通泰,有說不出的熨貼。回到老家,向叔父報告,自己笑著說:﹁行年二十,才知道了豆腐的價值。﹂叔父本是豆腐的謳歌者,就趁機會大加教訓,他說:﹁豆腐跟白菜並稱,惟其平淡,所以才可以常吃久吃,才最為養人,才最能教人做人。我們是以豆腐傳家,曾祖、祖父都是以學官終身。學正教授在清朝稱為豆腐官,因為俸給微薄,只可以吃豆腐。你生在寒素的家庭,開口是有肉不吃豆腐,不但不近人情,也對不起祖宗!﹂叔父的話並不使我心服,不過當時聽起來卻很聳然動容。以後自己也想,不管是﹁天誘其衷﹂也好,﹁實逼出此﹂也好,適當的場合,吃些豆腐,既可以恭承祖訓,又能得到實惠,何樂而不為呢?從此我就成為豆腐的愛好者。北平的砂鍋豆腐、奶湯豆腐,杭州的魚頭望豆腐,乃至於六必居的臭豆腐,隆景和的醬豆腐,鎮江的乳豆腐,我都領教過,留有深刻的印象。有一次還在北平的功德林吃過一次豆腐全席,那是一個佛教館子,因為要居士們戒葷,又怕他們饞嘴,就用豆腐作成大肉大魚的種種形式,雖有些矯揉造作,從豆腐的貢獻想,真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了。
在東京上學的時候,有一個研究文化史的日本朋友,立志要作豆腐考。一個深夜他同我談到淮南王劉安發明豆腐的文獻,談到明末聖僧隱元到日本輸入新的豆腐作法,又談到李石曾先生在巴黎的豆腐公司。照他看來,中國人在耶穌降生許多年以前,日本有文字許多年以前,發明了豆腐,要算文化史上的奇蹟。他為了向一個發明豆腐國度的人表示敬意,決意請兩毛錢的客,要我一同去吃﹁湯豆腐﹂。﹁湯豆腐﹂是一種白水煮的豆腐,有些和豆腐腦相似,寒冷的冬夜可以使我重溫平漢車站吃老豆腐的趣味,就欣然地同他去。在湯豆腐剛到嘴的時候,他說:﹁你看,這樣一大碗,只賣三分錢,從日滿經濟合作以後,豆腐可真賤。現在家家早上吃醬湯都要放豆腐。連德國人也在向大連躉購大豆呢。﹂他的話立刻激動了我,我把碗一推回答:﹁我感慨的是吃豆腐的人不是種大豆的人。聖僧隱元如果知道教會你們吃豆腐,還要送你們豆子,他一定後悔來日本吧!而且你們把劫掠的贓品賣到歐洲換飛機……﹂他看見我的眼淚掉在碗裡,像是很後悔自己的失言,想用一種滑稽的調侃收場,他說:﹁您還是多吃兩碗吧,種大豆的人如果知道運到東京的豆子,有一部分是給他們所希望吃的人吃去,他們的苦痛會減少一點。您多吃一點不拿錢的豆腐,也算是對於帝國主義的掠奪者小小報復。老兄啊,我的豆腐考可不是要曲學阿世……。﹂我無意於再藉豆腐罵座,傷不必要的感情,可是﹁湯豆腐﹂無論如何也再嚥不下去。我們終於默默地離別了,回來日記上記了一句:﹁同××吃哽咽的豆腐!﹂
在抗戰期間,河套有一次荒年,稷米、油麥都歉收,馬鈴薯也很少。只有潑辣的豆子照樣結子兒,黃豆成了軍民的主食。豆餅、豆麵、豆芽、鹽豆、豆腐、豆糕,顛來倒去,早晚是它。
大家一到飯廳,就皺眉嘆氣,咒罵:﹁該死的豆子!﹂是一次檢討會上,有人提出來:﹁如果沒有黃豆,我們多少萬軍隊除了吃草根黃土以外,什麼辦法都沒有。通過幾百里無人地帶的綏寧公路,根本不可能接濟大量糧食。是老天開眼,今年種豆得豆,豆餅豆腐使我們在塞外站住了腳,把國防線向東北推出了一千多里,我們有什麼理由詛咒豆子呢?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吃著豆腐,還有什麼事不可做?﹂這種道理一講出來,大家對於豆腐豆餅等,立刻改了觀感,不約而同地喊著:﹁感謝大豆!擁護豆腐!﹂在這段故事裡,我更從新體認了豆腐的價值,可是當時吃豆腐的滋味也還是辛酸的。
勝利以後,回到平津,滿指望可以吃到用東北大豆做的豆腐,醫療一下東京吃湯豆腐的心靈傷痕,親眼看見一船一船運到的是聯合國救濟總署從南北美搬來的施捨豆子,而松花江黑龍江平原的大豆卻是成千噸成萬噸一列車一列車地送到西伯利亞,去換叛國殺人的軍火。誰能想到這是本國人做的事,這種現象能延長到今天呢?
來到臺灣,每天清早還能聽到賣豆腐的聲音,走到郊外,看見的都是山嶺水田,哪裡來這麼多豆子呢?豆腐的來源還是求之於太平洋的對岸吧!想到路途是這樣遙遠,來路又靠不住,不必問當下價錢的貴賤,也就食不甘味了。
想起來我是生長在吃豆腐的家庭,童年悟道不早,迷於正味,等到艱難奔波,理解了食譜,吃到的豆腐,又常常陪伴著哽咽辛酸的眼淚,很少時候能體驗到豆腐平淡清醇的滋味。是我負豆腐,是豆腐負我,也真一言難盡。夢裡不知身是客,幾回從昏睡裡看到了無邊的豆田,黃莢纍纍像後套,像松花江平原,也像故鄉滋河的彎曲處!又幾回朦朧裡回到童年,看著叔父的顏色,吞下有苦澀味兒的豆腐。醒來只是在惆悵空虛裡,等候著﹁豆腐啦!豆腐啦!﹂臺灣勤勉的老婆婆的清脆聲音。
原載四十一年二月十八日中央日報副刊
茶話豆腐 子 敏
女作家林海音女士跟她所疼愛的兩個﹁不僅是名字美麗﹂的公主︵祖美、祖麗︶,計畫團結兩代的力量,合作編寫一本趣味的書:﹁中國豆腐﹂。如果這是一個已經確定了的書名,那麼,對中國人來說,它就含有﹁咱們的,值得自豪的﹂意味。對外國人來說,它的意義等於:﹁一種代表東方文化特色的中國民間食品﹂。
這個有文學意味的書名,﹁中國豆腐﹂,並不表示這本書純然是﹁純文學﹂的,她說,但是也絕對不是﹁純食譜﹂。她並不打算把它編成一部﹁以豆腐作為一種象徵﹂,﹁不懂英美文學的人絕對看不懂﹂的現代詩集,也不打算把它編成﹁水滾後,加鹽少許﹂的豆腐食譜。
她的意思,我想,是要費一番心血,把它編成一本﹁文學的,生活的﹂有意味的散文集。在﹁文學﹂的一面,它不但編入了許多有意味的﹁豆腐散文﹂,並且連那﹁食譜文﹂也要拿起文學的彩筆來寫得像﹁文心雕龍﹂,像﹁詩品﹂,像﹁茶經﹂。
在﹁生活﹂的一面,她要使豆腐成為我們文化精神中的一個重要角色,像長袍,像摺扇,像書法,像山水畫,像孔子的哲學,像﹁孝﹂,像﹁義﹂,像﹁信﹂。更進一步,她要使﹁談豆腐談得極端精彩的人﹂,至少能﹁深入生活﹂一點,知道做豆腐也有它的精彩處,吃﹁豆腐﹂也有它的藝術。
這樣的一本書,它所處理的﹁題材﹂是一種至少有兩千年歷史的﹁由淮南王到老百姓﹂都很愛吃的食品。這個﹁工程﹂的難,就像﹁處理﹂白話文一樣,也跟拿豆腐燒菜差不多。白話文的﹁白﹂像豆腐,但是你要釀造意味像釀酒。豆腐的清淡像白話文,但是你要把它﹁燒﹂得經得起品嘗,上得了桌。不過,我有理由相信,這幾年來有本領燒得一桌桌﹁純文學﹂好菜的林海音女士,並不怕這個﹁燒一道好豆腐﹂的挑戰,何況還有﹁美、麗﹂的兩個助手的協助。
前面那幾句﹁高談闊論﹂的背面,藏有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那是一種﹁交差動機﹂。這本﹁未來的書﹂的編寫人,在談到她的計畫的時候,就像少數最內行的編者一樣,用一種權威的,同時也是﹁冒險家﹂的口吻說:﹁你寫一篇豆腐﹃茶話﹄!﹂這就是我寫這篇﹁茶話豆腐﹂的真正的原因。
如果她用的是最外行的,同時也是最不﹁冒險家﹂的口吻,說:﹁如果您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寫一點關於這方面的東西。﹂那﹁如果﹂,那﹁也可以﹂,含有明顯的﹁豁免﹂的暗示,那麼,她就會永遠看不到這篇文章了。當然,我並沒暗示她所﹁看不到﹂的文章一定會是﹁好﹂文章。
所有出色的編者,都是天生的冒險家。不過,所有﹁出色的作者﹂並不都是天生的無賴漢。我不會為這篇文章將來是在﹁中國豆腐﹂﹁之內﹂﹁之外﹂嘆息,或者整夜枯坐,由狗吠一直聽到雞啼。我的口氣,在這兒,好像也含有另外一種友誼的權威:不管怎麼樣,不可以把這個計畫擱置起來。
一個﹁空談家﹂所能談的﹁豆腐﹂非常有限,而且難免會給人一種﹁霧裡的豆腐﹂的印象。不過我並不小看我自己。我相信我能不靠太太的幫忙,做到﹁霧中最大的明晰﹂。
我童年因為感冒,胃口不好,什麼東西都不想吃,坐在飯桌前用﹁不舉筷子﹂示意的時候,母親會說:﹁那麼,我另外給你盛一碗紅燒豬肉。﹂
我小時候,只要不鬧病,對豬肉的興趣是很濃的。我吃的是瘦肉,對肥肉懷著畏懼,因此造成了我現在的體型,在﹁橫﹂的方面毫無成績的體型。我幾乎可以說﹁我的身體完全是豬肉造成的﹂,我是指瘦豬肉。
儘管是那樣,在我感冒而胃口不好的時候,我竟會對紅燒瘦豬肉搖頭。
﹁既然連豬肉也吃不下去,﹂母親會說,﹁那麼我給你做一碟醬油拌豆腐吧?﹂
豆腐是我在任何情況下唯一吃得下的一道菜。它清淡,使我不因為感冒失去味覺難過,我知道它本來是清淡的。我嘗它的時候,並不覺得在味覺上失去了什麼,因為它本來就沒有什麼好失去的。那種感覺,就像我現在懷念幾個最值得懷念的朋友一樣。他們也是﹁淡﹂的。我們的友情是在沒酒沒肉的情況下培養起來的。失去一大碗一大碗的酒,失去一大塊一大塊的肉,也就失去了一個一個的朋友,這真是人生的悲劇;只有酒缸再滿,肉鍋再噴香,朋友才能再回頭。
但是我不是,我的好朋友隨時可以來,隨時可以去,沒有任何牽掛,淡淡的來,淡淡的去,像﹁豆腐﹂。我們互相尋覓對方清淡的滋味,不為酒香肉味所掩蓋的。
豆腐是嫩的,牙床的肌肉不必緊張你就可以﹁吃﹂它。它不是水,但是它像水,它﹁流動﹂在舌尖齒間。那感覺是輕鬆自然,像最知心的朋友那樣,像可以不﹁會話﹂的朋友那樣。他來看你,沒有﹁來意﹂,所以不必﹁說明﹂。他走,並沒完成任何﹁交易﹂,所以雙方都沒有條約上的義務。他像光,像影,像豆腐。豆腐像他,像最知心的朋友。
童年在我感冒的時候,我吃豆腐所獲得的那種感覺,在我成年以後,我從友情裡得到一次印證。
假如﹁喜愛﹂像﹁疼痛﹂一樣,也被醫生拿﹁度﹂來計量,那麼我對豬肉是八度,對豆腐是十二度。我是常鬧牙病的人,在苦難中唯一的知己就是熬得很爛的稀飯跟豆腐。苦難來臨,豆腐出現,那種溫情是很不尋常的。它不是賀客,它是穿白衣的平民,在你失去金線繡飾的蟒袍的時候,它悄悄的來看你,像一切﹁人生變化﹂都沒發生過一樣。它無力幫助你重建榮華,它只有能力陪伴你品嘗你永遠不會失去的東西。
一個人在品嘗豆腐的時候,心中會泛起一種﹁再也用不著擔心有什麼會失去﹂的安全感,那種安全感會使人產生道德的勇氣,那結果不只是﹁不懼﹂,也是﹁不憂﹂,也是﹁不惑﹂。聰明的人應該以豆腐做他的﹁人生基地﹂;豆腐以上的,用一種真正﹁豁達﹂的心胸去﹁迎接﹂,去﹁捨棄﹂。
事實上,我對豆腐有一股溫情,它甚至影響到我的處世態度。人跟人相處,你不能蠻橫的要求對方的心情﹁必須﹂永遠是春天。朋友難免有心情壞的時候,難免失言、失態、失禮、失約。那時候,只有像豆腐那樣﹁柔軟﹂的寬厚心情,才能夠容忍對方一時的過失。朋友相交,夫妻相處,如果沒有﹁豆腐修養﹂,很可能造成終身的遺憾。最令我難忘的朋友,並不是那﹁曾經對待我很熱情的﹂,而是那﹁曾經寬恕我的過失的。﹂
上館子吃飯到了該﹁點湯﹂的時候,在報過幾道湯都不合適以後,跑堂兒的也許是成心,報了一道想氣氣我的湯。我的大喜過望常常使他大失所望。那是我從童年就認識的一個好朋友的名字,我的﹁青菜豆腐湯﹂。
豆腐原是很平民化的食品。對我,它不只是這樣,它是含有深遠哲學意味的食品。它是平民的,但並不平凡。我們的﹁中國豆腐﹂!
豆腐革命 孫如陵
日本賣豆腐的,正分成兩派,各不相下,在鬧風波。沿用中國舊法製豆腐的一派,普遍受人歡迎;採用﹁機械化﹂的一派,所推出的圓筒形豆腐,則銷路甚慘。然大勢所趨,要大量生產,手工不如機械,所以舊派開會決定集資建廠經營,叫豆腐業也來一次﹁工業革命﹂。走筆至此,連帶想起兒時讀過一首詠豆腐的詩:﹁一顆豆子圓又圓,推成豆腐賣成錢,人人說我生意小,小小生意賺大錢。﹂也許日本的豆腐革命,是為了小小生意可賺大錢吧?
豆腐的原料︱大豆,原產於我國,﹁爾雅﹂曰﹁戎菽﹂,古時以享祭祀,視為珍品。我國大豆於一七九○年傳入英國時,僅供觀賞,經過八十三年,才作食用。一八七三年,奧國維也納開萬國博覽會,我國大豆製品,見稱於世,咸認為經濟食用作物。現在各國都栽種大豆,可說是一種世界性的食物。
我們曾戲稱豆腐為﹁國菜﹂,其實以它歷史的悠久和產地的廣大,它是當之無愧的。我國大豆的產量,曾佔全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八十,當時與絲、茶都是出口大宗,且居第一位。至於吃法,更是多到不可勝數,無論吃葷茹素,幾於每餐不忘,如果把豆類從我們的食品中抽出,那就所餘無幾了。美哉豆子,大哉豆子!
從前臺灣食用大豆,是經大陸運來;現在則是由美國輸入。美國自一八五三年的柏耳︵Belly︶收種子由我國輸入開始,迄今不過一百一十一年,而使我國的﹁國菜﹂要用美國豆子來做,吃起來總覺有些愧對祖宗!
原載五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大華晚報
豆腐閒話 孟 瑤
在日常生活中,我最愛吃的一味菜就是豆腐。它潔白,是視覺上的美;它柔軟,是觸覺上的美;它香淡,是味覺上的美。它可以和各種佳肴同烹,最後,它吸收眾長,集美味於一身;它也可以自成一格,卻更具有一種令人難忘的吸引力。它那麼本色,那麼樸素,又那麼繫人心神。
豆腐的營養價值很高,它是窮人的恩物,也是中國人的恩物,據說,有中國人的地方就能找到豆腐的供應,這證明,不愛吃豆腐的中國人一定不多。不僅如此,屬於華夏文化籠罩下的外國人,也一樣愛吃豆腐,譬如日本、韓國、中南半島的國家。
愛吃豆腐的人,都說不出它有什麼特殊的味道,但每一憶及它,卻總是依戀的。想想,當你忙碌或食欲不佳的時候,做一味香椿拌豆腐,或皮蛋拌豆腐、小蔥拌豆腐,只兩三分鐘時間,或就酒,或佐餐,都十分可口。時間允許,做一味麻辣燙三者兼備的麻婆豆腐,或煎得兩面焦黃的家常豆腐,還有如今毛豆正上市,毛豆燒豆腐,綠的碧綠,白的潔白,只顏色就令人醉倒了。假如就一碗蒸得鬆鬆軟軟的白米飯,只此一味,不令人終身不厭麼?其實豆腐也不只因生活簡單而食取果腹如我的人嗜愛它。饕餮者,美食家,也很難不常常惦念它的。譚公豆腐固不去說它,平常,在大吃大喝之餘,為了不肯糟蹋一味自己最愛吃的菜,常常用它的殘汁再燒一盤豆腐。我嗜豆腐如狂,是因它容易烹調使我留戀,只須用白水煮了,沾醬油吃,竟也非常美妙。但,我卻不愛凍豆腐,因為它似乎已不是豆腐了;就好像我不嗜甜食,豆漿我卻不吃鹹的,也因為它已不是豆漿了,理由是一樣的。
豆腐是黃豆的加工品,屬於這一系列的東西很多,豆乾、豆乳、豆腦……是其中最普遍的。它們,也各有美味。
記得兒時在南京念小學,路邊小攤,常常有許多吸引小孩的零食,其中便有豆腐乾。是圓形的,香的是醬色,臭的是灰色,好像由蒲葉包裹煮成的,上面印成了花紋,十分美觀。那時我對它便嗜之如命,常常就著馬路上飛揚的塵土,一路吃回家。那時我們的住屋是在淮清橋旁邊,後門,便是秦淮河,常常有一個小販,提著一個橢圓形的食盒,由河邊拾級而上,由我們家後門進來,然後打開盒蓋,裡面是各式各樣的豆乾。那年母親還在,常常一次買許多,其中有一種蝦﹁子﹂夾心的,最是美味。
回憶,常常是很美麗的,我出生漢口,大部分童年卻在南京度過,但故鄉事,也依稀記得,有兩樣美味,似乎在別的地方沒有吃到過,一是臭千張,一是臭麵筋。臭千張是豆類的加工品,所以由豆腐擔子上叫賣,買時上面還有一層白毛︵霉菌︶;吃時多半用油炸得焦黃,真所謂異香撲鼻。就著乾爽的蒸飯︵故鄉吃用木甑所蒸的飯︶,實在可口。
豆乳也有各種做法,現在臺灣就有好幾家十分出名,它,卻勾起我兩個忘不掉的回憶。抗戰時在重慶念大學,伙食一天比一天壞,因此長期陷於饑餓中,便不得不加點菜以謀一飽。最有錢的時候,當然是去飯館﹁吃油大﹂,這不是能每天如此的。等而下之,就是做一罐又鹹又辣的肉醬,又經吃又下飯,可以維持好一些日子。此外,臨時救濟辦法就是在飯廳門口買一塊豆乳,它是用竹葉包的,上面有辣椒粉,又鹹又辣,可以開胃。這種豆乳,卻不是豆乳中的上品,佐食而已。復員住在上海,門口常有叫販,一次,我便買到一種令我至今不忘,臭得美味的豆乳。好像是近郊的鄉下人挑進城裡來賣的。他挑著前後兩木盒,其形如飯甑,本色的,洗刷得乾乾淨淨,裡面,便是一圈圈、一層層的臭乳,一寸見方,排列得整整齊齊。當時,我只隨便買了一些,卻不想竟鮮美異常,以後也買,卻再也不如這次。如今,變得很有名的炸臭豆腐,但好聞不好吃,比我想念中的那一味,差遠了。
豆腐,也常給人一些聯想,譬如陳麻婆的故事,雖然傳說的內容有些大同小異,但是,一個寡婦,為了謀生,以她在烹調上的特殊會心,而燒出一樣眾人皆嗜的美味來,卻是其中不變的內容。想想吧,一個沒有丈夫的女人,甚至於也沒有兒女,丈夫拋給她的,只不過半椽破屋,於是她默默地、低著頭,為往來的客商,燒一味簡單樸素的菜,來換取自己的衣食,不妄求,也不苟取,就這樣謙抑地打發她的一生;這總是會增加人們一些淒涼寂寞之感的。所以戰時我曾住在成都,總鼓不起勇氣去拜訪與憑弔那一塊地方。
章回小說與舊劇中間,也常喜歡安排一對孤苦無依的老婆老頭以磨豆腐為生,如﹁天雷報﹂裡面的張元秀。其實磨豆腐應該是件很吃力的事,現在都用機器代替了。讓它與貧苦的人發生聯想,大概因為它利潤薄的關係。
抗戰時在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念書,一次,為趕一場話劇,一群人,只有一趟車錢,於是看完了戲便從城裡走回去,一路上又怕鬼又怕﹁棒老二﹂,便索性唱著鬧著往學校走。就好像走進舊小說裡一樣,在一片黑暗的路上,﹁前面忽然閃亮著燈光﹂,我們走過去,正是一家豆腐店在趕夜工,好追上明日清晨大家的需求。工作的人倒是一群壯漢,拿出熱燙燙的豆漿招待我們,望著夜色,喝著啜著,渾身充滿的,就是那一種說不出道不出的人情味。也因此想起,不知在哪裡看到的一則小故事:一個年輕人,父母留給他一爿豆腐店,每天辛勤工作,早上,把豆腐賣完了時,總愛坐在門口悠悠閒閒地吹起橫笛來,很難描繪那一份動心的自在與自足。它,打動了一位富家千金的心,終於嫁了他,幸福的他,也因此繼承了岳父的財產,成為富翁。從此,鄰人們再也看不見他橫笛而吹的自在了,代替它的,是晚上不停地撥算盤聲。這是個一點也不動人的小故事,卻常常會跳到我的腦子裡來。什麼有比平靜、樸素、無欲的生活更吸引人的呢?它就像豆腐一樣,說不出它有什麼特殊的味道來,但,你卻永遠懷念這平淡。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中國豆腐的圖書 |
 |
中國豆腐 出版社: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9-0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0 |
二手中文書 |
$ 175 |
飲食文學 |
$ 198 |
飲食料理 |
$ 225 |
飲食生活/文化 |
$ 225 |
科學‧科普 |
$ 225 |
科學科普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豆腐
本書由林海音女士主編,夏祖美、夏祖麗 助編。文中收錄了,林海音、樂蘅軍、朱介凡、子敏、伍稼青、彭歌、傅培梅……等名家的作品
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豆腐,作菜作湯,配葷配素,無不適宜;苦辣酸甜,隨意所欲。這是一本綜合介紹豆腐的書,除了簡單的豆腐菜單外,還包括有豆腐的散文、考據、諺語、典故、專訪等,作者更包括中、日、韓、美、德各國人。作家挖空心思寫出他們心目中的豆腐;他們的靈感之泉流出了光潤圓滑的汁液,凝聚成一篇篇雋永的「豆腐塊」,使本書不單有菜單的實用,更具文學的意義,是一本有思想、有情感的「中國豆腐」。
章節試閱
新的豆腐︱為修訂、增訂、重排而寫 林海音二十年前,我有一個﹁計畫編書﹂的構想,那就是以﹁中國﹂為主題,編輯一套中國的文、史、物之書,第一本就是﹁中國豆腐﹂。從策畫、邀稿到編輯,也煞費苦心;先安排內容,因為這不是一本豆腐食譜或豆腐歷史、豆腐坊如何做豆腐的書,要請什麼人寫什麼稿。這種點題式的邀稿方法,沒想到得到所有受邀者的支持,他們按時寄來了我特邀請譯寫的文章,如樂蘅軍的﹁古典文學中的豆腐﹂、朱介凡的﹁豆腐諺語﹂、子敏的﹁茶話豆腐﹂、伍稼青的﹁古籍中的豆腐﹂、彭歌的﹁海外吃豆腐﹂、篠田統的﹁豆腐考﹂、...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出版社: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9-05 ISBN/ISSN:9789866451089
- 類別: 中文書> 生活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