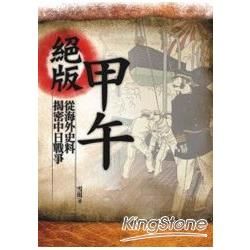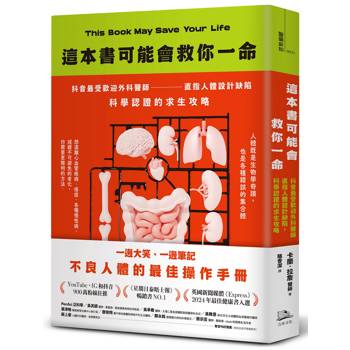自序
1
一艘「勇敢級」(Daring)驅逐艦就停在我的窗下,只要從電腦前一抬眼,就能看見它那灰色的艦身和4.5吋的主炮。澳大利亞的「南十字星」國旗,在艦首旗杆上飄揚。
在雪梨(Sydney)工作的每一天,我無數次地從樓上俯視這艘軍艦以及與它並肩停泊的一艘潛艇。南太平洋湛藍的海水一漾一漾地,拍打著這些作為海事博物館展品的退役艦艇。它們也如同家中的寵物那樣,不時需要開到外海去遛遛,或到船塢去檢修,每逢它們要移動的時候,我都會趕緊下樓,近距離地觀察這些「海狼們」的動作,百看不厭。
很難想像,這個寧靜而時尚的「情人港」(達令港,Darling Habor),曾經是抗日的第一線:入侵的日本潛艇驚擾了整個雪梨,當婦孺們被轉移到藍山(Blue Mountain)後,男人們便扛著槍炮,構築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線,而第一道防線,就設在這些美麗的海濱。
在澳大利亞這個遠離世界其他地區的孤獨大陸上,二戰時為防禦日本入侵而修建的工事,幾乎是唯一能找到的與戰爭直接有關的遺跡,儘管日本皇軍的鐵蹄一步也沒踏上這塊國土。
每次當我走過那艘滿載時排水量也才3888噸的驅逐艦,總會想起比它年長一個甲子的定遠艦和鎮遠艦。那兩艘威力巨大得令世界側目的中國主力艦,排水量為7000噸,主炮口徑為12英寸,如果與它們並列,眼前這艘澳洲軍艦,將會顯得侏儒一般矮小。但是,曾經威震一方的定遠和鎮遠艦如今又在何處呢?
日本人在這個城市依然頑強地展現著他們的巨大影響力,當然不再依靠槍炮,也不依靠人多勢眾。著名的紀伊國屋書店,就在古老的「維多利亞女王大廈」(QVB)左近開設了澳洲分店,不動聲色地向澳洲「輸出日本」。這是全澳洲規模最大的書店,除了大量經營英文書外,其日文書品種之多,與日本本土書店相比亦不遑多讓,而且還提供完善的訂購服務,可以購買日本出版的任何書籍。我就是在那裡買到了不少有關中日歷史的書籍;而其開闢的中文書銷售區,無論是書的品種、品質還是對閱讀潮流的把握,唐人街沒有一家中文書店可以媲美。
在這個寧靜的書店之外,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大量來自中國的遊客,他們興奮而高調地談論著,拿著大大小小的購物袋,滿臉洋溢著富裕起來後的自豪。他們當然忙得不會跨進這個日本人的書店,也不會去不遠處的海事博物館看看那些艦艇。而報亭裡正在熱賣的英文報紙,則在使勁地談論著是否應該允許中國人收購澳洲的礦業。在這個年代,日本是很難取代中國而成為新聞焦點的。
2
我總是很抗拒別人把我稱為歷史學者,因為在我看來,「學者」這個詞還是很崇高的。在一大群靠歷史吃飯的人群中,並沒有幾個人夠格能稱為學者,而最多稱為職業工作者而已。而歷史於我,好在並不是個飯碗,這是我的遺憾,也是我的幸運。
研究歷史便如同登山,登得越高,越是雲山霧罩,越是發覺自己的渺小。收集和研究海外晚清史料十多年了,隨著自己的文字得到媒體和朋友們的認可,我越發地感覺自己只是個淺薄的過客而已。這種日益強烈的惶恐感,令我終於發現了一個合適的定位:非職業歷史拾荒者。
是的,我無非是個拾荒者,鑽在別人草草開採過或不屑於開採的礦井裡,撿拾遍地的寶物。這個礦井,就是海外豐富的晚清史料。
我的一位美國收藏同道曾抱怨道:與中國歷史有關的考據,經常難以從中文資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為 「中國人只收藏對自己有利的資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敵對方的資料。的確,客觀上中國一向不注重對「蠻夷」的事態分析,主觀上則養成了「恨屋及烏」的習慣,但凡是敵人,他們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乃至於他們的文獻資料,亦多被視為異端,最多供一個小圈子「內部參考」。我們的歷史研究,便是在一個已經設定好的框架內,根據設定好的程序,根據需要對史料進行剪裁。此種剪裁,無論被冠以何種高尚的籍口,亦等同於電視新聞製作中所謂的「客觀鏡頭、主觀剪輯」,雖然每一個鏡頭都的確來自實況,但不同的剪裁和拼接卻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在對待歷史問題上,我們所表露出來的「選擇性健忘症」,絲毫不比日本人遜色。 「一史兩制、一事兩制」,我們在史識上和史評上體現出相當強烈的人格分裂和雙重標準。「反面人物」身上的「罪惡」行徑乃至「賣國」行徑,在「正面人物」身上就成了智謀和策略,最多是「多走了幾步彎路」、多交了點「學費」而已。這樣的人格分裂和雙重標準,與日本一方面否認南京大屠殺,另一方面時刻不忘廣島核暴的罹難者,似乎並沒有本質的區別。而同樣的「選擇性健忘症」,日本人更多地是以此欺人,而我們則更多地是以此自欺。僅此而已。
3
如果要海選「最不被中國人相信的口號」,「中日不再戰」或「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類,應當是榜上有名的。但在對日關係上,我們依然會奇怪地堅信:「以德抱怨」的單戀,可以彌合歷史的傷痕,緩解現實利益的衝突。大到國共兩黨,爭相放棄對日索賠,比著表現大國風度和天朝慷慨,小到一部講述南京大屠殺的電影,非要自作多情地從「人性」角度去描繪日本士兵的內心掙扎,而甚至忘了展示更有典型意義的殺人競賽。
來自中國的戰爭賠款,曾經是日本賴以崛起的資本;而同樣來自中國的放棄索賠,也對戰後日本的復興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等到我們的發展需要資本的時候,那些本該是戰爭賠款的日圓卻轉彎抹角地以援助貸款的方式登陸,如此先虧裡子、後丟面子的窩心事,難道不比要求日本下跪道歉更值得我們反思嗎?
中國文化,本不應如此阿Q。孔子當年就對「以德抱怨」嗤之以鼻,質問道:如果「以德抱怨」,那「何以報德」呢?大漢王朝時,出於「安全關切」,多次出兵「侵略」匈奴,著名將領陳湯從敵前給漢元帝發去一份奏摺,表示了「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決心,「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種「雖遠必誅」的陽剛精神,後來便逐漸消亡,對待外敵基本就是和親、懷柔,用子女金帛「贖買」回大國崛起的感覺,且美其名曰「以德抱怨」,聊以自慰。
寬容與和解或許是一種美德,但它有個基本前提:真相與懺悔!
4
中國人涉及日本的歷史記憶,的確充滿了太多的悲情,但遺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個甲子,我們卻還只沉溺於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訴的「傷痕文學」階段,難以自拔、難以深入。一個遭受了過度苦難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訴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強上;如果把紀念只是寄託在罹難者身上,而不是寄託在抗爭者身上,它在心理上還是一個弱者。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淚就是最無用的化妝品。我們今天或許該問問自己:我們是應該讓日本正視歷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視呢?我們是應該讓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們是應該反對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但如果他們就是拒絕接受呢?我們除了叫叫嚷嚷,還能幹些別的嗎?
悲情之外,我們大多數人還相信另一個神話:正義必勝。我們恰恰忘了:被凌辱與被屠戮,這不是正義;反抗凌辱與屠戮,這才是正義;勝利絕不來自正義,而只來自於實力。外侮只能說明我們無能和軟弱,並不能因此而賦予我們「正義」,更不能因此而賜給我們「勝利」。
在國際政治中,真正的普世原則就是「叢林原則」。已經上演和正在上演的所有爭鬥,無論其是民族之間的衝突還是民族內部的衝突,最後一定會歸結到「利益」,區別無非在於為誰的利益和為什麼樣的利益。而且,所謂的「正義」,彈性很大。甲午戰爭時期,日軍儼然以文明的傳播者和中華的解放者自居,對「征服支那」充滿了「正義感」。
中日歷史的研究,如果真要起到資治通鑒的作用,則必須擯棄毫無意義的道義之辯,而還原和探究其最殘酷的本質:中日之間的利益爭奪和調整。溫情脈脈的道德說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養出一大幫宋襄公。
5
我們對日史觀中,最可笑的自作多情,在於非要將日本的獸性歸咎到某種「主義」(軍國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似乎成千上萬的日本「人民」只是誤上賊船、被蒙蔽而已。這在「術」的層面上,作為一種公關、統戰工具,未嘗不可。但若真以為是,則不僅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險的。
「主義」固然在塑造著人,但「主義」本身也是人所創造,更是由人在實踐的。同一「主義」,在不同的人群手中,會實踐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現實體現來。日本侵華,與其說是軍國主義毒害了國民,不如說是其國民性格和利益訴求製造了軍國主義。
包括日本在內的大量海外史料,說明「日本人民」從來就不是什麼侵略戰爭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推動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就是強大的民意力量,其中包括那些屬於「被壓迫階級」的工農。如果非要說「廣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則他們並不受害於侵略或「軍國主義」,而只是受害於「不幸戰敗」而已。
把「主義」當作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癥結,最後就只能在「主義」的高低和好壞上進行無謂的爭論。
6
從日本和中國結下樑子的那一刻起,我們就從來不缺口水抗日的高調之徒,情緒化、非理性,充滿激情地追求劇場效果。這種速食「愛國主義」,與需要靜下心、沉住氣、臥薪嘗膽般地 「師夷長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價小,見效快,但結果是一方面逢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對日本的無知,甚至毫無「知」的願望。
歷史已經證明,「小日本、大中國」的輕佻心態正是造成「大中國」總是勝不了「小日本」的關鍵。甲午戰爭之前,日本的一些熱血青年,來到中國從事諜報工作,幾乎走遍大江南北,進行艱苦卓絕的實地調查,根據他們的情報編纂而成的《清國通商綜覽》,出版後居然有2300多頁之巨,比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國國情,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文獻。他們當然是中華的敵人,但這樣的敵人,在值得我們痛恨之外,難道不值得我們尊敬和學習嗎?我在海外傾己所有,收藏與晚清歷史有關的海外文物,也是力圖對這種實證主義、行動主義的一種實踐嘗試,「抗日」是需要行動的。
7
歷史研究,或者僅僅是嘗試對歷史現場進行還原,需要的是三要素:史料、史料,還是史料。史料就是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新聞採訪」,不同的當事人,不同的角度,這些是接近真相(但永遠不可能抵達)的基本條件。
我總覺得,歷史研究,必須要具備新聞記者和律師的兩種秉性:要像新聞記者那般敏銳,也要像律師那般挑剔和嚴謹。這是我所從事過的兩種職業,我覺得或許正是這兩種職業的訓練,才能使我從堆積如山的史料中淘出寶貝,也能使我從不迷信任何既定結論或任何權威。在「拾荒者」的定位之外,我總覺得自己還應是個藉著史料、穿越時空回到歷史現場採訪的記者,多看、多記、多思考,這樣的「歷史新聞」才可能是有價值的。
人生苦短,而歷史卻悠長得接近無限大。在歷史面前,我們永遠是盲人摸象,這是我們無法超越的局限。關鍵是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自己永遠不可能摸到整隻象,更不應假裝自己有能力看到所謂的全局。這樣,當我在自以為歷史或許是條毒蛇的時候,就不會對他人認為歷史是面戰鼓而感覺震驚。
因為,我只是摸到了大象的小尾巴,他卻有幸摸到了那偉大的象屁股。這時候,我只能說:不求最大,只求最佳!
(雪珥,2009年5月於南洲雪梨北石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