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袁世凱素描
袁世凱其實一身的矛盾:生就一副莊稼漢的面孔卻有「國之能人」的肚腸;人不足五尺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現代職業軍人」;倡言改革,卻一妻九妾,相信風水和宿命;一生為國事無數,卻留下「竊國」之名。(圖為當年荷蘭畫家胡博所繪袁世凱像)
袁世凱大事記(1859∼1893)
1859年
1876年
1878年
1879年
1881年
1882年
1883年
1885年
1891年
1893年
17歲
19歲
20歲
22歲
23歲
24歲
26歲
32歲
34歲 9月16日,袁世凱出生於河南省項城縣袁寨村。字慰庭(或慰亭、慰廷),別號容庵。
應考舉人落榜。10月,和陳州的于氏在家鄉結婚。
在陳州辦起了「麗澤山房」和「勿欺山房」兩個文社,同時捐「中書科中書」。
在陳州結識了來此地當塾師的天津孝廉徐世昌。
在上海的妓院結識了妓女沈氏。後去山東登州,投靠吳長慶門下,任幫辦文案。
袁隨吳長慶赴朝平亂,負責前敵營務處。10月,清廷賞以同知補用,並賞戴花翎。
為朝鮮王訓練新建親軍。
李鴻章奏派袁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大臣」,以知府分發,補缺後以道員升用,賞加三品銜。
嗣母牛氏病故,袁奉旨在家鄉服喪百天。
5月,補授袁為浙江溫處道員,仍然留在朝鮮署事。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絕版袁世凱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74 |
二手中文書 |
二手書 |
$ 77 |
Others |
二手書 |
$ 120 |
Others |
$ 221 |
社會人文 |
$ 221 |
人文歷史 |
$ 224 |
Books |
$ 252 |
軍事人物 |
$ 252 |
中國近代史 |
$ 252 |
社會人文 |
$ 252 |
歷史 |
$ 280 |
中國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絕版袁世凱
200 幅罕見歷史圖片‧60段百年前西方史料
親見親聞還原洹上村‧活靈活現細說袁世凱
【本書簡介】:
袁世凱究竟是怎樣的人?歷來眾說紛紜。袁世凱其實一身的矛盾:生就一副莊稼漢的面孔,却有「國之能人」的肚腸,人不足五尺却是中國近代第一個「職業軍人」,倡言改革却一妻九妾,相信風水和宿命,一生辦國事無數,却留下「竊國」之名。
比之國人的臉譜化,當年西人的報刊雜誌却對袁世凱有幾乎全然不同的描述和評價,且關注熱度經年不衰。光1900年至1916年的《紐約時報》就有超過500篇的時文涉及到袁世凱,讀來讓人有另一人之感。
《絕版袁世凱》之所以稱絕蓋出於三:
一曰「史料絕」。大量有關袁世凱的圖片史料包括口述回憶,或者來自於100年前西人報刊,或者由其親人,身邊人提供。其中不少為首次公開發表。
二曰「文風絕」。作者秉承《絕版李鴻章》的風格,以輕鬆詼諧的筆調講述一個「沉重的袁世凱」
三曰「親歷」。作者三下河南,造訪袁世凱出生地項城,最後歸宿地安陽,首次完整還原業已消失的「項城袁寨」和「安陽洹上村」並親繪了復原圖。
全書對袁世凱的刻劃描繪細節逼真,入木三分,令讀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作者簡介:
張社生,1984年在上海文廣集團任文藝編導,1994年獲美國紐約理工學院傳媒藝術系電影和電腦特技專業碩士學位,後在美國從事電視製作和電影獨立製片人工作。
2001年回國發展,多次和中央電視台合作,其作品在國內外多次獲獎。其參加執導的《森林之歌》獲得第24屆中國電視金鷹獎電視記錄片最佳編導獎。創作手法強調聲畫的作用,擅長在作品中設計跌宕起伏的奇特節奏效果。所著《絕版李鴻章》獲得2009年上海圖書獎。
章節試閱
第一章袁世凱素描 袁世凱其實一身的矛盾:生就一副莊稼漢的面孔卻有「國之能人」的肚腸;人不足五尺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現代職業軍人」;倡言改革,卻一妻九妾,相信風水和宿命;一生為國事無數,卻留下「竊國」之名。(圖為當年荷蘭畫家胡博所繪袁世凱像)袁世凱大事記(1859∼1893)1859年1876年1878年1879年1881年1882年1883年1885年1891年1893年17歲19歲20歲22歲23歲24歲26歲32歲34歲 9月16日,袁世凱出生於河南省項城縣袁寨村。字慰庭(或慰亭、慰廷),別號容庵。應考舉人落榜。10月,和陳州的于氏在家鄉結婚。在陳州辦起了「...
»看全部
作者序
前言
張社生
革命啦,運動啦!
每次來時都是轟轟烈烈,
每次都以十二級以上的破壞力橫掃千軍如捲席。
而且每次鼓吹者都向國人保證,這次將徹底開創一個全新的時代。
我們總是一次次相信,
一次次地湊熱鬧,
一次次地賠上老命。
誰叫我們這個民族就好一驚一乍的熱鬧。誰叫我們相信不需要長期努力,羅馬可以在一天之內建造成功的神話。
這不?突一日,有人登高一呼:革命啦!馬上漢口街頭風起雲湧。熱鬧過後,只是沒了辮子。月亮還是那個月亮,趙莊還是那個趙莊。
查「革命」二字,老祖...
張社生
革命啦,運動啦!
每次來時都是轟轟烈烈,
每次都以十二級以上的破壞力橫掃千軍如捲席。
而且每次鼓吹者都向國人保證,這次將徹底開創一個全新的時代。
我們總是一次次相信,
一次次地湊熱鬧,
一次次地賠上老命。
誰叫我們這個民族就好一驚一乍的熱鬧。誰叫我們相信不需要長期努力,羅馬可以在一天之內建造成功的神話。
這不?突一日,有人登高一呼:革命啦!馬上漢口街頭風起雲湧。熱鬧過後,只是沒了辮子。月亮還是那個月亮,趙莊還是那個趙莊。
查「革命」二字,老祖...
»看全部
目錄
絕版袁世凱
目錄
第一章 袁世凱素描
作為男人的袁世凱/017
袁世凱的女人緣/020
袁世凱的那雙眼睛/024
袁世凱體壯如牛/028
不明大勢卻能辦好差/032
「視黃金直如土塊」/038
辦事嘎嘣脆,什麼人都敢用/042
耐得罵 死豬不怕開水燙/044
從喜歡侃大山到謹言慎行/046
開會喜歡慷慨陳詞/049
和孫中山比袁世凱的演講差一個檔次/050
第二章 北洋袁世凱
小站練兵前的「買辦袁世凱」/058
軍人袁世凱/062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前世今緣/068
袁世凱手下的龍虎豹/071
山東巡撫任上,義和團發不了功/077
直...
目錄
第一章 袁世凱素描
作為男人的袁世凱/017
袁世凱的女人緣/020
袁世凱的那雙眼睛/024
袁世凱體壯如牛/028
不明大勢卻能辦好差/032
「視黃金直如土塊」/038
辦事嘎嘣脆,什麼人都敢用/042
耐得罵 死豬不怕開水燙/044
從喜歡侃大山到謹言慎行/046
開會喜歡慷慨陳詞/049
和孫中山比袁世凱的演講差一個檔次/050
第二章 北洋袁世凱
小站練兵前的「買辦袁世凱」/058
軍人袁世凱/062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前世今緣/068
袁世凱手下的龍虎豹/071
山東巡撫任上,義和團發不了功/077
直...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張社生
- 出版社: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05-10 ISBN/ISSN:978986645127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8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
圖書評論 - 評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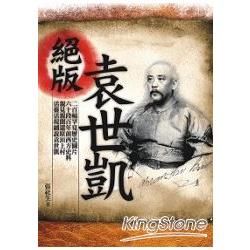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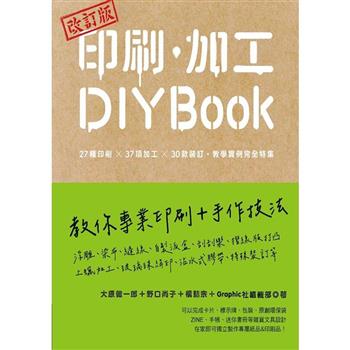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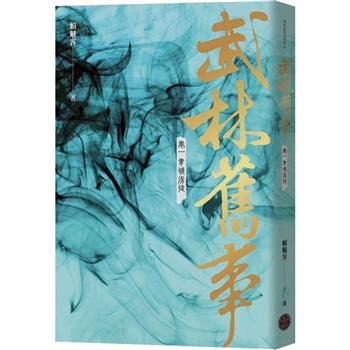








任何一個沒有被國民黨教育洗腦的頭腦都知道,袁世凱是中華民國的建立與退翻滿清政府的最關鍵人物,如果其晚年沒有恢復帝制而多幹幾年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話,中國歷史一定重寫,北洋軍政府的權力會更穩固,南方革命黨應該沒有機會壯大,蔣介石說不定只是歷史小龍套,而袁世凱的反日政策說不定會讓中日戰爭提早爆發,整個亞太情勢的發展或許\因此改觀…. 當然這些都是我個人臆測,絕非這本書的內容,袁世凱對於中國近代史的影響十分深遠,這亦是我多年以來喜歡涉獵的歷史人物,然而有關袁世凱的繁體中文的專書卻相當罕見,這本「絕版袁世凱」算是一本比較新的有關袁世凱的史料。 我承認讀完本書之後有點失望,失望的不是這本書寫得不好,而是本書作者剖析袁世凱的角度和面向不是我感到興趣,本書偏重於有關袁世凱的家庭婚姻子女,以及在清末民初時外國媒體筆下的袁世凱,與我感到興趣的面向不太一致,我對袁世凱有興趣的地方是他的北洋軍的運作和他對北洋軍的統御,因為中國當年的北洋軍其實也是後來國民政府軍隊的主要骨幹之一,蔣介石短暫的統治中國其實是和北洋軍系統的勢力妥協出來的。所以想要研究短命的中華民國史,我認為應該要從袁世凱以及其建立的北洋軍開始。 我對袁世凱感到興趣的是他與日本所簽定的二十一條條約,二十一條條約是中國甚至是亞洲歷史的關鍵,這條約曝露了中國的虛實,我對於二十一條條約相當好奇,如果當時沒有簽署的話,中日會提早十多年開戰嗎?袁世凱簽約時所遭到的壓力或狀況為何? 只是這本書並沒有對我感到興趣之處多加著墨,不過這本書倒是提供了許\多關於袁世凱和妻小家庭的照片,也寫了許\多袁式一族的家務事和後代子孫的故事,看了本書後方才知道原來一代開國梟雄、縱橫於滿漢兩族、歐美列強與革命黨之間的袁世凱,竟然身高不到150公分且長相十分老粗。 以及讓我震撼的是,當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在武昌起義成功\,雙十節黎元洪宣佈湖北獨立的當下,孫文當時竟然在美國丹佛一家唐人餐\館當「企台」(茶房)(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的論點)。 即便如此也不會損及所謂偉人形象,因為我從來不認為這世界上有偉人。任何一個沒有被國民黨教育洗腦的頭腦都知道,袁世凱是中華民國的建立與退翻滿清政府的最關鍵人物,如果其晚年沒有恢復帝制而多幹幾年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話,中國歷史一定重寫,北洋軍政府的權力會更穩固,南方革命黨應該沒有機會壯大,蔣介石說不定只是歷史小龍套,而袁世凱的反日政策說不定會讓中日戰爭提早爆發,整個亞太情勢的發展或許\因此改觀…. 當然這些都是我個人臆測,絕非這本書的內容,袁世凱對於中國近代史的影響十分深遠,這亦是我多年以來喜歡涉獵的歷史人物,然而有關袁世凱的繁體中文的專書卻相當罕見,這本「絕版袁世凱」算是一本比較新的有關袁世凱的史料。 我承認讀完本書之後有點失望,失望的不是這本書寫得不好,而是本書作者剖析袁世凱的角度和面向不是我感到興趣,本書偏重於有關袁世凱的家庭婚姻子女,以及在清末民初時外國媒體筆下的袁世凱,與我感到興趣的面向不太一致,我對袁世凱有興趣的地方是他的北洋軍的運作和他對北洋軍的統御,因為中國當年的北洋軍其實也是後來國民政府軍隊的主要骨幹之一,蔣介石短暫的統治中國其實是和北洋軍系統的勢力妥協出來的。所以想要研究短命的中華民國史,我認為應該要從袁世凱以及其建立的北洋軍開始。 我對袁世凱感到興趣的是他與日本所簽定的二十一條條約,二十一條條約是中國甚至是亞洲歷史的關鍵,這條約曝露了中國的虛實,我對於二十一條條約相當好奇,如果當時沒有簽署的話,中日會提早十多年開戰嗎?袁世凱簽約時所遭到的壓力或狀況為何? 只是這本書並沒有對我感到興趣之處多加著墨,不過這本書倒是提供了許\多關於袁世凱和妻小家庭的照片,也寫了許\多袁式一族的家務事和後代子孫的故事,看了本書後方才知道原來一代開國梟雄、縱橫於滿漢兩族、歐美列強與革命黨之間的袁世凱,竟然身高不到150公分且長相十分老粗。 以及讓我震撼的是,當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在武昌起義成功\,雙十節黎元洪宣佈湖北獨立的當下,孫文當時竟然在美國丹佛一家唐人餐\館當「企台」(茶房)(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的論點)。 即便如此也不會損及所謂偉人形象,因為我從來不認為這世界上有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