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出版社繼「明朝那些事兒」之後再度推出另一歷史巨著
全書七十五次劇情急轉.驚天秘密層層揭開
現代《論語》是拼貼版本?那真正《論語》去了哪裡?
探尋《論語》版本流傳真相,向中華文化的中樞神經開刀。
青年作家 冶文彪 為您解讀中華文化第一歷史懸案
故事梗概:
漢景帝末年,孔子舊宅牆壁中意外發現一部先秦古本《論語》,世稱《孔壁論語》。這部古書為當世孤本,又適逢漢武帝罷除百家獨尊儒術,卻秘藏宮中,從此失傳。後世流傳《論語》為漢代拼貼版本。
《孔壁論語》到底去了哪裡?其間究竟發生了什麼?
作者簡介
冶文彪
自由思想者,獨立創作人,著有作品多部。癡迷歷史,酷愛真相,痛恨不公,嚮往至善。才雖不濟,但務求字字源於體認,字字發自真心,每一部作品都能有所解構和獨創。力雖單弱,卻願盡一生之努力,保有求真悲憫之心,探求自我、民族和人類命運的來龍去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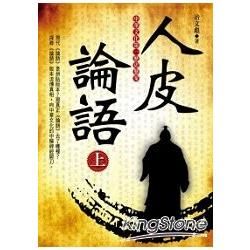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2025【精選作文範例】國文(作文)[快速上手+歷年試題](記帳士)](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0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