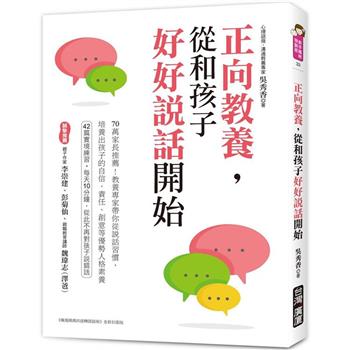【內文節選一】
人生好比一條「路」,人生的前途要有路,才能有所發展。我曾經把自己的一生,規劃為八個時期,以每十年為一期,第一個十年是「成長時期」,第二個十年為「閱讀時期」,第三個十年是「參學時期」,之後依序是「弘法時期」、「歷史時期」、「哲學時期」、「倫理時期」、「佛學時期」。
我從小就不是一個苦惱的小孩,由於家裡貧窮,出了母胎連母奶都不足飽腹,但是我天性容易滿足。對於童年往事,雖然現在已經不復記憶,只是偶而聽母親敘說,我經常把家裡僅有的一點食物,拿出來分享給其他小孩子吃;儘管家貧,也沒有多少東西可以分享給人,母親的話只不過說明,我從小就有喜捨的性格罷了。
我還依稀記得,三、四歲的時候就和外祖母學會念《般若心經》,也和七、八歲的姊姊比賽吃素,這一切大概都是受外婆的影響。我的童年,經常跟著外婆進出「道場」,其實當時我並不懂得什麼宗、什麼教、什麼神,只記得大都數的道場裡,都掛了「十殿閻羅」的圖。當時在小小的心靈上,就刻印了「人不能做壞事」的觀念!我雖然沒有進過正式的學堂讀過什麼書,但在童年時,就會背誦寺廟牆上所貼的《三世因果經》。
我從小就喜愛小動物,一群螞蟻圍困在路邊的水塘中,我會替牠們搭橋,讓牠們通過。幼小的昆蟲,我也細心把牠養大,再給予放生。我喜歡養小雞、小鴨,尤其喜愛養鴿子。記得有一次,為了一隻鴿子飛失了沒有回來,最初急得飯都吃不下,最後竟至投河自盡,所幸我深諳水性,自己又浮了上來。但是這一切,都被大人責怪,認為簡直是小孩子胡鬧。
我對於家中所養的小狗,每天只准餵食一餐,甚為不滿,總想:人可以吃三餐,為什麼狗子只能吃一餐呢?家人說:只有給牠吃晚餐,牠才肯看家守夜。我無法認同這種說法,經常在吃飯的時候,偷偷把碗盛滿了飯菜,再將狗引到僻遠的地方讓牠吃,我寧可自己少吃,也要替狗子加餐。
一隻殘缺的小雞,破殼而出還不到十天,有一次被雨水淋濕了羽毛,我怕小雞受寒,就把牠擺在爐灶的入口,想藉爐火幫牠把羽毛烤乾。那知小雞見了人,受到驚嚇就往爐子裡跑去。我一見大驚,趕快伸手把牠從爐火裡搶救出來,但是牠的羽毛已被燒光,一隻腳也燒掉了,甚至嘴巴因此缺了下喙。
被燒成這個樣子,照說小雞應該是必死無疑,但我想出種種方法照顧牠。起初餵食很麻煩,因為只剩上啄,不能啄食,所以三餐我都用杯子盛滿米穀餵牠。如此養了一年多,小雞不但沒有夭折,反而大到可以下蛋,儘管所下的蛋小如鴿蛋,但總是活了下來。這件事讓我感覺自己好像成就了一件大事業一樣,現在回想起來,這也是對生命的愛護,所以回憶起自己的童年,是有些許的仁慈性格。
記得是八、九歲的時候,因為家裡貧窮,看到父母為家庭日用艱難而辛苦,於是就有心想要幫忙。但是一個年幼的兒童,能有什麼辦法呢?想到狗子在路上屙屎,我每天早晨天濛濛亮就起床,然後到路上撿「狗屎」,把它推積在一起,幾天後也能賣給人家當肥料,而能賺得幾個銅板。
或者我也在下午時分,出門撿拾路上的牛糞,然後學習大人,把稻草剪碎,將牛糞及稻草用水和在一起,貼在牆上晒乾後,一塊牛糞幾角錢賣給人當木炭燒,如此也能賺錢。
後來「七七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開始,我的家鄉揚州江都被戰火摧毀,燒得只剩瓦礫一片,到處都有鐵釘,以及各種器皿損壞後的破銅爛鐵。我把這些撿起來賣,雖然不值錢,但當時小小年紀,也覺得為數可觀。甚至在桃李銀杏出產季節,鄉人吃過桃子、李子、杏子,裡面的核到處亂丟,我也滿街滿巷的撿拾,累積起來也可以賣點小錢。
過去自己一直覺得很難為情,不敢把這些事告訴別人;現在環保意識抬頭,我覺得自己童年所做,不但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也是對環保的實踐。同時也增強自己的信念,不論什麼人,只要對公益有所幫助,我覺得都非常有意義。
我在出家前的一、二年中,斷斷續續也讀過幾年「私塾」。所謂「斷斷續續」,原因是我們每天讀書要繳四個銅板,有錢的時候就帶著四個銅板去讀書,如果沒有錢,今天就主動為自己放假。斷斷續續當中,也不知道自己能認得幾個字,直到十二歲那年,我在師父志開上人的座下剃度出家。最初在南京棲霞律學院讀書,全班約有學生五十人,他們的年齡都比我大許多,大部份在二十歲以上,只有我還在幼童之齡。對於《成唯識論》、《因明學》、《般若經》等經論,都如鴨子聽雷,老師的語言,對我而言,只有聲音,完全不知道講的是何意義。
所幸在私塾裡認得幾個字,這時總算能夠派上用場,我經常到棲霞佛學院的圖書館,借幾本文學書籍來閱讀。我記得自己所看的第一本小說,就是《精忠岳傳》,後來又接觸《七俠五義》、《小五義》、《封神榜》、《儒林外史》、《水滸傳》、《三國演義》等,經常看得入迷,甚至真是看到廢寢忘食。之後又閱讀不少西洋文學,先後看過《莎士比亞全集》、印度泰戈爾的詩集、《戰爭與和平》,以及《基度山恩仇記》、《茶花女》、《老人與海》、《少年維特的煩惱》、《浮士德》等等。
那個時候,我愛看小說,終於慢慢被老師發現了,成為黑名單的學生。老師認為,一個不用功閱讀經論,只是沉迷於小說的學生,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罷了!但是不管別人怎麼樣嘲笑、歧視,我對東西方的小說、文學作品、歷史傳記,還是讀得津津有味,樂此不疲。因為經論看不懂,只有閱讀這些世間著作,能夠增添我的知識見聞。
我在棲霞律學院讀書的六、七年當中,可以說都是被人歧視、打壓。例如,有一次國文課中,老師出了一道作文題目,叫做「以菩提無法直顯般若論」。在那種年齡,對於什麼叫做「菩提」,什麼叫做「般若」,我都搞不清楚,又如何論議?如何能暢所欲言呢?結果老師給我的批語:「兩隻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我當時一看,還洋洋得意,以為老師寫了詩句給我,後來經過別人說明,才知道老師是在嘲笑我。所謂「兩隻黃鸝鳴翠柳」,牠在叫什麼你知道嗎?「一行白鷺上青天」,你又了解了什麼呢?所以總說老師的意思,就是說我的文章「不知所云」!
又有一次,作文題目是「故鄉」。這種淺顯易懂的題目,又是跟自己切身有關,加上我讀過一些文學小說,懂得怎麼樣形容故鄉,所以就寫道:「我的故鄉有彎彎曲曲的小河,河流上有小橋,兩岸翠綠的楊柳低垂,每當黃昏落日餘暉下,農舍的屋頂炊煙裊裊昇起……。」老師又替我批語:「如人數他寶,自無半毫分。」這一看就很明白,老師認為這篇文章是我抄襲而來,不是自己所作。
寫得好,是抄襲而來;寫得不好,是不知所云。幸好我的性格善於轉化,沒有輕易被摧殘、打倒,所以後來我一直主張,對青年學子要用愛的教育,要鼓勵他上進。所謂「良言一句三冬暖」,老師的一句話,一點鼓勵,是金錢買不到的,可是對一個青年學子而言,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是多麼需要師長大人的鼓勵哦。
國共戰爭之後,時局動盪,我率領青年同道,以參加僧侶救護隊的名義渡海來台。初到台灣,人地生疏,用「走投無路」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即使窮途潦倒,我仍然堅守自己對佛教的信念,保全一件僧衣。後來輾轉在宜蘭駐錫,最初成立念佛會、歌詠隊、學生會、文藝寫作班,之後創辦幼稚園,也成立幼教師資訓練班。我把宜蘭市四十八個村里,用佛教的義理,組成光明班、菩提班、清淨班、慈悲班……等四十八班,每班選出一個班長,有系統、有組織的弘揚佛法。
我在忙碌之餘還能抽空撰寫文章,我的《玉琳國師》、《釋迦牟尼佛傳》、《十大弟子傳》、《佛教童話集》、《佛教故事大全》,就是在宜蘭十年的初期完成的。《釋迦牟尼佛傳》和《十大弟子傳》,我都是用文學的筆調撰寫,尤其《釋迦牟尼佛傳》,曾由監察委員游娟女士編成連續劇,在台視八點擋播出;也曾拍成電影,在金國戲院上映。《玉琳國師》更加發揮威力,曾被空軍廣播電台列為小說選播,也拍成電影,尤其勾峰先生二度編成電視劇「再世情緣」,在電視台連續播出一個多月。
我在這個時候,鼓勵慈莊、慈惠、慈容等人,在台北三重開設「佛教文化服務處」,除為佛教界做一些文化服務以外,也出版通俗化、大眾化的佛教著作,如佛教的小說選集,如唱片的發行等。我自己也在全省各地巡迴講演之餘,努力撰寫文藝作品,尤其作了許多佛教歌曲,透過雷音寺歌詠隊隊員的演唱,甚至編成舞台劇,在台灣各地表演,一時造成轟動,但也引起傳統佛教人士對我的不滿,認為我荒腔走板,怎麼佛教還唱起歌來,真是大逆不道,這不是要滅亡佛教嗎?
但是佛教並沒有因為唱歌而給唱完了,反而接引了一批批優秀的青年進入佛教,對於帶動佛教的年輕化、知識化,發揮很大的功能。
我在宜蘭弘法十多年後,一九六四年時年三十八歲,先在高雄創辦壽山佛學院,接著購買了大樹鄉麻竹園五十多公頃的土地,就此開創佛光山,想為佛教創造歷史,開創另一個佛教的新局面。
儘管我一生都很努力在為佛教推展文教事業,但是在佛光山開山期中,佛教界的一些領導人放話,揚言要打倒佛光山叢林學院,不准我興辦教育。其實,天主教、基督教在台灣創辦了東海、輔仁、東吳等多所大學,佛教界也沒有人要打倒他們,為什麼我為佛教所辦的一所小小佛學院,就要打倒他呢?
佛光山開山數年之後,由於各種因緣推動,我分別在高雄、彰化、台北設立分院,雖然來自教界與政治的阻力不少,但我順應時勢的需要,不但沒有被打壓、阻礙,反而以創造歷史的精神,後來陸續到美國創建西來寺、中美寺,到澳洲創建中天寺、南天寺,到歐洲創建巴黎道場、荷華寺,到非洲創建南華寺,到馬來西亞創建東禪寺等。後來又成立國際佛光會,在五大洲成立一百多個協、分會,真是「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了。
【內文節選二】
苦行,是指佛教修行人所過的一種刻苦自勵的修持生活,是出家人應有的修行過程,也是僧侶應有的密行。我在「苦行」的生活中,能夠感覺到生命活得很踏實、很快樂,在自己後來的人生歲月中,一直以此感到自豪。
回憶起十五歲那年,我在棲霞山接受佛教的比丘三壇大戒,記得第一天報到時,戒師問我:
「你來受戒,是師父叫你來的?還是你自己發心要來?」
「弟子自己發心來的!」我這麼回答。
那知說過以後,戒師拿了一把楊柳枝,在我頭上猛打一陣,我頓時眼冒金星,感到很錯愕:我有什麼錯嗎?這時只聽得戒師慢條斯理的說:
「你很大膽,師父沒有叫你來,你沒有得到師父的允許,自己就敢來受戒。」聽了這話,覺得「說的也是」,心裡平服不少。
第一位戒師問過以後,走到第二位戒師面前(戒師就等於現在的口試官一樣),結果他問了同樣的問題:「你來受戒,是師父叫你來的?還是你自己要來?」
剛才被打過,懂得應該要「尊師重道」,因此趕快說:「是師父命令我來的!」那知話才說完,戒師又拿起一把楊柳枝,在我頭上猛打,一邊打一邊說:「豈有此理,假如師父沒有叫你來,你連受戒都不要了!」
想想也對,說的不無道理。這時他叫我再到第三位戒師那裡,問題還是一樣:「你來受戒,是師父叫你來的?還是你自己要來?」
前面被打過兩次,有了經驗,就回答:「戒師慈悲,弟子來此受戒,是師父叫我來,我自己也發心要來。」
自覺這種回答應該天衣無縫,合情合理。那知戒師仍然拿起楊柳枝,一陣抽打後責怪說:「你說話模稜兩可,真是滑頭。」
到了第四位戒師那裡,問話改變了,他問:「你殺生過沒有?」
殺生是嚴重的犯戒,我既然來受戒,怎麼可以說有殺生呢?因此毫不考慮的說:「我沒有殺生!」
那知戒師即刻反問:「你平時沒有踩死過一隻螞蟻,沒有打死過一隻蚊子嗎?你打妄語,明顯是在說謊嘛!」說過以後,楊柳枝再度狠狠的打在身上。
又再換另一個戒師,他一樣問:「你殺生過沒有?」因為剛才打過,只有直下承認:「弟子殺過!」
「你怎麼能殺生呢,真是罪過!罪過!」每說一句罪過,都要打上好幾下楊柳枝。下面再有戒師,他還沒有開口,我就把頭伸出去,說:「老師,你要打就打吧!」
所謂「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這種「以無理對有理、以無情對有情」的教育,就是要把你「打得念頭死」,然後才能「許汝法身活」。當初我心中雖有不服,但後來確實感覺到,這樣的訓練,讓一個人在無理之前都能委屈服從,將來在真理之前,還能不低頭接受嗎?
無情打罵的教育以外,在五十三天的戒期當中,每次聽戒師講話,都得跪在地上,經常一跪就是幾個小時,等到起來時,地上的碎石子都嵌在皮肉裡,雖然隔了兩層的海青、袈裟和衣褲,但是鮮血還是從褲子裡滲透出來。這讓我想起在一個漫畫故事裡,講到孫悟空的修行,需要一千天的時間才能成就,他能大鬧天宮,神通廣大,也是苦練出來的,我想自己只不過才五十三天,有什麼不能忍耐的呢?
不過,皮肉之苦其實還比較容易忍耐,更大的考驗是,受戒時我才十五歲,正是精力充沛,好奇心強烈的時候,對於身旁的事事物物,難免好奇的想要看一眼,但是每次只要被戒場的引禮師父看到了,楊柳枝馬上就狠狠的打在身上,並且大聲罵道:「眼睛東瞟西看的,這裡有那一樣東西是你的?」有時候聽到一些風吹草動的聲音,也會興致勃勃的聆聽,結果又是招來一陣責打與呵斥:「把耳朵收起來!小孩子聽一些閒話做什麼?」
確實,沒什麼東西是我的!因此我閉目不看、收耳不聽。在五十三天的戒期中,我生活在漆黑、無聲的世界裡,但是雖然如此,我的心中卻燃起了一盞明燈,我發現世界上的一切,原來都在我們自己的心中。於是我學會了不看外而看內,不看有而看無,不看妄而看真,不看他而看己。到了現在,我走夜路,上下樓梯,即使不用眼睛看,也能無礙自如。甚至我常覺得:用心眼去感受世間事,比用肉眼去觀察還要來得如實真切。
十八歲時,我升學上了焦山佛學院,因為是新生,立刻被分配到大寮典座,也就是負責三餐煮飯燒菜的職務。我擔任二年的典座,除了撿菜、洗菜,也學會烹調的方法。至今我對菜餚的煮法,烹調的技藝,雖不能稱為一流,但自覺有些心得。
在焦山佛學院期間,因為年輕,什麼事情都覺得應該當仁不讓,勇於維護正義;但也因為心直口快,經常惹來麻煩,因此自覺應該有「禁語」的必要。剛開始自己很不習慣,不知不覺就會脫口而出,明明知道不能說話,偏偏忘記而說溜了嘴。為了處罰自己,我經常獨自跑到大雄寶殿後面,人跡罕至的海島,摑打自己的耳光,並且自我責罵:「你真是豈有此理,自己歡喜持禁語,又沒有人勉強你,卻出爾反爾,不能持好。」
為了根除自己的習性,務必要給自己刻骨銘心的教訓,因此我重重地處罰自己,有時打得嘴角都滲出鮮血。就這樣實踐了一年的「禁語」,這一年不講話的經驗,對於青年時代初學佛法的我,在學習過程中,有很深的意義。因為我體會到,「禁語」不止口中無聲,更重要的是心中無聲。有時我們受了一點委屈,表面上雖然若無其事,但是內心的不平、怨憤,卻如澎湃的浪濤一樣,發出巨大的響聲,如果我們能夠止息內心煩惱的聲音,那就是寧靜無聲的證悟世界了。
總說我出家時雖然年齡很小,也沒有很好的環境學習,儘管生活艱苦,但我在佛門裡的學習,從「禪宗」的金山到天寧,「律宗」的古林律寺到寶華戒堂,「教下」的棲霞到焦山,我都曾經參學過。在參學的十年當中,因為遊走在許多叢林之間,所以也就懂得律宗、淨土宗、禪宗,甚至密宗等四大宗派的修行。可以說,我童年在佛門接受的叢林教育,用現在的話來說,等於一個軍官,陸、海、空三軍都受訓過,資歷完整。這是當時小小年紀的我,除了為常住勞動服務外,自己參學得來的經歷。
一九五三年我到宜蘭之後,在雷音寺前後二十六年,每年都要主持一次佛七,從早上五點第一支香開始,一直到晚上圓滿,從來沒有缺席過一支香。那時雷音寺雖小,但座落在中山路的市中心,每次佛七,在家信眾參加踴躍,遲到的人往往進不了門。尤其每年一次的佛七,宜蘭人簡直把它當成過年一樣,平時在外地工作的人,都會特地回鄉參加,大家念佛念得法喜充滿,當然我也非常認真。每到佛七,我就在紅綠招貼紙上,用毛筆寫一些念佛標語,把整個佛殿布置得煥然一新,每次總要寫上二天,才夠貼滿佛堂。
我一生沒有練過書法,如果說我能寫毛筆字,就是在這二十六年的佛七當中,我不但念佛,也讓我有機會寫字和信徒結緣。
其實,在各種修持當中,我自己受益最大的,應該是「拜佛」。雖然近年來因為腿部開刀,不能跪拜。但是在過去,我每天早晚都要各拜佛半個小時,雖然時間不長,但每天持之以恆,盡量不讓它間斷。尤其早在我十五歲那年,因為受戒時燒戒疤,把頭蓋骨給燒得陷了下去,之後我忽然好像失去記憶的能力,讀《古文觀止》、《四書讀本》,怎麼念就是背不起來,並不是我不用功,而是任我怎麼努力念誦,就是沒有記憶力。
因為無法背書,被教我的覺民法師罰跪、打手心,這是常有的事。有一天,我又再次為了不會背書而挨打,教務主任覺民法師一面打,一面罵:「你真笨喔!你要多拜觀世音菩薩,祈求聰明智慧哦!」真奇怪,那個時候不管老師怎麼打手心,我竟然一點痛的感覺都沒有,只覺心中好像忽然亮起了一盞明燈:「哦,原來拜觀音世菩薩就可以有聰明智慧,我有希望了!我有希望了!」
生來雖然不是很聰明,但也不是很笨的我,自從受戒失去記憶力以後,感覺人生好像從此沒有了未來。現在忽然聽到拜觀世音菩薩,可以有聰明智慧,一下子又燃起了我的希望。只是當時在叢林古寺裡,想要拜觀世音菩薩,也沒有地方可以拜。因為大雄寶殿除了早晚課的時間以外,不能隨便進入,其他的殿堂也都各有堂主。我在學院裡,除了一間共用的小禮堂以外,又能到那裡去拜觀音菩蕯呢?
所以,之後每到夜深人靜,我就偷偷起來到禮堂去,一個人面對觀世音菩薩,首先稱念:「悉發菩提心,蓮花遍地生,弟子心矇矓,禮拜觀世音。求聰明,拜智慧,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稱念之後就拜下去,大概留停半分鐘,自己垂淚感動的念「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就這樣,我一邊念,一邊拜,拜了一拜又一拜。
禮拜觀世音菩薩的靈感很多,聽說有人拜到後來,蒙觀世音菩薩甘露灌頂,或是摩頂授記。但是很慚愧,這些我都沒有。不過,時間過了三、四個月之後,奇異的現象發生了,從此之後我的記憶力忽然好了起來,而且是出奇的好。過去念書,一篇《古文觀止》念了二、三十次,還是無法背誦,現在只要兩三次就會背了。甚至《戰國策》、《史記》上的短論,未經老師教授,自己看一遍就能記得。至今時隔六十餘年,這些文章在我口邊,還是能夠朗朗上口。
坦白說,我一生經歷的各種苦行修行,雖然都能接受,但並不是太喜歡,可是閱讀小說,我真是興味盎然,樂趣無窮。那個時候,舉凡《三國演義》、《水滸傳》、《七俠五義》、《小五義》、《封神榜》、《蕩寇志》等,幾乎看過一遍就能記憶。有時我也信手拈來,順口說上一段《水滸傳》,由於我對梁山泊上一百零八條好漢的名字、綽號、身穿的衣服、手拿的武器,都能如數家珍,一一道來。弟子們對我在年輕時看過的書,至今還記憶這麼深刻,都表佩服不已。
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事,不得不感謝觀世音菩薩跟我的因緣。一直到現在,我對於一些年輕徒眾的修行,總認為他們應該要從拜佛下手。因為禮拜可以莊嚴身心,可以折服我慢、增加謙虛,可以跟佛陀傾吐心事。拜佛時,人雖拜下去了,心裡的情感卻昇華而與佛相應。所謂「鼓聲有打則響,鐘聲有扣則鳴」;人有誠心禮拜,佛怎麼會不垂慈感應呢?
說到苦行,我一生最感激的,應該就是很多的人事讓我有機會修持「忍辱波羅蜜」了。我從小出家,就受到前輩的歧視,因為我沒有經過小寺院的基礎養成,一下子就進入大叢林裡參學,當然陋習、缺點很多,所以學長經常取笑我,例如說我走路不威儀,叫我走來走去訓練走路,有時一走就是幾個小時,他們以教我為樂。
三餐吃飯時,雖然只是一個小職事,都可以叫我站在身旁,為他添飯、夾菜,我的師兄就是其中一個。他們吃飯時,還不忘揶揄嘲笑我,一個說「星雲是沒有出息的!」一個搭腔說:「哎呀,不可以小看他,他也會像某某人那樣聰明!」我師兄則說:「他如果能像某某人那樣聰明,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
我是被人看輕到如此的地步,但是我一點也不洩氣,因為一個人有沒有出息,豈是現在就可以看得出來的?還有十年、二十年以後呢!不過這倒是讓我聯想到,外面的一些境界,就像打棒球,壞球來了,不要接,就不會被三振出局,根本也不需要什麼忍耐。
我一生沒有學過建築,但我會建房子;我沒有學過書法,但會寫毛筆字;我沒有學過文學,但會寫文章;我沒有受過駢文、韻文的寫作訓練,但會作詞寫歌。因此,承蒙有些人誇讚我很聰明。如果我真的有一點聰明的話,我想都是從「為人服務」的苦行中修來的。
所以,跟我一路走來的佛光山千餘名弟子,我希望大家知道,修行不是片面的個人解脫,而是全方位的弘法與利生;生活的苦行也不是一時的功課,而是一生的修持。能夠懂得「苦行」的意義,那才是「行佛」的宗要。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