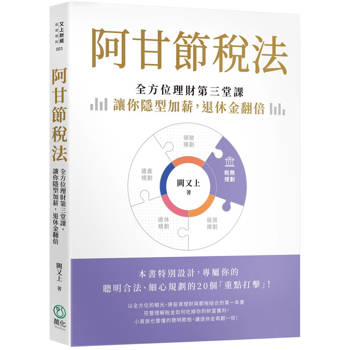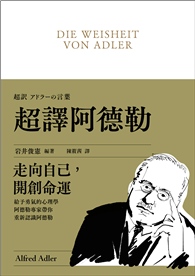常常聽到這樣的說法,每十人就有一人曾為憂鬱症所苦。極度厭煩與憂鬱症有何不同?我想兩者一定有許多相同之處。我也認為每個人幾乎一定曾經感到厭煩。厭煩不只是內在心境,也是外在世界的特質,因為我們所參與的社會活動本身就浸淫在厭煩之中。我們閒得發慌,終日厭煩,直到死亡才得以解脫。因此,我們不得不同意拜倫的說法:「除了感到厭煩與使人厭煩,什麼都沒有。」
齊克果說「厭煩是一切邪惡的根源」,這種說法雖然有點誇張,但厭煩確實造就了絕大多數的邪惡,包括殺人與戰爭。實際上,有些戰爭的爆發往往伴隨著毫不掩飾的喜悅,幸福洋溢的群眾湧上街頭,彷彿慶祝單調的生活終於被打破。然而,戰爭的問題不只在於它的戕害人命,更在於它很快就讓人感到厭煩;龐德說:「無趣的戰爭,無聊的百年戰爭。」不過,社會學家尼斯貝認為厭煩同時也遏止了一些邪惡,原因很簡單,這些邪惡漸漸也變得太令人厭煩了。他以焚燒女巫為例,認為火刑的消失不是基於法律、道德或宗教理由,純粹只是因為它變得太無聊:「只要看過一次火刑,就會覺得火刑不過如此。」
大學裡並未提供有關厭煩的課程,但學生在學習時倒是經常感到厭煩。過去厭煩曾是相關的哲學課題,如今顯然不是如此。在當代哲學中,幾乎所有主題都圍繞著知識論而發展,厭煩似乎因此成了哲學學科框架外的現象。時至今日,如果厭煩仍不被視為是相關的哲學課題,或許我們就有對哲學現狀感到憂慮的好理由。將自己與生命意義的問題切割開來的哲學,幾乎不值得人們投入其中。
根據維根斯坦的說法,哲學問題的形式如下:「我不知道自己要往何處去。」哲學問題的特點在於迷失方向——這不就是一種典型的深刻厭煩嗎?人們無法找到自己在這個世界的方位,因為他們已經喪失了與世界的關係。當我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或被迫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時,往往感到厭煩。然而,要是我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或沒有能力找出生命的意義時,又該如何?此時,我們會發現自己陷於喪失意志力的深刻厭煩中,因為意志無法牢牢抓住任何事物。佩索亞如此描述這種狀況:「受苦,卻感受不到痛苦;想得到某種事物,卻缺少欲望;想要思考,卻欠缺理智。」我們將從海德格對厭煩所做的現象學分析中見到,這種經驗將成為通往哲學的門徑。
目前並無完整可靠的研究指出,有多少比例的人口感到厭煩,但娛樂產業與酒類消費的規模不正好清楚顯示出厭煩的盛行嗎?一天看四小時電視的人不一定感到或坦承厭煩,但他們為什麼把四分之一的清醒時間花在看電視上?要不是為了消除過剩或不悅的時間,否則人們幾乎沒有理由每晚花幾個小時看電視。我們幾乎完全沒有停機的時候,我們慌張地從一個活動奔馳到下一個活動,因為我們無法處理「空虛的」時間。弔詭的是,一旦我們事後回溯這段緊鑼密鼓的時間,往往感到一股懾人的空虛。厭煩連結著「消磨時間」的方式,時間因此不是即將到來的機會,而是必須消磨殆盡的事物。或者如高達美所說:「消磨時間的時候,真正消磨掉的是什麼呢?難道不是消磨掉的時間嗎?其實我們指的不是空虛而持續的時間,而是持續得太久且具有痛苦的厭煩形式的某種事物。」
「厭煩」常用來表示不同處境下的情緒障礙與意義缺乏。文學中許多對厭煩的描述均極為類似,主要都在於表示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引起興趣,還有抱怨隨之而來的了無生趣。齊克果說道:「厭煩如此可怕──可怕地令人厭煩;我找不到更強烈的措詞、更真實的表達,因為唯有相似之物才能形容相似之物。……我全身伸展地躺臥著,動也不動,眼前看到的只是空虛;我賴以維生的唯一事物是空虛;和我生活的唯一事物是空虛。我甚至體驗不到痛苦。」
厭煩也可以當作各種事情的藉口。布希納在《倫茨》中說道:「絕大多數的人純粹是因為厭煩而找樂子,有些人因為厭煩而墜入愛河,有些人因此德行高尚,但也有些人因此無法無天。至於我,一切對我來說全無意義──我甚至連自己的命都不想要,活著實在太令人厭煩。」無獨有偶,斯湯達爾在《論愛情》中寫道:「厭煩從人們身上奪走一切,甚至連自殺的欲望也一併帶走。」對佩索亞來說,厭煩是非常極端的事物,即便自殺也無法克服厭煩,唯一的解決之道實際上完全不可行——人最好從一開始就不要存在。厭煩被用來作為行動與完全無行動能力的解釋。厭煩是絕大多數人類行動的基礎,不管這些行動是積極的或消極的。羅素說:「我相信,厭煩是歷史紀元中最大的一股動力,時至今日,它的力量仍有增無減。」
大多數的厭煩源自於重複。例如,當我同一場演說聽了四次,我感到厭煩;當我同一節授課內容講了四次,我感到厭煩。厭煩的樣態很多。我們會對事物或人感到厭煩,我們會對自己感到厭煩。但另外還有不具名的厭煩形式,亦即沒有任何特定的事物令我們厭煩。德勒曼區別了四種厭煩的類型:「處境的厭煩」,如等人、聽演講或搭火車;「厭膩的厭煩」,如得到太多相同的東西,而所有事物看來都很無趣;「存在的厭煩」,即靈魂缺乏內容,而世界也毫無特別之處;「創造的厭煩」,其特徵表現在其結果而非內容:人們被迫去做創新的事。本書主要討論的,是「存在的厭煩」。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最近比較煩:一個哲學思考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6 |
二手中文書 |
$ 190 |
哲學 |
$ 204 |
英美哲學 |
$ 211 |
中文書 |
$ 211 |
心理學理論 |
$ 216 |
社會人文 |
$ 357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最近比較煩:一個哲學思考
「世上只有一件真正可怕的事,那就是厭煩。它是沒有任何赦免可能的罪。」——王爾德
叔本華說它是「沒有特定目標的沉悶渴望」,杜斯妥也夫斯基稱它是「殘忍而無可名狀的痛苦」,布羅茨基則叫它是「時間對你的世界系統的消蝕」,然而,我們卻依然很難準確說出「厭煩」究竟是什麼。《最近比較煩:一個哲學思考》探究了「厭煩」這個當代最為執迷的主題之一——厭煩的性質、厭煩的起源、我們如何及為何受它感染,以及我們為何無法靠任何意志行動來克服它。
史文德森結合哲學、文學、心理學、神學與流行文化對厭煩的觀察。他探究了厭煩的中古世紀前身、從帕斯卡到尼采對厭煩的哲學思索,以及從貝克特到沃荷的二十世紀藝術家的異化與逾越。
章節試閱
常常聽到這樣的說法,每十人就有一人曾為憂鬱症所苦。極度厭煩與憂鬱症有何不同?我想兩者一定有許多相同之處。我也認為每個人幾乎一定曾經感到厭煩。厭煩不只是內在心境,也是外在世界的特質,因為我們所參與的社會活動本身就浸淫在厭煩之中。我們閒得發慌,終日厭煩,直到死亡才得以解脫。因此,我們不得不同意拜倫的說法:「除了感到厭煩與使人厭煩,什麼都沒有。」齊克果說「厭煩是一切邪惡的根源」,這種說法雖然有點誇張,但厭煩確實造就了絕大多數的邪惡,包括殺人與戰爭。實際上,有些戰爭的爆發往往伴隨著毫不掩飾的喜悅,幸福洋...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拉斯.史文德森
- 出版社: 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09-02-05 ISBN/ISSN:9789866472138
-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240頁
- 類別: 中文書> 心理勵志> 心理學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