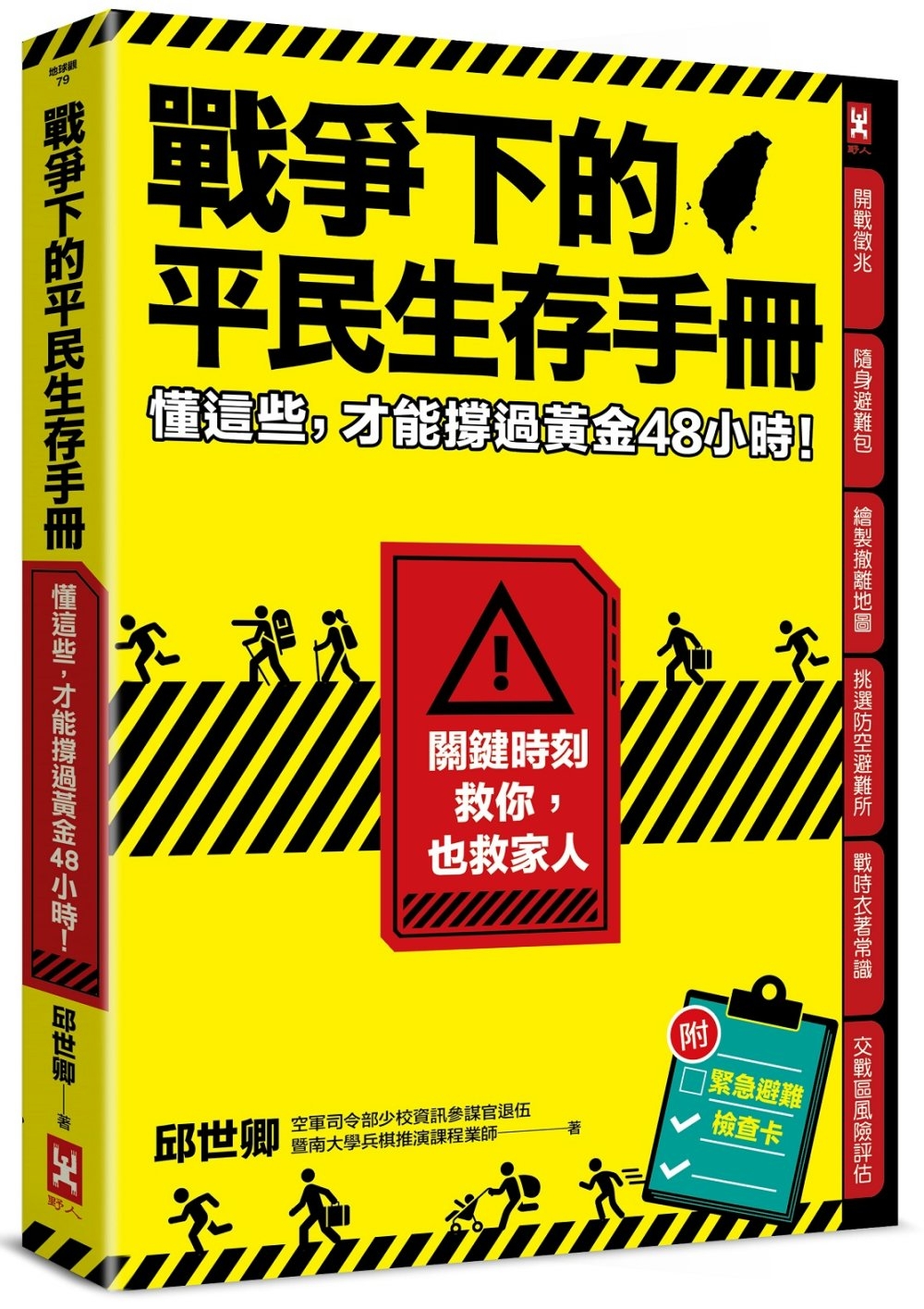專文推薦
愛與幸福的追求──《生命的意義是爵士樂團》評介
張炳陽
「生命的意義」是個既迷人但又令人困惑的問題,古往今來的智者、聖人、哲學家貢獻不少他們的智慧,就連文學家、藝術家往往也在他們的作品裡傳達出他們對生命意義的思考。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曾說,人是一種會發問「為什麼是存有而非空無」的特殊存有者,他稱人為「在此存有」。海德格的這種論述顯然只有少數學院哲學家才聽得懂他在說什麼。但是,如果說人是尋求「生命的意義」的存有者,可能連哲學門外漢都可以了然於心。伊格頓(Terry Eagleton, 1943- )是英國當代著名的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這本《生命的意義是爵士樂團》(The Meaning of Life)並無成一家之言的企圖,因此只在一般哲學史的知識上論述而沒提出自己獨特的觀點,有的話只是作者的分析和闡述能力,尤其是扣緊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差異特質來論述生命的意義。本書沒有一般哲學書的晦澀難懂,作者很明顯也沒打算將本書寫成嚴格的哲學書。本書從第一章到第四章有很清楚的邏輯性鋪陳,前後環環相扣、層層剖析,可說是一氣呵成,最後將生命的意義歸結為「愛與幸福」的追求。
伊格頓曾獲劍橋三一學院的文學碩士、哲學博士,他曾擔任過牛津大學英國文學教授(1992-2001),也擔任曼徹斯特大學英國文學教授至二○○八年,並在該大學退休,二○○八年十月起被聘任為蘭卡斯特大學英文與創作學系英國文學講座教授。在劍橋讀書時,伊格頓是左翼文學批評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學生,他研究十九和二十世紀的文學,後來主要研究七○年代學院馬克思主義,他的《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 1983)一書,是獻給威廉斯的。在一九六○年代期間,伊格頓曾加入左翼的天主教團體斯朗特(Slant)(*),寫了一些神學文章和《朝向新左派神學》(Towards a New Left Theology)一書,他對神學和心理分析理論特別有興趣。近年來他又回到劍橋大學時期,致力於傳統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再整合。
伊格頓在第一章〈問題與答案〉首先提出生命意義這個問題可能是有答案的,但我們可能永遠不知道這個答案是什麼。有問題,並不一定會有答案。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對生命意義的追求過程,就是生命的意義,可是不一定能找到最後的答案。這倒是很接近「哲學」(philo-sophia)的字源含意,哲學就是對智慧或知識的愛,這裡的愛就是親近和追尋,「哲學」的重點在作為活動本身,而非活動的結果。我們都希望問題有答案,可是偏偏有些問題是找不到解答的,像等待救贖的悲劇和一些道德問題是往往找不到答案的。
對自由主義者或後現代主義者來說,重要的不是生命意義的問題有沒有確定的答案,而是這個問題有那麼多奇特方式可以回答。對這些人而言,重要的是對話本身宜人的喧囂,他們認為這可能是我們所能發掘的最有意義的事了。換言之,生命的意義存在於對生命的意義的追尋,這是希臘的愛智精神。就此而言,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倒是與他們精神相通,自由主義者喜歡問題甚於答案,問題是自由的,答案則是受限的。
伊格頓認為,人思想的抽象性必須憑藉語言,語言讓我們可以認識自己,我們依靠符號而獲得抽象的能力,但是語言的抽象能力跟火一樣,同時具有創造性與毀滅性。我們這個時代出現了許多「偽導師」、「偽智者」誤導我們,哲學家往往淪落為「語言技工」,追逐語言而不知返,迷失在語言的叢林之中,綑綁在語言的網羅之內。哲學家似乎無法作為生命意義的嚮導,因此人生命意義沒有清楚的解答。伊格頓認為,後現代主義是有信念,但沒有信仰。後現代主義是一種世俗化的信念,它們貶抑一切深層的、整體性的、人性的、人生命等這些崇高課題。
另一種哲學家認為,生命可能有好幾個意義,它也可能具有很多不同的內在意義。如果我們的生命有意義,這個意義就是我們所賦予的,而不是與生俱來的。這似乎是存在主義的看法,也就是說,生命的意義是由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我們生命的意義不來自於自己之外,我們是自己成品的塑造者。伊格頓認為這種看法很接近真理,但仍然不夠充分。
在第二章〈意義的問題〉中,伊格頓認為「意義」這個詞的使用方式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有關人的意向或意圖;第二類是與指稱有關;第三類則將前兩類統合起來,也就是指那個「意圖指稱某事」的行動。藉由「意義」的這些不同的意義,對於「生命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問題就可以有不同的思考。
例如,當我們說「我的人生真是毫無意義」時,是指人生缺乏「重要性」(significance),意即缺乏重點、主旨、目的、品質、價值與方向等等。人們說這話的意思不是指他們不了解生命,而是不知為何而活。人活著的終極目標終不能不面對死亡,死亡剝奪了人的一切成就和存在,死神是最後的掌權者。但是如果人是不死的,人生命能有意義嗎?死亡是生命的終結,又是生命意義的賦予。人有一死,這本身帶給生命極大的悲愴性和悲劇性,生命的這種荒謬性由此突顯出來。像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這類哲學家或某些存在主義作家對生命的這種荒謬性極盡嘲諷之能事,生命雖任憑你濃妝艷抹,到最後仍然是一場虛空。「生命像華而不實的修辭,忙著用浮華炫麗的事物填滿空虛,而它本身就是那個空虛。」
伊格頓認為這裡至少有兩個「無意義」的概念在運作。一個是存在性的,但是人的存在卻是一齣空虛或空洞的荒謬劇。雖然有很多意義,但它們都是自欺欺人的華麗外觀而已。另一個我們可以稱之為語意學的概念,即生命的無意義就像一連串的胡言亂語,亂槍打鳥,一無所指。人生的真相除了空虛之外,還是無法了解、不可理喻的。文學藝術成為生命意義的最後避難所,尼采、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這方面都沒有逃脫叔本華虛假意識、「真相是醜陋的」的觀點,小說家、劇作家很能了解其中的真實與冷酷,也難怪連王國維都要悲嘆「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了。人等待真正的救贖,但救贖是否可能?文學藝術的審美能使人獲得救贖嗎?人還是最後仍然因真相而死?文學藝術似乎是悲觀主義的遮蓋和裝飾而已,日神藝術的美的外觀只是酒神遮醜的面具。
伊格頓在第三章〈意義的消蝕〉接著悲觀的虛無主義指出,即使主張生命沒有意義的人,也必須用有意義的話來回答,他們也不能哀悼說生命沒有任何意義。即使生命徹頭徹尾荒謬、盲目,沒有一個結局或目的,但生命不可能是毫無意義的。
在現代主義藝術家、文學家裡,像契訶夫(Anton Chekhov)、康拉德(Joseph Conrad)、卡夫卡(Franz Kafka)、貝克特(Samuel Beckett)及其同時代的人而言,意義向來俯拾皆是。但伊格頓認為現代主義藝術作品是懷著秩序宇宙觀的記憶與鄉愁,事實上意義是不斷地流失,他們將意義的消蝕視為極度的痛苦表現。在現代主義作家中,他們一邊追求永恆的意義,另一邊是卻是感覺到意義無從掌握的痛苦,現代主義表現出這種緊張是相當悲劇性的。伊格頓認為後現代主義並不會為真理、意義等存在的深度擔憂。這些意義的消失的事實並不代表生命就是膚淺的,只有在與深度對照時才會有所謂的膚淺。
貝克特的作品是擱淺在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思想之間的作品,整個痛苦、荒謬的時間凍結正是等待果陀(Godot)的到來,正如對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而言,歷史的空無藉著一種否定正好指明了彌賽亞的即將到來。果陀和彌賽亞的到來這類救贖信念是我們虛假意識的一部分。果陀的缺席將生命投入了極端的不確定之中,但這也不保證果陀一定不會來。
伊格頓在此就「內在意義」一詞給予明確的定義:「我們透過語言,對於存在的東西的理解。」他認為或許生命具有一個「內在」的意義,但我們一無所知,而且與我們每個人的生命所塑造的各種不同意義都不一樣。這個觀點很接近存在主義對「個體性」、「主觀性」和「可能性」的思考。然而也不單單是存在主義的思考而已,他認為內在意義「必須尊重世界的紋理與質地」。人是自我決定的存有者,但他必須與自然、世界以及他人有著相互依賴的關係。任何我為自己的生命創造的意義,本質上就被這樣的關係所限制。
在第四章〈人生是操之在己的嗎?〉中,伊格頓終於提出他所認為的生命意義的答案:愛與幸福。這生命意義的雙翼正是西方文化的兩個重要生命價值所在,並且是兩千多年來人們(不只是哲學家)的所思所想。希臘人(尤其是亞里斯多德)認為幸福是與德性的實踐息息相關的,而德性主要是一種社會行為,不是某種私人、內在的滿足,這也是為何亞里斯多德將倫理學與政治學緊密相連的理由,良善美好的生活需要一種良善的政治體制。而愛更是希臘人和希伯來人的重要關懷主題,希臘人精於探討作為 eros 的愛和 philia 的愛,而耶穌和神的 agape 的愛卻是充滿在《聖經》之中。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在差異中有著水乳交融的同化,西方人的倫理道德從來和他們的信仰是不可分割的。這讓伊格頓可以這樣說:「生命的意義並不是一個問題的解答,而是『以某種方式活著』的問題。它不是形上的,而是倫理道德的。它並不是可以從生命切割下來的某個東西,而是讓生命更值得活的東西,詳言之,某種生命的品質、深度、豐饒、強度。因此,生命的意義是以某種方式呈現的生命本身。」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前言
魯莽到會寫這種書的人,最好是準備好收到一大袋寫滿複雜神祕符號的信件。「生命的意義」這種主題只適合瘋子或喜劇演員,我希望我比較像後者而不是前者。對於這種崇高的主題,我盡量表面上輕鬆淺白,內心嚴肅。但是跟學術界的精深相比,這本書還是做得太過頭、太可笑了。好幾年前,當我還在劍橋讀書時,有本博士論文曾讓我眼睛一亮,叫做《跳蚤陰道系統的一些方面》(**Some Aspects of the Vaginal System of the Flea**)。大家可能認為這些近視進士做這種題目可能會太吃力了點,不過這卻大大表現了我從來都沒學會過的謙遜。至少我還能說,在所有談生命的意義的書中,我寫的是少數幾本不會重講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與計程車司機的故事的書。
特別感謝鄧恩(Joseph Dunne)讀了本書的手稿,給了一些珍貴的批評與建議。
泰瑞?伊格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