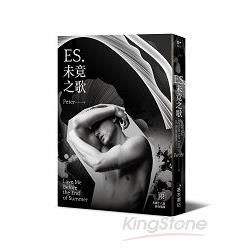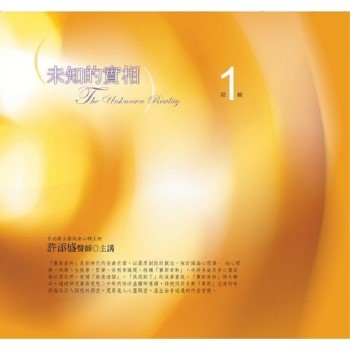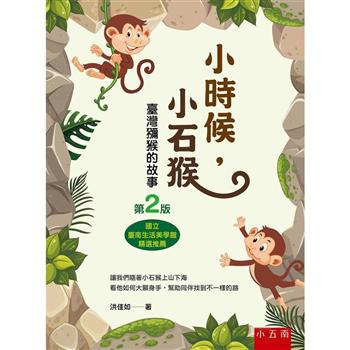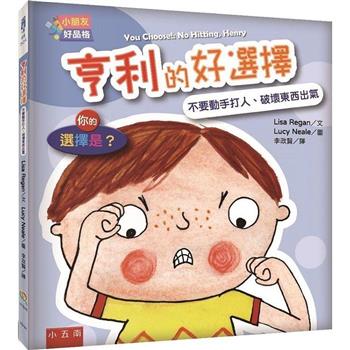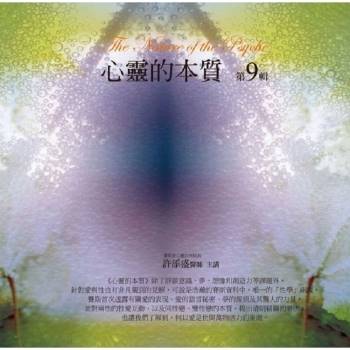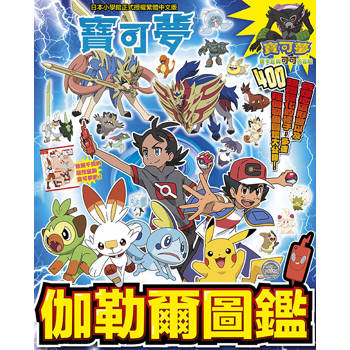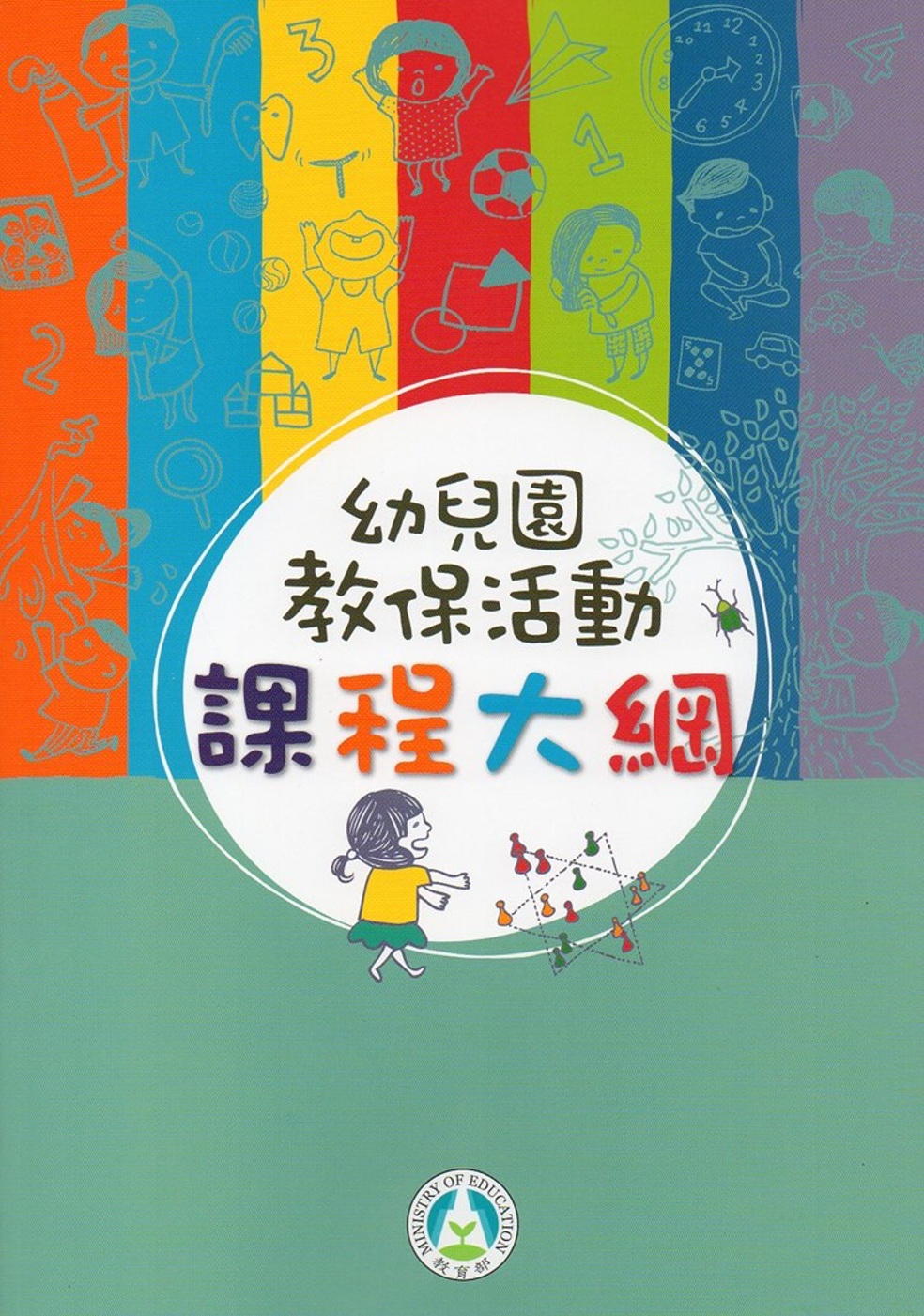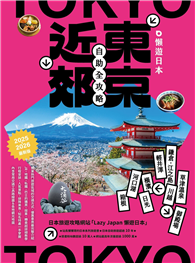導讀
同志藥物場景的真誠紀實
初聞基本書坊邀請我推薦這部小說,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是因這部小說初連載時,我就已是忠實的讀者,能獲邀推薦當然感到萬分榮幸。憂的是這部小說不但詳盡豐富的描述了台灣同志藥物場景,Peter 更以生花妙筆賦予作品極高的文學價值。要說清楚這本小說的好,對於非文學背景的我,唯恐吃力不討好。
幾番思考後,我決定從台灣同志藥物場景的發展歷程切入,這個決定恰與基本書坊期望一致。我們相信這樣能帶給讀者得更多閱讀樂趣。
對一般人來說,在接觸這個議題時,最直接想到的問題通常是:「為什麼同志會和藥物連結在一起?」顯然的,並不是只有同志才使用藥物。在二○○○年前,藥物使用一直被定位成社會底層問題;社會上充斥的是失業者或中輟生的用藥故事,同志並不在問題火線上。
直到二○○○年後,快樂丸的興起改變了一切。快樂丸時代正是建構「同志藥物問題」的關鍵時代。儘管原因眾說紛紜,但可以確定的是,快樂丸在台灣出現時,擁有與傳統「毒品」截然不同的形象。快樂丸的使用方便簡單,不需外觀像刑具的施用器材伺候。快樂丸的使用者既積極又正向,強調愛與分享,一改傳統觀念中墮落畏縮的毒蟲刻板印象。
千禧藥物潮吸引了台灣有史以來最多樣的族群下海逐浪:從黑道大哥到慘綠文青,從街坊快遞到片場導演,員工、老闆、小弟、全部加入了這場空前的愛之狂喜。凡事走在流行前端的同志,行樂自不落于人後,多才多藝的他們甚至也多在這場浪潮中扮演了推動者的角色。
這場狂喜維持了三個夏天。在這之中,許多老客因北市臨檢日趨頻繁,紛紛轉戰台北縣或桃園市;同志們則展現驚人的消費力與打死不退的勇氣,同時支撐TeXound、2F與Going 等舞廳日以繼夜的狂野派對。大約也是在這個時間點,威而鋼在台灣變得更加流行,混合快樂丸與威而鋼的馬拉松式性愛為性愛派對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擔保。
諸多條件透過當年開始興盛的網路交友平台匯流,職業轟趴(Home Party)於焉誕生──本書的時空舞台也在此搭建完成。
但即使在此時,同志用藥依舊不算是具體問題;社會輿論更熱衷批判電音舞曲、舞廳、戶外瑞舞或是KTV 搖頭文化,同志用藥僅是娛樂藥物問題的一環。轉捩點是二○○四年一月十七日的農安趴臨檢。該日,參與這場轟趴的九十二名男同志全數被帶回警局驗血驗尿。媒體跑馬燈二十四小時放送「現場有三百多個用過的保險套」,指證歷歷的說這是個「愛滋趴」,無視保險套的充分利用與HIV 感染兩件事多麼衝突。
即使事過境遷,北市性防所(北市聯合醫院昆明院區前身)追蹤發現該場派對並未產生新的感染者,也已經無助改變大眾的刻板印象。「同志使用藥物」被正式建構成獨特的問題,問題核心圍繞著愛滋防治,與娛樂藥物的減害並無太大關聯。
此後,在防治愛滋的大纛下,轟趴成為警方大力掃蕩重點。寶劍既成,天下伏誅,違反人權的釣魚或毫無法源的強制驗血自然都不是問題。轟趴最終因此瓦解,但能量不滅,反而如雨水滲入泥土般向四處流竄,伴隨著交友APP 的發展,化為野火燒不盡的私趴。
直到今日,搖頭丸匿蹤許久後,在歐美又因EDM 舞曲的風行而受寵;在台灣安非他命則像是窄筒褲一樣重新熱門起來,在同志圈內取代搖頭丸而掀起「菸嗨」現象。
流行走了一圈,「同志—藥物—愛滋」這個三位一體的魔咒依舊未曾消散。為什麼同志會和藥物連結在一起? 細數這段歷史,不難看出這是「歧視」。否則,異性戀同樣也身處其中,同樣有藥物性愛轟趴案件發生,其中甚至不乏政要名人或藝界人士,為何卻不見人們談「異性戀藥物問題」?
在用藥、感染與同性戀的多重歧視下,同志用藥感染者恐是受壓迫最深的一群。他們承擔著社會對用藥者的不諒解,對感染者的不接受,對同性戀的不尊重。而這些壓迫甚至也來自同志族群內部「ES 得愛滋活該」這樣的言論,言者卻常轉頭大談三溫暖獵豔心得。
因此,在認知到「同志用藥問題」的歧視本質以後,我們也需要更深刻的理解,同志用藥感染者確實有著特殊的遭遇與處境。無論是反毒或是反反毒陣營,都應該鼓勵更多人坦誠地說出他們的故事,就像這本小說所完成的工作。作者以血肉換來的生命故事,將是照亮眾人救贖之路的明燈。無視人們的真實經歷,缺乏對情感需求的關懷,再絢麗的論述都將顯得蒼白。
RainbowChild(電音文化網站耳朵蟲主編)
作者後記
感傷的價值
多年後重回此地,感覺自己像個鬼魂。常常是在深夜,的士安靜停泊後,總喜歡走上一段,讓幽森巷弄引領我環視四周,似陌生或熟悉的一切。
小城夜色深重,故里門扉緊掩。暗忖,此地可有我容身之處?
Ghost,我喜歡這個字眼:死去,飄忽,帶著一絲眷戀。
更重要的,ghost還代表一種眼光,隔著無法言喻的距離觀看這世界,深情款款卻又不妄加涉入。
這就是一個鬼魂的心情。
書寫這篇小說時,我對生命充滿困惑,書寫是一種向生命發問的練習。特別對於生命的殘酷與美麗,神聖與世俗,總是義無反顧地迎向前去,修羅地獄在所不惜。小說寫就,魂飛魄散。
多年後回首這種用生命寫小說的方式,頗有劫後餘生、心驚膽跳之感,另一方面也為自己內心深處的堅韌、寬廣遼闊,驚訝不已。
電影《鋼琴師和她的情人》終章,斷指主人翁艾達有情人終成眷屬,即將離開傷心地展開新生活。當時她堅持殘缺鋼琴沒有保留之必要,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向過去告別。棄琴時艾達慾望著琴毀人亡,果真決絕赴死。在這死亡的一刻,艾達擁有絕對的清明,對於過去現在未來忽然一目瞭然。
死亡往往伴隨著重生。
多年之後的艾達,過著全然平靜的生活。午夜夢迴,海底的鋼琴墳場,仍以強大的魅惑召喚著她,彈奏著屬於她私密的迴旋曲。
其實,生命中總有大大小小的死亡,睡眠的儀式,被褥間吱吱喳喳地訴說一切,就是不想睡去,或者將睡非睡時還要手牽手討抱抱,是有多眷戀人生?或者欲仙欲死的性愛,天堂地獄走一回,酣暢淋漓後總是重獲新生。又或者小說寫就,作者已然死去,文字卻有自己的生命。多年後再回首,這些文字長成自己的樣子,與其說是溫習不如說更像認識新朋友,回憶心情不復過往。面對這些已經逝去的事物,或者正在逝去的東西,也許只有文字可以保留它們。然面對時間這個虛妄的魔法師,我們又何嘗失去甚麼?
這就是為什麼我毫無保留的喜歡夏天,因為發生在夏天總有那麼多事情:畢業、軍旅、新鮮人踏入職場,熱烈燃燒的慾望……。夏天帶給我們絕無僅有的第一次,然後帶走它,如匆匆趕赴之江水,無情地啟迪我們,拋下我們,傷害我們,卻也讓我們用後半生去思索,成長。
所以我是一個熱愛感傷的人,因為感傷我們才得以迎向失落,品嚐失落。感傷以一種絕美的形式讓我們頻頻回首,讓我們全然打開自己,深刻地思索。
這本小書也許是那不忍卒讀的一頁,但也許也是生命中最美麗的ㄧ頁。
失去的不會重來,沒有昨日種種,那成今日我?從這個層面看來,生命又何曾失去?
Pe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