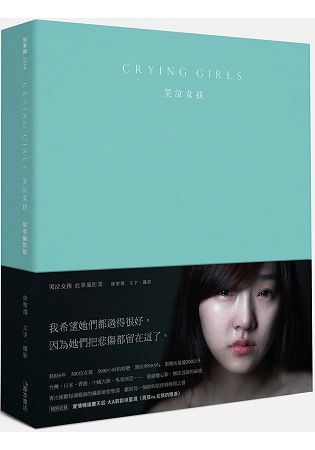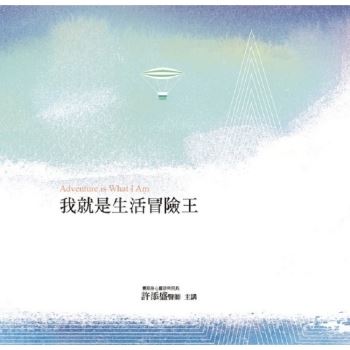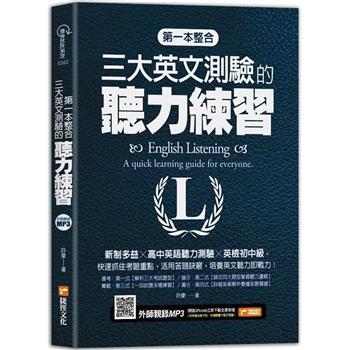自序
「致我們終將失去的膠原蛋白」
現場所有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小徐,徐聖淵,我是一名攝影師,偶爾也會兼差當個藝術家,我今天來到這個舞台上是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件我花了六年終於在今年剛完成的作品──《哭泣女孩》故事攝影集。
我在2010 年底從英國念完攝影碩士之後回台開始創作這件作品,除了台灣之外期間還曾經到了日本、香港、馬來西亞、北京、上海來拍攝,三年前我人生第一次踏上北京以及上海就是因為拍攝這個計畫,嗨,在北京的哭泣女孩們,如果妳有看到這一集,還記得我們在朝陽區竟園相處的時光嗎?我想跟妳們說,妳們的眼淚我都好好地收著了。真的很高興在這本書即將正式出版的時刻可以重新踏上這塊土地跟大家分享我這一路上嚐盡的苦澀眼淚。
《哭泣女孩》這個計畫是我在網路上邀請素昧平生的女孩們來到我的鏡頭前大哭一場,用眼淚正視自己最私密的悲傷,向過去的自己道別,然後堅強的在人生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很像是一種另類的告解室,而我就化身為那位傾聽她們悲傷的閨密暖男。
一開始我是希望能夠拍攝到一百位哭泣女孩來完成這本書,沒想到拍著拍著就超過了五百位,這是我對作品質量的要求以及堅持,日本攝影大師森山大道也說過一個觀念就是「先有量才有質」。
很多人知道我在拍《哭泣女孩》之後,第一個會問我的問題是「為什麼你要拍哭泣女孩呢?」在我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來先分享一個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故事:
有一次,在台灣的時候,有位哭泣女孩跟他的兄弟姊妹三人一起到我家拍攝,簡單的寒暄了一下就準備要開始拍了。只是女孩才剛坐下來準備要醞釀情緒我連燈光都還沒調好時,女孩的妹妹就接到一通電話然後走進拍攝的房間轉交給她,突然間,我看到她神情緊張表情大變的說出:「什麼?弟弟出車禍了?好,好,我馬上過去。」我一聽就知道事情肯定嚴重了,她急急忙忙地掛了電話然後很不好意思的跟我說抱歉,事發突然,她們必須要先離開趕回彰化,我當然是說:「沒關係妳們趕快去吧!」就這樣,我們兩人見面不到十五分鐘,她就消失在我的人生之中,我本來以為我這輩子可能再也不會見到她了。
我還記得她們離開一段時間後我在Facebook 上傳訊息給她說:「希望妳弟弟平安。」時間是十月二十號下午五點四十八分,直到隔天凌晨的兩點十七分我才收到她回覆我說:「謝謝你,但他過世了,今天很抱歉。」
我當下對著電腦螢幕看著那冷靜的淡淡的十三個字噤聲無語。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原來離我們那麼近,我跟她弟弟中間只隔著一個人的距離,我永遠也忘不了她接到電話時的表情,那種恐懼、慌張的感覺,就在我眼前三十公分的距離真實上演,而上一秒的我們還在過著平淡無奇的人生時,有一條生命就在不遠處消失了,沒有了,停止了。
後來有一天,過了一個月左右,我收到女孩從Facebook傳來的訊息:「還記得我嗎?我是NINI,上個月要拍哭泣女孩,突然接到弟弟車禍過世而離開的女孩,弟弟的後事辦完了。」
「我搬到台北了,這段期間一直想著那天的一切,我不想忘記弟弟,想記念著那一天,那一刻,我失去弟弟的那一天,10/20 中午在你家接到弟弟的噩耗。」
「如果可以,我想回到那個地方,拍下未完成的照片,弟弟生前知道我要去拍攝哭泣女孩,一直期待著照片,不僅完成未完成的照片,也想記念那一天那一刻那一個地方,我永遠不想忘記我是在那時候失去弟弟的,謝謝你。」
「但如果不方便,希望也不要造成你困擾,謝謝。」
怎麼會不方便呢?這是我莫大的榮幸啊!我在心裡這樣想著。
後來女孩跟我約在她二十五歲生日那天留下了眼淚給我收藏,當作是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用另外一種方式讓她的弟弟繼續活在我們的心中。而如今這位哭泣女孩更是已經辭掉原本工程師的工作成為一位創作歌手,她跟我說,想要用自己創作的音樂療傷並陪伴與她有同樣遭遇的朋友,我真的覺得替她感到開心,也希望自己面對創傷時能夠跟她一樣堅強、勇敢面對傷痛。
而這個故事,也只是我聽到的那麼多的真實故事之中其中的一個,還有許許多多的哭泣女孩都藉由拍攝這個計畫而得到療癒,身為作者,其實我自己也從女孩身上得到了許多勇氣。
在去英國念書之前,我的外公因為腦中風而得了阿茲海默症,也就是俗稱的老人失智症,所以從台中搬來跟我母親、也就是他的女兒一起住在台南,那是我人生當中唯一一次機會跟自己的外公長時間相處、生活在一起,但是他卻已經不再是我小時候每逢過年就去開開心心要紅包的那位外公了。
很多電影都用過阿茲海默症作為主題,但是在我看來往往都是過於輕描淡寫、避重就輕,完全無法真實呈現這個疾病帶給身邊的人有多大的壓力,藥物的治療頂多是延緩程度加重的時間而非根治,這是一種不可逆而且是長期、永無止盡直到生命終結的那一天為止的痛苦,尤其是對周遭至愛的親人們,你們知道嗎?重度的老人失智症是會產生被害妄想症、以及暴力傾向的行為,我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都要聽著外公在床上一直重複的哀叫,又或者是看著外公全身赤裸地在浴室對想要幫他洗澡的看護揮拳攻擊,眼神充滿著疑惑以及憤怒,一次又一次的大喊:「你幹嘛?你幹嘛?」
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來我們人類是可以連自己是誰都不記得的。死亡是公平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死,或者我們真正應該要問的是:「死了之後我想要怎樣被人們記得呢?」
身為一位創作者,我就很想要留下一件代表作品是值得被記住的,即便我待會走出攝影棚就被車子撞死但是還有這件作品可以代替我繼續存在這個世界上持續的被討論,這些來拍攝過的哭泣女孩會記得我是誰,我也會記得她們是誰,女孩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就是她們的眼淚。
而聽完這篇演講的你們,在今天過後或許也會幫我記住──「我是誰」。
如果我的生命因為我做的這件事情幫助了這些女孩而產生了意義,那我想我也應該可以理直氣壯的說:「好險,沒有白走這一遭」了吧?
這也是為什麼我這樣想要完成這件作品的原因之一,每次女孩拍攝完時對我說的那句「謝謝」,就足以支持我繼續走下去,也因為她們的分享,讓我學習到怎樣去勇敢的面對自己的人生。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也想邀請各位朋友一起來思考一下,你想要成為怎樣的人?你想要怎樣在這個星球寫下一篇屬於你獨一無二的故事呢?
謝謝大家的聆聽,我們有緣再見。
徐聖淵
(* 本文原為參選北京衛視節目《我是演說家》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