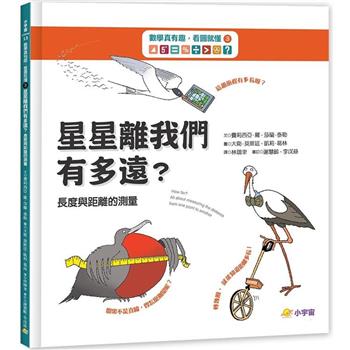全美狂銷100萬冊的「暮光之城」系列
史蒂芬妮.梅爾(Stephenie Meyer)最新作品!
橫掃全美各大排行榜冠軍
紐約時報排行榜逾48週
我無法將自己與這個軀體的渴望切割開來。
這個軀體就是我,比我預期的還像是我。
究竟是我的渴望,還是它的渴望?
事到如今,再區分是誰還有意義嗎?
梅蘭妮拒絕就這樣消失。
外星生物入侵地球後,寄生在人類體內,控制人類心智,抹滅人類天性。寄生在梅蘭妮身上的入侵者,雖然深知要控制人類心智,可能會面臨到人類感情太過豐富、過往的記憶太過鮮明而難以駕馭,但仍舊毅然決然接受挑戰。
只是這個入侵者萬萬沒想到,梅蘭妮抗拒讓出她的心智。結果入侵者思緒裡滿是梅蘭妮所愛的人的身影,一個仍躲藏著、還未被外星生物入侵的男人。漸漸地,入侵者也愛上了這個未曾謀面的男人。由於因緣湊巧,她們心不甘情不願開始合作,一起找尋兩人共同所愛的人。
這是一個關於三角戀的故事,但主角只有兩人。這也是一個關於友誼與愛情、復活與倖存的故事。
重要事件
●2008年時代週刊選為全球百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
●2008年娛樂雜誌選為年度風雲人物
●2005年最佳新秀作家
●2008年亞馬遜年度讀者票選選書
●2008年亞馬遜5月選書
作者簡介
史蒂芬妮.梅爾(Stephenie Meyer)
1973年12月24日生於美國康乃狄克州,在亞利桑納州的鳳凰城長大,有五個兄弟姊妹。1995年她自楊百翰大學畢業,主修英文。1994年婚後育有三名子女,目前仍定居在鳳凰城。
現年36歲的梅爾以處女作「暮光之城」系列成為家喻戶曉的暢銷作家,是2008年全美最暢銷的作者,光2008年一整年便有兩千兩百萬本的銷售佳績。2008年時代週刊將她選為全球百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娛樂週刊也評選為2008年度風雲人物第五名。
2008年5月在美出版的《宿主》一出版便登上全美各大暢銷排行榜冠軍,目前仍盤據在紐約時報排行榜逾48週。這是第一本梅爾寫給成人讀者的小說,把浪漫愛情與外星人元素融合起來,作者說,這是一本專為不看科幻小說的讀者所寫的科幻小說。
除了「暮光之城」系列與《宿主》之外,目前梅爾正在構思其他小說,包括一個命名為《夏季別墅》的鬼故事、一本與時光旅行有關的小說,以及關於美人魚的故事。


 2014/02/15
2014/02/15 2011/01/14
201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