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一份集體犯罪的真相報告
王秀文
菲立普.克婁代(Philippe Claudel)是法國當代文壇暢銷作家,他的第一部作品為《被遺忘的莫芝省》,之後陸續發表《灰色的靈魂》、《林先生的孫女》、《波戴克報告》等小說。《波戴克報告》出版於2007年,榮獲高中生龔固爾文學大獎,除了寫作之外,克婁代同時從事拍攝電影和教書工作。
《波戴克報告》描寫主角波戴克從事花草生長記錄工作,某日被村民要求,為村裡謀殺事件寫報告。撰寫報告的過程中,他不斷地回想過去生活的片段,想起前往首都唸書、與妻子相遇以及戰爭爆發時,身處集中營過著煉獄般生活。故事的尾聲,隨著謀殺案真相的謎底揭曉,波戴克同時意外發現自己當年被送往集中營,竟是遭到同村村民的檢舉,看似平凡樸實的村民臉孔底下,卻藏匿著人性的醜陋面,於是報告完成之後,他也帶著妻小離開了村莊。
菲立普.克婁代以推理小說的架構鋪陳懸疑情節,將歷史事件透過文學書寫的方式陳述,儘管小說中並未明確描述事件發生的時間,連主角波戴克所居住的村莊,也只能隱約得知是位於歐洲某一國家邊境。然而,整部小說中依舊喚起人類歷史上沉痛的集體記憶,透過波戴克的倖存和見證,受難者被集中營守衛當成畜生奴役,時時處於飢餓、恐懼、殘暴凌虐以及死亡的威脅,集中營裡最為慘烈的受苦景象,透過文字一一描述出來。
在這部作品中,克婁代揭露戰爭扭曲人性,它是一種意識操作的行為; 是一場鏟除異己的「淨化工作」。同時透過小鎮裡村民們所犯下的集體罪行,作者似乎意圖表達這種仇視外人的意識形態,並沒有從戰爭之後消失。故事一開頭,村民替來訪的外地人取名為Anderer,意指他屬於「其他人」,原文中作者以斜體字標明這個綽號,象徵他是村民眼中的「異者」、「異類」。而就深層涵義來看,「異類」這個貶意似乎等同怪物,對「同類」而言,生存空間受到侵入,構成了威脅要素,就會被消滅。Anderer的到來,他的沉默寡言,出沒神秘,不愛與人交談,卻熱愛和他的驢子、馬說話的怪異舉止以及他身著華麗的服飾外表等等,一再地和居住在當地農莊,粗茶布衣的村民形成強烈的對比。此外,Anderer出眾的繪畫才能,敏銳的觀察力,將每個村民靈魂深處的虛偽、脆弱等陰暗面,以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肖像畫,赤裸裸地呈現在他們眼前,引起村民的恐慌,最後卻為自己招致死亡的命運。同樣地,村民雖是戰爭的受害者,但是在戰爭的洗禮下,為求自保,卻變成自私的加害者,在外國軍隊佔領村莊期間,他們出賣自己的良心,將波戴克交給外國軍隊,只因為他並非土斯土長的當地人。這兩位異鄉客的命運,突顯的都是本地人/外地人、同類/異類之間的相斥、衝突。
克婁代曾在監獄中教過受刑人長達十一年之久,他擅於運用密閉空間的喻象,鋪陳小說中懸疑的情節和神祕的氣氛。例如: 故事中的背景- 小村莊本身就是一個封閉空間,位於山谷之間的隱蔽處,四處被山谷遮蔽,與外界隔絕,密室環境形成村民心態上的狹隘。此外,密室亦具有神秘性,波戴克寫報告的地點位於儲藏室,打字機的背面是一道牆,幽閉的空間可以杜絕其他村民的監視、監聽; 同樣地,村民聚集在許洛斯客棧裡頭,緊閉大門謀殺了Anderer,之後他們在同一個地方,以集體力量要求波戴克撰寫謀殺案報告,客棧密室甚至成為犯罪的場所,這個內在空間牽引著小說的主題,隱藏著不可告人的秘密,匯集集體犯罪的真相。
主角波戴克並非英雄,相反地他只是一介平凡人物,然而他的學識,不僅還原村長以及其他村民集體犯罪的事實,同時揭露這股象徵父權專制力量的黑暗。克婁代以簡潔雋永的文筆,讓小說呈現童話般的詩意,寓言故事般的哲思,讀者在閱讀作品的同時,可以重新對戰爭、對歷史、對人類生存條件進行一番省思。
落雨的小村
吳明益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暨創作研究所籌備處副教授
寫這篇序的這一個月中,我恰好有一個機會和孫大川老師同台演講。演講時他提到一開始漢人稱原住民為「番」,是把原住民當成非人的動物。(確實如此,《說文解字》中的「番」就解作「獸足謂之番,(人人)采田,象其掌。」)後來日本人來了,把番字加上草字頭,變成「蕃」。他說,好像我們從動物變成植物一樣。台下哄然大笑,那麼熱烈的笑聲讓我有點感傷。讓我想起已經讀了數遍的《波戴克報告》,那些「他者」(the other)。
《波》的敘事結構看似簡單(為避免打擾讀者閱讀,我不打算提太多情節),以小村一位居民波戴克的敘事展開,他被迫記錄「那件事」,並且寫出報告。而波戴克報告中的主人翁,是一個被稱為安德雷(de Anderer)的異鄉訪客。Anderer在德文中便是「他者」的意思,而小村居民有時候叫他禿眼仔、喃喃人、月亮來的,或從那裡來的人。
寫異鄉客、戰爭或種族問題的小說在當代都不少見,傑作也不少。我個人就深深被柯慈(J. M. Coetzee)、莫莉森(Tony Morrison)震動過。但克婁代的敘事別具魅力之處,在於他善以一種「擬偵探」的方式寫作,不斷反覆鋪陳謎面,而將謎底留待小說最後揭露,或讓讀者發現,一切根本沒有謎底。這在之前的《灰色的靈魂》和《林先生的小孫女》已現其端,《灰》本質上就是一個關於戰時小女孩被謀殺案件的重述,而林先生的小孫女的敘事源起於戰爭中極其平凡的死亡(在一次轟炸中子女雙亡,於是爺爺只好帶著小孫女在難民營中生活),卻要到小說的末尾讀者才知道一路閱讀時掛心的小孫女並不是「活著」的小女孩……。而《波戴克報告》呢?我必須承認,從一開始讀到波戴克開始倒敘「那件事」是怎麼發生的,我就不斷在心裡建構那場「可能的」殺戮場景,但一直讀到安德雷站在村民房屋門口,不斷高喊「兇手!兇手!」那一刻,才恍然覺悟克婁代做為一個敘事者的高明與殘酷。我已和村民一樣,涉入了「那件事」,做為一個讀者,我已在「心中」參與了那場殺戮。
儘管我在讀《灰》和《林》時,就深深被克婁代「綿裡針式」的文字力道懾服,但讀到《波》時我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惆悵情緒出現。波戴克為什麼會被選為「那件事」的記錄者?那是因為他「讀過書」、「會寫字」、「會用打字機」……而這就是留下記錄的條件:文字。無人知曉那個被克婁代創造出來的村落位於這個世界那個地方,他甚至刻意塑造了一種接近德文的方言,來呈現這個虛構村落的話語。但我在閱讀時毫無猶疑地相信那個在夢中告訴克婁代「我的名字叫做波戴克,我跟那件事毫無關係」的敘事者,所說的一切盡皆為真。因為全書的文字如此深沉、有力,像一把匕首剜出我們的靈魂,我們的思想。村民要波戴克寫下記錄原是為了「脫罪」,但在戰爭中,波戴克自己就是被村民以「外來者」的身份出賣給占領軍的。波戴克因此在集中營中像狗一樣被對待,唯一支持他回到村子的,是對家人的愛。因此,波戴克的報告究竟是「記錄」,還是「自述」?是脫罪還是控訴(甚或自訴)?做為一個書寫者,我們究竟如克婁代所說,是「一個隱去自己情感的人,好讓自己成為一隻手,一隻在紙張上劃下文字、以便拯救記憶的手」,抑或我們的文字就是情感、記憶的本身?除此之外,再無依藉?
克婁代讓波戴克原本扮演的職業是記錄村莊的「植被、樹木、不同的季節與獵物、思托比河的枯水期、雪量及雨量的狀態」,但「波戴克報告」,會不會在本質上跟這樣「幾乎被遺忘」的,彷彿自然觀察的報告並無二致?人類社會發生過太多這樣的事了,多到幾近於季節流轉,河流豐枯,多到我們隨時都會忘記,於是我們得靠書寫者來幫我們記起。
拿到書稿後,隔天我便毫無歇息地一口氣讀完,並深深被它所震顫,因此不自量力地寫下這篇文章,邀請願意檢視自己靈魂的讀者閱讀。而那份編輯寄來的書稿,可能因為印表機墨水不足,從作者刻意安排的一場雨的描寫後墨色漸淡,到最後幾頁文字幾不可見。克婁代正讓重要情節逐步在雨中揭露,而我竟有了一種看著落雨的小村所發生的一切,卻又看不清一切的錯覺。我的閱讀變得極慢,像是得避開雨水,才能透過克婁代彷彿雨般具有滲透力的文字,試圖感受他所「報告」給我們的「真相」。
可是波戴克說:「真相,可是會斬斷雙手的。」因為真相可能是「秘密、苦惱、醜惡、錯誤、困惑與卑劣」。而小說家為什麼寧可被「斬斷雙手」,也要以文字「報告」?這個問題,或許只有那些願意為Anderer寫作的作者,才得以回答。而你手中的書,正是其中一本,它可能讓你的靈魂遍體鱗傷,也同時讓你的靈魂尋得微光。
作者序
波戴克報告
給台灣讀者序
這本書是在某個夜裡誕生的。在那天夜裡,我夢到了一句話,就好像有時候我們會夢到某張面孔、某個景色,或是某個場面,在我們腦海中變換主題卻不斷重複上演那樣。那是頭一次有這樣的事發生在我身上。然而,仔細想來,一個作家夢到一句話,倒也是再自然也不過的事……隔天早上,我一醒來,便立刻記下了這句話,彷彿它是一個奇蹟的果實,來自一個脆弱的奇蹟,也許只需白晝便足以讓它永遠消失蹤影:
「我的名字叫做波戴克,我跟那件事毫無關係。」
重讀一遍之後,這些字句撼動了我,原因是這個句子的單純爽直,也因為這個名字,波戴克,他是這句話的核心,想要吐露一些事情。這個波戴克是何許人?他來自何方?他是怎麼、又是為了什麼原因,來到我的夢裡拜訪我,以他沒有形體的聲音碰撞我的睡意?人家是對他有什麼責怪,以致於他要這樣為自己辯護?
我喜歡提問題,卻嘗不到答案的滋味,總之是得不到立即的答案。波戴克擊打了我的夜晚,敲著我的窗戶,卻留下我一個人。孤獨一人,與他單薄卻堅決的告白同在,是那種值得在法庭上陳述的告白。我不需要更多資料了,當天便在手提電腦上開啟了一個新文件,寫下那個句子,並把文件命名為「波戴克的告白」,而很快、在短短幾分鐘後,我又把文件標題改成了「波戴克報告」。
接下來,一切便只是取決於時間了。
我只在我想寫的時候、在書寫的渴望變得十萬火急的時候才會書寫。對一個作家而言,寫東西是沒有行事曆、沒有時間表的。有的僅是渴望,那是一種灼燒的感覺,當它變得那般強烈到無法承受時,作家便得馬上放下所有其他活動,毫不耽擱的讓自己專心投入寫作之中。
我便是如此與波戴克一起生活了將近三年的時間。他來到我背後,一付若無其事的樣子,然後在我忙著別的事情的時候,在我身旁坐下。他就待在那裡,不吭聲,也不引人注意,但也不離去:於是我便心知肚明,自己必須繼續他的故事。我很少這樣清晰地感覺到一個角色的存在,幾乎像人一樣的存在,靈敏的肉體,具有呼吸,有點駝背、順從的小小身軀,卻滿懷著某種痛苦的平靜。我的這位人物就是這個樣子。沒有面孔。只有聲音。儘管在形體上如此抽象,他的存在卻是十分強烈。
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從來沒有忘記來自黑夜的波戴克,他來自我的夜,也來自所有人類的夜。他是黑暗與晦澀世界派來的使者。他來自一個話語已經不再通行的國度,因為那裡的人已經摧毀了話語,一如他們毀滅了其餘一切:世界的美妙與期望。正常來說,沒有人會從這個國度裡回來。沒有人。除了波戴克。波戴克回來了,而且他來找我,他找到了我,要我把他的聲音與他的故事記錄下來。
這段過程對我來說從來不覺得痛苦,即使我所訴說的故事承載著最高的痛苦程度。書寫的動作,使得我所敘述的這個故事能夠存在於現實環境中,但書寫卻也讓我保持了距離。我是個擺渡人,而不是見證者。我是抄寫人,一個隱去自己情感的人,好讓自己成為一隻手,一隻在紙張上劃下文字、以便拯救記憶的手。
有時候,好幾個月過去,在這長長好幾個月之中,波戴克都沒有來找我,於是我便幾乎完全忘記了他,忙著進行別的書籍或是別的計畫。然後他便會在我最料想不到他會來的時候出現,安頓下來,就再也不動。我便明白我該再度開始寫作。
以上所言,是關於這本書的誕生的表述方式之一。我也可以用別的方式來說。表達的方法有上千種。我也可以說,這句某個夜裡夢到的話,就好像有人給我的一把鑰匙──是誰給的呢?──它讓我終於開啟了一扇門,而我已在門外耐心等待了那麼多年。我也可以說,這本小說是三部曲的最後一部份,從「灰色的靈魂」開始,然後是「林先生的小孫女」,而把這三本小說結合在一起的,是對於戰爭與戰爭所帶來的影響、對於人在歷史中所占的位置、對於人面對重大事件的脆弱,所做的反思。同樣地,我也可以說,「波戴克報告」是我自童年以來,對於亡族滅種的大屠殺行為所做的反省,所得到的笨拙而未完成的結果。當年,應該是我十來歲的時候,我發現了納粹死亡集中營的存在,以那個時候來講,事件發生在還不算太遙遠的過去。這個真相的痛苦,這一切就發生在我也身為一份子的人類之中的這個事實,那些變成了劊子手的人們就是些跟我一樣的人。這一切,從此便不斷糾纏著我、砥礪著我。而我繞著這本書打轉了這麼多年,一如我至今仍繼續繞著那個人性陷落其中的巨大黑暗深淵打轉。
不過我也可以說,「波戴克報告」的構思與醞釀,宛如一本愛情小說,因為這點跟我先前所說的一切,也同樣是千真萬確。我夢想寫作一本愛情小說。我不知道我是否具有寫愛情小說的能耐。我也不知道我是否有一天能做得到,不過儘管如此,在這本書裡,我往往是因為思索著將主角與他的妻子艾梅莉亞、他的女兒普雪與他的老母親費朵琳結合在一起的這股龐大的愛,我才找到力量繼續他的敘述。今天,經過將近三年的時間,我寫完了這本小說,我所留下來的便是這一點:在這個殘酷、痛苦、差點吞沒了波戴克、摧毀他、讓他淪為無物(或一無是處)的無盡暗夜之上,存有一線微弱卻永恆的愛情之光,像是一個堅實嚴密的承諾,任何一切都無法玷污。是的,有這麼一絲清明而溫暖的光線,這麼一隻伸出的手,這麼一個吻和這樣一個擁抱,讓我相信並且希望,永遠都會有明日的存在。
Philippe Claudel寫於2009年11月 2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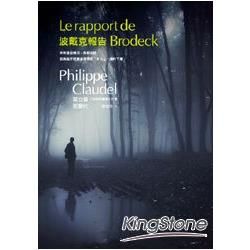












這本書是典型的以小喻大,以一個小村莊為背景去書寫出大時代的悲歌與省思,當然本書從頭到尾沒有提到納粹、集中營與猶太人這些字眼,不過讀者絕對可以讀的出來作者的企圖與故事的背景。波戴克是戰爭的受害者,是集中營的倖存者,也是他的村子的集體罪刑的犧牲者,當他從戰爭回到村子後,他卻又被村子的人要求為他們的另外一起集體罪刑書寫脫罪的文件報告。 作者想透過波戴克的報告表達什麼?對集體犯罪的批判?還是受害者的自述?亦或是對集體施暴或共犯者的「沒有反省」作出深沉控訴?納粹固然是可恨,但千千萬萬的幫兇呢?難道只是一句「誰知道誰要為這一切付出代價?」就可以卸下責任。 戰爭也許\是各國人民所需要的惡夢,他們蹂躪自己花了好幾個世界建立的東西,他們毀滅自己昨天所讚頌的,他們允許\自己從前禁止的,他們喜愛自己昔日譴責的。而戰爭的責任與反省可以集體遺忘嗎? 極權者或其被其馴服的群眾幫兇,往往會喊出「向前看!」的口號,把那些對過去的反思當成進步的阻礙,一如書中的村長對波戴克說:「我就像位牧羊人,羊群指望牧羊人來避開所有的危險,而所有危險中,最可怕的就是記憶了,是該遺忘的時候,人們有遺忘的需要。」 當一個獨夫要求人民遺忘或無條件諒解,這個民族不是成為共犯就是成為被馴服的羊群,別忘了,羊群存在的目的是用來宰割或剝削的。 本書給我最大的收獲是:「被害者無法透過原諒來結束苦痛,若沒有得到轉型正義,剩下的唯一出口就是出走。」讀完這本書,多少可以體會猶太人在二戰之後建立以色列國的心情。 當然本書所提到的東西,絕對是可以傳世警惕的,但立論正確的書不代表是好看的書,這是本很憂傷的故事,也具備了厚重的穿透人心的哀愁,但是書寫的文字與篇幅卻流於華麗的辭藻,故事的敘述中少見精彩的轉折,濃濃的說教與刻意的意識流形容佔了過多的篇幅,不時會穿插一些時空跳躍的心理對話,沒有閱\讀過大量的法國文學的讀者恐怕會難以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