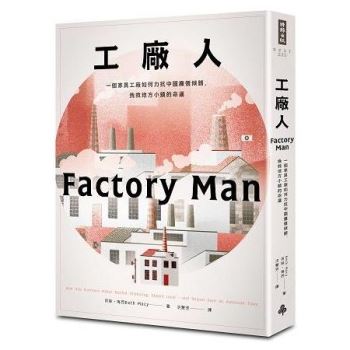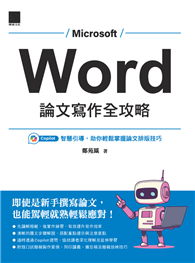食物,對於不同文化與種族,是一重要的區隔的象徵。不同人他們各自的食物的品味隨著文化有著不同的喜好。但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對於不同文化與種族的食物有著多元的經驗。我們可能在中餐吃了一頓日本料理,到了晚餐,我們可能選擇酸辣的泰式料理。對於一些美味的佳餚,在一我群的場合當中,它成為我們與他們最大的不同。這個不同不是我們留在嘴巴內的美食而已,它有一段食物的文化、歷史。「食物」在為人類果腹的同時,人類亦隨之表現了對待食物的方法、態度、儀式與精神。觀察原住民在面對食物所展現的現實、審美、歷史與文化意義,有助於現代人反思「飲食」之於人類生存與生活的價值。
主編簡介
焦桐
一九五六年生於高雄市,已出版著作包括詩集《焦桐詩集:1980-1993》、《完全壯陽食譜》、《青春標本》,及散文《我的房事》、《在世界的邊緣》、《暴食江湖》、《臺灣味道》、《臺灣肚皮》,童話《烏鴉鳳蝶阿青的旅程》,論述《臺灣戰後初期的戲劇》、《臺灣文學的街頭運動:1977~世紀末》等等二十餘種。編有年度飲食文選、年度詩選、年度小說選、年度散文選及各種主題文選四十餘種,二○○五年創辦《飲食》雜誌,展開臺灣的年度餐館評鑑工作,並任評審團召集人。焦桐長期擔任文學傳播工作,現任教於中央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