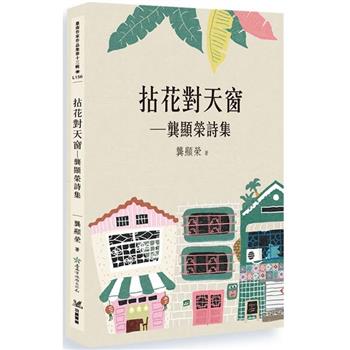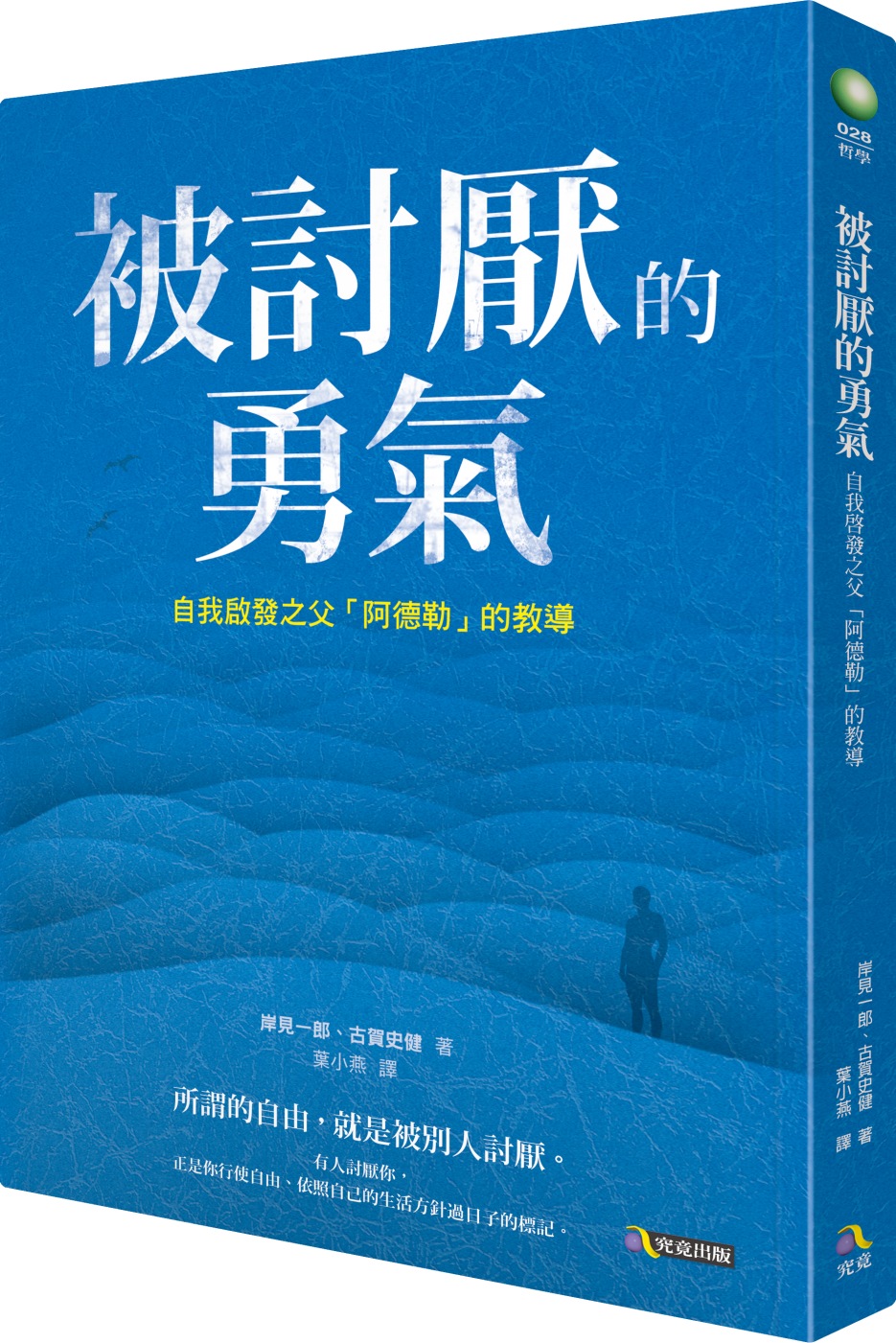序論
主編 楊佳嫻
壹、
〈春秋茶室〉中使少年發仔和讀者同感震撼的,是被輾轉賣為娼妓的原住民少女林美麗所說的一句話:「我已經認命了。」作者吳錦發描寫了這句話是如何地使愛慕與悲憐著林美麗的少年,終於窺見了所謂命運,不可解的現實世界和成人的醜陋;小說最後彷彿變得雲淡風清,然而發仔早已經不是那個愛鬧的逃學孩子了,他心中已存在著記憶與悲哀的種子。
廣義的「成長小說」以少年啟蒙過程為書寫主題,在中國古典便能找到,讀者最熟悉的大抵是賈寶玉如何目睹青春烏托邦「大觀園」一步步的崩毀,乃至體歷人間劫難,覺悟真假,向佛道尋求脫解--著重的不是發展,而是覺悟,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地認識世界、發見時間與現實之本質的悲劇性。論述現代「成長小說」或「啟蒙小說」時,往往會追溯到兩個歷史點,一是十八世紀康德在〈何謂啟蒙〉中揭示的,所謂啟蒙,便是走出無他人之教養監護便無法使用一己之思索能力的未成年狀態,當然,同時也必須具備使用這種自我思維能力的自由;另一則是十九世紀歌德創作的小說《威廉˙邁斯特的學習年代》,創造了德文中所說Bildungsroman的小說類型,主要呈現的是少年人格的成長、世界觀的定型,尤重於文化教養、自我教育的義涵,屬於狹義的「成長小說」--歌德與康德筆下,無論文學或思想,皆涵藏著發展的、向上的、正面的意義。
拿「少年」當作新生命勃發的意象,且賦予改革變化、救亡圖存的意義,「發現少年」與「想像中國」息息相關,自晚清以來可見端倪[1]﹔然而,當「少年」進入現代小說創作,特別是在台灣文學的範疇中,持續和國族寓言糾纏不已,更進而在「台灣」抑或「中國」的矛盾中徘徊[2],複雜化了成長小說可能帶來的被詮釋面向﹔其中可能是白先勇《孽子》中對於那群來自失去父親的家庭、血緣上涵蓋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日本人等的「青春鳥」在融合與茁壯上的期許,讓他們勇敢地一一踏上追尋父親/自我的路途,也可能是張大春筆下逃家逃學的大頭春,通過週記形式,透過一個未成年的孩子的眼光去窺看現實世界的傾斜處,在胡說八道的自以為是中,包含著純真和世故。
本書選文的過程中,採取廣義的角度;但是,早有識者追蹤台灣成長小說寫作情況時,即指出當中含有強烈的悲劇傾向,樂觀的、以人文的正向發展為主旨的,少之又少。本書最後擇定的篇章,包括同意入選與不同意入選的,歸納起來發現,絕大多數都以人間的悲哀、理想的幻滅作為成長的代價,且強烈地以感性作為小說驅動的力量,少年在淚水中成長,放棄了一些什麼,懂得了一些什麼,明瞭了某些事務上自我的無能為力,對於自我和現實的認識,乃是在於發現裂縫,而非與群體社會達到更好的接合。
由於期望能在選本能呈現各個不同世代小說家在成長小說書寫上的同質與異質,因為兼顧戰後日治時代出生到所謂「六年級」的一代;選本本就具有經典意義建立的意味,選擇篇章上也往往優先考慮藝術歷程與成就較為成熟的作家,本書自不例外,卻也同時希望納入較多的年輕作者;再者,以成長為主題的台灣小說不少,篇章的擇定中自然在各種客觀考量之下,不免還透露著選者的主觀品味與愛好,但仍力求在主客觀之間平衡。因此,選本最後呈現的,便是自楊逵、葉石濤、王文興等早已備受肯定的老作家,到張惠菁、許榮哲、伊格言等近年來崛起的年輕小說家;除了因私人理由不同意被選入的陳映真〈我的弟弟康雄〉、童偉格〈我〉之外,楊青矗〈在室男〉鮮活動人,勇敢的酒家姑娘「大目仔」令人印象深刻,以篇幅太長而割愛,我更感遺憾的是以去世的顧肇森〈張偉〉一篇,此篇完成於八十年代,是白先勇《孽子》之外較早的明確以男同志生活與心境成長為主題的小說,筆觸俐落,在論述上卻較少受到注意,近來雖有陳雨航先生策劃選書,將刊有〈張偉〉的《貓臉的歲月》一書重新出版,仍希望能在選本中鄭重提出,惟因為聯絡顧肇森家人不易,故而作罷。另外,如白先勇的諸篇作品,不少皆集中於成長的議題,尤其《孽子》透過城市地景、父子關係來描述邊緣族群,亦有較為積極正面的自我成長意義,只是白先勇的作品流布極廣,閱者已眾,此處不再添花。
以下分成兩個小節,概述本書所選各家特色與其對於成長、啟蒙議題的發揮,書內另附有各家小傳與簡評,簡評中已提及處,這裡不再贅述。
貳、
選本從日治時代作家開始,自然是希望不拘泥於「戰後」「日治」的普遍文學史分期,而以與成長主題有關的現代小說一脈貫串,同時彰顯作家特色與主要關懷。楊逵作品為日治時代完成,〈種地瓜〉表現出兒子立定意志、體會父親心情而願意挑起生活擔子﹔比他晚二十年出生、經歷日治時代後半期的葉石濤,自十六歲發表第一篇小說以來,除了羈獄前後幾年,均持續發表創作,小說與評論皆豐[3],尤其對於塑造本土文學意識與價值、藉著書寫勾勒台灣五十年代風貌,具有貢獻,〈玉皇大帝的生日〉也有這種味道。這兩位作家的文筆較為質樸,而由於所處時代與文學發展的關係,葉石濤在文學技巧上又較楊逵前進。
王文興以苦行緩慢的書寫與形式的執著著稱於台灣文學史,一部前後長達二十餘年才完成的《背海的人》,以及符號、形式的曲折,被年輕一代文藝工作者稱為「文學史的驕傲,排版工人的惡夢」[4]。在眾所關注的《家變》、《背海的人》之外,集結了大學時代作品的《十五篇小說》或許較不為一般讀者熟悉,但這些即是王文興發表過的僅十五個短篇小說,且有不少可就成長、啟蒙角度切入討論者。本書選取〈命運的跡線〉,講一名憂慮自身康健的少年,如何在同儕流行的算命話題中加倍地感覺受到傷害,陷入強大的憂鬱,而以刀片劃傷手掌,意欲延伸過短的壽命線,而幾乎真正地縮減了性命--孱弱敏感的少年,王文興另一篇〈玩具手槍〉亦曾塑造過一個年紀較長的類似角色,他們都極為在意身體健康與其帶來的自卑,也往往陷入同儕的嘲笑中,擴大了那些嘲笑的效應,在內心迴響成更大的威脅,逼迫少年作出極端的行為。〈命運的跡線〉中的少年以未來的詩人自命,期許自我能以文字闖出一番事業,可是那醜陋孩子的算命結果,卻宣布他只能活三十歲,則所有的努力或將成為枉然罷,則再多的努力與想像都敵不過宿命,過份的執著造成偏激的行徑,傷口痊癒後留下了疤痕,「看來就跟那真的壽命線一模一樣」,像一條銘刻在身上的,永恆的反諷。
以〈春秋茶室〉聞名的吳錦發,在這篇得獎小說中,以山花陳美麗、少年阿發仔以及家裡開茶室的好友富林為主角,透過發仔的眼睛,描述少年之間歡樂的友誼、對成年人的不屑和懼怕、情竇初開的心境;遭遇悲慘的原住民少女陳美麗從富林口中描述出的形象,到實際窺看得的形貌,深植發仔腦中,逐漸成為夢中女神般的存在,而在現實中女神卻是被迫風塵的。和愛情與欲望同時萌發的,是發仔同時揣度著富林營救、看顧林美麗的心情,遠遠地看著成人如何施展心理與行動上的壓力,如何因為一股年少意氣與自己未必真正懂得的愛欲的驅使,而挺身對抗現實的橫暴;這驅使的力量,可以說是非理性的,而是出自於本善與感性,彷彿完成了營救,便不枉青春,對得起友情與愛情。然而,陳美麗對於雷雨夜的懼怕、藏匿時的飢餓寒暖、車錢等等,是可以解決的,社會大環境卻不是兩個少年能轉動乾坤的,陳美麗被抓回茶室了,失去了和命運奮鬥的激情,小說主角透過失望與無力感而成長--
……我的年齡還無法明白什麼叫做「命」,她,陳美麗和我一樣小,她一定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命」吧?
「我已經認命了﹗」
但她為什麼要這麼說呢?她說這句話的時候心裡在想些什麼?她這句話是從哪裡學來的呢?小說嗎?廣播劇嗎?
「我已經認命了!」
她一定不知道,她這句話不但擊敗了她自己,連帶的,也擊敗了我年輕的愛、夢及公義之心……。
李永平曾如此評論:「在體裁上倒是很強有力的三結合……少年的初戀,非常美麗浪漫的故事,然後一個小鎮的生活,然後社會問題,現實社會問題,販賣人口的問題……。」[5]清楚說明了〈春秋茶室〉故事魅力的來源,雖然,九十年代以來這樣的故事情節可能在小說、電視電影與某些戲劇性的新聞報導中被熟化了,年輕一代讀者所受到的衝擊會小一些。不可否認的是,〈春秋茶室〉不以嚴肅的面孔探討社會問題,而以少年情感的生發與挫折做為主軸,大幅增添了小說動人的力量。吳錦發也在序中表表示:「〈春秋茶室〉寫的是我年少時候的激情,我的心理成長歷程」,並明確地自我定義為「成長小說」,乃是主角「在性心理、生理成長過程中所碰到的『事件』,使『我』逐漸省悟到:『我』在生命中的『位格』在哪裡,以及『我』在整個生存的大社會中所能扮演的『角色』是什麼……。」[6]
「成長小說」既然寫的是成長歷程,不免摻入作者個人經驗,特別是台灣的「成長小說」都帶有相當強的情感取向和悲劇性,描摹少年困厄、惆悵心境時,相較其他類型的作品,更多地借鏡於自我是書寫過程之必然。
〈春秋茶室〉末了,發仔跑到茶室送客出門的陳美麗面前,以自我傷害表達稚幼的愛情,這個動作可和王文興〈命運的跡線〉並觀,證明愛情,或延長人壽,其實為的都是落實自我生命的重量。然而,〈命運的跡線〉著力描繪的,屬於少年內心隱微的糾結,那自我認知的歧錯,卻是〈春秋茶室〉沒有的﹔王文興往心理描寫發展,同時也涉及了「家」所不能解決與滿足的個人的裂縫,吳錦發則把視野延伸到現實面,各有所優。〈春秋茶室〉的帶血腥氣的愛情啟發,若跟夏烈〈白門再見〉相較,則傳說中的「白門」與成長中的少年們的關係還是稍微含有喜劇成分的,「白門」是女神,也是友情的聯繫、青春的證明,成年後那出其不意卻又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隱隱可以想見的結尾,不禁使得曾經經歷輕狂歲月的讀者們都泛出微笑來﹔和李昂〈花季〉相較,則〈春秋茶室〉的情欲戲是普級電影那般地以光影推挪、跳接來表現,李昂素來不迴避情欲話題,〈花季〉中的年輕女孩隨花匠他去的路途上所作種種性與暴力的幻想,這不是溫暖優美的愛情事件,卻是理應被規入「純潔」年齡的女孩脫軌的想像與渴望,最後什麼事情也沒發生--當所有的成長小說談的都是「現實的醜惡」,李昂偏偏要反其道而行,指出人內心本有不合理的欲求,人人都有在思想與身體超越規範(包括性別與年齡的規範)的可能,幾乎是反過來給成人讀者們上了一課。
本書所收小說篇幅最長者,便是超過三萬字的郭松棻〈雪盲〉,八十年代中期發表。郭松棻小說少而精,質地稠密,具有高度的不可分割性,難以只截取一段,故整篇收入。事實上,早在我的老師梅家玲教授為二魚編選《小說讀本》,便已考慮過〈雪盲〉,也是因為篇幅太長不得不割愛﹔但我以為這篇是郭的小說中,最複雜且完整的篇章,涉及了一代中國文人痛苦的身影,和台灣殖民地長成的知識份子所遇見的文化與政治難題,同時包含了哲學的、啟蒙的主題,此次編選便希望能完整收錄。
因為政治的牽連,郭松棻曾經長時間不得回到家鄉台灣,這一羈留漂泊的形象,在〈雪盲〉中亦貫串全文。小說從阿幸仔到小學校長家拜訪寫起,錯綜寫校長與瘋女米娘的情愫,寫校長如何回憶亡兄,把亡兄留下的魯迅文集轉送給阿幸仔校長,寫校長亡兄學醫的悸怖,寫阿幸仔對於米娘的暗慕,寫阿幸仔與母親相處的零碎片段,那越洋電話裡頭卡拉達卡拉達的雜音夾在各種生死興亡消息當中,簡直如同芥川〈齒輪〉那樣的使人憂躁的幻狀了。
全篇出現篇幅最多的,除了阿幸仔,便是校長。固然,讀者可以很快發現校長在家庭生活中的不愉快,校長太太的嘮叨中可以發現,這對夫妻彼此之間是相當疏離的,而校長對於米娘近乎偏執的愛情,和對亡兄的思念,似乎都不是妻子所能明瞭的[7],反而是阿幸仔在魯迅小說的陪伴中成長,一點一滴地,或者逐漸能捕捉彼時校長內心的苦悶罷--
生前父親常說,校長是台灣人中難得的一個教育家。從年輕時代就立志作一個小學校長。必要時,校長還能說一口上品的日文,比任何一個殖民地的文官都不差。你還記得星期一的週會,校長面壁朗誦國父遺囑的聲音。遇到捲舌音時,校長都能夠把他的舌頭認真地捲上去,而發出不令人厭惡的舌音。
郭松棻的寫法素來含蓄,並未針對日治與戰後的「語言創傷」大作悲痛文章,但是,在〈雪盲〉這樣跨越時間與空間較大的小說中,語言問題畢竟主宰了知識份子與寫作者,是不能迴避的。從他對於校長的描繪,一個在戰前戰後均認真學習官方語言的教育者,可以看到台灣知識份子努力適應外在變化,符合國家機器的需求與規定,讓自己納入其中,運轉為有用的一部分,而非噤啞的受淘汰者。
而除了米娘閃現在水井旁與往事中的那雙金扣紅鞋,最使阿幸仔念念難忘的便是魯迅的〈孔乙己〉了,孔乙己悽涼的、跪作沉落的姿態,成為他往後孤獨生命中一個不可避免的自我之投射。在沙漠的留學與工作生涯,炎熱且規律無聊的日子,情欲和對魯迅的體悟微妙地並立為生活的出口﹔「回到你的國家,你也教不了你的魯迅」,這毋寧是漂浪生命一個扎痛的註腳了,十七年未曾返回台北的阿幸仔,家鄉早已成為一座巨大的城,而他卻是在美國沙漠中的警察學校教學生咕嚕咕嚕地讀著魯迅,年復一年,阿幸仔從台灣到美國,成長過程中所領略的也就是如孔乙己那般折斷了雙腳,跪落在這似乎不可變易的時代與命運中。
李渝寫溫州街,同時涵蓋了成長啟蒙的經驗,原本書中欲收錄者乃是收在《溫州街的故事》裡的〈朵雲〉,為的正是能和郭松棻〈雪盲〉相對照,這對文學夫婦以不同的筆調和文體,描寫以魯迅為象徵的一脈中國文學以及民族苦難,如何地在台灣以及海外的中國人身上,流轉,牽繫;郭松棻所寫固然深雋繁複,李渝的溫暖明淨卻也同樣動人。惟因為〈朵雲〉已在他本小說選收錄,遂改選〈菩提樹〉,背景一樣是戰後大陸遷移過來的知識份子家庭,一樣以溫州街日式宿舍為故事的空間,也一樣涉及了人如何無助且堅持地對抗著時代,以及這些傷害給予主角少女阿玉的啟蒙。〈菩提樹〉是透過阿玉的眼睛,看在台大任教的父親與學生的往來,學生看來聰敏而脆弱,實際上卻培育且實踐著某種政治的堅持,阿玉對他產生了莫名的感情--
昏懵的時光裡,倒有一件事在萌芽滋長。是什麼,阿玉不想探個究竟,不如讓他原原本本,水藻一株盪漾在海底,漂撩著夏日的沉悶和孤寂。
愛情勃發以一種懵懂但是甜美的狀態,不需要被明瞭,而需要被感覺,暈開來像霧籠罩著青春,而愛情事件也是成長小說常用來表現生命轉折的情節。〈春秋茶室〉主角的愛情挫折,來自外在社會施加的橫暴,陳美麗的墮落風塵讓少年看清了自我的無力感,而〈菩提樹〉的愛情挫折也是來自外在社會,思想澎派的學生與政治禁忌起了衝突,被迫必須監禁消耗十五年的時光,這次看清了個人的無力的,卻是疼愛學生的阿玉的父親--知識份子的痛苦的醒悟--他們的思維與熱血,是不能夠和權力的運作相抗衡的,連拯救一名學生都不能。這場悲劇在李渝寫來,仍然延續了其一貫的筆調,讓小說結尾收束在上揚而非下沉的局面;阿玉平靜的生活受衝擊,愛情的夭折與父親的絕望,一一收在眼底,她的心情也是難以排遣的,然而,人是能夠從自我生發救贖力量的:
除了蟲子的咬囓聲,在徹底的黑暗裡,樹說,倒有另一種聲音從不遠的地方傳來。
是什麼呢?阿玉問。
哦,是海,海的聲音呢。
阿玉用手攏住耳輪,努力地聽。在漆黑的庭院外,果然起伏著海水的聲音。
孤寂的生活,也就略略有了些安慰。樹說。
把你一個人關在黑屋子裡,可以做些什麼呢?阿玉問。
哦,是的,正要告訴你呢,樹說。我的口琴吹好起來了。
……你聽聽看。
他說。雙手拿起口琴,放進唇的中間。
……手肘撐扶映月的臉頰,向窗椽斜靠去頭肩,聽著聽著,阿玉終於放心了。
想像帶來寬慰,李渝〈朵雲〉、〈菩提樹〉、〈號手〉、《金絲猿的故事》等篇皆是如此,這當然涉及了王德威所論述的:「當保釣激情散盡,文革痛史逐步公開,失落的不應只是政治寄託,而更是一種美與紀律的憧憬……歷經政治的大顛撲後,他們反璞歸真,以文學為救贖。昔時釣運種種,其實不常成為敘事重點,然而字裡行間,畢竟有許多感時知命的線索,竄藏其間。」[8]
確實,政治風雲並不以直截的面貌出現在李渝的小說內,而是以提煉過後的光色出現,特定的時間,空間,特定的文化政治氛圍,決定了某些人的命運方向,「感時知命」之外也包括如何掙脫這「時」與「命」的束縛,最重要的便是心要有所寄託與拔昇了--這也正是經歷過政治運動的李渝所欲強調者,關注民族與政治,然而也須超越,才不至於走入死胡同。
八十年代初期朱天文寫〈小畢的故事〉,時間與朱天心寫眷村記憶的中篇《未了》差不多,可能都是受到「隔年畢伯伯退役下來,搬離了村子,退休俸跟河南鄉親合夥開雜貨店。彼時正值我們村子拆遷為國民住宅,眾皆紛紛在附近覓屋暫住」的觸動,台北市進行都市更新,規模地改建外表較為疏破的眷村,促使眷村出身的作家急於寫下這樣的一個成長空間的故事。〈小畢的故事〉並不複雜,講一名把母親氣得自殺的年輕男孩長成氣概昂揚的軍人,投軍的原因是「他是決心要跟他從前的世界了斷了,他還年輕,天涯地角,他要一個乾乾淨淨的開始」,小說裡清淺卻爽朗乾淨的世界,眷村雞犬相聞的人際交往,無不是具體而為地展現出一個「有信仰的時代」。黃錦樹觀察朱天文二十年來的寫作變化,發現改變最多的卻只是表面場景而不及其他[9]﹔即使朱天文明明經歷了許多,包括了曾攻擊「三三」的「鄉土文學運動」,翻天覆地的各種政治運動和台灣都會的擴張,和她所參與的帶著模塑本土意識功能的台灣新電影工程。在真正觸及都會本身的活動的〈炎夏之都〉以前,她書寫的都算是家族/族群記憶,即外省族群(尤其是眷村)戰後在台灣島上的生活與心境,一個有波折但仍值得信賴的時空,〈小畢的故事〉正是這個時期的作品。
參、
三十幾歲一輩作家的成長小說,不可不提袁哲生。如果說《寂寞的遊戲》中的躲藏哲學,雖然袁的個人風格尚未完全確立,其中透露出來的優美與凝重卻使人印象深刻,到了《秀才的手錶》一書,大量追憶自我的童年,根據序言所寫,確實是以自身的童年記憶為底寫成的小說﹔他雖然在背景上屬於所謂外省第二代,卻能在小說對白中圓熟書寫閩南話,增添了人物的活氣與幽默效果,彷彿一則長長的,以溫暖逗趣的筆調完成的鄉土傳奇。被歸類為具有外省背景、主要在台灣成長的小說家,如文學讀者熟知的白先勇、李渝、朱天文、朱天心、駱以軍、孫瑋芒等人,在大範圍上均傾向書寫城市,則袁哲生幾可視為一異數,他擅長且集中心力表現的乃是鄉土題材,且並非繼承七十年代以來陳映真等人提倡的具有批判性的寫作,而是透過少年眼光去注視那仍然雞犬相聞、未經過開發的土地聚落,以及通過幼稚的感受與想像詮釋過的,具有魔幻與傳奇特質的成長過程,特別是在確立其風格的《秀才的手錶》,以及後來的《羅漢池》。袁哲生曾自言喜愛沈從文與汪曾祺的小說,確實,他自己的作品中也透露著一份烏托邦式的,對於純美世界的想望,且通常就是以自己成長的地方當作烏托邦的藍本,真正實踐了李渝提過的「鄉園」與「心園」互通的想法,因而筆下也時時流露暖意。另一方面,他有意在鄉土書寫中,加入對身世的反省,只是較為內斂,不如朱天心或駱以軍那樣大張旗鼓﹔本書擷取的〈天頂的父〉:
「嗯唉?﹗日也哭,暝也哭,吃飽哭,哭飽吃,外省的講勿通啦。」阿公的聲音雖然激動,但是手上剃刀的動作還是非常細膩,不愧是燒水溝的頭號師傅。
這是我第一次錄下「外省的」三個字。
在我還沒錄下「爸爸」這兩個字之前,我老爸的代號就是「外省的」。
坦白地說,自從我和武雄一樣學會開口說話之後,燒水溝便再也不是從前的模樣了。
「外省的」在一整本燒水溝傳奇的《秀才的手錶》中,出現的部分不多,也沒什麼機會表白自我,後來就「在外島無去了」--然而,父親的消失,卻是「我」進入世界的開始--開始脫離單純的「錄音機」生涯,使用語言,學習如何定位自我,表達思想。開始說話後,燒水溝再也不是從前的樣子了,因為語言作為個人心靈與他者溝通的媒介,畢竟仍需要一層轉譯的手續,那真純的只存在於自我的沉默中的燒水溝,隨著少年的成長而變化著。
袁哲生小說中戲謔的部分,一直是讀他小說的樂趣之一,這方面倒是就戰後台灣文學裡笑謔一脈,延續了王禎和、林宜澐、郭箏等小說家著力經營者。但是,袁哲生的笑謔絕非王禎和式趨於鬧劇的諷刺,而是增添鄉土淳樸人物魅力,使小說別有一份親近,不張致的。而本書選入的郭箏〈彈子王〉,如袁可以流利運用各式閩南俚語般,也同樣暢快地運用各種青少年族群的話語,增強作品的節奏,小說內逞強胡鬧、意/義氣用事且對未來與現實仍有一份迷惘的少年們,耍酷中流露著一絲可愛與軟弱--通過少年群體來表現成長主題,本書中除了吳錦發、郭箏,還有許榮哲〈那年夏天〉亦屬於此類,少年以熱情秘密守護著的國度,必須和現實碰撞,產生裂隙,才能促使他們反視自我與世界的關係。〈那年夏天〉就氣氛與表現方式來說,頗類似〈春秋茶室〉和袁哲生小說的混合體,就與現實問題的結合來看,涉及美濃水庫興建問題的許作無疑與吳錦發作品可以參看。
至於早慧,但近年來才以連綴體長篇舖寫國族寓言、性別交鋒與城市光怪的駱以軍,已因為各種選本拱衛而具備當代經典資格的〈降生十二星座〉固然也在繁複的架構中涉及成長議題(畢竟,羞澀、猥褻但是歡快的童年與青少年時代,本是駱以軍小說中取之不竭的場景),惟此篇過於常見,我以為更應該提出的是黃錦樹認為乃是「詩的轉折」後的第一部小說《妻夢狗》,那揭露「自我的技藝」的重要結集[10]
這部小說藉著大量華美繁複的獨白語言書寫內在,囈語中如一名神經質的詩人呶呶而徘徊,所有的奇想魅影均指向善感的、傷害的核心,那在親子、愛情以及更多人際關係中碰撞擦痛的靈魂,就這一點來說,在《妻夢狗》中駱仍在追尋(或迴避?)了解的可能,愛的焦慮,唯恐自我終於在無數轉譯與記憶過程中被扭曲,稀釋。駱以軍曾自言這是他寫得最沒有拘束的作品。《妻夢狗》中有一部份短章命名為〈夢十夜〉,題目取自夏目漱石同名作品,以不可解的夢境暗示真正的情感,其冷澀、費解,更增添解讀與想像的空間,甚至可以進一步說,當中不無私淑川端康成《掌中小說》的味道;駱以軍〈夢十夜〉的夢境,包含了逃難、病痛、愛欲、死亡等景觀,可以說是日後作品的雛形。本書擇取〈ㄩ〉、〈川端〉兩個章節,篇幅均幼;〈ㄩ〉的故事空間是睡眠中的教室,主角暗地裡伸過手,越過好友永昌兄,碰觸戀慕的女子ㄩ的胸乳,ㄩ並未閃躲,默默進行著的,私密的一場愛情對話,睡眠結束後,永昌兄卻把事情揭露了,「完了。我想。寂寞的愛意的私語和美的顫索全要變質為猥褻的醜行。完了」主角在美的墜落和道德的恐懼中,以哀示的眼神望著友人,「由於一向永昌兄對我即表現著拘謹的愛惜,我知道他對我懷抱著崇拜揉合著顛覆的複雜情緒,便保持著被崇拜著若即若離的狡猾的冷漠」,和〈春秋茶室〉一樣,不只是難以啟齒的愛情,還包括著和同性朋友之間情感與關係強弱的角力,帶著負氣、輕忽以及其他的什麼。最後,永昌兄突然放棄了嚴厲的追問,看著ㄩ羞赧的臉,他突然明白了永昌兄或許也跟他一樣,正被無出口的愛情所纏困--那麼,他對ㄩ的戀慕和行動,對自己的好友也是一種傷害吧--一經領悟,則小說的重點不再是愛情,而轉為一種諒解了,雖然必須通過那無法公開張揚的愛情才能明瞭。另一篇〈川端〉,地點一樣是教室,在嘈雜中,川端康成以女性般敏感優美的樣貌存在著,主角逢著知音那樣地感受著這個老人:「同樣是幽微易感如曲折巷弄底心靈呵。同樣是墊著腳尖著魔地在發狂邊緣如同調得太高的琴弦上踩空著。老人像貴族那樣被眾人不理解地拱衛著。」這樣的類比洩漏了主角(或作者?)對自我的不合時宜的體會。
我該說一句什麼呢?我突然發現自己是那麼地愛他而淚流滿面。
「我被你騙了。」我把手勒在他的脖子上。是嗎?他怯懦地問了一句。雖是個老人,但她的身軀像沒經驗的的處女一樣柔弱溫順。我是那麼地愛他呵。
教室裡的人們哄鬧了起來。
不只是知音,還像戀人與神明那樣存在著的川端康成,必然是主角閱讀或寫作過程中一道強大的指引、召喚和阻礙吧,彷彿最後的誘惑那般地橫阻在胸口。「我被你騙了」,被騙了什麼呢,是川端以美的意境與形式所誘引而出的,主角深藏的脆弱自我嗎?耽溺,而且孤寂的……。這是美夢也是噩祟,要結束這種欺騙與引誘的關係,唯有死亡--並且是張揚的,在青春的教室裡當眾勒殺神明,四周的嘈雜帶來的只是疏離,然而「我」碰觸且殺害川端的瞬間卻是痛苦且熱愛。這是屬於駱以軍的,包括少年的「我」與作家的駱共同之沉墜與覺悟。
張惠菁先以小說名世,近來的散文創作力卻似乎更強於小說﹔她那知性的、十足現代生活的散文,與著重結構、隱喻和崇拜神秘力量的小說,是很不一樣的。本書收錄的〈哭渦〉,是某一屆台北文學獎的得獎作品,該屆張惠菁同時以〈先後〉一文奪得散文獎,這兩篇都包含了兄妹/情欲這樣帶著危險意味的主題,而小說更強烈地展現了張惠菁隱喻的天賦與對神秘的愛好。
〈哭渦〉主要講的是一名父母很年輕時便生下的少女,母親在生產後死去了,父親僅在嬰兒的記憶中留下驚鴻一瞥的印象,也失卻了蹤影﹔後來,哥哥出現了,少女和哥哥住在一起,窺看兄長情欲上的往來,那了解且理所當然的敘述口吻彷彿她是洞視著一切的。小說中還穿插著《搜神記》與伊底帕斯神話,以及和少女交往的男子小節,和臉上的「哭渦」﹔關於小節的描寫不算很多,他的作用在於引起了少女對於自己臉上「哭渦」的注視,以及對於哭泣和罪孽的辯証。伊底帕斯直接與間接地造成了父母的死亡,他剜下的眼睛流著眼淚,償還著宿命的罪,而少女出生亦同樣造成了母親死亡和父親必然的缺席--他在多年後以哥哥的名義重新降臨少女的生活,演出疏離的親密,隔壁的床戲,然而那宿命之傷害從出生時便已造成,當她十七歲時流掉了小節的孩子,昔時母親也是十七歲時把她拋入世界,把自己拋進過去--
天黑了。週遭逐漸安靜下來。十七歲的罪人初始蜷縮著身體側睡一如母親腹中的胎兒。漸漸她舉起手來,對著路燈透進窗格而在旁邊牆壁上形成的光塊比手畫影。這是鹿。這是狗。這是老鷹。這是吐信的蛇。這是馬。這是罪人。因她害死了自己的母親,窺看自己的父親。
少女的成長在於領略悲劇,領會了自己和「哥哥」之間的牽聯,以及這虛偽的關係內絞纏的死亡、慾望和傷害,當她逐漸回憶起母親,父親,和自己的誕生,固執地認定了自己正是罪孽的樞鈕,使倫常倒轉彎曲的關鍵,那注定了的「哭渦」未承受過任何眼淚,罪人的罪並未如伊底帕斯那樣藉著眼淚洗滌。即使那只是徒勞的洗滌。
談論宿命,書寫倫常,〈哭渦〉可說是當代版的「家變」,又一次的家庭崩壞,只是這並非王文興所指陳的,因為都會文明和人內在的惡心理的互動,而是呈現了一種神話般的,迷離的原罪意識,且如前面談到的,因為典故的使用,因為筆調,因為情感出發與詮釋的方式,字裡行間盪漾著神秘的氛圍。較張惠菁的神秘猶有過之的是伊格言的〈鬼甕〉,這位來自南部的新銳小說家,能以詩般精緻靈韻的語言完成小說文體,意圖接壤現代與鄉土,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