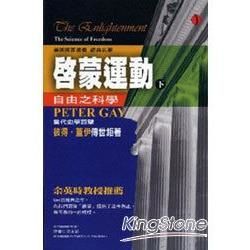這是一本很令人動容的著作,不但具備學術研究的嚴謹,且雅俗共賞,適合大眾閱讀,有極高的可讀性,喜歡讀史的人,能從本書中獲得閱讀的喜悅。
蓋伊學問淵博,文體優雅,主要論點信而有徵。這部煌煌鉅著共一千餘頁,百餘萬字,出版後廣泛獲得學界的激賞,並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其經典名著的地位屹立不搖,在當代同類研究中已無人能出其右。
啟蒙運動是蓋伊一生用力之所在,這部著作開啟了他一生從啟蒙運動以降的系列精彩歐洲社會與歷史的研究與著作,並奠定其史學巨擘之地位。
全書由《啟蒙運動: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1966)、《啟蒙運動:自由之科學》(1969)兩本相關卻又獨立的書所構成,作者將全書內容分三部份:Ⅰ.對古代的訴求、Ⅱ.和基督教的緊張關係、Ⅲ.現代性的追尋。作者表示,第Ⅰ、Ⅱ部別代表「正」、「反」,第Ⅲ則代表「合」,安排為辯證性的三部曲,是為了反映啟蒙思想家大體的心路歷程,企圖全面性地探討啟蒙運動。
《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與《自由之科學》為各自獨立又互相聯繫的兩部作品,是彼得.蓋伊對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精彩再詮釋的姊妹篇。
在《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中,蓋伊分析了啟蒙思想家如何利用古代異教思想家作為資源,擺脫自身繼承的基督教文化遺產。
《自由之科學》則可視為是一部啟蒙運動的社會史,書中,蓋伊描述了啟蒙思想家身處的時代,他們的行動綱領、進步觀、科學觀、藝術觀、社會觀和政治觀。作者解釋了啟蒙思想家與其時代的複雜互動關係,指出他們的思想既汲取自時代氛圍和從中得到支撐,復有一部分反對這氛圍和開風氣之先。他們部分是時代的領導者,部分是其縮影,部分是其反對者。作者指出:「這關係是錯綜複雜的,而如方才說過,啟蒙思想家與其環境時而敵對,時而友善。但不管有多錯綜複雜,不了解它們,就無由給啟蒙運動下一個充分定義。可以換一種方式說:儘管約翰生(Johnson)與伏爾泰(Voltaire),波普(Pope)與休謨(Hume),或衛斯理(Wesley)與萊辛(Lessing)的歧異處所在多有,但共通處一樣所在多有。
本書雖然把重點放在伏爾泰、休謨和萊辛,但沒有忘記其他人。例如,他說:「……我們當然不可忘掉狄德羅和萊辛的美學是不同的,不可忘掉休謨和伏爾泰的政治哲學是相異的,不可忘掉不同啟蒙思想家有關進步、科學、教育和其他課題的觀點涵蓋幅度頗寬的光譜。我把這些差異都記錄了下來——本書上下兩冊會那麼長,主要原因在此。這也是為什麼我對啟蒙思想家的一般定義不涉及他們的政治或美學觀念。以這種方式,我設法既忠於歷史的豐富性、微妙差異性和個人癖性,又忠於共性和完形(Gestalten)——它們都是啟蒙運動之所以為啟蒙運動的原因。」蓋伊的精闢評價為讀者打開新的視野,讓人對啟蒙運動的批判方法和其人道及自由願景有更深入認識。
作者簡介:
彼得‧蓋伊(Peter Gay)
一九二三年出生於柏林,一九三八年移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目前為耶魯大學史特林(Sterling)史學教授、古根漢與洛克菲勒基金會學者、劍橋邱吉爾學院海外學者。歷獲各種研究獎如海尼根(Heineken)史學獎等,其著作多次獲美國國家圖書獎。
章節試閱
第Ⅲ部
現代性的追求
The Pursuit of Modernity
所謂啟蒙,就是人之超拔於自找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是一種必須靠他人指引、無能於自行運用理智(Verstand)的狀態。若非缺乏理智所致,而是因為缺乏決心和勇氣,不敢不靠他人指引而自行運用理智,這種不成熟狀態便是自找的。勇於求知吧!因此,鼓起勇氣去運用你的理智吧!這便是啟蒙的座右銘。
── 康德(Immanuel Kant),〈答何謂啟蒙〉
為什麼只因締建一個大型共和國的實驗包含著新東西,我們就要反對它呢?美國人民一向不同凡響之處,不正是他們雖尊重從前時代和其他國家的經驗,卻不盲目崇拜古人、慣例或顯赫者的意見,而會遵從自己的明智判斷、切身處境和自身經驗的建議嗎?因為這種雄糾糾的精神,美國舞台上已經出現過許多有利於私人權利和公眾幸福的新變革,它們既會讓後代子孫感激,也為世人樹立了楷模。
── 麥迪遜(James Madison),《聯邦論》(The Federalist)第十四篇
各帝國的歷史是一部人類的悲慘史。各科學的歷史是一部人類的偉大與幸福史。
── 吉朋(Edward Gibbon),〈文學研究〉
1
膽氣之復甦
The Recovery of Nerve
一、現代性的前奏:膽氣之復甦
1在啟蒙運動的世紀,受過教育的歐洲人向一種新的生命感(sense of life)醒轉。他們感受到人駕馭大自然與人自身的力量大大增加了:各種循環不斷困擾著人類的磨難──疾疫、饑饉、生活的朝不保夕和夭折早殤、兇悍的戰禍和搖搖晃晃的和平──看來終於屈服在人類理智的批判性檢視之下了。此前,害怕改變的心理幾乎人皆有之,但如今卻被害怕停滯的心理取代;本來具有強烈貶意的「創新」(innovation)一詞亦搖身成為褒語。保守主義觀念的出現,本身就是普遍求新求變之風的產物,因為在一個寂然固定的社會裡,根本沒有保守份子用武餘地。在在看來,在人與自然的角力賽中,人已轉佔上風。
這之前,人未嘗沒有信任過自己力量的時候,卻從沒有像這一次來得理直氣。十八世紀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人的自信是建立在現實基礎上而不是烏托邦式空想。自然科學家、商人、官員和哲學家的自信滿滿不是一種用來掩飾無能的偽裝,而毋寧是出於對理性與行動力量的信賴。在打造這種新氣氛的過程中,啟蒙思想家扮演著一個戰略性角色,而他們會著手設計各種方案(社會、倫理、政治和美學方案),為的是促進自由,而不是要為無政府狀態鋪路。啟蒙運動也許是一種革命性新心態的產物和反映,但它也是這種新心態的主要推手之一。
然而,各種古老的災殃並未終止(不過倒是會裝成沒以前那麼可怕的面貌出現)。戰爭、疾疫、饑饉、不安全和不公義的陰影繼續籠罩人的生活,抑制他們對未來的期望。進步本身帶來了新的受害者,而許多人的生活之所以獲得改善,正是以其他人痛苦的加劇換來的。在當時大多數人看來(約翰生是其中之一),十八世紀仍舊是一個須忍受者多而可歡欣者少的時代。新的思考方式主要是保留給出身好、能文善道或幸運的人:鄉村與城市裡的低下群眾少有能分享到這種新趨向者。不管是思想觀念還是生活方式方面,西方社會就像是同時活在幾個不同的世紀裡似的。法國啟蒙思想家杜克洛(Duclos)在一七五○年指出:「那些住在離首都一百英里遠的人,其思考與行動模式亦距首都居民一個世紀遠。」窮人貧窮如故,英國如此,瑞士、法國與那不勒斯亦復如此。母親繼續會殺死她們的非婚生子;普魯士與俄國的統治者雖然自稱根據啟蒙原則治理國家,但這兩國的農奴繼續過著原始的、近乎次人的(subhuman)生活;在自詡是世界最文明國家的英國,窮人繼續以酒澆愁,繼續因酗酒短命。晚至一七七一年,伏爾泰猶感慨說:「在有人居住的世界部分,有一半以上面積仍然是住著一些過著近乎原始狀態恐怖生活的兩腳動物,他們食不足以餬口,衣不足以蔽體,極少能夠享受語言這種恩賜,極少意識得到自己過得有多可憐悲慘,渾渾噩噩地活著,渾渾噩噩地死去。」
因此,對很多人來說,時代進步所意味的,不過是壓迫、剝削他們的力量換上前所未見的新裝。尊卑模式是在慢慢改變,但尊卑之分依然倔強;有產階級則找到了合理化他們忽視或剝削低下階層的新理由,而不管博愛的基督徒和人道的啟蒙思想家再怎樣抗議,這種忽視和剝削繼續存在。肺病取瘟疫而代之,而有人道心腸的人則把目光從農村的窮人轉向城市的窮人。因糧食短缺而引發的暴動是減少了,但仍偶有爆發,繼續威脅著全歐洲搖搖晃晃的公共秩序。越來越多受害者把無奈和怨氣發在沒有自衛能力的天主教徒或胡格諾派信徒(Huguenots)身上,要不就是發在貪婪的雇主身上。讓農業得以合理化的圈地運動,長遠來說固然嘉惠了包括窮人在內的大部分人,但挨飢忍餓者卻等不了那麼久。在英國,流離失所者擠滿臭兮兮的貧民窟,而在法國,失業農村勞動人口在市郊連群結隊行乞或搶劫。經濟繁榮去到哪裡,可憐景象都如影隨形。幾乎十八世紀的所有進步 ──不管是工業、農業、教育還是政府管理上的──都是福中帶禍的美事。但它們仍然是美事。雖然消極和悲觀心態繼續殘存(甚至殘存在啟蒙思想家身上),但對那些有幸受惠於時代大潮流的人來說,展開在他們眼前那幅前所未有的怡人前景,仍然是讓人興奮雀躍的。
我說「前所未有」,是因為這種心靈狀態雖然幽微難辨,也大概是無法證明的,但我確信我準備要描述的十八世紀氛圍在人類歷史上是見所未見的。它絕不僅僅是一些古已有之的態度的重拾,而它表現出的自信,也是任何最自信的古代理性主義者不敢想像的。我並不是說所有古代人一律不快樂,或一律把一切委諸運氣:他們也會研究醫術、築路與管理領土。他們也會有志於過理性的生活。但他們意識到,面對鋪天蓋地的冷酷現實,這種志氣只是徒勞的夢想。然後,到了羅馬帝國早期,他們的消極性更深沉也更普遍了。基督宗教的世界觀比它所取代的世界觀還要灰暗,而它既是這世界觀的肇因,也是其病徵。曾研究過這部活力與理性衰竭史的默里(Gilbert Murray)在一個著名的段落裡指出,隨理性衰竭而來的是:「苦行主義的崛起、神祕主義的崛起,某個意義下是悲觀主義的崛起。人們失去了自信,失去了對塵世生命的寄望,失去了對人類努力的信賴。他們不再相信耐心探索可帶來什麼,只渴盼得到絕不會錯的天啟;他們對國家福祉漠不關心,一意轉向上帝。」默里給這種「屬靈感情的白熱化」一個名字:「膽氣之失落」。十八世紀的經驗(我準備稱之為「膽氣之復甦」)卻剛好相反:那是一個神祕主義沒落的世紀,人們越來越對人生充滿希望和信賴努力,熱中於探索和批評,世俗主義與日俱增,而且越來越願意去冒險。
這種態度──值得再提一遍──是嶄新的。文藝復興時期因為把歷史看成是一則衰落的故事或各種無情循環上演的舞台,人的無能顯得相當突出。其時,人文主義學者(humanists)仍然依違於新柏拉圖主義者的認命心態和煉金術士對無窮力量的夢想之間。命運之輪(fortune’s wheel)是他們用得最多的形象化比喻:一切都會變動不居的,國家必會由盛轉衰,家族必會由榮轉枯。哪怕是馬基維利(Machiavelli),仍然相信人儘管不懈的努力,也只能指望搶到命運女神手中的一半東西,其餘一半將始終掌握在反覆任性的女神手裡。首先與這種歷史宿命論分道揚鑣的人是培根(Bacon)和笛卡爾(Descartes)。在《論方法》近尾聲的一個感人段落裡,笛卡爾談到有一門實用科學說不定將可使人成為「大自然的主人和佔有者」,又說這科學可以帶來的好處「不只是數不清的技術進步,讓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享受地球的各種礦產、各種便利,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保護我們的健康,而健康無疑是人最重要的一種幸福和一切其他幸福的基礎」。之前不久,培根才刻意重提一句幾已被人忘掉的羅馬古諺:「人是自己命運的設計師。」又依這種精神制定一個知所謹慎節制卻極為雄心勃勃的行動綱領。
到了啟蒙運動的時代,這種自信態度在新哲學的熱愛者之間已屬稀鬆尋常。洛克(Locke)在筆記裡這樣寫道:「有一大片知識田野等著人去加以利用和受益」,換言之,人可以去「找出一些縮短和減輕勞動的新方法,或是精明地調配好幾種催化物和緩化物以帶來一些新而有益的產品,讓我們的財富(即任何可為生活帶來便利的東西)得以增加或更好保存。」然後,他又意味深長補充一句:「所有這一類發現,皆為人之心靈所勝任。」比乃師洛克更注重內心生活的沙夫茨伯里伯爵(Lord Shaftesbury)則把前述古諺運用在人的律己上:「有智慧和能幹的人要是能夠在內心建立起秩序、平靜與和諧,就是為自己奠定了一個持久的穩固基礎」,而這樣的人將能成為「自己人生與命運的設計師」。不奇怪地,這諺語與這心態也傳播到英國的美洲殖民地: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一七七○年把「人是自己命運的設計師」列為他最喜愛的格言之一,而在那一些年前,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則推行一個殖民地間的科學合作計劃,希望以此解開自然界的謎團和擴大人「駕馭物質的力量,使生活的便利或快樂能以倍數增加」。在德意志文學界,詩人們在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的神話中發現了新意義,高舉它為培根著名口號「知識即力量」的象徵。「我有一個看法,」年輕的康德帶點謹慎口氣這樣說,「有時候我們應該對自己的力量寄予若干高貴的信賴。這樣的自信可以為我們的努力增添活力與氣魄,對真理的探索具有高度的裨益。」稍後,在《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中,康德的語氣不再猶豫,斷言人的才智是世界中的一股活潑力量。他指出,理性會一手執著它的原理、一手執著實驗,逼近自然,從中學習──但不是抱著學生的被動態度,而是像法官一樣,「要求證人回答他設定的問題」。實務家亦有志一同,例如,伯明罕印刷商暨地方文史工作者赫頓(William Hutton)在一七八○年就以其時代的可愛自信精神呼應了培根。「每個人的命運都掌握在自己手裡。」他說。
2
「膽氣之復甦」是許多力量的共同產物:不管是自然科學的壯觀成就、醫學的進步、禮儀的改善、人道感情的成長、傳統社會層級的慢慢剝落,或是糧食生產方式、產業、人口模式上的變遷,全都指向這同一個方向。這也是一個各種新科學被發明出來的時代,發明它們的人是哲學家(大都是啟蒙思想家),而目的全都是為了擴大人駕馭環境的力量。啟蒙運動產生了各種休謨所謂的「倫理科學」(The moral sciences):社會學、心理學、政治經濟學和現代教育。
時代需要這些新的科學,因為那是一個行政管理上極為動盪的時代,負責進行改革的政府官員一再與既有利益團體和傳統習尚發生衝突。其時,理性化的公共管理與理性化的統計學還處於強褓階段,但它們已預示著現代福利國家的來臨。雖然行會(guilds)和教士階層沒落的主要受益者是工業和商業資本主義,但同時受惠的還有負責管理事務的政府僱員。中世紀的福利社會是以慈善單位、不容質疑的社會層級制和基督宗教的博愛理想為基礎的。但到了十八世紀,至少是在歐洲大陸上,這些慈善團體大都失去了經濟基礎與情感誘因:經歷了一段無政府時期和一些有時事出偶然的殘忍暴行之後,世俗意識開始抬頭。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驅逐了耶穌會,沒收其財產,用之以賑濟,而其他國家的君主則奪去教會辦的濟貧院、醫院、孤兒院和學校──要嘛是直接據為己有,要嘛是置之於公共監督之下。在整個歐洲大陸,賑濟機構的部分國有化都與教育機構的部分國有化齊頭並進。
雖然這種社會技術尚屬粗淺,而且因為根深柢固舊習俗的頑抗而進展緩慢,但理性在產業與農業上的應用仍然帶來了革命性的後果。及至一七六○年代,改革的節奏已經快得讓人目眩,使為之驚恐的人與為之滿足的人幾乎一樣多。例如賓夕法尼亞的斯密牧師(William Smith)就抱怨當時的各種建設「是沒有多少深度的急就章。增補、改動和修飾此起彼落,沒完沒了。好一幅推倒又豎起、豎起又推倒的永恆景觀」。他可不是面對進步而唯一茫然的人,絕非反動派的約翰生同樣有所嘀咕:「這時代發瘋地追逐創新,世界一切行當看來都行將改頭換面。吊死人犯的方式看來也行將換新,泰伯恩刑場(Tyburn)可別想不受創新的怒火波及。」但為進步歡呼喝彩者仍大有人在:一七七○年代的《大英百科全書》驕傲地告訴讀者,說十八世紀的「各種新發現與改善」已為「這個不可征服或宰制的國家流布上一層榮光。」
這種流布異常迅速,因為它是有組織性和自動自發的。十七世紀為促進交流而出現的科學學會是十八世紀仿效的楷模。啟蒙時代是一個學會的時代,各種醫學學會、農業學會、文學學會各有各的獎項、期刊和參加者眾的會議。在學會內外,在工廠、作坊和咖啡館,知識都從傳統的桎梏中解放了出來──它們往往不管美學考量和宗教拘束,只一心一意追求實效性。在一六六○至一七六○年的一百年間,英國的專利權發給件數是平均每十年六十件,但到了一七六○至九○的三十年間,平均值卻升高至每十年三百二十五件。與浪漫的傳說相反,只有少數專利權擁有者是神思煥發的孤獨天才。該時代的代表性發明家是瓦特(James Watt),他充分體現了理論與實用、科學與技術的結合。早在一七五三年,當瓦特還是年輕人時,狄德羅就已經在《對自然的解釋》為他預畫了肖像。在這本小書中,狄德羅透過反覆引用培根的比喻,闡明十七世紀諸種思辨與十八世紀諸種現實的關係,闡明哲學與社會變遷的關係。狄德羅力主,理論與實用兩方面的思想家必須聯合起來,以折服「自然界的抵抗」。帶玩心的思辨就像耐心而系統的實驗,皆為重大發現發明所不可少:兩者結合在一起可以讓自然哲學家成為一個征服者,成為可把採得的花粉轉化為蜂蜜的蜜蜂。在狄德羅的書頁裡,藝術是預期著自然的:瓦特的蒸汽機(工業革命最決定性的一項發明)只是狄德羅這個理想最卓異的體現,因為要不是有虎克(Hooke)和牛頓的發現,要不是有當時全歐洲科學家的研究工作,不可能會有瓦特的發明。蒸汽機的觀念絕不是他看到一壺煮沸開水時跳入他腦子的:他是做過一些精密實驗和進行過系統思考以後才造出他的模型的。
帶來機械創新的同一種實用哲學也帶來了讓這些發明可以廣泛應用和獲利的新制度。工廠、勞動的細部分工、工人與管理者的紀律,以及信用制度和運輸的改善,這全都像蒸汽機或飛梭(flying shuttle)一樣,是刻意和理性的發明。它們名副其實是(就啟蒙時代對這個字的理解)哲學性的:誠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指出,他時代的一些改進是「由那些被稱作哲學家或抽象思維家的人做出的。他們的職業就是不從事任何具體的工作,只是觀察一切」。而約翰生自己的經濟觀雖然原始,但仍捍衛斯密對政治經濟學進行哲學反思的權利:「沒有什麼比貿易更需要哲學來闡明的了。」他說。
第Ⅲ部現代性的追求 The Pursuit of Modernity所謂啟蒙,就是人之超拔於自找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是一種必須靠他人指引、無能於自行運用理智(Verstand)的狀態。若非缺乏理智所致,而是因為缺乏決心和勇氣,不敢不靠他人指引而自行運用理智,這種不成熟狀態便是自找的。勇於求知吧!因此,鼓起勇氣去運用你的理智吧!這便是啟蒙的座右銘。── 康德(Immanuel Kant),〈答何謂啟蒙〉為什麼只因締建一個大型共和國的實驗包含著新東西,我們就要反對它呢?美國人民一向不同凡響之處,不正是他們雖尊重從前時代和其他國家的經驗,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