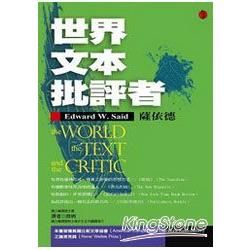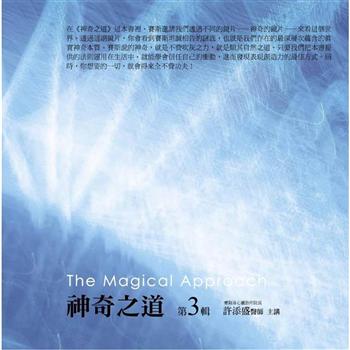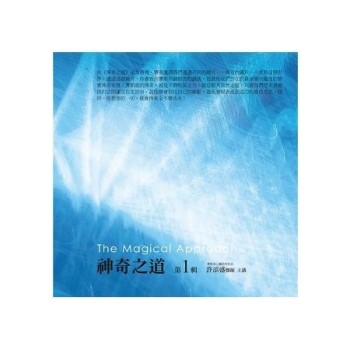本書是薩依德於1969至1981之間完成的系列文字,這些文字涵括了當代文學批評裡的四種主要類型,分別是實用批評、學院式文學史、文學賞析與闡釋和文學理論。薩依德在本書中更試圖超越上述四種類型所進行的嘗試,即對這些批評活動所奠基的專業和慣例賦予特色。
薩依德論述了文化的特質,認為文化權力絕不小於國家權力,文化常常與國家、家園、共同體和歸屬的一種盛氣凌人的含義相關聯。他認為假如文化創造了讓人們感到有所歸屬的環境和共同體,那麼,它也將一直存在著對於文化的抵抗。這種抵抗又往往出於宗教的、社會的或者政治的原因,而採取了徹底的敵視形式。
薩依德同時討論了文本與現實世界的關係,認為,文本生產是一種「世界化」的過程,不存在不食人煙的離世文本,文本一旦產出就構成了「文本世界」。文本「供應世界、占領空間、隨著讀者對它的謄寫和閱讀而坐大」,因此只有聯繫著文本與世界的「世俗批評」,著眼於文本背後政治權力的生產以及知識霸權的再現,通過誰的再現、如何再現和再現什麼的檢視,才能析離出文本在現實世界中的作用。
薩依德更主張批評家應與下面兩者保持距離,一是批評理論,二是權威體制的既有思考。他提倡批評家應對歷史、政治價值觀、社會價值觀與異於我們的生活經驗保持自由意識和獨立思考,不向權威靠攏,也不向權力低頭。而這些特徵在他的作品中展露無遺,更有別於其他的作家和作品。
學界咸認為薩依德在本書中為批評理論領域提出了新方向。
作者簡介: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文學與文化評論大師、後殖民思潮先驅、也是一位特立獨行的集大成人物。薩依德1935年出生於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1950年代赴美國,取得哈佛大學博士,1963年起任教哥倫比亞大學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所,這位知名的巴裔美籍學者,也公認為是巴勒斯坦獨立運動在西方最雄辯的代言人。2003年9月24日薩依德因白血病逝世。
薩依德著作等身,尤以「中東三部曲」:《東方主義》(Orientalism)、《巴勒斯坦問題》(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遮蔽的伊斯蘭》(Covering Islam)開啟「東方學論述」場域,影響了整個西方對東方研究的思考與研究的方向。薩依德尚著有《世界、文本與批評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最後的天空之後》(After the Last Sky)、《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以及他的回憶錄《鄉關何處》(Out of Place)等書。其作品已被譯為二十四國語言,並在歐洲、亞洲、非洲、澳洲等地區出版。
章節試閱
第1章
世界,文本,批評者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加拿大鋼琴家顧爾德(Glenn Gould)自一九六四年走下音樂會舞台以後,工作範圍就只限於灌唱片、上電視、廣播。關於顧爾德是否從來都是,或有時候是,某一首鋼琴曲令人信服的詮釋者,批評者的意見不一,但是大家一致公認,現在他的每一次演奏至少也是不同一般的。顧爾德近年來如何運作,有一個實例正適合在這裡談談。一九七○年間,他發行了一張演奏李斯特改編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的唱片。除了顧爾德選中這首曲子出人意料(即便顧爾德這樣極端古怪的人物選這一首都顯得奇怪了)之外,灌這張唱片另有一些怪異之處。就鋼琴演奏者的觀點看,李斯特改編貝多芬不但是十九世紀之事,而且是十九世紀改編作品中最異於尋常的面向:把音樂會體驗改頭換面成演奏家盡情的自我表現還不滿足,甚而侵襲其他樂器的文獻資料,把它們的音樂變成鋼琴家炫耀技巧的機會。多數的改寫曲不免聽來厚重沉濁,是因為鋼琴往往企圖複製管弦樂團的質地。李斯特的《第五號交響曲》比起多數改編曲是較不那麼唐突的,主要是因為非常巧妙地簡化成為鋼琴曲,但是即便在琴音最清澈的地方聽來也不似往常的顧爾德。他的琴音本來是所有鋼琴家之中最清澈而不加修飾的──他正是因為有此風格而能把巴哈的對位法變得好像是一種視覺體驗。總之,李斯特的改寫曲完全是另一種語法,顧爾德卻非常得心應手。這張唱片的李斯特風味十足,一如顧氏以前的巴哈風格那麼道地。
奇的還不止於此。和主打的這張唱片一併發行的另一張是一段相當長的非正式訪談,我記得訪問者是一位唱片公司主管。顧爾德告訴這位主管,他之所以逃離「現場」演出,是因為他自己養成了不良的表演習慣,即在風格上誇張的舉止。例如,他在蘇聯巡迴演出期間,他發現,如果場地是大型會堂,為了加強「迷住」並滿足三樓聽眾的效果,他就會歪曲巴哈組曲的樂句──說到這裡他便示範了一段歪曲的樂句,之後又把這一段再彈了一遍,證明沒有聽眾在場時他彈的正確得多也比較不誘惑人。
從這個情境──改寫、訪談、示範的演奏風格都包括在內──找出諷刺,也許嫌粗糙了些。但是這符合我要說的要點:凡是一方面包含美學的或文學的文獻與經驗,另一方面牽涉批評者的角色及其「現世性」(worldliness)的情況,都不可能是單純的。顧爾德的對策的確有些像在嘲弄我們為了要掌握現世與美學事物或現世與文本之間的關係而執行的方法。這位一度是為了音樂而自我鞭策極嚴格的演奏者代表,現在變成一個不知害臊的炫技家,主要的美學立場應該比一個音樂娼妓好不到哪裡去。這個人把自己的唱片當作一個「首度」推上市場,而且添加了不是音樂的東西,而是吸引人注意的個人訪談製造的即時性。此外,這一切都固定在一個可以用機器一再重複的物件上,這個物件外表看來是個無聲的、用後可丟棄的黑膠盤,卻掌控著即時性的最顯而易見的符號(顧爾德的說話聲,李斯特改寫曲的炫示風格,以及訪談的自以為是與不拘禮節,加上不見其人演出的包裝)。
想想顧爾德和他的唱片,會覺得頗可能有與書寫作品相比擬之處。第一是有可再製的有形文本,這在班雅明的機械再製時代的最晚近階段中已經大量一再加倍而超過了一切想像的限度。然而,灌錄的與印製的東西一樣,在持續製造與銷售方面都受到某些法律上、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的約束;至於為什麼銷售、如何銷售,兩者卻是兩碼子事。重要的是,我們關注的書寫文本最初是因為作者與媒材之間有直接接觸的結果。因此這個文本可以為了裨益現世、按照現世訂的條件、在現世之中再製;不論作者對於自己受到公眾矚目存有多少顧慮,一旦文本變成不只一份,作者的工作成果就到了現世之中,不聽作者的支配了。
第二,書寫的作品與音樂表演都是風格的呈現,乃是就表演作品這非常複雜的現象所做的最簡單也最不含敬意的釋義。我又要武斷地排除一整串有趣的複雜性,以便堅決主張(從製作者與接受者的立場皆然)風格是應對觀眾的作者的一種可辨認、可重複、可保存的符號。即使觀眾和作者一樣是受約束的,同時又浩瀚如整個世界,作者的風格仍有部分是一個重複與接受的現象。不過,風格之所以被人接受做為作者風貌的標幟,是因為有一套他自己的特色,一般稱之為個人語型、發聲、不可削減的個人特性。弔詭的是,像文本或唱片這本應不具人格的東西,竟能傳送像「發聲」這麼生動、立即、轉眼即逝的印象或痕跡。顧爾德的訪談只不過老實不客氣地說出,即便最質樸、最被尊崇得高高在上的文本也經常需要被接納、受肯定。這種需要的常見形態之一是,舞台搬演的(或灌錄的)一個說話聲於特定時間在確定場所對某人而說。按我這想法來看,風格會抵銷現世性──即孤獨文本沉默的、看似沒有境遇的存在。任何文本,只要不曾立即被毀滅,都是往往互相衝撞的力量網絡,而且實際存在的文本就是現世中的一個生命;所以它對每一個讀它的人說話,一如那張唱片(假定應當代表顧氏退出現世,以及他在無現場觀眾時演奏的「新的」沉靜風格)之中的顧爾德。
的確,文本說話不同於一般的言語。但是如果說言語和文本是直接的對立──言語有情境和參照予以連接,文本攔截或中止言語的現世性──我認為這是誤導而且基本上太過簡化了。以下是保羅.黎戈爾(Paul Ricoeur)所描述的這種對立,按他說這只是為了分析說明才提出的:
言語之中的參照功能是與語言交流範圍內的「論述語境」(situation of discourse)的角色相連:言語交流時說話者在彼此的面前,而且有論述的條件場景在,不只是感知的周遭環境,還有說話者彼此都知道的文化背景。論述因這個情境有關係而具有完整意義;與真實的參照關係其實就是可以從論述實例的「周圍」指出來的真實之間的參照關係。語言……以及語言的所有明示指標的作用是,把論述扎根在環繞論述實例周圍的依環境而定的那種真實之中。所以,在活的語言裡,說話的理想表意會傾向一個「真正的」參照關係,亦即所說的「相關對象」……
文本取代言語後,情況就不是這樣了。……文本並非沒有參照;正是要由閱讀的功課──例如詮釋──來實現參照關係。至少,在參照關係暫緩的懸置狀態中,文本在參照延宕時「懸在空中」了,在現世之外或是沒有了世界;憑這樣消滅與現世的一切關係,每一個文本都可以隨意與所有其他文本產生關係,所有其他文本從而取代活的言語所表明的那種取決於環境的真實。
按黎戈爾所說,言語與依環境而定的真實均以臨場狀態存在,書寫與文本卻以懸置狀態存在──即是在隨境的真實以外,要由讀者兼批評者將它們「實現」而變成臨場存在。黎戈爾這樣說就好像文本和情境真實(我稱之為現世性)在玩搶位子遊戲,按照相當粗糙的訊號由一個把另一個攔截並取代之。但是這個遊戲是在詮釋者的腦中進行,這個所在可能沒有現世性和隨境事實。批評者兼詮釋者的地位被降格成為交易中心,這裡發生的交易把明明在說Y的文本顯示為X的意思。至於黎戈爾所說「暫緩的參照關係」,在詮釋過程中會變成如何?很簡單,基於直接交易的模型,它會回來,藉由批評者的閱讀變得完整而真實。
這些變來變去的根本難題是,黎戈爾未經充分說理就假定隨境真實正對稱言語的屬性也只能是言語的屬性,或言語情境的屬性,或是寫作者如果不曾決定寫出來也應該會想說的話的屬性。我的論點是,現世性不會來過就走;也不是像我們指稱歷史時常有的不好意思又傷感兮兮地零星散布各處,這是用委婉的說法表達一個再籠統不過的意思:一切事都是在時間裡發生。此外,批評者並不只是能點石成金把文本轉化成隨境真實或現世性的人;因為他們也會受環境條件影響,會製造環境條件,不論他們用的方法有多客觀,都可以被感覺出來。重點是,文本自有存在之道,即使是最精練純化的形態也總離不開環境條件、時間、地點、社會。一言以蔽之,文本在現世裡,所以有現世性。
不論文本是保存妥當的或是有一段時間被擱置的,不論是不是圖書館上架的,不論是否被視為有害的;這些事都與文本存在現世裡有關,這是比個人閱讀的過程複雜得多的事。批評者具有現世中的閱讀者和寫作者身分,無疑也牽涉同樣的關係。
我用顧爾德灌錄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的例子,其實只是要找個實例證明,近似文本的東西嚙合現世的方式既多不勝數又極其複雜,比黎戈爾劃清文本和言語的界線複雜得多。這些嚙合便是我一直在說的現世性。不過我在這裡主要感興趣的不是一般的美學客體,而是特別針對文本而論。多數批評者會同意這個想法:每個文本多少都被產生的因由所累,擔負著它由來的經驗事實。這種想法走到極端,就會獲得麥可.瑞弗泰爾(Michael Riffaterre)這樣的文體研究家給予理由正當的批評了。瑞氏在〈自給自足的文本〉(The Self-Sufficient Text)一文中曾說,任何把文本降格至其環境條件的作為都是謬誤,是傳記的或起源的、心理的、類比的謬誤。3多數批評者很可能贊同瑞弗泰爾,會說:對,我們一定不能讓文本被這些謬誤壓得消失了。不過(我主要是發表自己的意見)。他們對於文本自給自足之說不盡然滿意。除了各種謬誤之外,唯一的選擇只剩下神祕難解的文本世界嗎?──這世界的主要意義層面是如瑞弗泰爾所說完全向內或知識性的嗎?除非把它們與日常的、現世的語言比較顯然迫切的問題一刀兩斷,就無法克服文學語言的難題了嗎?
我找到從一個出人意表的起點著手解答這些問題的方法,所以我現在似乎得要岔出題外了。且看看大家比較陌生的中世紀阿拉伯語言學的思考領域。許多當代批評家感興趣的是歐洲語言思辯,即是把理論的想像與經驗觀察做成特別的結合,這是浪漫主義語文學、十九世紀早期語言學興起、傅柯所謂的「發現語言」的整個多彩多姿的現象都具備的特徵。但是,十一世紀的安達魯西亞(Andalusia)早已有了非常精密而且帶預言性的伊斯蘭哲學語法學家的學派,他們的辯論學為二十世紀的結構主義者與生成語法學家的辯論、描寫語言學家和行為學家的辯論開了先河。還不止於此。有一小群安達魯西亞語言學家把能量導向抵擋敵營語言學家,以防止對方把語言中的含意變成深奧祕傳及寓意的習作。這一群人之中有三位語言學家兼理論語法學家,伊本.哈吉姆(Ibn Hazm)、伊本.金尼(Ibn Jinni)、伊本.瑪達.阿爾庫托比(Ibn Mada’ al-Qurtobi),都是十一世紀時在科多瓦(Cordoba)工作,也都屬於扎希爾學派(Zahirite),並且都反對巴丁學派(Batinist)。巴丁學派的人主張,語言的含意隱藏在字詞裡;所以唯有向內的詮釋能夠找到含意。扎希爾(這個名稱來自阿拉伯語的「清晰;明顯;可知覺的」,巴丁含有「內在的」意思)學派認為,字詞只有表面含意,按特定的使用、環境條件、歷史與宗教的情境而定。
兩個對立的學派可溯源到神聖文本《古蘭經》的閱讀,以及後世信徒應該如何閱讀、理解、傳播、教導《古蘭經》這件大事(《古蘭經》是一樁事,和《聖經》是不一樣的)。科多瓦的扎希爾學派人士抨擊巴丁派作為過當,認為語法(阿拉伯語即「nahu」)這一行從事的乃是從原本神聖宣告的,所以不可改變的穩定文本引申出個人的意義。按伊本.瑪達所說,把語法和理解的邏輯扯到一起都是荒誕的,因為語法這門學問假定 ──而且往往進而憑回憶創造 ──只有入行的人能懂得有隱含意思的字詞該如何使用並解釋的觀念。一旦往這隱藏的層次去找,要怎麼詮釋都可以:不會有精確的意義,沒有某個字詞其實受什麼意思的控制,對字詞沒有責任負擔。扎希爾學派要做的是用合理化過程恢復閱讀文本的系統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可感知的字詞本身,要看它們在特定情況下表露的可謂是一勞永逸的意思,不要只注意它們以後可能應該隱含的意義。科多瓦的扎希爾學派尤其積極努力要提供一套閱讀方法,要盡可能嚴密地控制閱讀者及其環境條件。他們主要是用一種說明何謂文本的學說來達到目的。
我們不必細講這個學說。但是,點出爭議本身如何從一部神聖文本產生,文本的權威又來自它是真主在某一時刻直接授予「使者」,是有助益的。反觀猶太教基督教傳統中以神啟為核心的文本,不可能縮小到上帝出手干預的一個確切時刻,再因這個時刻而有上帝的「道」進入人世的果;上帝的道是持續不斷進入人類歷史的,在歷史中發生,也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所以,阿諾戴斯(Roger Arnaldez)所謂的「人的因素」在這部文本的接收、傳播、理解之中都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由於《古蘭經》是一樁獨一無二的大事帶來的後果,文本確實「降下」到現世性,以及其語言和形式,都應視為固定而完整的。此外,文本的語言是阿拉伯語(阿拉伯語因此成為享有殊榮的語言),文本的承納者是先知(或使者)穆罕默德,也是享有殊榮的人。這樣的一部文本可以說是具有一個絕對確定的源頭,所以不可以往回參照任何特定的詮釋者或詮釋方式,雖然巴丁派擺明了要這麼做(有人曾說這也許是受了猶太教基督教經典注釋方法的影響)。
阿諾戴斯做的伊本.哈吉姆研究之中,把《古蘭經》描述如下:《古蘭經》講述歷史事件,本身卻非歷史性質。它重述過往發生的事,把這些事簡潔敘述、具體列舉,但它本身不是實際體驗過的經歷;它打斷人類的生活延續,但是真主並不藉持久的或協同的作為涉入世俗事物,《古蘭經》教人記得的行為內容一直在以警告、指示、律令、懲罰、獎賞的相同形態重演。總之,扎希爾派的主張是視《古蘭經》為絕對源於環境條件,卻並不因而讓現世性左右文本的實有意義:這一切都是因為扎希爾派最終要避開通俗化的決定論。
因此伊本.哈吉姆的語言學理論是以祈使語氣之分析為基礎,由於按這個論點《古蘭經》從最根本的文字層次看乃是受兩種範式要求控制的一部文本,一個是iqra(阿拉伯語指「讀」或「誦」),一個是qul(阿拉伯語指「告知」)。由於這些必要作為明顯左右著《古蘭經》隨境的與歷史的樣貌(以及它之所以為一樁大事的獨一無二特性),也由於這些必要作為必然支配文本以後如何使用,所以伊本.哈吉姆把他做的祈使語氣分析與hadd的司法含意結合起來(阿拉伯語「hadd」既指邏輯語法的定義,也指限度)。在祈使語氣之中──介於讀與寫的指令之間──發生的是把話說出來(阿拉伯語為khabar
,阿諾戴斯譯作e+’nonce+’),即是用文字體現示意的意圖,阿拉伯語即niyah。注意:示意的意圖並不等於心理的意圖,而是只與用文字描述的意圖同義。文字描述的意圖是高度現世的東西,只在現世裡發生,它的應時隨境屬性非常明確又徹底相關。示意只是使用語言,使用語言是按某些詞典的句法的規則使用,語言憑這些規則而存在現世、屬於現世。扎希爾派認為語言是受實在用途制約,既不聽抽象規定指揮,也不受思慮自由左右。最重要的是,語言居於人和龐大的不確定之間:既然現世是字詞與事物匹配的一個巨大系統,那麼,能讓我們把指明的事物從這其大無比的整齊系統中挑出來的就是文字形態──也就是按實際語法使用的語言。所以,如阿諾戴斯所言,忠於語言的「真」面向乃是想像的禁欲苦行。一個字詞按理必須有一個精確的意思,除這個意思之外還要有周詳定下的一系列與其他字詞及意思相似之處(對應之處),這一系列,嚴格而論,是在這個字詞的周圍發生作用。如此一來,比喻的語法(如《古蘭經》中出現的)就是語言實際結構的一部分,從而是語言使用者全體的一部分,否則比喻的語言原本是難以捉摸而任憑詮釋行家操弄的。
阿諾戴斯提醒我們,伊本.哈吉姆所做的是把語言看成具備兩個看似對立的特性。一個是神意授予的制度,不會改變,不可更動,有道理,合理性,明白易懂。另一個是純粹偶然性的工具,表明以特定表述為本的意思。正是因為扎希爾派用這個雙重觀點看待語言,所以反對把字詞及意思降回可能從語法上追溯根本(至少就阿拉伯語而言)的那些閱讀方法。每一句話是它自己的時機,所以每一句話都是安頓在使用它的那個現世脈絡裡。因為《古蘭經》這部神與人的語言範例的文本包含了說、寫、閱讀、告知,扎希爾派的詮釋本身就同意,不可避免的不是言語與書寫的分離,不是文本與隨境性的分離,而是它們必然有的相互作用。扎希爾派這麼嚴峻的意義概念之所以能夠形成,就是憑這個相互作用。
第1章世界,文本,批評者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加拿大鋼琴家顧爾德(Glenn Gould)自一九六四年走下音樂會舞台以後,工作範圍就只限於灌唱片、上電視、廣播。關於顧爾德是否從來都是,或有時候是,某一首鋼琴曲令人信服的詮釋者,批評者的意見不一,但是大家一致公認,現在他的每一次演奏至少也是不同一般的。顧爾德近年來如何運作,有一個實例正適合在這裡談談。一九七○年間,他發行了一張演奏李斯特改編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的唱片。除了顧爾德選中這首曲子出人意料(即便顧爾德這樣極端古怪的人物選這一首都顯得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