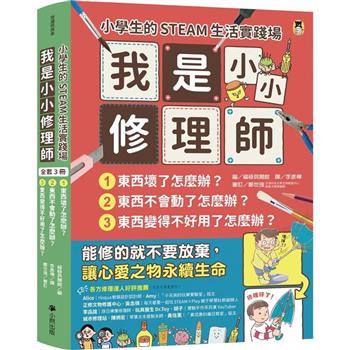餐桌上擺了一罐九百多元的高檔椰子油,冰冷的標籤說,原產地菲律賓,進口地卻是德國,也許它沒說的還有:罐子是保加利亞做的,標籤是台灣印的等等。全球化現象濃縮成一罐椰子油,出現在眼前,背後的故事卻仍然隱蔽著。真實與虛擬就這樣混種起來……。商品如此,文化更肆無忌憚地跨界了。《消失的現代性》為全球化的文化研究提出一全新框架,它指出想像在今日世界的作用具有現實的社會力量:想像不但為身分認同提供了新的資源,也為民族—國家(某些人認為其時代行將終結)的替代方案創造了新的動能。阿帕度萊審視了當今全球化時代——其特色是大眾遷移與電子媒介的孿生力量——還為大眾消費模式、多元文化主義論爭與族群暴力提出了嶄新的觀點。他也思索影像——生活風格的、大眾文化的或自我代表的——如何透過媒體而流通國際,且經常以(在影像原作者眼中)驚奇和有創意的方式為人所挪用。
作者簡介:
阿君.阿帕度萊(ArjunAppadurai) 現任紐約大學斯坦哈特(Steinhardt)學院文化、教育與人類發展學系教授。曾任新學院(TheNewSchool)全球倡議(GlobalInitiatives)資深導師、芝加哥大學人類學與南亞語言及文明教授、芝加哥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主持過芝大全球化計畫,並關切族群暴力與現代民族—國家領土形象的關聯方面議題。著作豐富,包括WorshipandConflictunderColonialRule(Cambridge,1981)、TheSocialLifeofThings(編者,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Gender,GenreandPower(編者之一,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1991)、FearofSmallNumbers(DukeUniversityPress,2006)。
譯者簡介:
鄭義愷 台大哲學所西洋哲學組碩士,碩士論文《謝勒的倫理學奠基:實質價值與位格的現象學倫理學》探索現象學作為社會理論的潛能。學術興趣為古典哲學、政治哲學、社會理論。譯有《傅柯說真話》(群學,2005)、《什麼是社會學》(群學,2007)、《臨終者的孤寂》(群學,2008)。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阿君.阿帕度萊研究新制度派中所謂跨國公共領域的部分,是先鋒的社會理論家。他的觀察敏銳而不同凡響,他的語言則叫人目眩,並發人深省。他取材多方,信手拈來,涵括了自傳性質的與高度理論的,板球與統計學,甚至塔米爾那督或矽谷。阿帕度萊的智識如此細膩,不會只因事物新奇而全然認同之;但同時,已然陳舊者他也能斷然捨棄之。」─帕沙.恰特吉(ParthaChatterjee)《民族主義思想與殖民世界》(NationalistThoughtandtheColonialWorld)作者 「一部重要作品……雖然目前有許多人著書談論跨民族世界中的全球文化,然而實際上沒有人能像阿帕度萊一樣,對人類學文獻及其世界觀有精深掌握,或者有他的全球觀點。這部作品的成果不時閃耀得令人暈眩,對現代性及後現代性問題提出了令人滿意且嚴肅的質問。」─謝利.奧特納(SherryOrtner),加州柏克萊大學
名人推薦:「阿君.阿帕度萊研究新制度派中所謂跨國公共領域的部分,是先鋒的社會理論家。他的觀察敏銳而不同凡響,他的語言則叫人目眩,並發人深省。他取材多方,信手拈來,涵括了自傳性質的與高度理論的,板球與統計學,甚至塔米爾那督或矽谷。阿帕度萊的智識如此細膩,不會只因事物新奇而全然認同之;但同時,已然陳舊者他也能斷然捨棄之。」─帕沙.恰特吉(ParthaChatterjee)《民族主義思想與殖民世界》(NationalistThoughtandtheColonialWorld)作者 「一部重要作品……雖然目前有許多人著書談論跨民族世界中的全球文化,然而實...
目錄
推薦導讀:自傳式的全球化致謝第一章 這裡、當下第一部全球流動第二章 全球文化經濟的裂散與差異第三章 全球族群景觀:初論跨國人類學的一些問題第四章 消費、持續期與歷史第二部現代殖民地第五章把玩現代性第六章殖民想像裡的數字第三部後民族地帶第七章民族原生論後的生活第八章愛國主義及其未來第九章生產地方性參考文獻索引
推薦導讀:自傳式的全球化致謝第一章 這裡、當下第一部全球流動第二章 全球文化經濟的裂散與差異第三章 全球族群景觀:初論跨國人類學的一些問題第四章 消費、持續期與歷史第二部現代殖民地第五章把玩現代性第六章殖民想像裡的數字第三部後民族地帶第七章民族原生論後的生活第八章愛國主義及其未來第九章生產地方性參考文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