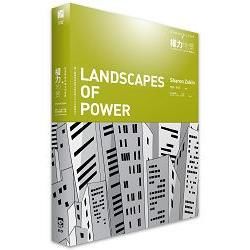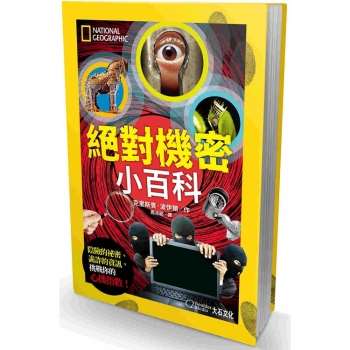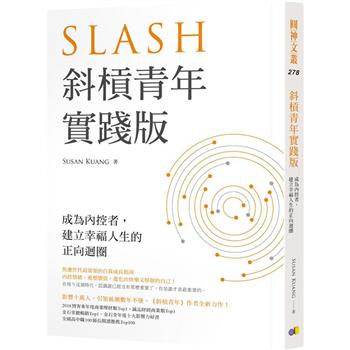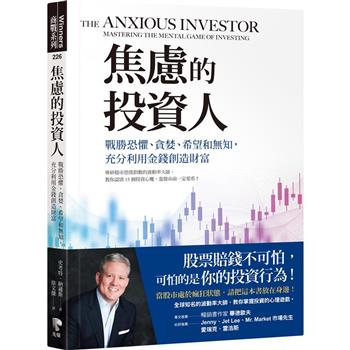本書共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導論」包含三章,從兩個截然不同的結構變遷經驗著手——內在地景和都市地景,說明兩者同時再現並抗拒新市場經濟的抽象化、國際化和消費偏向。
第二部分「五個二十世紀地景」,再以一系列個案研究探索去工業化與後工業或服務業經濟之間的變化光譜。案例一是西維吉尼亞州威爾頓的歷史,這同時顯示地方自主性的力道和弱點。若未能連結全球市場,沒有任何傳統產業公司可以存活;加上沒有明顯的政府干預,這些連結就必須透過能汲取新投資泉源的銀行家。別具意義的是,滋養威爾頓的地方支持來自居住或消費社區,而非僅奠基於工作的社區。這點強調我們必須認識到超越工業生產的新動員形式。再者,若沒有連結在地與全球資本,「拯救」一個地方社區是行不通的。
案例二是麥克路斯鋼鐵在工業撤資的情況下,生產性勞動的弔詭力量。麥克路斯鋼鐵遭其主要顧客汽車工業拋棄,顯示城市或公司都無法在缺乏生產工作下存活。債權人的「政治決策」,而非資金成本或比較利益這類「經濟因素」,使麥克路斯鋼鐵缺乏金融機構的投資,生存兩度受到威脅,這種情況唯有透過其他政治壓力才能對抗,而本案的壓力來則自工會和州政府。麥克路斯鋼鐵擔保債權人之間的合作也提醒我們,一切投資都發生於社會脈絡中,對於接管交易或投資債券、房地產和高階消費的偏好,顯示特定的欲望社會化。再者,以正面方式介入麥克路斯鋼鐵的是地方政治、金融和工會菁英的成員,他們無法將投資導引到其他可能關閉的工廠,決定投資方向的是生產的意願。
案例三是威切斯特郡顯示地方菁英可以補充國際經濟菁英的決策。企業總部的遷址令當地維持高房地產價值的欲望獲得新的力量,而這得壓抑工業生產。支持這項目標的菁英凝聚力,排除這些工業城鎮裡的非白人、非工會勞工,以及當地民選官員。和麥克路斯及威爾頓相反,引導威切斯特變遷的社會均質抽象意象,排除了既有人口中經濟最弱勢的一群。
最後兩個案例是縉紳化和迪士尼世界,顯示從消費角度重組空間的其他情景,它們仰賴文化與經濟之間,以及中產階級消費者和全球企業之間的明顯連結。但這些地方地景也遇到投資、菁英支持和現有人口抵抗所引起的限制。縉紳化和迪士尼世界在任何情況下是否為經濟成長的可行情景,還需要進一步檢視。它們意味金融投資和文化生產的持續互動,而這可能導致兩種方向:服務業更深刻的社會根源與企業對視覺想像的更廣泛控制。
最後的「結論」的部分除了總結全書,更提出未來議程的主要焦點應該是公共價值的觀念。在地景的自然與社會力量之間,應該有無可化約的最低均衡。藉由限制開發來保有公共價值也是民主行徑,因為這容許成長由地方控制來節制。因此,公共價值並非無法與自我利益共存。它與私人價值不同,不僅回應市場力量,也反映地方的文化。公共價值保留生產和消費間的均衡,並且發現工作地景是道德秩序的最佳基礎。
然而地景具有歷史和文化上的局限,它們總是顯示權力的不對稱。在大部分地區裡,菁英與富人合力排除那些無法跟上市場力量帶來的改良的人。公共價值藉由排除來保障安全,以致地方文化屈服於市場價值。比起在工業地景裡,這在消費地景中顯然是更加危險。公共價值往往受困於私人價值。儘管如此,批評者無法再呼籲勞工階級拯救社會,他們已過度分化並過度捲入消費,無法回應舊有的工業改革願景。也不能指望藝術家和建築師對抗經濟力量,他們也深深捲入市場生產而無法描繪另類出路。籲求地方社區產生變革也是浪漫的想法,地方行動者一點也無法自主(即使曾經自主),雖然意圖保留風土形式,最終卻常令自己緊緊依附權力地景。
從公共價值角度形成議程的問題是它很模糊,無法解決全國層次的議題,也不能處理權力的不平等。然而,公共價值讓我們注意到菁英如何脫離某種資本投資形式而轉移到其他形式的關鍵問題。再者,對於以公民資格而非所有權為基礎的發展目標,公共價值能促進其討論。過去100年來,市場文化強調消費甚於公民資格。但美國與生俱來的民粹主義樂於接受強調地方社區的政治,強調投資要有給公民的社會回饋,而非給持股人的財務報酬,而企業也要有扎根的義務。人們依然希望生活於特定地方。或許,這可以成為開啟另類市場文化的標誌。
作者簡介
雪倫.朱津(Sharon Zukin)
紐約市立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布魯克林學院(Brooklyn College)與研究生中心(Graduate Center)社會學教授,出版了數本涵蓋文化與經濟、購物與消費空間、都市發展與藝術、房地產與種族聚居區等議題的書籍。曾獲都市社會學林德學術成就獎(Lynd Award for Career Achievement in urban sociology),《權力地景》一書曾獲美國社會學會頒發之C. Wright Mills獎。
譯者簡介
王志弘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與傳播研究所兼任教授
王玥民
台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美國南加州大學歷史碩士,現專事翻譯
徐苔玲
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台灣大學社會系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