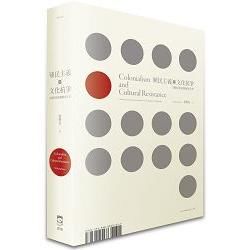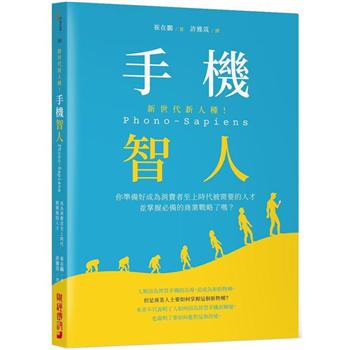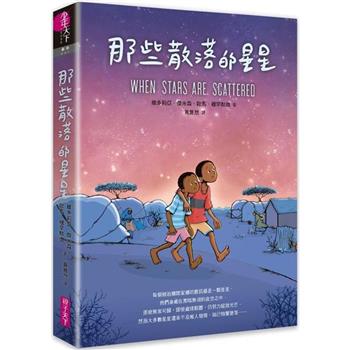不論是解嚴前的中國民族主義反抗史觀,或解嚴後研究立場「客觀化」的新史觀,都是與強權站在一起、侵奪臺灣主體地位,將臺灣「邊緣化」的殖民化論述;而左翼知識分子由反支配的本土主義立場出發,對新、舊知識分子進行精神殖民化的批判,不僅在殖民時期就起著內部解殖的功用,也是清理後殖民知識分子精神殖民化時可以憑藉倚重的歷史資源。本書通過對這段歷史的研究,突出當中「反支配」與「本土」的價值立場,指出對解嚴後才真正邁入後殖民時期的臺灣社會而言,解精神殖民化才是重建臺灣主體性的關鍵。
日據時代臺灣作家的認同問題,近來成為臺灣文學研究的重點之一,儘管對個別作家的討論為數不少,但相關研究多止於對被建構者的認同進行個案式的分析與討論;由於對形成這種主體狀態的根本原因鮮少追本溯源,無法對日本殖民主義如何建構臺灣人的主體性進行比較完整的研究,所以不能給出令人滿意的答覆。
為彌補這方面的缺憾,本書第2章對日本殖民主義及其如何建構臺灣人主體的研究探討,先是由日本殖民主義的形成歷史入手,接著探討日本如何接收西方殖民主義的進步意識形態,並用以建構「被殖民者」認同的日本主體。日本殖民主義通過文化二元分類系統,深入臺灣人的日常生活網絡,導致臺灣人除非接受日本文明的同化,否則便無所逃遁,只能被分類為非文明的存在。
奠基於本書第2章的分析,第3章則以殖民主義論述內容為對照系,分析殖民地知識分子的認同位置與殖民主義的親疏關係。實際討論則以1937年為界,將日據時代的文學活動分為兩大階段,這兩個歷史階段最大的不同在於進入戰時體制的第二階段,言論受到更嚴苛的控制,臺灣作家不僅不能公開批評日本殖民統治,還要被迫配合國策發表言論。
而第一階段的漢文作家中,賴和無疑最具代表性。他沒有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背景,但素樸的反強權支配立場,卻讓他將殖民地問題直接放在弱肉強食的不義上,發展出本書所稱的「原生本土立場」,讓他的文學創作既能不受「近代意識形態」的宰制,又能充分發散政治上去權、文化上解殖的文化政治效應。因此第4章以賴和的思考及文學創作為焦點,探討他如何將殖民問題重新聚焦在權力支配,由此與殖民主義、啟蒙主義的進步意識形態對話,進行「全方位的去殖」。
而在活躍於 1940年代的臺灣作家當中,張文環是真正能繼承左翼本土主義路線的人,所以本書第5、6兩章以他為主,兼及黃得時、呂赫若、龍瑛宗等人在文化論述及文學上的表現,探討戰爭體制下這批臺灣人作家如何堅守臺灣人立場、如何逼近皇民化論述中的文化差異界線,以「想像與象徵的再定位」挑戰殖民主義二元制所欲鞏固的等級關係,亦即鬆動殖民權力的支配關係。
這批臺灣先人選擇了「更艱難的途徑」——站在「反支配」立場,與較為不幸、被威脅、面臨完全滅絕危險的被統治者站在一起,由異化的文化位置回歸「本土」立場,為「屈從的經驗以及被遺忘的聲音和人們的記憶」發聲,這是我們身為被殖民者無可迴避要走上的解殖民化漫漫長路。本書討論的左翼知識分子、賴和及張文環,已為臺灣人的精神解殖邁出第一步,後續當然還有很多解殖民化的精神工程需要我們持續面對戰前、戰後的殖民主義接力進行。
臺灣的左翼運動及其思想遺產被埋葬在歷史最陰暗的角落,這份寶貴的左翼「後殖民理論」遺產,一直未能作為重要的思想參照系而對當前臺灣社會的解殖民化產生作用。長久以來,掩蓋在這份思想遺產上的各種歷史與文化偏見已非常深厚,本書對左翼反支配本土主義的闡發,只是用「後殖民」這個有限的視角,開挖這份思想遺產一個很小部分的意義。這份思想遺產對當下的臺灣究竟還有什麼啟發意義,則有待後續研究繼續發掘與闡發。
作者簡介
游勝冠
臺灣雲林人,1961年9月生,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曾任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現任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
著有《臺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