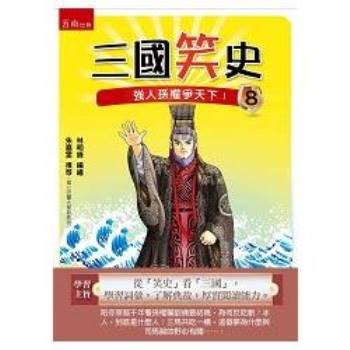推薦序
讀史,讓我們知道何謂「進步」 文/公孫策(歷史評論家)
本書是知名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的經典著作《世界文明史》的最終結論,在三十多年前就已完成。他在本書中毫不留情的敲醒了人類的自大:即使現代交通工具時速可達兩千英里,我們還是兩隻腳穿著長褲的猿猴。
我認為,上述這段話是本書,甚或說是全套《世界文明史》的基本出發點。威爾.杜蘭將我們拉回「以生物法則重新檢討人類歷史」,相對於晚近的顯學「大歷史」,又多開啟了一扇讀歷史的窗子,讓歷史不再只是帝王、將相與戰爭。
雖然本書完成至今已三十多年,但是威爾.杜蘭對文明史的「獨到見解」(中國語言學家季羨林教授對他推崇備至)卻一直被「人是地球的主宰」的主流思想刻意漠視。但可堪告慰的是,威爾.杜蘭並非第一個有此獨到見解,且被刻意漠視的哲學家。中國的先秦哲學書《列子》就有如下一個寓言:
齊國貴族田氏大擺流水席,來了上千食客,珍饈滿桌,有魚有雁,田氏感嘆的說:「老天對人類真是太好了,繁殖五穀,生育魚鳥,以供人享用。」眾食客聞言附和:「是啊!是啊!」
另一貴族鮑氏的小孩年僅十二歲,也在席間,他趨前對田氏說:「不是大人講的那樣吧,天地間萬物與人類並存,類無貴賤,完全看智慧高低、力量大小,相制相食 (生存競爭、物競天擇),並沒有誰為誰而生。如果食物是為人類而生,那麼蚊蚋吸人血、虎狼食人肉,也是人類為蚊蚋、虎狼而生嗎?」(《列子.說符》)
這一則寓言「埋」在典籍之中兩千多年,也是被「人為萬物之靈」的主流思想刻意漠視,中國的列子對美國的威爾.杜蘭應該有知音之感吧!
人類的災難早有預警
「生物法則」最令人驚嘆於威氏之先見的,是他在書中寫到:「人類的歷史是浩瀚宇宙的一個小點,它給我們的第一個啟示是『戒慎恐懼』,隨時隨地都可能有顆彗星太靠近地球,……讓居住其中的人和所有物種一起同歸於盡。」
「歷史受地球的地質所影響,日復一日, ……有些城市就此沒入水底,沉陷的教堂敲起輓鐘……人類生活在其中,其驚險程度有如伯多祿走向步行海面的基督。」寫這篇推薦序時,正好是日本發生世紀大海嘯之刻。而威氏卻在三十年前就發出了警語。
回歸到生物法則之後,人類應該更謙卑對待地球、對待萬物,當然也包括對待周圍的弱勢族群。
貧富差距問題的省思
威氏也點出了羅馬帝國滅亡的原因,原來蠻族之所以能入侵羅馬,是因為之前羅馬軍隊的戰士多半為農夫,他們吃苦耐勞願意為保衛土地而戰,但後來廣大的土地為少數人所有,原本吃苦耐勞的農夫成了在土地上無精打采的農奴。《莊子》的寓言:
東野稷向魯莊公展示駕馬車的技術,只見馬車進退自如,車輛在地上壓出的軌跡,直得像木匠畫出的墨線;馬匹左旋右轉,輪跡像圓規畫的一樣圓。魯莊公直誇好,認為這已經是駕車技術的極致了。魯國大夫顏闔說:「東野稷的馬車就要翻了」,不一會真的翻車了,莊公問顏闔:「何以知之?」顏闔說:「他的馬已經力竭,仍然驅策不停,怎麼可能不翻?」(《莊子.達生》)
對馬尚且不應窮竭其力,何況對人。看看北非、中東發生的「茉莉花革命」,再看看威氏在書中寫的:「美國……已逐漸拉大了人與人之間財富的距離,目前(一九七五年)最富者和最貧者之間的差距,是自羅馬帝國以來最遠的。」美國人大可以慶幸美國並沒有發生如威氏所言:「來場革命,導致均貧」。但美國的主政者難道可以沒有反省:中東發生革命的,大都是親美政權,孰令致之?而相較於一九七五年的美國,今日中國貧富之懸殊,北京政府難道不應該也有所警惕?
對人類有利才是好
威爾.杜蘭這本書的最大啟發,是將哲學思想灌注於史學之中,在他的觀念裡,「保守是對的,創新也是對的;科技有好的,也有壞的。」重點在於這些造就了文明,文明製造了新種族(而非種族製造文明)。而一個種族的成功或失敗,正在於他們在每一個關鍵時刻,選擇(或不選擇)某一種科技創新。《墨子》的寓言:
公輸子(即魯班)用竹木削成了一隻鵲,可以飛在天空三天不落下來,公輸子自認為手藝極致高超。
墨子對他說:「你做這隻鵲還不如匠人做車轄(固定車軸的插梢)。他只用三寸木料就能承受五十石的重量(一石為一百二十斤,五十石為六千斤)所以做事要對人有利才叫做巧,對人無用就叫做拙。」(《墨子.魯問》)
我不敢說目前世上有沒有那個不用燃料可以飛行三天不落地的玩意兒,如果果那真是太可惜了,因為居然沒能發揚光大。這個故事的重點在於,當時的中國人沒有選擇公輸班的「鵲」,而選擇了每個人都用得上的「車轄」,也就是揚棄創新,而選擇了保守。威爾.杜蘭的史觀同樣也是「對人類有利才是好」,在他眼中,「對環境的控制增加了才叫做進步」這句話今日聽來確是警世鐘聲,但卻被刻意漠視了三十多年。
所幸時間仍不嫌遲,人類還來得及與地球環境修好,前提則是揚棄「人為萬物之靈」的價值,重新以「生物法則」為思考原點。這應該是本書的最大意義。
自序
讀史,是為了採取行動
對任何將歷史發展硬套入理論模式或邏輯框框的作法,「歷史」總是一笑置之。
歷史學者在完成研究工作之後,通常得面對下面這個挑戰:「你的研究有何用處?只是聊些城邦興亡、理念的消長,並重述些君王崩殂的悲慘故事」嗎?
比起那些很少看書、光聽街談頭巷議就能對人性了解一二的人,你有沒有更透徹的領悟?你能否藉歷史燭照出現今的情勢?藉歷史之見做出更好的判斷及政策?藉歷史為殷鑑,免於對重大變革與重挫措手不及?你能否藉過去的事件觀察出一些規律,進而預測人類未來的動向或一個國家未來的興衰?
又或者像某些人所認為的「歷史不具任何意義」──它不能教導我們什麼,浩瀚的過往只不過是錯誤一再發生的排練和預演,而且未來注定要上演一齣錯誤更大的悲劇?
有時我們(作者自稱)真的有如此感覺,歷史學家的專業經常遭到無以計數的懷疑。首先,我們真的能知道過去發生什麼事嗎?或者,歷史只是一篇「杜撰」,不可全然相信?我們對於過去任何史實的理解都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正確的,歷史已經被那些全然相反的證據或存有偏見的歷史學家蒙上一層薄霧,或者被我們自己的愛國心或宗教熱情所扭曲。
「歷史大部分是臆測,其餘則是偏見。」即使那些自認能超越國家、種族、信仰或階級的歷史學家,他們在資料選擇與遣辭用字上的偏差,仍免不了洩露出個人的偏見。「歷史學家經常過於簡化,在浩瀚的人物及事件中,隨便挑出一些容易整理與編排的部分,甚至對於這些複雜的人事物從未全然真正的領悟與了解。」──因此,我們從過往得來的結論,在瞬息萬變的今日,更難以推論未來。
一九○九年,著名詩人作家夏勒.貝基(Charles Pequy)曾說:「自耶穌基督以來的世界變遷,遠不如過去這三十年以來的改變。」某個年輕物理學博士也曾說,物理學自一九○九年至今的變化,遠比有史以來的還要多。
每一年(若是在戰時,甚至是每一個月)總有某些新發明、新方法、或新的情勢迫使人們的行為及觀念做出改變。
例如,我們已經不能確定「原子」,更別說是微小的有機體,會像以前我們所認定地那樣發生反應。如今我們知道「電子」,就如英國浪漫派詩人庫波(William Cowper)筆下的神祇,以神秘的方式展現它的奇妙。反之,歷史不像科學,某些奇特的人格特質或行徑可能弄亂國家的發展,如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因酗酒而亡,使其新帝國分崩離析,或者如普魯士腓特列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因一個迷醉普魯士文化的俄國沙皇繼位,使國家得以躲避戰禍(西元一七六二年)。
很顯然的,歷史的編纂不能像科學一樣,其理至明。它只能像某種工業──因為它實事求是;像藝術──因為它將紛亂的資料理出頭緒;像哲學──因為它提供不同的視角與啟蒙。「將現在視為過去的縮影以求行動;將過去視為現在的鋪展以求瞭解。」──至少我們這麼想,也希望如此。哲學教我們由宏觀入微觀,在「歷史的哲學」中,我們嘗試藉過去的歷史來理解現在。
幫你學會耐心看待現實
我們了解這樣的方式並不完美,面面俱到的觀點並不存在。畢竟我們無法全盤了解人類的歷史;在蘇美(Sumerian)或埃及文明之前,可能已經有很多其他文明存在;我們現在才開始發掘而已!因此我們得有「歷史是片面」的認知,並暫且安於目前的臆測;我們對於歷史,也該和科學、政治學、相對論和其他法則一樣,抱持懷疑的態度,對於所有的說法都該存疑。「對任何將歷史發展硬套入理論模式或邏輯框框的作法,歷史總是一笑置之;『歷史』不受概論約束,打破所有成規,就像巴洛克(baroque)般不規則。」或許在這些限制下,我們能從歷史中學會耐心對待現實,並尊重彼此的歧見。
人,只是天體運行中的一小點,是地球的短暫過客、小胚胎的發軔、某種族的後裔,一個由身體、個性、和心智組成的複合體,是家庭和社群的一員,是某種信仰的信奉者或懷疑者,是某個經濟體的一個單位,或許是某個國家的一個公民或某個軍隊的士兵,我們大可由這幾個項目──天文、地質、地理、生物、種族、心理學、道德、宗教、經濟、政治、與戰爭──來探究歷史對人類天性、行為、及未來的看法。這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也只有傻瓜會嘗試將好幾百世紀的歷史發展,濃縮在結論還不確定的兩百頁裡。而我們真的嘗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