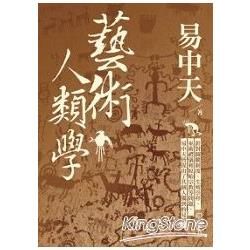一部結合美學與文藝學更甚文化人類學的著作
易中天帶你一探史前藝術、人類與文化的奧祕
當人類學家和藝術學家在討論人類文化和藝術現象時,往往要追溯到遙遠的史前藝術。這裡所提到的「遙遠」,不只是指年代的久遠,也是指文明的陌生。現代的印第安人、布須曼人和波利尼西亞人,帶給研究者與考古遺跡一樣的遠古回聲,使人陷入深深的困惑和好奇,不由自主地想要去一探史前藝術的奧祕;但是由於資料的缺乏和方法的陳舊,這奧祕始終籠罩在迷霧之中。
易中天的《藝術人類學》,在當今眾多同類著作中獨樹一幟,最顯著的特點在於:他首次表明了,史前藝術的奧祕並不只是在史前人類一閃而過的念頭中,也不只是封閉在重見天日的石斧、陶罐和洞穴壁畫中,而是仍沉睡在我們自己心裡。它就是人們自己的奧祕、一般藝術的奧祕,即「人」的奧祕。
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出發,運用其方法與材料來研究藝術本質。不從固有的理論、定義出發,而從事實考察切入。因此,這不再是一種「哲學美學」,而是「科學美學」,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藝術學」。針對圖騰制度、生殖崇拜、巫術禮儀和原始宗教等問題,易中天提出其個人獨到的見解及自我研究的一套藝術理論「人的確證說」。
作者簡介:
易中天
一九四七年生,湖南長沙人,一九八一年畢業於武漢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現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長期從事文學、藝術、美學、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多學科和跨學科研究。
著有《〈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藝術人類學》、《帝國的惆悵》、《讀城記》、《黃與藍的交響——中西美學比較論》(與鄧曉芒合作)、《漢代風雲人物》等著作。近年撰寫出版了「易中天隨筆體學術著作.中國文化系列」四種:《閒話中國人》、《中國的男人和女人》、《讀城記》和《品人錄》。
因在電視臺開講三國歷史而迅速走紅,成為中國人氣最旺的「親民學者」;也因《三聯生活週刊》封面標題,而享有了「學術超男」的稱號。
章節試閱
導 論 人類學與藝術本質的還原
哲學並不要求人們信仰它的結論,而只要求檢驗疑團。
──馬克思
一
一七六八年,英國航海家和探險家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一七二八─一七七九)受命前往南半球探險。他指揮的「努力」號帆船從普利茅斯起航,八個月後繞過合恩角,登上兩年前英國人命名為喬治三世島、一年前船長布幹維爾又命名為新西泰爾島的大溪地島。在這個遠離英吉利海峽的南太平洋荒島上,庫克第一次注意到一種久已被歐洲人忘記、以後也曾同樣引起英國人類學家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一八○九─一八八二)驚異的文化現象──紋身。庫克驚奇地看到:那些彷彿屬於另一世界的大溪地人赤裸的身體上交叉塗滿黑色的線條,眼睛周圍塗著白色,臉部其餘的地方則裝飾著紅色和黑色的垂直線。可以想見,他們這副「尊容」會怎樣地使那些衣冠楚楚的英國紳士們目瞪口呆。所以後來同樣見過這類「奇裝異服」的達爾文回憶說:「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看見荒涼而起伏的海岸上的一群火地人時所感到的驚訝,因為我立即想到,這就是我們的祖先。這些人是完全裸體的,周身塗色,長髮亂成一團,因激動而口吐白沫,表情粗野、驚恐而多疑。」無疑,庫克顯然不會有達爾文那種關於祖先的聯想,但是,當三個月後他在新荷蘭(即今之澳洲)的東部海岸再次看到當地土人那畫滿紅色花紋的裸體時,他也許已確乎感到應該待之以一種新的態度了。於是,當一七七二年重返大溪地島時,庫克便詳細地考察了當地土人的紋身──不僅是畫身,也包括刺身,而且還親自參加了幾次紋身儀式,並把這一切都詳細地記載於他的筆記之中。一七七九年二月十四日,庫克在探險途中遇難身亡,但他對現代原始部落紋身習俗的發現和研究卻和他的死訊一樣震驚了歐美兩大洲。人們為他的探險精神和他死後公布的筆記中所描述的那個神奇世界所傾倒。從此,人文學科的研究序列裡又增添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新的對象,它的名稱就來自大溪地島的土語「Talu」,英語稱之為「Tattuo」。
作為一個航海家,庫克當然不可能意識到他的發現對於人文學科會有什麼樣的意義,更不會想到在一百多年後出版的第一部藝術人類學著作──即我們下面將要談到的格羅塞的《藝術的起源》一書中,首先被作者加以介紹和研究的就是他的發現。實際上,庫克只是那些最先走出歐洲文化圈的眾多的冒險家、旅行家和傳教士中的一員。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由於這些人對人類原始狀態的發現、考察、介紹與研究,才無意之中使一門新的學科──人類學得以誕生。人類學(Anthropology)就其本義而言,就是研究人類自身的科學。從字源上講,它源於希臘文Anthropos 加上Logos ,意為「研究人的科學」。由於這個原因,人類學通常都定義為「人的科學」(The Science of Man)。毫無疑問,有史以來,人類就非常重視對自身的研究。古希臘號稱「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Herodotus,約前四八四年─約前四二五年)的著作中便有一半是人類學的資料,羅馬詩人盧克萊修(Lucretius,約前九八年─前五四年)也曾在其哲學詩中討論人類起源與文化發生等問題,我國古代的《山海經》中也頗多這方面的記載。而無論是蘇格拉底(Socrates,前四六九年─前三九九年)把人定義為「一個對理性問題給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還是我國的孔子(前五五一年─前四七九年)和儒家學派把人看作一個具有內省能力的道德和群體的存在物,都無非證明,在人類最早的思想裡,就已蘊含著哲學人類學的內容。如果追溯得更早,即追溯到對宇宙世界進行神話學解釋的時代,就不難發現,一個原始的宇宙學總是和一個原始的人類學比肩而立,世界的起源問題總是與人的起源問題難解難分地交織在一起,而一個偉大的神或一群偉大的神,也總是在創造了世界之後,就立即或過不多久便創造了人。這說明即使在神話形態的原始意識形態中,世界觀也同時包含著兩個方面的內容:怎樣看待世界和怎樣看待人自己,而且前者實際上又總是由後者決定的。正因為人把自己的創造力神化為某種外在力量,他才在把自己看作上帝的選民的同時,也把世界看作為上帝的創造物;也正因為人在自己的創造活動之中建立了科學理性,從而意識到自己是理性的存在物,才會把世界看作一架齒輪和發條都耦合得井然有序、運轉自如的機器;至於天尊地卑、月陰日陽的宇宙觀,更不過是人類社會倫理觀念的折射罷了。顯然,無論是特創論的神學世界觀,還是機械論的科學世界觀,抑或道德論的倫理學世界觀,背後都有一個人類學的影子。可以說,自人類有意識以來,他就在審視、研究和探索自身的奧祕了。
儘管人類學的前史可以追溯到這樣久遠的時代,但它作為一門獨立的、專門的、帶有自然科學性質的學科的誕生,卻是近代的事,而且正是由庫克們的發現所促成的。毫無疑問,這些最先走出歐洲文化圈的探險家、旅行家、傳教士或其他什麼人的原始動機當然不是要建立一門新的學科,甚至其中不少人還是出於建立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罪惡目的而深入「不毛之地」,但無論如何,這些發現卻讓自以為文明高貴的歐洲人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樣的種族!那麼,這些「形同禽獸」的「野蠻人」,這些不曾「開化」的「吃人生番」,究竟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他們究竟是我們不同文化的現代同類,還是我們遠古祖先的現代殘存呢?總之,這些新發現就像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漣漪,從而使得一些對人類自身特別感興趣的人覺得有必要專門建立一門新的學科,來研究這些新發現和由此引起的新問題。這門新的學科就是「人種學」(Ethnology)。
人種學就其本意而言,是要研究現代原始部族和原始民族與歐洲諸文明民族之間的種族差異,因此一開始主要是從體質方面的差異入手的,後來這方面的研究就形成了人類學的一個分支──體質人類學(Physical Anthropology)。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人種學家們開始發現,各民族之間的區別,與其說是體質的差異決定的,毋寧說是文化的差異決定的,於是人種學也就逐漸地改變了它的內涵,將原始民族的文化變成了它的主要研究對象。同時,愈來愈多的研究者開始思考這樣的問題:「在空間上處於最遙遠地區的現代原始人和在時間上處於最遙遠時代的史前原始人之間究竟有沒有共同點?」至少就生產工具和物質文化而言,二者之間的相似是驚人的。那麼,他們的精神生活是不是也會大同小異呢?也就是說,如果這個共同點,是確實存在的,那麼,我們就完全可以將人種學對現代原始文化的考察和考古學對史前原始文化的研究結合起來,來研究整個人類文化的起源和演進了。
於是人種學便讓位於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並退而變成後者的一個分支,即「民族學」。較之人種學,文化人類學有著更為廣闊的研究領域和更為多樣的理論視角。舉凡人類語言、宗教信仰、審美意識、道德行為和社會結構諸方面,都是它興趣所及之處。但是,它又不像一般語言學、宗教學、美學、倫理學和社會學那樣孤立地研究這些文化現象,而是在整個人類文化和人類歷史的廣闊背景下宏觀地和深入地研究它們的本質規律,並一直追溯到它們的原始形態,從而勾勒出人、人性、人類文化和人類精神現象的歷史本來面目。總之,「它是關於人類研究最全面的學科群」,是「唯一能夠廣泛透視種種文化經驗的學問,又具備兼跨生物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基礎,因此有資格對人類、人性、人的生活方式提出問題並加以研究」,當然,也有資格對藝術的本質作出全新的探索。
由於文化人類學具有這樣的理論優勢和生命活力,因此,當它帶著一股新鮮空氣闖進社會科學領域時,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強烈反響,甚至使某些學科,如歷史學、宗教學、語言學等,不得不放棄已有的結論和成見,重新審視和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至少,也「都已認清人種學的昌明給予了文化科學一種有權威的、不可缺少的幫襯」。因此,美國人類學家克羅伯(A.L.Kroeber,一八七六─一九六○)宣稱,現在已進入了一個「人類學的時代」(Age of Anthropological Science)。在這樣一個時代,「藝術科學研究者如果還不明白歐洲的藝術並非世間唯一的藝術,那就不能原諒了」。也就是說,「除非它自甘愚蒙,它已不能再不顧人種學上的種種材料了」;而藝術人類學作為一種藝術學與人類學的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它的誕生,也就是勢在必行和理所當然的了。
二
現代藝術人類學的建立,是和德國人類學與藝術史學家格羅塞(Ernst Grosse, 一八六二─一九二七)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
一八九四年,格羅塞出版了他劃時代的著作《藝術的起源》。在這部為人類藝術的研究開拓了新視野和開闢了新途徑的天才著作中,格羅塞一開始就闡述了他對於文藝學方法論的新見解。在他看來,文藝學(他稱之為「藝術科學」)應該包括兩個部分,即「藝術哲學」和「藝術史」。前者是關於藝術本質、規律、特性和目的的邏輯研究,後者則是關於藝術發展歷史事實的實證研究,其共同目的,「就是描述並解釋被包含在藝術這個概念中的許多現象」。但是,就整個藝術科學的全部歷史而言,這兩個方面的工作都是遠非令人滿意的:狹義的藝術哲學,即由哲學家們構造的藝術理論體系,總是附庸和從屬於他們自己的思辨哲學體系,並隨同後者一起行時於前,又衰亡於後。因為他們只想「將那思辨哲學的空中樓閣造得高聳入雲」,卻不肯回到人間,屈尊看一下眼前俯拾皆是的藝術現象和藝術事實。結果必然是:當古典哲學終結之後,無論是黑格爾派(Hegelians)還是赫爾巴特派(Herbartians)的藝術哲學,「在現在都已只有歷史上的興趣了」,至多不過留下些讓人讚嘆的體系的精密而已。另方面,廣義的藝術哲學,即那些從批評家們個人的鑑賞趣味和審美標準出發所作的「藝術評論」,雖然「往往也裝著哲學系統所標榜的那樣十全十美的儼乎其然的樣子」,但卻只不過提供一些不免會互相矛盾的「片斷的演繹和提示」。因為「那些意見和定理,都不是以什麼客觀的科學的研究和觀察做基礎,只是以飄忽無定的、主觀的、在根據上同純科學的要素完全異趣的想像做基礎的」,因此雖然也有存在的價值,但卻很難稱得上是「藝術科學」。至於藝術史,本應該為藝術科學提供科學觀察的實證材料的,然而遺憾的是,截至十九世紀末,藝術史家們的眼光竟仍然是那樣地狹隘。他們固執地「昂然在古舊的迷園中徘徊」,只注意到「歐洲諸文明民族的藝術」,至多將墨西哥人和祕魯人的藝術納入他們比較研究的圈子內,而「對於人種學所介紹的原始民族的粗鄙的產物,依然用著不屑一顧的態度」。顯然,「從一個這樣狹小的基礎上所產生出來的理論,怎能有一種普遍的真實性呢」 ?因此,格羅塞明確提出:「藝術科學的研究應該擴展到一切民族中間去,對於從前最被忽視的民族,尤其應該加以注意。」「所以藝術科學的首要而迫切的任務,乃是對於原始民族的原始藝術的研究。為了便於達到這個目的,藝術科學的研究不應該求助於歷史或史前時代的研究,而應該從人種學入手。」
毫無疑問,格羅塞的觀點現在看來實在不無偏頗之處。他過分強調人種學的意義,竟然認為連歷史和考古學「都是無濟於事的」。這一點當然很難令人接受。與之相反,後來更多的學者都更重視考古學和歷史學,寧肯只將人種學的材料作為一種可資借鑒的參考,甚至極端一點如英國動物學家和人類學家莫里斯(D. Desmond Morris),乾脆就認為人種學的研究根本不足為憑。莫里斯指出:「至今尚存的那些頭腦簡單的部落成員,其實並非原始落後,而是泯滅了靈性。真正的原始部落絕不會數千年如一日地存在下去。裸猿(即人──引注)在本質上是一個勇於探索的物種,所以任何一個未能進步的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失敗了的、誤入歧途的社會。某些因素拖住了它的後腿,破壞了其成員探索周圍世界的自然傾向。早期人類學家從這些部落中概括出來的那些特徵,很可能正是妨礙其進步的因素。因此,將這些材料作為人類行為模式的基礎,風險很大。」
不過,對於人種學的這些批評,已是格羅塞去世以後的事情了,更何況莫里斯的觀點,也未嘗沒有可以商榷之處,因此我們大可不必據此來苛求古人。恰恰相反,在十九世紀末,像格羅塞這樣高度評價人種學的研究,高度肯定它對於藝術科學方法論實現變革的意義,不但需要理論勇氣,而且確實是一種革命行動。因為在此之前,無論曾經有過多少美學和藝術科學的派別,都幾乎無一例外地把藝術僅僅只看作是文明社會的產物,而且是一經誕生便在各個方面都具有永恒合理性的東西。美學和藝術科學的任務,就是要找到這永恒不變而又普遍適合的美學原則,以便一勞永逸地解決藝術的本質和規律問題,並為每個人提供一張通向任何藝術殿堂的通用門票。然而格羅塞卻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傳統觀念,並用他所搜集整理的人種學昭示於我們的原始藝術現象,卓有成效地將美學與藝術科學的理論眼光,導向一個向來所忽視的問題──藝術的起源。在這部使人耳目一新的傑出著作中,格羅塞以翔實的材料和生動的描述,為我們展示了一個人類早已遺忘的原始藝術圖景,即展示出藝術在其發生時代所可能有的原始形態,從而為美學和藝術科學展示出無限廣闊的前景。因此,它的意義絕不僅僅只是把我們帶到一個前所未聞的蠻荒世界,更不僅僅只是陳列出「野蠻人」稀奇古怪的面具、腰飾、歌舞和繪畫以供獵奇,而首先在於通過「文明社會」以外「野蠻藝術」的展示,徹底摧毀了那種靜止、孤立和僵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人們這才發現,原來藝術並非從古希臘時代起就一直如此的、按照某種前定和諧的先驗理性原則結構的事物的集合體,而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甚至連古埃及藝術,也還不是它的原始形態和歷史源頭。在我們之前和我們之外,還有著「另一種」藝術,它們才是藝術的遠古始祖,以及這個始祖的現代殘存。美學理論和藝術科學如果將它們排斥在自己的理論視野之外,那麼,無論其體系如何嚴整,如何堂皇,如何自以為是,都不可避免的只能是殘缺不全的,甚至有可能是先驗唯心主義的。因此,要使我們的美學和文藝學成為真正的科學,除了與傳統的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的觀念作徹底的決裂,並將人類學的成果與方法唯物地引進自己的研究領域外,實在也是別無選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格羅塞的大膽嘗試,不但是一種革命的行動,而且也是一種富於成果的革命行動。他的成功實踐,也不僅使人種學以及以人種學為先驅的人類學,得以作為一種嶄新的科學被引進了美學和文藝學領域,從而建立起一門新的邊緣學科──藝術人類學;而且也在美學和文藝學領域內實現了觀念和方法的更新。
三
的確,藝術人類學的誕生,本身就意味著觀念與方法的更新,而這一更新,又有著極其深刻的歷史背景。
我們知道,人類思想最深刻的變革是從近代哲學開始的,「它的最大的功績,就是恢復了辯證法這一最高的思維形式」,從而一舉動搖了「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在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事實上,過去幾乎所有成體系的美學理論和藝術學說,差不多都是在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下建構的。它表現了人類的一種理性衝動,即人類無論如何也要追求和把握自身本質的那種精神。而所謂本質,在他們看來,也就是絕對、唯一和永恒的東西。只有這樣的東西,才是真實的;也只有真實地反映出這一真實的理論,才是真理,才是「常道」、「恒道」、「至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上」之「道」較之「形下」之「器」,總是更為本質,更為深刻,更為永恒。因此,要想真正把握藝術的真諦,就必須找到藝術的「形上之道」,於是他們這才總是處心積慮、不辭辛勞地在藝術之外或藝術之中,去為藝術尋找一種普遍適用而又一成不變的理性規定和理性原則,以便一勞永逸地解決從創作到欣賞的全部問題。這一點,可以說中外無二。只不過在歐洲,從十五世紀下半葉開始,這種世界觀由於自然科學的發展而變本加厲,並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即靜止地、孤立地看待世界:「不是把它們看做運動的東西,而是看做靜止的東西;不是看做本質上變化著的東西,而是看做永恒不變的東西;不是看做活的東西,而是看做死的東西。」這樣一來,在以這種思維方式看待世界的那些人那裡,藝術也就必然被割斷了它與歷史和現實的聯繫,必然被抽去了活潑潑的生命,而變成一個泡在酒精瓶裡失去了鮮明色彩的標本,或者一具可以放在手術臺上任意解剖的殭屍。
顯然,「在形而上學者看來,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應當逐個地和分別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變的研究對象」。如果說,這種思維方式或多或少地與十五世紀至十九世紀「四百年來在認識自然界方面獲得巨大進展的基本條件」有著某種因果關係的話,那麼,十八世紀以來自然科學的發展也同樣雄辯地證明了,這種思維方式只能造成「使教師和學生、作者和讀者都同樣感到絕望的那種無限混亂的狀態」。因為正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自然界的一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發生的」。「因此,要精確地描繪宇宙、宇宙的發展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辯證的方法,只有經常注意產生和消失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後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
於是,第一位對舊自然哲學進行變革的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Kant,一七二四─一八○四)一開始他的科學生涯,就把牛頓的穩定的、從有名的第一次推動作出以後便永遠如此的太陽系,變成了一個由旋轉的星雲團產生出來的過程。接著,另一位同樣偉大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Hegel,一七七○─一八三一)則進而第一次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絕對理念的自我運動史。由於絕對理念的自我異化和自我實現,人類的精神生活就呈現為一個由藝術而宗教最後到哲學的正、反、合過程,而藝術自身的發展也如此,即由象徵型藝術而古典型藝術而浪漫型藝術,最後為宗教與哲學所取代。這樣,黑格爾就不但把藝術從一成不變的概念變成了自我運動的過程,而且第一次試圖揭示出這一過程內在規律與外部表現之間的關係,從而實現了藝術科學的邏輯與歷史的一致。
邏輯與歷史相一致作為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肯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的源頭也許應該追溯到十八世紀義大利的傑出思想家楊巴蒂斯塔‧維柯(Giambattista Vico,一六六八─一七四四)。作為近代歷史主義的創始人,維柯提出了將歷史的眼光引入純學術研究的大膽設想,並由自己的巨著《新科學》作了成功的嘗試。在這部充滿了究本窮源的實證精神的著作中,維柯提出了「人類世界是由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這一蘊含著樸素的歷史唯物主義萌芽的著名論斷,從而實際上把世界看作了人類自我創造的歷史過程。同樣可貴的是,維柯在西方思想界較早地摒棄了僅僅將歷史的源頭焊接在希臘時代的傳統觀念,不但充分地研究了希伯來、迦勒底、西徐亞、腓尼基和埃及文化,而且極其敏感地注意到了當時還只是嶄露頭角的人種學,多次引用美洲印第安人的社會制度作為部落自然法的例證。儘管他在使人類學成為科學方面的貢獻,也許要遜於晚了近一個多世紀的達爾文和摩爾根(Morgan,一八一八─一八八一),──維柯的《新科學》發表在一七四四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表在一八五九年,而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完成於一八七七年。但如果我們知道,維柯用人種學材料充實他的新科學構架時,庫克還至少要再過二十四年才會發現原始部族的紋身,就不會不對維柯肅然起敬了。同樣的,儘管作為義大利人的維柯,不大可能具有德國人那種訓練有素的思辨習性,因此他的著作在思想的深刻、邏輯的嚴密和體系的井然方面,都要遠遜於黑格爾。但是,維柯所擁有的,正是黑格爾所缺少的。顯然,在後者高貴的頭腦和體系中,世界──亦即絕對理念的自我運動史,只該以象徵形式開始於古埃及藝術,最後則必定以思辨形式終結於黑格爾哲學。
於是,黑格爾哲學解體了,這個解體的命令實際上是他自己發布的。一八四一年,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Feuerbach,一八○四─一八七二)出版了他的《基督教的本質》一書,「它直截了當地使唯物主義重新登上王座」,雄辯地證明了「在神的本質的觀點中肯定的東西僅僅是人的東西」。由於這個原因,費爾巴哈又把自己的哲學稱之為「人類學」。這時,距達爾文出版《物種起源》和世界上第一個人類學學會成立(均為一八五九年)只差十八年,一種新世界觀和新方法論可以說已是呼之欲出。遺憾的是,費爾巴哈雖然拒不為那種「變得敵視人了」的舊唯物主義負責,卻也同樣未能倖免於從前一切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這就是:「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這就使他最終未能跨出至關重要的一步。在這個關鍵時刻,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毫不客氣地把任何哲學都撇在了一旁,連費爾巴哈本人也被擠到後臺去了。
幸虧,「從黑格爾學派的解體過程中還產生了另一個派別,唯一的產生真實結果的派別。這個派別主要是同馬克思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站在新世界觀的歷史高度,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德國哲學從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這裡我們是從地上升到天上」──「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也就是說,「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於是,黑格爾的邏輯學被揚棄了,但不是被簡單地放在一邊,恰恰相反,「他的革命方面,即辯證方法,是被當做出發點的」,把世界看作一個過程的「偉大的基本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但卻是唯物主義的肯定和弘揚;同樣的,歷史也再一次被引進了哲學,但「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礎上」。邏輯與歷史再一次而且是真正科學地相一致了。它熔鑄為這樣一個命題:「整個所謂世界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它也熔鑄為這樣一門科學,即「按歷史順序和現在的結果來研究人的生活條件、社會關係、法律形式和國家形式以及它們的哲學、宗教、藝術等等這些觀念的上層建築的歷史科學」。
毫無疑問,這樣一門科學──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稱它為自己僅僅知道的一門唯一的科學,是絕不會無視於人類學的誕生及其成果的。恰恰相反,人類學的科學方法和研究成果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辯證方法的唯物史觀,可以提供大量的實證材料並起到支持的作用。事實上,馬克思本人無論是其早期或是其晚年,都對人類學以及有關人的本質的一切問題,表示了極大的關注和熱情。早在一八四四年,年僅二十六歲的青年馬克思,就在其著名的《巴黎手稿》中深刻地分析和闡述了有關人的本質的若干重大問題;而在他逝世的前幾年,又把注意力從政治經濟學轉向了社會學和人類學,大量閱讀了歐美人類學家的著作,並作了詳細的質量很高的筆記。這就是新近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的《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一書摘要》、《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亨利‧薩姆納‧梅恩〈古代法制史講演錄〉一書摘要》、《約‧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狀態〉一書摘要》以及未收入全集的《約‧巴‧菲爾〈印度和錫蘭的雅利安人村社〉一書摘要》,其中拉伯克著作的摘要,是他在逝世前幾個月完成的,是他真正的最後手稿。這些筆記證明,正如恩格斯追述的,馬克思的確一直打算聯繫他們的唯物史觀來闡述人類學家們的研究成果,「並且只是這樣來闡述這些成果的全部意義」。這個工作後來由恩格斯完成了,這就是一八七三年至一八八三年間和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六年間寫作的《自然辯證法》中《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節,以及完成於一八八四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前者用唯物史觀闡述了達爾文的自然科學人類學的成果,後者則將摩爾根的文化人類學成果真正上升到唯物史觀的高度。直到現在,這兩部著作還仍然是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經典著作和綱領性文件。
的確,人類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自身、尤其是研究人類起源和人類文化起源及其原始狀態的科學,是天然地接近歷史唯物主義的。所以摩爾根竟在大洋彼岸「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四十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並且以此為指導,在把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加以對比的時候,在主要點上得出了與馬克思相同的結果」。這當然無非更雄辯地證明了唯物史觀的科學性而已,同時也告訴我們,文化人類學如果自覺地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就會對人類認識自身的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甚至會引起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重大變革。在藝術科學領域內,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革命成果。如果說,格羅塞作為第一個從藝術領域收集證據來支持唯物史觀的人,他的劃時代著作竟使一門新的邊緣學科──藝術人類學得以誕生的話,那麼,當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自覺地站在唯物史觀的立場上,運用他當時所能掌握的幾乎全部人種學文獻來駁斥關於藝術起源和審美發生的種種唯心主義理論時,其意義就不僅僅是美學和藝術學一個分支學科的建立,而是美學方法論的革命和新藝術觀的確立了。總之,無論是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八七七年)、格羅塞的《藝術的起源》(一八九四年),還是普列漢諾夫的《沒有地址的信》(一八九九─一九○○年),都無可置疑地證明了:唯物史觀的發現是整個世界史觀的根本變革,捨此就不會有真正科學的文化人類學的建立,不會有真正科學的藝術人類學的建立,也不會有真正科學的美學和藝術學理論體系的建立。
導 論 人類學與藝術本質的還原
哲學並不要求人們信仰它的結論,而只要求檢驗疑團。
──馬克思
一
一七六八年,英國航海家和探險家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一七二八─一七七九)受命前往南半球探險。他指揮的「努力」號帆船從普利茅斯起航,八個月後繞過合恩角,登上兩年前英國人命名為喬治三世島、一年前船長布幹維爾又命名為新西泰爾島的大溪地島。在這個遠離英吉利海峽的南太平洋荒島上,庫克第一次注意到一種久已被歐洲人忘記、以後也曾同樣引起英國人類學家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一八○九─一八八二)驚異的文...
目錄
序:人的確證需要産生藝術 鄧曉芒
導論 人類學與藝術本質的還原
上篇 發生機制
第一章 走出自然界
第二章 人的確證
第三章 圖騰原則
第四章 原始衝動
第五章 實踐思維
第六章 理性精神
第七章 神話模式
下篇 原始形態
第八章 工藝
第九章 建築
第十章 雕塑
第十一章 人體裝飾
第十二章 舞蹈
第十三章 戲劇
第十四章 繪畫
第十五章 音樂
第十六章 詩歌
結論與補充:再論「藝術本質確證說」
後記
注釋
序:人的確證需要産生藝術 鄧曉芒
導論 人類學與藝術本質的還原
上篇 發生機制
第一章 走出自然界
第二章 人的確證
第三章 圖騰原則
第四章 原始衝動
第五章 實踐思維
第六章 理性精神
第七章 神話模式
下篇 原始形態
第八章 工藝
第九章 建築
第十章 雕塑
第十一章 人體裝飾
第十二章 舞蹈
第十三章 戲劇
第十四章 繪畫
第十五章 音樂
第十六章 詩歌
結論與補充:再論「藝術本質確證說」
後記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