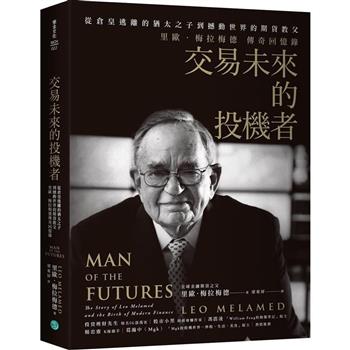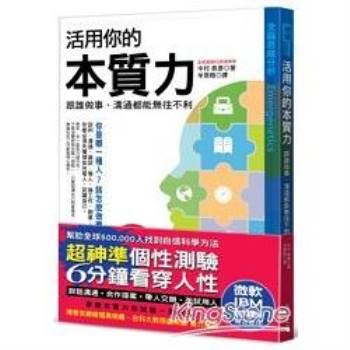沈序i
善豪從台北寫信到多倫多來,盼我能為他的《 批判與辯證 》寫序。前此我已經拜讀過一些善豪的學術論文與政論性文章,頗為欣賞。猶記得過去善豪還在大學生時代,當時我正在政治大學任教,他常來修習我的課,課後也常來討論其所關心的問題,對於所論問題之關注,學術志趣之專一,令我印象深刻。他在政大政治學研究所的碩士論文,也是我由我指導的。後來,他負笈德國攻讀博士,期間我也曾借赴歐講學之便,到柏林去探視過他。我關心學生,總希望多知道一些他們的學術進展。善豪在取得博士之後,返台任教多年,勤於研究和著述。現在知道他將這些論述集結成冊,我實在感到欣喜,答應為他寫序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等到書店把清樣寄來,拜讀之下,才知道善豪在柏林求學期間,住在維鼎區之時,對於了解馬克思的 《 資本論》,曾經有過類似王陽明龍場悟道的經驗。雖然不像王陽明那樣通天徹地、照見本心,而只是搞懂了馬克思的 《 資本論 》 而已,然而,就解悟事理而言,也可以稱為善豪的維鼎悟道經驗吧。善豪這一體驗雖僅集中於對「自由人聯合體」之嚮往,然也能擴大其心, 類比於陸象山「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之大義,可見其胸懷並不止於研究馬克思,而對於象山「先立乎其大者」之義,亦可有所體會。我之所以把柏林的 Wedding區譯為「維鼎」區,不同於善豪譯的「微酊」,是因為我覺得一個人在醉意酩酊之時,雖仍可讀懂馬克思的著作,然卻著實不易有頓悟本心的經驗。再說,善豪在本書首章便質疑所謂「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主義三位一體」之論,也因此這本表達其悟道成果之書,也可視為出自善豪對此一鼎論的思維與批判。
自從蘇俄與東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陸續放棄共產主義,而資本主義一時之間洋洋得意,頗有「提劍四顧,敵手何在」的氣慨。然而,曾幾何時,在資本主義全球統治之下,今日整個世界遭逢金融危機,經濟衰退,百業蕭條之際,研究者都必須反省這兩個相關的問題:到底在今天談馬克思主義還有什麼意義?到底資本主義出了什麼問題?在此問題脈絡下,我們更能明白,為什麼善豪要思之再三,仃細考訂,深入探掘,研究馬克思的思想。在我看來,在今天來思考馬克思主義,其最適切的脈絡,當在於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尤其對當前資本主義的全球統治的批判,如何還能從馬克思獲得啟發。如此追問之時,當然還須更進一步追問:何謂批判?在批判方法上,如何可從馬克思獲得啟發?
我覺得,此書雖是善豪多年創作的論文收集起來的成果,然其中仍可發現有一基本的問題意識,那就是恢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向度,重現馬克思本人的批判鋒芒。如果把馬克思主義晚近遭逢的重大變局與當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問題聯繫起來看,此書的意義便益趨明朗。如果說前此第二國際的馬列主義是受到恩格斯的扭曲,然而像盧卡奇、馬庫色等人的黑格爾式辯證轉向,是為了區隔馬克思本人的思想,與恩格斯及其後利用恩格斯所謂自然辯證法與歷史法則對馬克思的曲解及其所造成的歷史災難;那麼”善豪本人則是在今天資本主義危機重重之時,希望再度昂揚馬克思的批判精神,無論是從馬克思的原典尋覓其中的批判之劍,或是從其康德批判哲學的相似性找尋批判,並將受到第二國際污染的辯證法去除實體化,藉以釐清批判與辨證之間的真正關係。
我想,善豪在此書中所要張舉的批判精神是深遠的,也是適切的。面對當前資本主義的全球統治,批判的力量當不僅止於對資本主義提出質疑或予以否定,雖然質疑與否定也是批判的面向之一,然而總還缺乏積極的動力。所謂批判也不能僅止於康德哲學的意義,只在人的主體內尋求數學、物理學、形上學,甚弄道德、美感與人生目的等之先驗可能性條件;更不能像恩格斯那樣,將機械式的「心物倒轉」視為批判,甚或是用「以物代心」式的「替代」,來詮釋「倒轉」。馬克思的批判,一方面要回到人群在歷史中呈現的生活世界,來指陳某特定勞動與交往關係發生的可能性條件;另一方面,馬克思的批判更要指出人的普遍性,也就是人的勞動性與價值,決不可等同於某種特定的勞動形式與金錢;而人群由於相互交往而形成的社會,也決不能等同任何具體形式的社會,如資本主義社會。如此的等同,是將特殊拜舉為普遍,於是形成崇拜金錢的偶像或馬克思所謂的金錢拜物教。在此,馬克思的批判既有對於金錢拜物教的否定之意,更透過此 一否定而指向那普遍的價值與人的勞動本性。
就前者言,馬克思著重在客觀實在界,其實也就是在人的歷史與生活世界中,尋找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條件,而不再如康德那般僅封限於主體性之內尋求科學、道德與美感的可能性條件。馬克思著重於價值本身和人的勞動本性的全面展開與實現,而不再像他所繼承的猶太人的默西亞主義,一味等待一超絕的默西亞的來臨。他主張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不可踰越的差距、金錢與價值的差距、社會本身與資本主義的差距,可以說是以其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轉化了康德所謂「現象與物自身」、「理念與經驗」的差距,以及猶太傳統所謂「不可敬拜偶像」、「凡已出現者皆不是默西亞」的信仰的結果。
在我看來,人是出生並成長於多元他者之間,自始即動態地指向多元他者,以不斷的外推( Stlangification 》 與內納 《 appropriation) 的辯證歷程,產生有意義的世間。人作為意義的動物不只有狹義的勞動性,更可透過種種物質生產、聲音、圖像、語言、藝術、創作、人際交往、正經社會制度、倫理關係、宗教信仰等等,層層推進的歷程,視為人整體(兼物質與精神)的勞動歷程,其間人由於與多元他者的自由、真誠與負責任的交往,將可形成真正意義的社會。換言之,人由於原初慷慨,不自我封限地走出自己,經由外推歷程而形制產品,並經由相互外推而交談。在創作與交往之中,實際蘊藏了多少偶然性( contingencies ) ,然而,也正因為這無數的偶然性,更凸顯了人的自由、創造與仁愛的可貴。資本主義把這人性中的原初慷慨閉塞在私己的佔有與享用中,將人的理性封限於算計理性與策略理性,使得資本的網絡不斷自我擴張,吞噬所有的能動力為其所用。馬克思的批判的確有助於了解資本主義的困境,鼓舞人性發揮其出自原初慷慨的能動性。
當然,我們不能再像馬克思那樣,將人性僅定限於抽象勞動,在我看來,人性有其「即有限以應無窮」的尊嚴與崇高目的。
就某種意義來說,善豪把人的抽象勞動視為人的本性,把建立「自由人聯合體」說為人的終極目的,雖然也是出自他的人文主義胸懷,然而多少仍有一些本質主義的意味。也因此,他會把辯證視為由「抽象勞動」到「有用勞動」、由「價值本身」到「使用價值」的歷程,把一種頗似黑格爾所謂理念實現為具體存在的歷程,視為辯證之意。我想指出的是:原先在古希臘哲學中,「辯證」的本意原是「對話的藝術」。在柏拉圖的 《 對話碌 》中,往往表現為蘇格拉底與其弟子或訪客的對話。雖然在一篇對話碌中可以引進多人進行對話,但每次對話都是個人一對一的進行。對話者彼此是師徒、朋友的親近關係,然而在對話中,為了真理 ‧ 往往要針鋒相對,否定對方的論題,以便前進到更接近真理的論題。換言之,在柏拉圖那裡 ‧ 辯證是朋友之間為了真理而進行的針對性或敵對的論辯性對話,在敵對中有友誼,在友誼中有敵對。然而,到了馬克思那裡,對話成為一種在歷史中、在社會中進行得交往形式,也因此辯證的場所是在具體的社會關係中,不僅限於個人與個人,也不像黑格爾那樣失去對話向度,以辯證為精神自我出走上升以致完成於絕對精神的步驟;更不像.恩格斯那樣,將辯證視為自然甚或宇宙全體所遵循的法則。我雖然欣賞馬克思將對話放入社會交往脈絡之中,然而,無論如何,我所不能同意的是,由於其所謂的「抽象勞動」終非「有用勞動」,「價值本身」終非「使用價值」,馬克思的辯證終究否定、敵對與揚棄者多,積極創造、保存與友愛者少。
說到恩格斯將辯證視為自然、歷史甚或宇宙全體所遵循的法則,這在第二國際以及其後的共產主義統治中被取來做為證成極權統治宰制人的歷史與自由的藉口。也因此,我贊成將馬克思的思想與恩格斯的嫁接史分別開來。然而,我如此的看法並不是要忽視宇宙向度,將人框限在「太過人性」、封閉的人文主義中,而是主張向宇宙開放的人文主義。從馬克思到恩格斯的轉折,也洩露了從人至其宇宙關聯的必要發展,有必要在宇宙之中重新定位人。可惜的是,恩格斯將此僵化為宇宙和歷史的法則,其後更被用來作為極權者宰制人的歷史性的藉口。於今,我們所需要的是具有宇宙向度,能開展人的自由與創造,發揮人「參贊天地化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開放的人文主義精神。
閱讀善豪的著作,使我在他的字裡行問看到一個嚴肅的馬克思學學者,一位真誠的思想者,本書所呈現的研究成果顯示出一位台灣學者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力道,並以其慷慨心胸,將之分享於學界和一般讀者。相信本書對於近一世紀來這段歷史的底層問題,有更進一步的深思和了解。祝福善豪,也祝襠各位讀者。是為序。